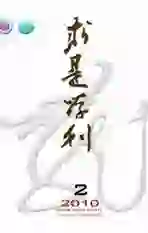仁义的内外\\人我之争及其意义
2011-01-01雷震
求是学刊 2011年2期
摘要: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告子、孟子、董仲舒曾对仁义的内外、人我问题进行争论,形成了三种典型的仁义观,即告子的“仁内义外论”、孟子的“仁义俱内论”和董仲舒的“仁外义内论”。文章通过呈现思想家们在相同的论述主题下不同的思想特质和伦理诉求,尝试发掘仁义之争的思想意义及现实启发。
关键词:仁义观;告子;孟子;董仲舒
作者简介:雷震,男,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师,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从事伦理学研究。
基金项目:黑龙江大学青年基金项目“先秦儒家伦理的逻辑”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1)02-0053-05收稿日期:2010-12-11
仁义是中国传统伦理学中的重要概念。历史上很多思想家在不同语境、不同意义下使用、论述过这个概念,因此形成了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独具特色的仁义观。本文从文本出发,解读历史上三种典型的仁义观,凸显仁义的内外、人我之争的思想史意义及对我们今天道德思考的启发。
一、告子的“仁内义外论”
告子的仁义观点今仅见于《孟子》一书中: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告子上》,下引《孟子》只注篇名)
告子首先明确提出他的论点:仁内义外。为了阐述“仁内义外”,告子分三个步骤对其观点进行论证,“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告子上》)。他年长我就尊敬他,不是我预先就有尊敬他的念头;就犹如一样东西是白的,我就认为它白,这是由于它的白显露在外。所以说,“长之”即尊敬是外。这是他对“义外论”的初步论证。
接下来,面对孟子的诘问,告子进一步论证和辩护道:“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是我的弟弟我就爱他,是秦国人的弟弟我就不爱他,这是以我为标准由我来决定的,所以称之为内,这是告子对“仁内”的论证。尊敬楚国人中的长者,也尊敬我自己国家的长者,这是以长者为标准,即:只要他是长者,我就尊敬他,所以称之为外,这是告子对“义外论”的进一步论证。
最后一步的论证是由替告子辩护的孟季子完成的。“孟季子问公都子曰:何以谓义内也?曰:行吾敬,故谓之内也。乡人长于伯兄一岁,则谁敬?曰:敬兄。酌(斟酒)则谁先?曰:先酌乡人。所敬在此,所长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孟季子认为,如果义是诸如表达我的敬意这样的行为,是以我内心的敬意为依据,据此就认为义内,那么你内心明明尊敬的是伯兄,但行动上却先给乡人斟酒,实际上尊敬的是乡人,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行义分明不是表达内心的敬意,分明不是以内心的尊敬念头为依据,而是以乡人长于伯兄一岁这个外在的客观事实为依据,这怎么能说义内呢?恰恰相反,这说明义行果真是由外因引起的,故“义外也,非内也”。
从告子的“仁内义外论”看,告子所说的“仁”典型的表现是“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这种“爱”是自然的爱悦之情,是本于人性的天然情感,如同孟子说的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是以家庭为生活单元所产生的一种对亲属关系的眷恋,是出于我内心的血缘亲情。而且这种爱的情感和行为不取决于对象是否为“弟弟”,而取决于“谁的弟弟”,这种爱是根据对象与“我”的关系而决定的,是“以我为悦者也”,所以“内”。告子所说的“义”的典型表现是“彼长而我长之”, 是“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这种对长者的态度和行为取决于对象“长于我”这个客观的事实,无所谓他是吾长还是楚人之长,敬之与否的关键不在于我,不在于与我有没有内在血缘宗族这样的关系,而仅仅在于对象是否年长,是否“长于我”这个外在的因素,是“以长为悦者也”,所以是“外”。
告子的“仁内义外”直接源自他的人性论观点——性无善恶论。告子认为,人性本无所谓善恶,“性无善无不善也”(《告子上》),他更以“杞柳”和“湍水”为喻,认为如果“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人性之无分于善与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告子认为,孟子的错误在于将先天材质与用先天材质做的后天的人为产品混为一谈,将无善无恶的人性与后天培育而成的道德混为一谈,因此,与生俱来的先天的“食色”为性,而道德则是“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全看后天的环境影响及人为引导。可见,性无善恶的人性论决定了告子必然要说“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在道德实践中也必然追求对外在客观环境、事实等的探究与把握。
二、孟子的“仁义俱内论”
孟子的“仁义俱内论”是在与告子仁义观的辩驳过程中展开的。针对告子的“仁内义外论”,孟子分四个层面对其进行了机智的批驳。
首先,针对告子的“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的论证,孟子发难:
异于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异于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告子上》)
孟子认为,“长马之长”与“长人之长”,“白之”与“长之”看似相同,其实质有本质的区别,“白之”与“长之”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判断。马白,所以我们“白之”,这是实然的知识判断;而人长,所以我们“长之”,这其实是一个应然的道德判断。既然是两种不同的判断,那么我们就应该以不同的标准予以对待,对于“白之”这种实然的知识判断我们可以从其白于外,但对于“长之”这种应然的道德判断则不应该完全从其长于外。
其次,“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是孟子批判告子的关键环节。该设问明显地表露出孟子的观点:尊敬长者这种义行不在于长者,而在于尊敬长者的人,在于尊敬长者的人内心有对长者的尊敬之情,孟子强调的是尊敬之情由内而发,以内在的情感为基础,在遇见长者的时候表现出来,这才是我们称尊敬为义的关键。如果没有内在的情感,那么外在的“长之”言行只是形式、伪装、作秀而已,我们怎么会把形式、伪装、作秀看做行义呢?所以不可以说“义外”。
再次,针对告子的“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进行驳斥。孟子反问,“耆(嗜)秦人之炙(烤肉),无以异于耆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耆炙亦有外与?”按照告子的论证逻辑,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那么,耆秦人之炙,亦耆吾炙,是以耆为悦者,因此耆也应谓之外,但耆炙亦有外与?若如此,那么这就和你的“食色,性也”相悖。
最后,孟子通过驳斥替告子辩护的孟季子来驳斥告子。以敬兄酌伯兄(斟酒的次序)而得出“所敬在此,所长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的结论,孟子同样假设一种情形,以敬叔父尊在“尸位”的弟弟(即,如果弟弟在祭祀时居于受代理人之位,在这种场合下,是敬叔父还是敬充当“尸位”的弟弟呢?)来回应孟季子,将内心敬此、行动敬彼解释为“庸敬(平日的敬)在兄,斯须之敬(特殊场合下暂时的敬)在乡人”,但孟季子认为孟子虽解释了为什么“所敬在此,所长在彼”的问题,但没有说明义行是由什么决定的,而且说这种解释反而论证了告子的敬是由于外在因素(所敬对象长伯兄一岁及其所处的特殊地位——“尸位”)决定的,争论以“冬日饮汤,夏日饮水”结束,又以饮食来反驳。很多研究者都不解为何孟子一系总以饮食之事类推人之“仁义”,甚至认为这是诡辩。诚然,“饮什么”要考虑冬夏这些外在的天气条件,但“饮本身”却是内在的要求,而且也和告子的“食色,性也”相符。同理,“敬谁”要考虑所敬对象及其所处的特殊地位等外在因素,但“敬本身”却不是外在的,是人的内在的要求,故义非外而为内。
以上是《告子》篇中所记述的孟子对告子“义外论”的批驳。孟子从否定的方面论证了“义非外也”的观点,从中可见二人对峙和交锋的激烈程度。仅就这些论辩本身看,技巧上的争锋远胜于思想本身的碰撞,如果说孟子获胜,更多的也只是论辩技巧上的胜利,是缺乏深入的理论论证的。不过,孟子对告子义外论的批驳是建立在他的性善论的基础之上,与他对“仁义”内涵的理解是一致的、一以贯之的。
孟子所说的“仁”大致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以“亲”来论“仁”。“亲亲,仁也”(《尽心上》),“仁之实,事亲是也”(《离娄上》)。在孟子看来,仁的原初的、基本的含义是对父母的亲爱亲近,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这表达了孟子所理解的爱与仁的内在关联。其二是以“心”来论“仁”。“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公孙丑上》),“恻隐之心,仁也”(《告子上》),孟子也常以“不忍人之心”言仁:“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尽心下》)将“仁”看做人性中所固有的先天的善端。其三是以人之本质属性来论“仁”。“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尽心下》),将仁作为人道的本质,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本质的特质。从孟子所理解的“仁”的上述三个方面的含义看,仁都是非由外铄于我,我固有之,由内生发,往外推扩,仁的与生俱来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仁对于人来说是先天的、固有的,因而也必然是内在的。
孟子所理解的“义”基本上是从道德规范的意义来讲的。他说过,“敬长,义也”(《尽心上》),“义之实,从兄是也”(《离娄上》),这都是从人伦规范的角度来释“义”。由此具体的“义”的含义,孟子进一步将其抽象为人之所当为,他说:“义,人之正路也”(《离娄上》),“义,人路也”(《告子上》),将“义”理解为人适宜选择和适宜走的道路,即“应当”之意,即“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尽心上》)。可见,“孟子所谓义,则是自己裁制之意,不顾一己利害,决然毅然自己裁制其行为,便是义”[1](P265)。但孟子的“自己裁制”的力量不是来自主体之外,而是以内在的“羞恶之心”为基础,“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公孙丑上》),通过羞恶的情感体验及其心理活动来“裁制”人、规范人的行为,将内心的羞愧、不安,培养扩充起来,“义”也是内在于人的一种善端。因此,“义”同“仁”一样,“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因而也必然是内在的。
三、董仲舒的“仁外义内论”
张岱年先生说过,自孟子后,论仁义最为清晰详尽的,当属汉代的董仲舒。[1](P268)与先秦时的仁义内外之争不同,董仲舒的仁义观不但解释了仁义的来源,而且将“仁义”问题与“人我”问题相关联,将孟子与告子的“内外”之争转换为“人我”之论。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仁义法》中开宗明义提出了自己的仁义观:
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众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义设人,诡其处而逆其理,鲜不乱矣!……是故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春秋繁露·仁义法》,下引《春秋繁露》只注篇名)
董仲舒认为,《春秋》的首要问题是“人”与“我”的问题,既然如此,那么就要建立治人与治我的原则、方针以及如何治理的方法。董仲舒说仁之法是治理群体的原则,义之法是整饬自我的原则,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就是治理人我的方针,一般人的行为却是以仁自裕,而以义设人,对自己很宽容,对别人却很严厉,这既违背了治理人我的原则,又颠倒了治理人我的方针,所谓“诡其处而逆其理也”是造成社会混乱的重要原因,因此董仲舒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仁人义我”的仁义观。
很显然,董仲舒“仁人义我”的仁义观是对先秦儒家仁义观的继承和发挥。他强调了“仁”之“爱人”的内涵,“仁者,爱人之名也”(《仁义法》),强调了“义”的“正我”内涵,“义者谓宜在我者”(《仁义法》)。这些论述与孔孟的“仁者爱人”、“义者正路”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同时,董仲舒的“仁人义我”又发挥了孔孟的仁义观,将孔孟对所有人都适用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仁义观赋予了政治伦理的含义,使董仲舒的仁义观表现出了明显的汉代政治哲学特点。关于此点,徐复观先生曾说:“在仲舒心目中,孔子作《春秋》,是为后王立法,现实上即是为汉立法。用现代的语言来表达,他要使《春秋》成为大一统专制帝国的宪章。”[2](P221)从董仲舒的整个学说体系看,他的灾异论、天人三策及天的哲学等,都有明显的服务(包括制衡)王权的现实指向,故徐复观先生此说应该不是牵强附会。
如果说,董仲舒的“仁人义我”的仁义观具有明确的政治指向的话,那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董仲舒必须对此进行理论上的论证。首先,他阐述了“仁”的内涵。“何谓仁?仁者,憯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诐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如此者,谓之仁。”(《必仁且知》)这里的憯怛、谨翕、心舒、志平、气和、欲节,指的是人的感性心理活动,但在董仲舒看来,人的感性心理活动不是“仁”,“仁”是指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诐之事,无辟违之行等,即“仁”是人在与他人交往中表现出来的某种德性,因而是外在的。其次,他阐述了“仁”来源。董仲舒说:“为人者,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为人者天》)仁的根据不在人自身,是人的血气在禀受了天的意志之后而形成的,是天的意志与人的血气相结合的产物。人从天的存在、运行、功用中获得启发,从天那里领悟了仁,并效法天,取法仁,使自身也仁,因此“仁”是外在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义内”,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先前的观点,重新界定了“义”。首先,他以“宜”释“义”,“义者,谓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故言义者,合我与宜以为一言。以此操之,义之为言我也。故曰:有为而得义者,谓之自得。有为而失义者,谓之自失。人好义者,谓之自好。人不好义者,谓之不自好。以此参之,义,我也,明矣!”(《仁义法》)董仲舒按照古义界定“义”为“宜”,意为适宜、恰当,但董仲舒对“宜”作了限定,将“宜”和“我”连起来解释义。 “义”之宜,是针对我而言的适宜、恰当,义与不义、宜与不宜以及自得与自失、自好与不自好,完全取决于“我”自己的个人因素,因此义非外,而是内。其次,他以“正”释“义”,“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为了说明义在“正我”,董仲舒从正反两方面予以论证。楚灵王自身不正,“托讨贼行义”去正别国人,虽然“执人之罪人,杀人之贼”,但他令所讨伐的国家的臣民失望,不满意,所以《春秋》不称其为义者。相反,《春秋》称不能正别人,自己行为端正的潞氏为“有义”,“潞子之于诸侯,无所能正。《春秋》予之有义,其身正也”(《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董仲舒还详细阐述了正我行义的方法,首先要“自称其恶”,正确对待自己的错误,勇敢地揭露自己的错误,然后“反理以正身”,使自己的言行返回到理上来,合乎理。
董仲舒对“义”的两种重新界定,都将“义”和“我”联系起来,一方面认为“义”主要是正我以反(返)理,能否“反理”,是否“称义”,取决于自己;另一方面认为“义”与“我”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关联,把“我”和“宜”结合在一起,让我得适宜,做我应该做的事,走我应该走的路,这里的宜与不宜也取决于我,所以董仲舒主张“义内”。纵观董仲舒对仁与义的界定和论述,“仁外义内”的结论清晰而明确,“仁谓往,义谓来;仁大远,义大近;爱在人,谓之仁;义在我,谓之义。仁主人,义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此之谓也。君子求仁义之别,以纪人我之间,然后辨乎内外之分,而著于顺逆之处也。是故内治反理以正身,据礼以劝福;外治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仁义法》)。
四、仁义之争的思想史意义
作为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论题,围绕着仁、义的各自内涵、来源以及仁义的内外、人我之争,思想家们各陈己见,给我们留下了独具特色的仁义观。其间,他们的思想既有延续也有发展,既有对峙也有融通。看似一个简单概念的解析、论述和辩驳,其实表达了他们各自的道德观,具有思想史的意义和现实启发。
第一,思想家们关于仁义观的争论,其实是他们对道德形上问题的“形而下”表达。他们对仁、义究竟是内还是外的争论,其道德哲学的指向,是要回答道德之对于人如何可能的问题。道德源自人内心的血缘情感、恻隐之心还是后天环境、教化的产物?它是一种事实判断还是一种价值判断?比如孟子对“义内”的论述,孟子并不否认道德价值与外在客观事实有关,但强调道德价值要高于客观事实,要超越于客观事实,唯其如此,才能显示出人作为万物之灵的高贵和尊严,才能凸显人禽之别。的确,人是环境的产物,但人在道德上不能被外在的环境所左右,人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道德面貌,这也是孔子“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的内在意蕴。
他们对仁、义究竟是人还是我的争论,其道德哲学的指向,是要回答道德如何在社会中应用的问题。“仁我论”揭示了爱这种道德要求只有发自“我”内心真诚的动机才具有道德上的价值,才是社会希冀的,它主要强调道德在社会应用时的动机问题。爱人应是出于真心实意,虚伪便是不仁(“巧言令色,鲜矣仁”),假仁假义历来受到人们的憎恶。但是,作为协调人际关系的爱,仅仅出于真诚还是不够的。即使是真心实意的爱,也会出现偏差、不当。为使爱之所发皆当,就必须按社会准则对这种质朴的情感进行加工、规范,使其所发皆中节。[3](P155)所以还要关注“仁人论”,它揭示了爱这种道德要求不能只停留在“我”这个范围,应该从血缘宗族扩展到他人甚至物事上;不能以“亲亲为大”为原则,应该具有更为宽广的胸襟;必须打破自我中心主义,跳出亲亲的案臼,把仁爱推及群民众生,以至于鸟兽虫鱼,这样才能有利于博爱情怀的形成。没有对群民众生的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仁。“仁人论”主要强调道德在社会应用时的效果问题。“义我论”揭示了自正是做到适宜的前提,它主要强调道德原则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义行需要主体付诸行动,需要考虑相关外在条件,比如社会上通行的礼制规定。然而,这种外在的考虑并不表示义行就是由外因引起的,是外在于我的,义行若非由我内心而发,它就是无源之水,也就没有集义、养气的可能性了。[4](P322)“义我论”强调道德在社会应用时的自律;“义人论”强调道德原则的客观性与权威性,强调道德在社会应用时的他律。
先哲们把这些具有浓郁的道德哲学意味的思考,寓于机智的论辩和具体的比喻中,既给我们展示了一种独特的中国式的道德智慧,也给我们留下了深邃的思想遗产,即:内外与人我是中国传统仁义论的关键,它们从不同层面引导我们关注道德自律、他律以及动机和效果等重要问题,需要我们好好地研究。
第二,思想家们对仁义观的争论,都是他们各自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他们哲学思想的必然的逻辑结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石一是天道论,二是人性论。三种仁义观是他们的天道观和人性论的具体展开,反过来,人性论和天道观为他们的仁义观提供了理论基础。从人性而论,因告子言性无善恶,故力主“义外”;而孟子主性善,故力倡“仁义俱内”。从天道观而论,因孟子主张尽心、知性、知天的同一,在他看来,人性既受之于天,也源于内心,仁、义等道德都是人心性的体现,故“仁义俱内”;而董仲舒主张天人相类,人副天数,人之道德的价值依据在宇宙之中,仁不在人,而在人之外的“天”,故“仁”是外在于人自身的。可见,他们的仁义观与他们的哲学倾向是一致的。这也使得他们是在自己的逻辑体系中与对方进行交锋,很多时候,同一个概念,所指不尽一致,甚至迥异。比如孟子与告子争论的“性”,孟子所说的“性”乃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即人的道德性,而告子所说的“性”乃指人的自然本能。孟子强调的是人之应然属性,而告子描述的是人之实然特征。出自不同的逻辑前提,必然会得出不同的逻辑结论,也自然会使他们的争论只是技巧之争,而非真理之争。
第三,思想家们对仁义观的争论,表明了思想史上的每一种伦理主张都在试图干预社会生活,体现了伦理学的实践品格。如果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伦理学就应该是最关怀世道人心的道德声音。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功利的时代之一,孟子初见梁惠王,梁惠王最关心的是孟子“何以利吾国”。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需要思想家再去为功利主义鸣锣开道,社会更需要有责任感的思想家以前瞻性的主张为急功近利的社会补偏救弊。而在董仲舒的时代,大一统专制王权的巨大威力已使思想家们敏锐地意识到以“天”来制衡王权的必要,故而董仲舒的仁义观必然要引入“天”的核心范畴。因此,孟子指责告子“率天下人祸仁义”,他的道德理想主义看似迂阔,其实是他为战国时代所开出的道德良方;董仲舒强调“仁外义内”、人副天数,实质是为了论证王者行南面之治,以教化为大本的政治伦理。
参 考 文 献
[1]张岱年. 中国哲学大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2]徐复观. 两汉思想史[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张锡勤. 中国传统道德举要[M].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
[4]傅佩荣. 傅佩荣细说孟子[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责任编辑李小娟付洪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