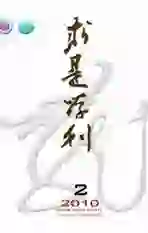正义的等级和上行的哲学内涵
2011-01-01高挪英
求是学刊 2011年2期
我们在阅读一部作品的内容之前常常就已经知道了作者和标题。知道作者是谁,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就清楚是谁在对我们说话,而标题则是作者所说的第一句话,常常也是主旨的凝练表达,理解了标题我们就可以把握整部作品。然而,我们面对《居鲁士上行记》(以下简称《上行记》)时情况有些复杂。就作者而言,它明明出自色诺芬之手,他却在《希腊志》中将其假托于一位子虚乌有生名下。至于标题,乍看之下则不免让人怀疑色诺芬取名的能力,居鲁士上行的过程在卷一就结束了,余下的篇章讲述的是希腊人的下行。可以说,我们在进入《上行记》的大门之前,就面临两道难关,它们一开始就使我们迷惑,在阅读中我们念念不忘,读毕后会掩卷反思。色诺芬设置这些曲折的意图是什么?
一、托名纪事
按照《希腊志》的叙事脉络,到了应该撰写居鲁士夺位和兵败后希腊雇佣军返回希腊的事情时,色诺芬表示已有人写过,“居鲁士纠集了一支军队,率领这支队伍向内陆进发,攻击一母同胞的兄长,至于战况、居鲁士之死、居鲁士死后希腊人活着回到海边这些事,叙拉古的忒迷斯托革涅斯(Themistogenes of Syracuse)写过”(《希腊志》III.1.2)。这段文字引发了如下问题:确实有一个名为忒迷斯托革涅斯的叙拉古人写过居鲁士和希腊人的故事吗?如果有,我们可否进一步获得作者的信息?如果没有,色诺芬为何要将《上行记》托于此人?事实上,除了色诺芬的这段叙述外,古往今来还没有哪位学者发现过忒迷斯托革涅斯及其作品存在的痕迹。在拉尔修陈列的色诺芬作品目录中,《上行记》赫然排在第一位。[1](P117)其他古典作家的引述也证明了拉尔修记录的真实性。波吕彼奥思(Polybius)在作品(《历史》III.6.9)中提到了色诺芬《上行记》中记述的色诺芬率领万人军返回希腊的壮举。金嘴狄翁(Dion Chrusostomos)在《修辞》(Orationes 18)中自陈他常被色诺芬《上行记》中的演讲感动得流泪。在当今的欧美古典学界,也无人反对《上行记》是色诺芬的作品。《希腊志》当中的这段文字如何解释?普鲁塔克在《伦语》(Moralia 345E)《论雅典的荣耀》中主张色诺芬是托名叙拉古的忒迷斯托革涅斯来出版自己的作品。由于任何人都找不到其他的旁证来证明忒迷斯托革涅斯及其作品的存在,人们普遍采纳了托名说。但问题仍旧存在:色诺芬为什么偏偏托名于此公呢?
研究者们大都提到了《上行记》的托名之事,但几乎无人给出一番圆通的解释。到了哲人施特劳斯这里,情况才发生转变,他指点我们注意Themistogenes的含义。它是由Themis(正义)的属格单数Themistos加上genos(后代)组合而成,意思为正义的后代,而色诺芬(Xenophon)的意思是异乡人的杀手。施氏推断,忒迷斯托革涅斯可能是色诺芬安排的一个理想化名字。[2](P34)那么,接下来的疑问就是:理想化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时我们就必须结合义理来加以理解。Themis是掌管习俗和法律的正义女神,她是天(Ouranos)与地(Gaia)的女儿(赫西俄德《神谱》第135行),她的后代是她与宙斯所生的新正义女神狄克(Dike《神谱》第903行)。当我们思考《上行记》的重要主题时,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色诺芬为何以忒迷斯的后代自称。《上行记》呈现了色诺芬——一位政治实践中的哲人——什么样的正义呢?我们知道,色诺芬处于实际的政治境遇中,而且是战争境遇,四面都是致命的蛮族敌人,他必须拯救自己和其他希腊人的性命,带领他们回到希腊。最后的结果证明色诺芬完成了拯救希腊人的光辉事业,成为这些希腊人的施惠者,得到了父亲这个称呼(《上行记》VII.6.38,下引省略书名)。在完成这一政治功绩的过程中,首领色诺芬必须带领希腊人迎战蛮族敌人,对这些敌人行恶,这样做完全等于向希腊同胞行善。至此,任何一位色诺芬的读者都必定想到了他对政治美德的归纳。在色诺芬笔下,居鲁士,无论是帝国的创建者还是起兵谋反的小王子都是这种美德的化身。政治美德是:对朋友做好(或善)事胜过朋友对自己所做的好事,对敌人做坏(或恶)事胜过敌人对自己所做的坏事(I.9.11,《居鲁士的教育》VIII.7.28)。它看似简单可行,实则问题丛生。将政治美德付诸实践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辨别敌友的判断力,二是分辨好坏的知识,而大多数人恰恰缺乏这两种能力,尤其是关于好坏的知识。就理论而言,它包含的恶因素使其从根本上无法成为真正的美德,美德意味着纯粹的善(柏拉图《王制》335d)。将领色诺芬践行着一种与居鲁士的美德不同的美德,这一点无论从色诺芬的行动还是言论中都可以看出来。他在面对威胁时表态:人若做好(或善)事则回报,人若做坏(或恶)事则报复(V.5.21)。我们看到,战争中的色诺芬没能彻底告别“必然产生于人类生活必然的政治性,或产生于这种必然的政治性之诸种根基”[3](P50)的政治正义。然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色诺芬竭尽全力地摆脱了回报和报复中的慷慨意味。“胜过”一词充分展现了这种大方,从而使得政治中必要的恶行在合适的界线上止步,以胜过敌人的方式对敌人做恶事必然意味着超过分寸的恶或残酷。居鲁士们是这种过分残忍的化身。《上行记》中的小居鲁士极端残酷地处罚那些他眼中的邪恶、不义之徒(I.9.13);老居鲁士在自己参与的第一场战争之后,迷恋地盯着敌尸的脸庞(《居鲁士的教育》I.4.24)。相比之下,色诺芬绝对没有残酷的言行。如果习俗所主张的政治美德的确是政治生活中必然的意见,色诺芬则以自己的事例表明它还有升华的空间。色诺芬还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政治美德的拒绝。[2](P49)尽管亚美尼亚王在《居鲁士的教育》(以下简称《教育》)中杀死了儿子的教师,一位苏格拉底式的人物(《教育》III.1.38-39),但《上行记》中万人军在亚美尼亚的行程是一段欢乐的时光。色诺芬没有报复,此举与他在罗列苏格拉底的美德时没有提起男子汉气概(《回忆》IV.8.11)含义相同:报复敌人向自己施加的恶行是男子汉美德的应有之义。
从好(或善)的角度来看,色诺芬躬行的美德高于居鲁士的美德,是对后者的超越,当我们将色诺芬的美德与苏格拉底相应的美德进行对比的时候,一种更高级别的优越立刻显现出来。在《回忆》中,色诺芬以“我”的口吻这样评论苏格拉底的正义,“苏格拉底是如此的正义,他从不伤害任何人,哪怕是微小的伤害,而是最大限度地施惠于那些利用他的人”(《回忆》IV.8.11)。《回忆》的主旨是在城邦面前为苏格拉底的正义辩护。色诺芬在其中向我们展现了苏格拉底的关系性正义,即苏格拉底作为一个朋友、教师(《回忆》I.6.15)、伙伴、父亲、城邦民在与别人交往时表现出来的正义品格。苏格拉底的正义显然要高于《上行记》中色诺芬的正义,前者当中不包含伤害带来的恶行。这时我们发现了施特劳斯观点的意义,色诺芬的正义确实居于苏格拉底与居鲁士的正义之间的某个位置[2](P58),既体现了苏格拉底正义中纯粹的善,又包含了居鲁士正义中必要的恶,它是哲人之善实现的保障。苏格拉底的正义在政治生活中代表了正义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①,在色诺芬的政治实践中扮演着根基的角色。色诺芬用忒迷斯与狄克这对母女的关系来比喻苏格拉底的正义与色诺芬的正义之间的亲缘关系。尽可能地去除人类生活中的恶是哲人的政治理想,是哲学给予政治的教诲,《上行记》中的色诺芬便是这种教诲的化身。这时,居鲁士上升和色诺芬下降的意义也随之变得清晰起来。哲人的绝对正义出现在以苏格拉底的思考为主题的《苏格拉底的辩护》(16)中:满足于自己的所有,不需要别人的任何东西。亚里士多德对智慧生活的自足性持有相同的观点:相比于其他的人类生活,只有智慧的人靠自己就可以思考,而且越是这样,他就越是智慧(《尼各马可伦理学》1177a30)。
色诺芬所处时代的一种现实可能是促使他选择叙拉古人的理由。当时雅典与叙拉古是海军和海上贸易的强大力量,《希腊志》对此现象有所反映,提到叙拉古人的时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雅典人,反之亦然。《上行记》中叙拉古人是托名的对象,而在《会饮》中,表演者叙拉古人在众人谈话中的表现像是苏格拉底的对手。施特劳斯在公开出版的作品中,仅仅是稍微暗示了一下色诺芬两次选择叙拉古人的做法互为原因[3](P178),而在写给克莱因的私人信件中,他陈明了《会饮》中的三种人物影射关系:安倜斯忒尼(Antisthenes)代表苏格拉底,菲利普斯(Philippos)代表色诺芬,叙拉古人代表柏拉图。[4](P305-306)我们知道,在柏拉图笔下叙拉古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他曾经试图在这里实现哲学与政治的结合。而色诺芬将一名哲人在蛮族土地上从事政治并创建了业绩的故事托于一位叙拉古人名下。托名他人的做法也为色诺芬带来了方便,它使得作品中的色诺芬与作者色诺芬之间的距离变得遥远,第三人称单数的叙事口吻顺理成章,这样,色诺芬在记述自己的经历时不可避免地要抬高自己的观点[5](P332)成为毫无依据的论调。在卷一和卷二中,作者偶尔以 “我”(I.2.5;I.9.22;II.3.1)的口吻说话,但自从色诺芬的下行开始之后,“我”从未出现,直到这支希腊军队的下行之旅结束,新的上行之旅开始之时,也就是在全书的末尾结言中,作者才以第一人称复数“我们”(VII.8.25)的面目出现。作为读者,我们切不可将“我”混同于色诺芬本人。
二、书名的意蕴
书名是Kyrou Anabasis,由两个名词构成。如果我们孤立地看待它,我们将无法确定究竟这是哪一位居鲁士,是波斯帝国的创立者,还是武力篡位失败的小王子。我们提到这种混乱并非毫无根据,因为色诺芬还著有一部伟大的作品——《教育》。倘若色诺芬在“居鲁士的上行”前加上“小”字,或者在“居鲁士的教育”前加上“老”字,就可以避免纷乱,因此,许多后人替色诺芬做了这样的工作。色诺芬本人是不是特别热衷于在读者心里制造混乱,还是另有深意,旨在提醒我们两部作品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实际上,这两部关于居鲁士的作品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仅仅是题目中有一个相同的人名。小居鲁士在《教育》(Ⅷ.8.3)结尾作为波斯帝国堕落的结果而现身,老居鲁士在《上行记》(I.9.1)中则以“最有帝王之气,最配得上统治”的波斯王室典范出现。有一种十分流行的意见是:色诺芬在与小居鲁士有过交往之后,才构思了《教育》这部小说,因而小居鲁士是老居鲁士的真实原型。笔者大致同意这种主张,不过对原型意义的理解还需要深入一些。色诺芬与小居鲁士的交往经历是写作的一个动因不足以解释作者何以在两部作品的书名中不加分别地使用同一个名字,表面上的相同可能意味着内在的深刻一致。作为原型的小居鲁士与色诺芬笔下完美君王的老居鲁士在本质上相同吗?阅读《教育》和《上行记》之后,我们不难发现两位居鲁士表面上的差别。比如,老居鲁士是一个合法的王位继承者,小居鲁士则是一个犯上作乱的奴隶(I.9.29);老居鲁士创建了庞大的帝国,小居鲁士则兵败身死;老居鲁士寿终正寝,小居鲁士身首异处。然而政治功业上的差异和个人命运的不同并未掩盖两位居鲁士本质上的相同,将一名极端成功的君主与一个落得枭首示众下场的奴隶相提并论,如何可能?色诺芬使之成为可能。因为,从哲学的高度来看,两位居鲁士都缺乏真正的教育,都不具备真正的美德,因此都需要教育。施特劳斯如此总结《教育》的宗旨:《教育》是对野蛮的丑恶即缺乏教养的丑恶所作的极其不野蛮的描述,因而是对教养极其有教养的劝导。[4](P282)
我们以节制为例来具体地理解施特劳斯的归纳。在色诺芬笔下,古老的波斯对贵族子弟实行禁欲式的教育,节制被奉为美德,政治上的荣耀是国家为舍弃了肉体享受的人们准备好的替代性奖赏(《教育》I.2)。老居鲁士就成长于这样的环境之中,然而,他的一段少年时光是在穷奢极欲的米底亚度过的。这种双料教育对老居鲁士产生的影响在他建立帝国前后的行为差别中显现出来。之前老居鲁士一直穿着简朴的波斯服装,之后他便穿上了雍容华贵的米底亚长袍,不只如此,他还蹬上了鞋底加厚的靴子,涂了眼霜,在身上抹油(《教育》VIII.1.40-41和VIII.3.13)。然而,色诺芬并未直接揭露这个堕落过程,复杂的装饰被当做一位君主获取治下臣民爱戴的一种必要的方式。饮食上的节制也是波斯贵族子弟接受的教育课程(《教育》I.2.8),在帝国创立前,居鲁士严格地奉行这条习俗,之后他时常大摆宴席,作者在赞美居鲁士对待臣属体贴入微时暗示了宴席的丰盛(《教育》VIII.4.6)。老居鲁士还将自己表现为一个完全缺乏男女爱欲的统治者。他甚至拒绝看一眼亚细亚绝世独立的美人潘蒂娅(Pantheia)(参《教育》V.1.8),果断地拒绝了戈布里亚(Gobryas)送来的女儿(《教育》V.2.7),最后他娶了米底亚国王的女儿,以这种方式彻底获得了这个王国(《教育》VIII.5.18-19)。当我们阅读《上行记》的第一卷时,我们发现小居鲁士正是撕去美德伪装的老居鲁士。施特劳斯的总结尤其完全适用于卷一第九章的小居鲁士颂文。色诺芬以委婉的笔法揭示了小居鲁士的浮华。作者在描述居鲁士身边波斯贵族的穿着打扮时引发我们联想居鲁士自己的穿着(I.5.8)只能更为豪华;在表现居鲁士慷慨地赏赐投诚的西里西亚国王时,间接地告知我们此时他已经采用了波斯国王的豪华排场(I.3.27)。在称赞居鲁士对朋友无微不至的关心时,我们获得了关于他饮食上的信息:酒肉相伴(I.9.24-26)。在罗列国王的俘获物时,我们知道其中有居鲁士的两名妃子,至于居鲁士与别人老婆的情事,作者表示自己并不知道事情的真假(I.2.12)。
居鲁士的教育不仅意味着居鲁士接受的教育,还可以表示居鲁士施加给别人的教育。下面我们就来看老居鲁士如何以美德来教育他的宫廷卫队,当他作为一名施教者发言的时候,支配其行动的理念就暴露出来。他所教导的是审慎(sophrosyne)与节制(egkrateia),他在两者之间作出了清晰的区分,分别给出了定义:审慎就是在不可见的情况下也逃离可耻的东西,节制是在有人看见的情况下避开可耻的东西(《教育》VIII.1.31-32)。可耻的东西自然是指波斯的风俗和法律力图压制的一些身体欲望。按照居鲁士的意见来看,审慎是彻底或真实的节制。老居鲁士自己并非审慎之人,他仅仅在需要的场合才表现出节制,他要传授给部下的也是所谓的节制,帝国的品位就是由老居鲁士的虚伪美德而塑造,臣民与老居鲁士一样,表面上是谦谦君子,实际上则蝇营狗苟。他们在特定的条件下拒绝欲望的满足仅仅是为了克服羞耻感,即避免让别人看见或听到,羞耻感仅仅与耳朵和眼睛这两种器官有关,无关乎灵魂秩序的塑造,伪装却常常可以轻易地骗过眼睛和耳朵。至此,我们就不会对老居鲁士前后判若两人的现象感到奇怪,因为他的一生致力于追求的是政治荣誉、权力、财富,而不是美德,当目标达到之后,作为手段的美德就随之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欲望堂而皇之地登上宝座。到了小居鲁士生活的时代,审慎与节制的分别在宫廷教育中已经消失,审慎变成了仅凭听和看来加以教授和学习的东西。色诺芬质疑了这种教育和学习所能达到的效果(I.9.3)。
就书名的结构而言,“居鲁士的教育”与“居鲁士上行记”非常相似。它们都是一个偏正结构的短语,其中教育和上行(anabasis的意思是上行、攀登,攀登的路、山路)都是含有行动意味的名词。就书名与内容的关系而言,这两部著作也最为相似。《教育》除了第一卷讲述居鲁士所受的教育之外,余下所有篇幅是在讲述居鲁士的政治作为和功绩,是其所受教育的应用和后果——有必要加上后果两字,因为最后一章讲述的是帝国的坍塌。正是后六卷看似偏题的内容揭示了真正教育的必要性,最后一章尤其以一种急迫的口吻召唤真正的教育。最后一章看起来与全书的内容十分不和谐,然而是叙事必然的落脚点,随着居鲁士的死去,他以欲望为纽带建立起来并加以维持的秩序必然崩溃。看来,“居鲁士的教育”这一题目,除了表面上的意思,即居鲁士所接受的教育和居鲁士施加的教育外,还旨在引出真正的教育。在色诺芬笔下,老居鲁士站在政治世界的顶峰,并在后世受到推崇,堪称完美君主的典范,如果没有超越于政治之上的立场,对居鲁士的批判和教育几乎就不可能。
“居鲁士的上行”这个标题只能涵盖第一卷的内容,之后便是哲人色诺芬的下行。对观之下,“居鲁士的上行”与其内容的偏离程度更高一些。郝岚德对标题的解释[6](P351)可以弥合这种表面上的偏差。希腊语中的属格或二格通常可以用来说明来源,即来源二格。如果我们从来源二格的角度来理解书名,那么,Kyrou Anabasis的意思就是“从居鲁士那里上升(Asent from Cyrus)”。上升意味着对居鲁士的超越。是谁从居鲁士那里上升呢?我们知道,经过卷二短暂的过渡,从卷三开始,色诺芬便成为了主人公,率领希腊人开始了返回希腊的行程。而色诺芬在出行的事情上首先就寻求苏格拉底的指导,他背负着苏格拉底的教导开始了哲人的政治之旅。哲人开始参与政治生活这一事件被描写成地理意义上的一个由内陆向沿海的下行过程,地理位置上的由高至低喻示着哲学之于政治在种属等级上的优越。基于相同的理由,两位居鲁士合为一体在《上行记》中被置于一段上升旅程的起点,政治在哲学的指引下上行,从邪恶上行至美德,从野蛮上行至教养。看来,上升与下降在色诺芬笔下与在柏拉图笔下有相同的内涵。在此,我们想起《王制》开篇的第一句话中的第一个动词下行(katabainein)和洞穴比喻(《王制》514b)。对于那支由希腊各个民族或城邦的人组成的雇佣军而言,他们在《上行记》中的行程是一个圆圈,先是居鲁士将他们从海边低处的地带领向高处的内陆,在居鲁士死后,他们在色诺芬的率领下下行“退回”到希腊,然后他们又跟随斯巴达人从海边出发向内陆进军攻打波斯人。上行之后又下行,下行之后又上行,这种从某一点开始行进、之后又向原点复归的运动似乎喻示着色诺芬关于政治生活的一种悲观认识。
作为最长的苏格拉底作品,“回忆”作为书名同样容易引起误解,它既没有显露这部著作的主人公,也没有揭发主题。如果我们同意文学评论界的意见,即色诺芬的《上行记》是西方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自传体小说,“回忆”一词也许更适合于《上行记》。然而,这仅仅是我们的假设,色诺芬没有这么做,他在《回忆》中说过:回忆苏格拉底是受益的事(《回忆》IV.1.1)。其他的三部以苏格拉底为主人公的作品《齐家》、《会饮》和《申辩》都是他对苏格拉底的回忆:苏格拉底是美德和知识的最高典范,他的言、行、思最值得回忆。[3](P84)
参 考 文 献
[1]拉尔修. 名哲言行录,马永翔,赵玉兰,祝和军,张志华译[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2]施特劳斯. 色诺芬的《上行记》,高挪英译[A].经典与解释13:色诺芬的品味[C].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3]LEO STRAUSS. Xenophon’s Socrates[M]. St.Augustine’s Press,1998.
[4]施特劳斯等. 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施特劳斯通信集,朱雁冰,何鸿藻译[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5]COLONEL WILLIAM MURE. A Critical History of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Ancient Greece,Vol.5[M]. London,1857.
[6]郝兰德. 色诺芬的哲人之旅——《上行记》和柏拉图的《王制》,邱立波译[A]. 古典诗文绎读,刘小枫编[C].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