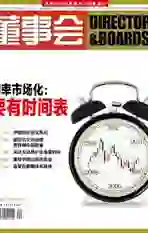商学院
2011-01-01
董事会 2011年4期
管理层单一的日本教训
J. Stewart Black
“二战”后,日本企业迅猛发展。20世纪90年代,当这些日企收购洛克菲勒中心时,它们看起来几乎马上就要主宰世界了。在当时的全球财富500强企业中日企占了整整36%,而美国仅占30%。然而今天,全球财富500强中日企只占12%,日本经济也已经淤滞不前20年。这一切主要源自日企全球扩张的失败。
日本企业虽然已经在美国、欧洲开设工厂,拓展海外市场,却疏于管理层的多样化,管理结构远未全球化。据调查,欧洲公司的高管78%是本土人士,美国大约是82%;而日本企业的高管99%是日本人,日本跨国公司的高层里往往一个外籍人士都没有。这导致公司在作重大决策,特别是拟定全球战略时,没有人能给战略注入与众不同的他国观点。甚至日本企业驻外子公司的高层也多是日本人,公司的直接报告都由日文书写。
即便目前日企已经决定开始本土化,但是起码还要20年,这些当地人才能由地区分支晋升到全球总部。而日本企业并没有另一个30年可以等待。其实,日企完全可以直接引进外籍管理人才,但至今它们仍没这么做。而值得注意的两项个案——尼桑聘请CEO Carlos Ghosn和索尼任命CEO Howard Stringer,都是迫于金融危机的压力而为。
日本的经验提供了不少值得深思的教训,而最重要的一点是:日本企业以及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应该确保领导层的多样化。在同样的教育、文化、语言背景下长大的人会有相似的想法。只有新的与众不同的人才,才能给公司提供新思路。在本国成长、壮大,最终成为成功的出口商,与扩张到海外然后整合全球资源成为一家跨国公司,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在国内,标准化生产能够帮助公司降低成本,从而以低廉的价格实现出口,进入海外市场。但是标准化在公司的全球扩张中却不太起作用,因为全球各地的人们想要的东西不可能完全一样,公司必须调整产品。
其次,公司在国内管理员工的手段也不适用于其他国家。各国的人各有特质,国内的管理技巧、激励方式不一定会起作用,公司必须因地制宜改变管理风格。
最后,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应当谨记:必须积极培养拥有他国背景的领导人。目前,巴西、印度、中国和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的大型跨国公司高管依然主要由本土人士担任,很少有外籍员工能进入管理层。因此,为了避免在进入海外市场时水土不服,这或许是这些公司当前最应该关注的事情。
遏制贪婪
Chris Bones
各行各业对公司领导的信任都一落千丈。更糟糕的是,领导人统辖的制度和结构也随之出现种种问题。这种情绪源自公众的一种普遍感受,即上层社会的人们拿走了最多的好处。
事实确实如此,能够展示领导层与普通工薪阶层薪酬增长不对等的统计数据实在太多了。1998年到2008年,英国最富有的10%的人口实际收入上升了近40%,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收入却下降了约2%。
尽管来自公众的批评声不断,但在银行业、政界、商界和公共服务领域,收入差距扩大的态势依旧,领导人似乎毫无察觉。身处领导岗位的人大多有着盲目的自信:我能做到这个位置必然是因为我很有天赋。而高额薪酬再次加强了他们对自身“超然”地位的信心。
但是,没人能成为完美的领导者,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完美。事实上,如今充斥着领导层和领导人培养过程的宗教式个人崇拜极其危险,不仅会威胁公司也会对整个社会产生不利影响。此外,人才战争助长了组织自我崇拜的现象。奖励和晋升制度不断地对个人能力进行肯定,导致个人信心的过度膨胀,依循这一路径培养出来的领导人常常认为自己获得的收入完全是基于自己的能力——自己比普通人更加优越,理应获得更多报酬。却不知道,当一家公司的领导人四处标榜自己为公司所作的个人贡献时,这种自我陶醉便已埋下悲剧的导火索。
妖魔化银行家和商界领袖对社会并没好处,但是这一切很难停止,除非他们能够认同:自己的薪酬应该与公司中其他员工的收入保持相对公平。政府或许不应该插手这一过程,毕竟,真正能决定薪酬多寡的正是公司领导自己,领导层必须勇敢而理智地面对这项考验。
战略协调藏“金”
Donald Sull and Alejandro Ruelas-Gossi
战略协调能够让企业更快地进入市场、适应环境变化、减小公司的投资压力,因而能够让公司获得更多机会。那么,战略协调可以解答一些什么问题呢?
怎样服务金字塔底部的新兴市场客户才能有利可图?墨西哥水泥公司CEMEX与五金店、银行和社会团体领导合作,建立了一个销售网络,来帮助贫穷的客户扩建家园。CEMEX没有选择自己去铺设整个网络,虽然因此导致销售价格相对较低,但依然赢得了合理的投资回报。
如何才能摆脱有限产品带来的限制?瑞士的一家保险公司Baloise通过与商业伙伴合作,开发了品类众多的保险产品。譬如与商业服务提供商合作,为客户提供商品保险以外的保险策略,与防汛公司、数据安全公司和消防安全公司合作,为客户提供防范风险的综合方案等。
如何在公司核心市场外的其他市场获得发展?1986年,全球速溶咖啡领导者雀巢就推出了Nespresso牌咖啡机,但之后却从未组建过家用咖啡机的销售系统。其销售完全依赖于与咖啡种植者、机器制造商、经销商、服务公司和高端伙伴(包括丽思卡尔顿酒店和国泰航空)的合作,携手构筑了一整套销售服务网络,为消费者提供奢华体验。
如何为客户提供综合体验?苹果公司自创立起就一直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无缝体验。在Mac机时代,公司始终亲力亲为所有事情。然而,到了iPod以及之后的iPhone和iPad时代,苹果公司明智地改变了策略,通过整合内容提供商和配件制造商系统,让客户能够更加便利地享受各种苹果产品的使用体验。
如何利用低成本产品实现收入增长?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2010年的平均票价为35欧元,是欧洲大型航空公司中的最低价。然而机票价款并不是该航空公司的全部收入,通过与Hertz、Booking.com、Costa游轮和Banco Santander银行的合作,航空公司还为乘客提供汽车出租、酒店客房、游轮和品牌信用卡等低成本的配套服务,并据此从每位乘客身上获得平均10欧元的收入。
金融创新挑战公司治理
Henry Hu
公司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即股权和债权的“脱钩现象”。这种脱钩现象很可能会影响到经济与金融系统的核心机制。
公司的基础架构本来十分清晰。股权代表与之相应的经济权利和投票权(当然还有其他权利与义务);而债权与之类似,也代表了包括取得本息、贷款协议赋予的控制权或债券契约等一系列经济权利和相应义务。总之,在经典的定义中,股权和债权都同时包含着经济权利与相应的义务。
但是,这些对股权和债务的经典解释如今不再适用了。衍生工具的重大变革,对冲基金的兴起,将这种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打破。
首先是股权脱钩,即股票的投票权与股票的经济利益相分离的现象。几乎所有公司都遵循一股一票的惯例,而现存的公司治理理论也普遍基于这种经济利益与投票权的耦合。虽然无论从工具角度还是法律角度,这一制度都很合理,但是,对冲基金的出现使得投票权和经济利益不再必然相关。对冲基金可能拥有一百万的某公司股票,因而享有一百万选票。但是,该基金可能同时持有该股权的衍生工具空头,从而几乎可以覆盖所有的风险头寸。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有着可能是最高投票数的对冲基金却与这家公司的经济利益毫不相干。甚至,如果对冲基金持有的衍生工具空头头寸超过一百万,那么其利益事实上是与这家公司冲突的。这时对冲基金就成为了“空投票人(empty voter)”,很可能利用手里的投票权遏制公司发展,甚至搞垮公司。
其次是债务脱钩。无论是企业直接贷款还是资产支持证券,债务脱钩都可能出现,悄悄削弱企业的实力,增加整个经济体的系统风险。目前,贷款协议和破产法都以债权人不希望借款者破产为前提。然而事实上很可能出现例外,不妨考虑这样的情况:债权人借给公司一亿,但随即买了2亿的信贷违约掉期,会怎样呢?显然,债权人会因为借款公司的破产而受益。这时他就成了“空债权人(empty creditor)”,与公司的经济利益相冲突。
股权、债权的“脱钩现象”仅仅是一个开始,未来公司治理必然面对更多来自金融创新的挑战。企业应当审慎地使用衍生工具,小心防范金融创新带来的潜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