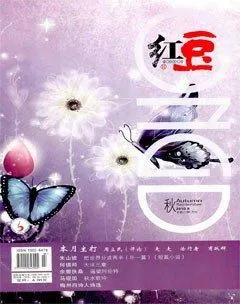窗台上有一群麻雀
2010-12-31高维生
红豆 2010年9期
高维生,吉林人,满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滨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散文集《季节的心事》《俎豆》《东北家谱》《酒神的夜宴》《午夜功课》。从1988年开始在《中华散文》《文学界》《作家》《美文》《北大附中远程教育》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多次获得各种奖项,在韩国、新加坡发表作品。并被选入《21世纪年度散文选·2001散文年选》《1979-2008中国优秀儿童文学典藏》等多种选本。
一
清晨,我还没睁开眼睛,走进意识中的是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执意地想透过窗玻璃伸进房间的深处。
这时,我不会在床上多躺一分钟,马上穿好衣服,为它们开饭。我不知道,这群野生的麻雀,它们的家在哪儿,它们从哪儿来的。我在窗台上撒金黄的小米,麻雀飞来,十几只栖在窗台上,强健的短嘴,不停地啄食。这是一个家族,分工严密,对外来的麻雀绝不手软,逐出领地。
不管是雨天,还是浓雾的日子,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喂麻雀。然后,我坐在沙发上,一边刮脸,一边看麻雀吃食。麻雀对屋子里的声音已经习惯,时间长了和家里的人熟悉了,有时吃饱了的麻雀,小巧的爪子,攀在钢窗棂子上,倒挂在那里,小脑袋在玻璃后面晃动,顽皮地向屋子里观望。有几次,我们目光碰撞时,麻雀不但没惊慌和奔逃的意思,漫不经心地和我对视。吃饱的麻雀吵嚷、追逐、游戏,箭一样地向天空飞去。
养麻雀是受父亲的影响,他养过一群野生的麻雀。济南的家被水泥楼群包围,楼前不大的院子,铺上了水泥地,没有一株树。雨天阴得像要塌落下来,雨水无处渗漏,积一片片水洼。夏日的阳光下,水泥烤得烫人,一潮潮地淹没行人,黏稠的热缠在身上,贴在脸上,撕也撕不掉,腾起烤人的热气。麻雀给我家带来了不尽的欢乐,它们的叫声,不是电视机里的娱乐节目能替代得了的。父亲每天坐在靠窗的白蜡杆的圈椅上,看看报纸,喝一壶清香的茶水。父亲说,满族人有养野鸟儿的习惯,这和满族人长年山南水北在外征战,渔猎生活,人和动物,人和土地,人和自然和谐相处,表现满族人对自然崇拜中所表现的朴素的感情。有一次,病后出院的父亲,站在窗前,对麻雀吹口哨,父亲的口哨麻雀的叽喳,一问一答。
回到滨州后,在窗台上发现了麻雀,我便开始用小米喂养它们。一天,家里没小米了,我抓一把大米放在窗台,麻雀飞来,一口也不吃,只是不停地在窗台上跳动、吵叫。我知道大院门外的街对面有一排门市房,一家卖粮食的小店,小米一斤是1.5元,色泽不新鲜,我怀疑是陈化米。银座超市的小米一斤是1.6元,路程又远,我还是每次都去超市买。
二
麻雀是流浪的“吉卜赛”,它们没自己的家园。四处漂游,无拘无束,一群麻雀就是一个家族。生活在一起,无牵无挂,浪迹天涯,是我向往的一种生活。麻雀是动物中的“草民”,没华美的外表,漂亮的名字,更没有高贵的身份。对生存也无过多的要求,却曾经被我们当作敌人。人们敲打脸盆。击鼓打锣,放鞭炮,摇动绑布条的竹竿,庄稼地里竖上草人,越打越猛,令麻雀们闻风丧胆。
E.B.怀特认为:“人类太精明于自己的利益了……我们对待自然的办法是打击它,使它屈服。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多疑和专横,如果我们能调整好与这颗行星的关系,并深怀感激之心地对待它,我们本可有更好的机会存活下去。”
2009年夏天的时候,几个穿白大褂、戴口罩、背着喷雾器的人,对着大院的角角落落、几株孤零零的树一阵狂喷。空气中凝固一股刺鼻的药味。他们隔几天来一次,黏稠的热和药味混成一团,贴在人的肌肤上,极不舒服。现在城市的楼盖得高,绿地越来越少,街树上喷洒的药虫剂,使很多的麻雀丧生。报纸和电视上没有动员全民封杀麻雀,大量的化学药剂,汽车的废气出现,树木的减少,却使麻雀难以生存。
三
我和这群麻雀成了邻居,窗台成了它们的餐厅。清晨听到麻雀的叫,我知道到点起床,下午不用看天色,听麻雀的叽喳声,我就知道暮色将降临了。我回家做的第一件事是喂麻雀,如果稍晚一点,它们就聚集在窗台上大声吵嚷。
我站在窗前看麻雀吃食,清晰的啄食声,让我有了满足感。观察每一只麻雀,想弄清家族史,它们的家谱是从那一代开始的,到它们到第几代了。毛绒绒的麻雀,娇小可爱,背上的花纹,没有明显的图腾标志。谁是家中的族长,谁是夫妻,谁是最受宠爱的小儿,我无法分清。
麻雀饱餐后,栖在窗台上,沐浴在阳光中,让阳光洗去身上的尘土。
麻雀们穿梭于城市的高楼之间,来窗台吃食、戏耍。
而我,常去超市买小米,每天准时、准点喂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