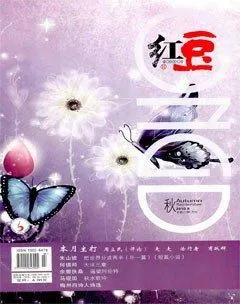咩嘟咕
2010-12-31霁虹
红豆 2010年9期
霁虹,实名祁开虹,男,彝族,生于1967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凉山州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会理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文联主席。1984年发表作品。著有诗集、散文集四部,作品入选《青年诗选》等45部选集。2004年就读于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第四期。
在一个汉子长长的歌声的尾端,我看见了那个村庄。
它也许是由彝人的英雄支格阿尔不经意地从哪一个地方拎来,随手放置在那里;它也许是从一个彝族人悠长的梦里生长出来,在那里沐风浴雨。它仿佛是一簇忧郁的云,它仿佛是一群^用生命注释的符号。
这个古老的村庄名叫“咩嘟咕”。
“咩嘟咕”,说成汉语就叫“屯兵的地方”。
眼前几棵高大的攀枝花树,每一棵都伸出上百只手臂。而此时正值花开,一片灿烂的红霞就这样笼罩着这个村子。
从村子到金沙江边尚有一段距离,在村里看金沙江,就好像是一条蓝色的飘带横在山下。小村这边是四川,江那边是云南,这一个小小的村子便成了控扼川、滇的要塞。因此,明朝皇帝把江南的战士们不远千里地搬移过来,叫他们驻扎在这里,为大明统治的殿堂竖起一根安稳的梁柱。
无论用什么做的梁柱,总是会被时间损毁的,大明的神殿最终倾覆了,远来的戌卒们,把籍贯留在遥远的地方,把子孙后代遗留在这一片神性的土地上,他们与这里的土著融合在一起,生育了一群有着江南籍贯的彝人。在沿金沙江一线,无论走到哪一个村子,见到村子里的人,你问他们的族别,都是彝族,而你进到他们的家里,却见他们俨然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神位,在来历那一栏,都写着他们的家族来自于江南某处。
不走不动的石头呵,不绝不断的水流。几百年前的兵营的号角声再也听不到了,可是,在村后的断崖上还有一圈一圈声音的符号,在张显着嘹亮;高高耸立的山峰,一定和着乡愁压得远戌人从心底里挤出阵阵悲歌;山脚下蓝色的飘带,一直飘绕而去,飘到江南水乡,飘进白发父母的梦里,飘进织布女子的机杼。我抬头望山顶,江岸的顶端那一抹飘浮不去的云,是否就是兵卒们思念的泪水蒸发而凝成。
上游鱼鲊渡渡轮的汽笛声穿峡而来,阳光被震动得闪闪发亮。那里是汉代开辟的古老的“清溪道”的渡口,也是现在“一〇八国道”的渡口,那些远来的兵卒们,沿“清溪道”到鱼鲜渡,再从那个渡口沿江而下,再爬上一段陡峭的山坡,就到达这里了。他们远望江对面的高山,再回望身后的高山,目光被山阻断了;他们沿金沙江望去,苍茫之中升腾着雾瘴,在这一条空远的幽谷中,他们的目光迷失了,甚至,他们的心也迷失了,以至于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村前有一座土台,上面有一块浑圆的石头,我试着登上去,一阵峡谷风吹来,吹乱了我的头发,挟着沙石的风抽得我的脸一阵阵疼痛。这个土台也许曾无数次地被士兵们攀爬过,在上面吹响号角,在上面遥望远处,放飞思念。这个土台和石头,为他们排解过无数的忧愁,也为他们带来如水如波的惆怅。吹向我的风,是他们在遥远的过去,传达过来的问候,我的那一份疼痛,是来自一个王朝的疼,是来自一个历史的痛。我捋了捋头发,任这一阵阵苍凉的风,把我的泪吹下。
引领我的那个汉子,朝前面走了过去,他经过一排旺长的仙人掌林,山随他绵延而去。看着他的背景我激动不已,你看,他向小路那样执著地走去,他不就是那些士兵中的一个吗!风吹过他的肩头,吹过他的头发,他的脚下的尘土随着风飘起来,渐渐升高,仿佛是战地的烽烟。而落日的阴影大跨步地跨过江来,像潮水一样,一不经意间竟把他淹没。时间好像现出了一个巨大的漩涡,这个漩涡在吸纳着他,我生怕与他匆忙错过,因而,张开双臂向他狂奔而去。
夜色是拽着他的歌声悄然坠地的。苍老的村庄好像喝醉了酒,在夜晚里一摇一晃。火塘里的火苗上窜下跳,似一群顽皮的孩子,任性地在我们的脸上跳舞。他有时用彝语,有时用汉语唱歌,有的歌甚至没有歌词,没有歌词的歌声透着无限的苍凉和忧郁,随着那歌声,我的心就像在梦里一样,走得很远很远。
后来,他告诉我,没有马匹了,没有毛驴了,汽车的喇叭声没有马嘶驴鸣亲切;唱调子的少了,唱古谣的少了,VCD的音乐哪有自己肺腑里唱出的抒情。
咩嘟咕,这个明朝屯兵的地方,曾经是那么的不起眼,藏在西南的群山之中,藏在一条古老的河岸,未有几人能识得;它曾经又是那样的重要,它是一个王朝伸向四方的手臂,这只手臂托住了一方的安宁,托住了一个王朝江山万年一统的梦想。
离开咩嘟咕的时候,我看见咩嘟咕的人们都走向村外,他们为我的匆忙而来匆忙而去感到悲伤,他们天生的忧郁的情感促使他们为每一个相识而后分别的人流泪。他们向我挥手,在山的阴影里,他们高举手臂,风飘着他们的发,就像是一面面呼呼拉拉扬动着的明朝军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