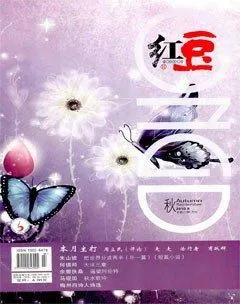是偶非偶
2010-12-31汪莉莉
红豆 2010年9期
汪莉莉,女,汉族。祖籍安徽休宁。任过电台台长、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文联主席。上世纪80年代起开始在各级报纸、电台、文学杂志发表消息、通讯、报告文学、散文、广播剧等各类文字作品,有部分作品获得国家和省、市级奖励。现为主任编辑、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
在人们的印象中,木偶本该是没有生命的。因为它们只是一段木头,是一段产于漳州、泉州一带的樟木、银杏木、香梓木抑或是产于台湾的梧桐木,经过雕刻师的磨光、粉底、开眉、打花面,装上发须之后,成为或哭或笑或男或女或老或少的“头”,再装上手足、布身和鞋靴,一个高约一尺的偶就诞生了。
可是,当我走进漳州闽台布袋戏博物馆时,一大群形态各异、神采飞扬、栩栩如生的偶,骤然间仿佛从四面八方齐齐地涌了过来……心,立刻被占得满满当当的。那一瞬间,我真切地感受到一种生命的悸动。
木头布身的偶,为什么可以这样地撞击着人的心灵?
我在寻找着答案。
“我们这个馆主要展示闽台布袋木偶戏的历史渊源、交流与发展,资料很珍贵,你看,这尊是拿过国际大奖的偶头;这些比较大的木偶是台湾现在流行的‘金光偶’、‘霹雳偶’;对了,玻璃柜里这几件木偶的‘行头’,还是宋代的呢!”领我参观博物馆的漳州市木偶剧团团长岳建辉如数家珍,满脸的自豪。
岳团长当然有理由自豪。这是大陆首家闽台布袋戏博物馆,博物馆的筹建,倾注了岳建辉和他的团员们大量的心血。不大的空间里,容纳了漳州和台湾几代木偶表演艺术家、雕刻家们的智慧结晶,也牵拽住了一段长长的、闪烁着两岸木偶大师们熠熠光彩的历史时空。在这里,我看见,闽南布袋木偶表演一代宗师杨胜、李伯芬和祖籍台南的陈南田,联手主演《大名府》、《雷万春打虎》在第二届国际木偶节上荣获金质奖章;我看见,被尊为“木偶之父”的江加走、徐年松,还有被文化部授予“中华一绝”的木偶雕刻大师徐竹初,如何吸收继承前人艺术精华,创作出具有形象陛、夸张性的木偶雕刻国宝;我看到了台湾著名布袋戏艺师李天禄和与之并列“台湾北部掌中傀儡戏双绝”的“小西园”头手许王,看到了台湾布袋戏宗师、百岁寿星黄海岱,看到了“金光戏”的开创者黄俊雄、钟任壁……
我在群偶中穿行。历史的风,穿越千年徐徐吹来,雷万春、秦叔宝、武松、少年岳飞……以及众多的我不认识的被扮演生、花脸、旦、神道、精怪的木偶们,在风中起舞。
它们来自何方?
很多年前,在游览敦煌莫高窟时,借着导游昏暗的手电光,我看过一幅壁画,一位妇女手上拿着很像木偶的玩具,对坐在她身边的一个孩子演示着。这是否就是最早的木偶?带着这个问题,我查阅过很多资料,说法不一。本世纪初,曾有报道说,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了商代的奴隶陶俑,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发掘出了乐俑、歌舞俑,多数学者认为,这就是最初的木偶,中国木偶艺术“源于俑”。而对于何时开始有中国木偶戏这个问题,学者们普遍的观点是“源于汉,兴于唐”。
那么,漳州的布袋木偶戏又是何时兴起的?查阅《漳州府志》,上面有这样的记载:南宋时,漳州、泉州布袋木偶戏已相当兴盛。以“节民力、易风俗为首务”的朱熹来漳州任州官,曾颁文“谕俗”,“约束城市乡村,不得以禳灾祈福为名,敛掠财物,装弄傀儡”。由此可知,当时漳州傀儡戏之盛,连郡守都被惊动了。
很难想象,在汉赋精丽的字行里,在华美的大唐歌飞曲扬和宋词的委婉韵律间,这些“于掌中备百兽之乐,宛转屈曲于指间,人形或长数分,或复数寸,神怪倏忽,衔丽于时”的小精灵,是怎样在闽南上空游走作怪,以至于惊动了一方官员导致痛下禁令?
触摸漳州年代久远的脉络,我看见,一千多年前的傀儡“相公爷”踏棚头唱着“欲问傀儡何人制,汉时陈平造出来”的古老传说,飘飘而来;我还看见,被瘴疠笼罩的古老的漳州腹地崇山纵横,滨海蛮荒,因生活波动,祸福难料和疫病流行,人们对未来充满恐瞑,所以“敬天礼神,崇鬼尚巫”祈求平安,于是,神秘的傀儡,就成了人们娱神的道具,成为凡人与神交流的使者。
可以说,那时的偶,是一种精神寄托。
在传统剧《雷万春打虎》的木偶造型前,我停下了脚步。一只虎偶沿着记忆长长的甬道咆哮而来。记忆来源于儿时居住的老街,一个叫做北桥的地方。那时小学正“停课闹革命”,无所事事的我背着年幼的弟弟,常去邻居家看“弄偶”。在当时,古装戏是不能演的,木偶也只能演“八亿人民八个戏”的“样板戏”。剧团演出是《智取威虎山》中“打虎上山”片段,那个邻家男孩耍的就是老虎。那只老虎会蹭痒、挠痒、回身咬尾和打瞌睡,而配合杨子荣的英雄豪气,被激怒的老虎又凶猛无比,张牙舞爪,展闪腾扑。更神奇的是,邻居会一手演英雄,一手演老虎,双手创造出人与虎两种截然不同的形体动作,口中还有台词配音,一会儿是杨子荣“啊-呀”、“嗨!”地使劲,一会儿又是老虎长啸的“吼-吼!”,我总是看得目瞪口呆,背上的弟弟更是兴奋不已手舞足蹈,忘情时还曾经把尿赏赐给我的脊背。几年后,弟弟被市艺校木偶班的老师挑中,哭闹着要去演木偶,恐怕与这段趴在我背上的“启蒙”有很大关系。不过弟弟终究没有当上木偶艺术家,由于外公的坚决反对。这个栽培了一群大学生儿子,并“引进了”一批大学生女婿的老人,断然不允许他的孙辈没领文凭就“溜号”。其实骨子里,外公是对木偶表演这种“做戏的”行当的未来有着深深的担忧。他曾亲眼目睹旧社会那些木偶艺人流落街头卖艺乞讨,沦落到和“打拳头卖膏药”的江湖郎中为伍的悲惨境地。
所幸的是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这种被封建卫道士和统治者视为“伤风败俗的”布袋戏,如今已成为共和国文艺舞台上的精品,来自民间的娱乐,上升到艺术,甚至是受国家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做戏的”下九流,成为人民的艺术家。我的那位邻居洪惠君从“打虎上山”起步,在《大名府》中舞狮、在《卖马闹府》中卖马,30多年来导演和主演了许多获奖剧目:木偶剧《森林里的故事》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少年岳飞》获第九届全国“文华奖”。他所在的漳州木偶剧团,刚刚过了50岁生日。剧团先后到过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友好访问演出,精湛的演艺被外国艺术家誉为“世界第一流艺术”,漳州木偶则被誉为“东方艺术珍品”。如今,剧团还与媒体“联姻”,制作电视木偶故事片,正尝试与动漫相结合,争取让老百姓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艺术精粹。可以说,布袋木偶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终究没有被流年的风吹得像落叶一样散去,也没有被现代文明吞没,反而焕发出时代的光彩,这是政府远见和民间智慧的汇聚凝结,是传承文化同改革创新的和谐胜局。
有了国家的强大支持,木偶,成为一种艺术,一种文化。
对于两岸木偶渊源,台盟中央两岸关系委员会主任、福建省文史馆馆员陈正统认为,清朝康熙年间开放海禁以后,闽南一带的百姓大量移民台湾,带去了自身的文化并在台湾当地沿袭至今。台湾木偶艺术同仁中普遍推崇的“北派”,就源于漳州的漳浦。陈正统是台湾人,在研究闽台文化方面颇有见地,他说,闽台布袋戏同根同源。从人文历史考证,闽台文化原属一体。其母体为闽文化,是炎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布袋戏是闽文化在台湾的移植和延伸,已成为台湾民间文化的重要象征之一。
台湾布袋戏同行中,这种认同感尤为强烈。“在这个博物馆里我看到了原汁原味的闽南木偶艺术,看到了祖辈们发展的轨迹。我找到了原乡,找到了根源,找到了祖辈们一直梦寐以求的根的感觉。”台湾民轩文化艺术团艺术总监许国隆激动不已。
词中泪字,缠缠绵绵漫卷海峡两岸半个世纪丝丝缕缕的牵挂。岁月犹如潮汐一般,一阵阵,一遍遍,那一种割不断的根源,总是让人梦魂萦绕。据《台湾通史》记载,在台湾开发史上,最早率领漳泉移民纵横台湾海峡,对台湾进行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拓垦的,是漳州人颜思齐。400多年前,这位被尊为“开台王”的海商首领,率领“亦商亦盗”海商集团,驾驶“戎克船”纵横台湾海峡时,颠簸逐浪的船仓里,有一批又一批讲闽南话的漳州人,有价格“时时腾贵”的漳州名产漳缎、漳绒,茶叶和瓷器,也有各种造型的或藏或塞在这些远离家乡的游子的背包或木箱里的布袋木偶。这些漂洋过海的小精灵,在台湾生存、发展,逐步演变成如今深受年轻一代喜爱的“金光偶”、“霹雳偶”。布袋戏被台湾民众票选为“台湾意象”,金光偶戏被拍成影视打进了好莱坞,有的木偶甚至拥有自己的网站和“粉丝”。然而,无论如何发展变化,它们的根,还是在大陆,因为,从它们诞生的那一天起,它们就注定属于一个源头,就如同一个人一出生,就无法改变他的肤色一样。布袋木偶印着的,是华夏民族的底色,它的语言它的服饰它的坚韧深沉的精神力量,都打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的烙印。它们的根,永远在大陆,在闽南,在漳州。
所以,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陈正统建议:“台湾岛内90%文化都来自福建乃至大陆,目前福建是大陆仅有的可与台湾文化共通的地区,应该将海西纳入真正的国家战略层面,与台湾展开互动。”
血,总是浓于水。偶,是一种血脉,一种根源。
与大陆的木偶相比,台湾现在流行的木偶造型较大,约高60~80厘米,身材比例接近真人,有的偶头内有特殊装置,可以用绳子拉动控制眼睛睁眨。偶们身着的衣服也更华丽且多层次。“大陆的木偶造型都比较传统、古朴,传承了传统的精华;而台湾的木偶造型比较现代,想象力丰富。但无论外形如何变化,闽台两地的布袋木偶戏,都是用指掌直接操纵偶像进行表演,用手由下而上,以手掌作为偶人躯干,食指托头,拇指和其他三指分别撑着左右两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庄陈华,当即舞起一生一旦两偶。如同被注入了生命的元素,两个偶立刻翩然起舞:那旦拈襟揽袖,婆娑摇曳,袅袅婷婷,飘飘欲仙;而生的一举手一投足,似乎都会说话,一招一式,满满盈盈荡漾着的都是款款隋韵,真可谓指掌天地,春光无限。
不用借助铁线,不用借助仗头,也不用借光投影,只凭几根手指就能演绎两个性格、感情各异的偶人或者偶动物,这是否就是布袋木偶戏的独特的魅力?
其实布袋木偶戏的魅力远不仅此。2009年6月,漳州木偶剧团出访波兰时,听说克拉科夫市儿童医院有许多身患癌病的儿童,十分希望看到来自中国的木偶表演。全团成员立刻赶往医院,为病童们举行了专场义演。那是一群多么让人心痛的不幸的孩子啊,他们生命的花蕾刚刚含苞,癌症,这个凶恶的病魔就开始无情地吞噬那些鲜嫩的花瓣,一点,一滴……当剧团的演员们舞动着木偶,来到孩子们的病床前时,笑靥浮上了孩子们苍白的小脸,欢声在白色的病房里回荡。一位喉头插着人工呼吸器的女孩儿,在医护人员的陪护下,全神贯注地看完了整场演出;一位坐着轮椅的男孩子,在演员拿着木偶来到身边时,伸出纤弱的小手,紧紧抓住了木偶的小手,演员的手木偶的手病孩的手,就这样握在一起,黄皮肤“木皮肤”白皮肤就这样靠在一起,人心偶心孩童的心,就这样贴在一起,在最质朴也是最直接的人性光芒中,彼此温暖交融着。病童的眼睛里放出一种奇异的光彩,那是积聚了整个生命的能量,如火山爆发一样的光彩啊……
孩子们笑了,家长和医生护士们却哭了……
我不知道那女孩、那男孩如今是否尚在人世。这场演出对他们来说是第一次,也许也是最后一次,但是,相信所有在场的人和所有看过电视、照片报道的人,都会记住那样的目光,那样一种从孱弱的生命的最深处发出来的光亮。
那么,如果所有的光亮都积聚起来,所有的希望都热烈起来,是不是势不可挡,坚不可摧?
原来,偶,还是一种希望,一种点燃生命之光的希望。
我感觉到偶的厚重了:它是精神,是文化,是根源,甚至是一种燃烧生命的力量。可是,一尺多高的木头布身的偶,它为什么能够承载那么多那么多?
我情不自禁拿起一个偶。当我把食指套进偶头,中指和拇指套进偶的两手之后,我发现,掌心的位置,正好就是偶的心脏。十指连心啊!原来,是人的血脉通过手指,汩汩地流到偶的身上、头上、脸上,泽润着偶,人偶融为一体。因为有了心血的滋润,所以偶永远那么光彩亮丽,无论是腾挪在灯火辉煌的舞台上,还是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柜子里。无论多少时光过去,偶依旧那么新鲜、清洁,完好如新;无论多少重负在肩,偶都能够承受、担当,继往开来。它是有生命的,是古老的中华民族民间文化传流永恒的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
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会有一种发自生命底层的悸动,在不经意间,缓缓地深入骨髓……
耳边依稀有涛声漫过,我看见,偶们正站在风中,迎着海西建设涌动的热潮,欣然起舞。一种从心间、从手指间流淌出来的七色光彩渐渐弥散开来,在台湾海峡的上空飘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