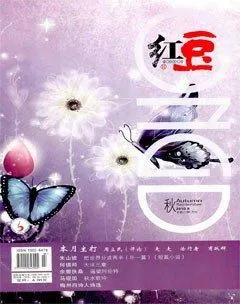白雨(短篇小说)
2010-12-31甫跃辉
红豆 2010年9期
甫跃辉,1980年代生于云南。保山人。复旦大学文学写作专业首届研究生。2006年在《山花》发表处女作,中、短篇小说相继在《大家》《中国作家》《上海文学》《青年文学》《长城》《西部》等杂志发表。有作品入选年度选本。获得2009年度上海文学短篇小说新人奖。
雨下到第二十六天,一个老人死了。也可能是第二十七天,没人记得清楚。那个黄昏,檐口的雨线断落成珠,厚厚的云层豁开一条口子,似沉睡的人眼睛睁开一线,荡出万顷光明。被雨水拘禁太久的村子,鲜得像一朵毒蘑菇。灰暗的瓦楞、爬上墙角的青苔、一汪汪浑浊的积水。无一不闪耀着灼灼光亮。人们眯缝着发霉的眼睛,举起手挡住晃动的光影,挡不住哭声一波一波地穿过手指缝隙,水雾一样蒙住他们同样已经发霉的脸。短暂的惊诧和交谈后,他们恍若一群沉默的黑鱼,游进李秉义家。
院落泥泞不堪,人们恍若置身一条黄浊的大河,鞋子和裤管糊了厚厚一圈黄泥巴。三五个妇女站在猪圈边,对空空荡荡、散发着霉味的猪圈啧啧连声,说李家损失比我们大呀,瞧这猪瘟闹得慌。另一个眼圈红了红,说哪家损失小了,养多少死多少,哪受得住啊。多数人聚在堂屋前,瞪着一双双鱼类的呆滞的眼睛,看到堂屋当中两条板凳架成的简易床板上,粗白被单的轮扇,勾勒出一具人形,白布尽头突兀地露出一颗白发凌乱的脑袋。那是在村路上走了七十年的李秉义媳妇。她和他们彼此熟悉,此时却有一条陌生的河流横亘在彼此之间。她紧闭眼睛,嘴角隐含讥笑,对四周投来的目光漠然置之。
不止一个人看到老太太的耳朵跳动着,仿佛在谛听生前几个姐妹的哭泣。哭丧的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有一位灰白头发的,叉开腿坐在地上,一只手扶在床沿,头垂在胸前,哭声低低的,勉强听得清说的是和老人同一年嫁到这个村子,天天吃稀饭的日子都熬过来了,怎么到现在还没享福就回去了。鼻涕挂成一条线,悬悬地坠到胸前,眼看沾上暗蓝衣襟,她抬手一撩,顺手抹在鞋底,手指沾了一片黄泥。那手又抹一把脸,脸就黄了,如戏台上的戏子,脸上的悲哀有着千百年不变的感染力。旁边几位老人鸣地大哭了,年轻的女人们也眼圈红红的,鼻尖坠着一滴泪珠。不少人眼前浮现出老太太生前的样子。老太太身子瘦高,面色白净,常年戴一顶白布宽边帽子,穿一件青色褂子,冬天就在里面衬一件毛衣。慢慢走在村路上,和人遇上了,远远地就会站下,手蓬在额前,眯着眼觑上一阵,小心翼翼喊出对方的名字。声音细细的,和对方寒暄两句,等对方走出好远,她才又慢慢走去。现在老太太彻底走了,她们才觉得,老太太曾如此温声细语地在村里活过。
李秉义的儿子恒山和媳妇跪在母亲头侧,听到老人的哭诉,恒山擤了一把鼻涕,把鼻涕在两只粗黑的手上搓着。恒山媳妇低着头,身子一抖一抖的,说哪个想得到啊,早上还好好的,只说胸口闷,要带她去卫生所瞧瞧,她说等雨小些再去,哪个想得到呀,下午雨小了,人已经不行了。有妇女就劝,说生死有命,做子女的尽了孝心就行,老太太到那边也含着笑。
灰白头发的老人想起往事,心里涌上无限悲伤。她说,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去乡里交粮,满大路全是人,你是小脚呀,挑不动挑子,还是我帮你挑了一程。第二天一早,就见你笑笑地站在家门口,拎着一小个从自留地摘的南瓜……老人越说越难过,哭诉一句,两手就拍一把床沿,随手带到了覆盖遗体的白被单,被单一点一点被拉下,露出了躺着的老太太核桃般布满皱褶的下巴,然后,是脖子。脖子软塌塌的,赫然嵌着一道生硬的红色。
哭声猛地就停了。逼仄的堂屋饔塞了庞大的寂静。午后的太阳照耀着湿漉漉的地面,静静发出一大片嗞嗞声。阳光透过灰蒙蒙的窗玻璃,在老人身上切出一角明亮。老人面色如生,脖颈上那道血痕水面游动的蛇一样晃了一下。恒山脸颊一抖,慌忙掖了被单,遮住母亲的脖子。媳妇的哭声迅速接上,其他停滞的哭声随之被重新唤起。可哭声不再是原来的哭声了。大家心照不宣,老太太不是病死的。灰白头发的老女人啪啪拍打着老人的身子,哭骂道,你这是做什么呀!你怎么这么狠心!恒山夫妇跪在另一边,不再哭泣,恒山媳妇絮絮地说,要是不说等雨停,也不会这样啊,老天这场雨真是要人命呀,说话时目光怯怯地在人们脸上扫过。恒山则不时拉一下白被单,老太太的嘴巴都给盖住了。
对老太太如何故去的议论,在人群中如雨后墙角的青苔一样飞速滋生。住在李家旁的人很快成为中心,他们仔细回想起过去一天李家院子的动静。一个瘦脸小眼睛的男人说,早上见到恒山拖死猪出去埋。我还和恒山开玩笑呢,小眼睛男人说,我说不错呀恒山,这时候了还有猪死。恒山苦笑,说是最后一头了。我也笑,还在雨里敬了他一根烟。妈的!小眼睛男人很愤怒地骂了一句,火机打了半天,才冒出个火星子,烟才点上,一家伙就被雨打湿了。
那就是了!一个宽脸女人说,我说怎么一上午听到他家吵架呢。就听李秉义骂她,说要不是她贪小便宜,从路上捡回那只病怏怏的小猪,家里养的这么多壮猪也不会死光。老太太分辩说,自己不是贪小便宜,是觉得小猪可怜。李秉义发火了,说老太太贪小便宜的脾性年轻时候就有了,要不是老太太不想离开村子,他也不会辞掉县上的工作,回来跟兄弟分房子。要是不回农村,在县里好歹也有个前程了,儿子也不会在地里掏食。恒山好像也抱怨了几句,后来就只听到老太太哭,说家里日子不好过,全怪她,她死了他们就好过了。李秉义又凶她几句,也就任由她哭去了。一个穿红衬衫的小少妇说,吃饭的时候,我还听到恒山喊她吃饭,就听她说,从今天起不敢吃你们的饭了,怕把你们吃穷。李秉义又骂,骂得很难听,后来老太太就勒脖子死了。宽脸女人说,这个你不要瞎说,会有声音吧?他们一家又不是死人。红衬衫少妇说,谁说没有声音,我听到啊啊啊的叫唤了,以为是快死的猪哼哼呢。一个小男孩尖尖喊了一声,我也听见了!也以为是猪叫呢。嘴角咧出一个笑。小孩子家懂什么!宽脸女人在小男孩后脑勺拍了一下,沉默着,似乎也回想起了那声音。
太吓人了!宽脸女人一只手抚着胸口喃喃自语,难不成他们一家子就那么听着?李秉义平时看着仁义,怎么这么狠心?
他家做什么不说明呢?许久,穿水红衬衫的小少妇说。
这不明摆着?宽脸女人白她一眼,她娘家人晓得了,发丧时不来闹?就算她娘家人不来闹,在村里也不是什么有脸的事儿,还要像她孙子考上大学那样,满村子宣扬呀?
水红衬衫的小少妇赤红脸,哑口无言了。
院子东边的角落里,四五个六七十岁的老头或蹲或站。李秉义蹲在中间。想开点,想开点,老头们劝着,有个穿中山装的老人递一支过滤嘴给他,他接了夹在耳后,仍旧抽自己卷的草烟。他也不让旁人,自己掏出烟包,格外仔细地卷着烟卷儿,自己点上,吧吧地发出声音。白烟从鼻孔蓬开,蒙住了一张皱纹如刀刻的脸。他眯着眼睛躲避夕光,夕光照着他一头乱发,如腾腾的火焰。无论旁人说什么,李秉义老人始终无话,起初大家以为他受不住打击,他和老太太向来是村里模范的夫妻。好长时间过去,他只是一支接一支抽烟,每一支烟都卷得一丝不苟。大家的担心放下了,又有些不高兴,心想,你心肠就这么硬?好歹一张床上滚了一辈子了!几位老人先后留下不同的借口,走了。李秉义独自蹲在墙角,脚前散着十多二十个烟蒂。夕阳只照得到他的一丝头发尖儿,如洪水上浮动的一蓬老草。
终究没人质问主人家老太太是不是上吊自杀的。许多事是不能点破的。悲哀如同黄昏,很快在大多数人身上滑过,接下去是现实的事务,无论如何,丧事需要操办。只有那几位哭泣的老人还沉浸在悲哀里,在她们的哭诉中,悲哀和一辈子的岁月一般漫长。
有人买菜,有人到村里借桌椅板凳,有人去向老人的娘家报丧。忙乱中竟有一些热闹的气氛。回家拿菜刀的妇女在李家门口见到李秉德媳妇,脸上不禁露出几分诧异之色。听说不是病死的?李秉德媳妇拉住宽脸女人,询问道。妇女们那时候都没注意观察她的脸色。宽脸女人说,大妈你怎么不进去看看呢?话说出口才想到,李秉义和李秉德两家不说话几十年了。就低了声说,大妈,这话只能和你私下说说,是这个死的。说着扬起下巴,用右手虎口掐住脖颈。似乎这样还不够,她又加了一句,说,吊死的!她以为李秉德媳妇会幸灾乐祸,不想她脸色黯下去,低低说,她还比我小一个月呢,怎么就走了这条路。
妇女们走后,李秉德媳妇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她身子向前探着,细细倾听院子里的声音。门口人来人往,看到李秉德媳妇都露出了诧异的神色。不止一个人向她打招呼。大妈,你进去看看?她支吾着,脸上似笑非笑,说不进去了,有什么好看的。
她什么也没做,回去了。她家和李秉义家很近,中间只隔着一户人家,走一段下坡路,拐个弯就是。两家虽然多年不交往,在村里脸碰上脸也不说一句话,对彼此反倒知根知底。不用打听,村里人自会告诉他们对方家里出了什么事。不知道是希望他们两家和好呢,还是希望他们“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正因为彼此了解,两家人做事都会尽量避开。就说一件事吧,李秉德媳妇从来不和死去的老人同时回娘家。
两位老人结婚前就是一个村的,还是远房堂姐妹,从小玩到大。死去的老人先嫁过来,一年后把小叔子介绍给自己的堂姐,也就是现在的李秉德媳妇。她对堂妹是心存感激的,若不是堂妹撮合,她不可能离开东山嫁到坝区。她们村离得很远,要翻过几座大山才到,起初每次回娘家两姐妹都要同去同回,后来为了分家产,两家大吵一架,两姐妹再不来往,回家都是各走各的。她们回家次数越来越少,因为不知如何回答娘家人对另一个人的询问,也因为那么一段路,一个人走心里总有些怕。时间久了,好不容易回娘家一趟,李秉德媳妇有时就后悔,当初要是不吵那一架多好。两个人走在路上说笑的情形,似乎一时间又回到眼前,不免心里一阵惆怅。又想,不晓得堂妹有没有后悔过。
约莫四年前,健壮如牛的李秉德在操劳几十年后,瘫了,吃喝拉撒离不开人。老人和子女们并无怨言,悉心伺候着。李秉德身子动不了,脾气却比往常大了,发怒的次数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成天绷着一张缺少阳光照拂的脸,动不动就以绝食抗争,可即便他一顿饭不吃,声音照样洪亮如钟,把家里的人一个个骂遍,村路上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嬉笑着说,哟,又开骂了!渐渐的,子女们暗地里对他很嫌恶了。老人明白这些,很果断地和两个儿子分了家,自己一个人精心照料李秉德。李秉德并不领情,对她照样吆来喝去,有一次竟为了菜里没肉,动手甩了她一巴掌。几十年来,他从没打过她。李秉义也从没打过堂妹。两姐妹在这方面似乎都暗暗较着劲儿。可现在李秉德动手打了她,她不知道堂妹知道了会怎么笑话她。她忍住泪,不想让子女们知道,在丈夫的骂声中拾好碗筷,走到大门口,默默坐在大青石上,她不由得想起堂妹来,如果和堂妹家没闹翻,好歹会有个人安慰一下。
几十年了,不但她们这一代不说话,两家的子女也不说话,可那算得上多大的仇恨呢?老人怎么也无法在心里找回当初那么强烈的仇恨了。那不过是鸡毛蒜皮的事儿罢了。可这么多年了,彼此间的罅隙那么大,要跨过去不容易。
她这么想着,很凑巧地,她看到堂妹从村路那边走过来了。堂妹眼睛不好,还没看见她。待堂妹看清她时,她看到堂妹站住了。她知道,以往碰到这种情况,她总是退回自家院子,这样堂妹就可以顺利通过家门前的一段路。在这一点上,不单是她,他们两家人都很默契。可这次她没有回避,她仍旧坐在大青石上,直直望着堂妹。堂妹提着篮子,要去做什么事吧。堂妹踌躇着,好一会儿,她看到堂妹慢吞吞地朝她走来了。她听到自己的心咚咚跳着,心想堂妹也希望和自己和好了吧,和堂妹说些什么呢。终于,两个老人碰面了,可在交汇的一刹那,谁都没说话。堂妹朝她看了一眼,彼此的目光轻轻地碰了一下,闪开了。她竟然有些难为情,她看到堂妹的脸也红了。一时间恍然回到在家里做姑娘的光景。堂妹走后,她一个人呆呆坐着,心里有些暖。
她盘算着,下次再和堂妹碰上,总能搭上话了。怎会想到堂妹一下子就故去了。
村里的习俗,人死后第三天才发丧。老人焦躁着,暗暗备好香钱纸火,装了满满一竹篮,一次次想要拎了出门,到堂妹灵前尽一份心,一次次想着,到时该向堂妹哭诉什么。是哭诉这么多年来各自的艰辛,还是哭诉在家里做姑娘时的情谊?老人想不好。延挨了两天,眼看第三天就要出丧了,她仍旧没出门,也没再到堂妹家门口去。她只不时站在自家院子里,努力想要听清堂妹家那边的每一声哀哭。每一句哀哭都软软地打在她的心坎,让她眼中含泪。她养的黄狗跑过来,偎在脚面,呜咽声唤,得不到回应,抬起沾满黄泥的前脚,在她裤腿上扒拉着。老人和堂妹一样,是极爱干净的,若在平日,一定会把黄狗训斥一顿,这时候她没动,任凭裤腿上留下了一道一道黄色污迹。
老人的反常被躺在屋里的李秉德透过窗户看得一清二楚。你就痴心妄想吧!李秉德骂道,你要是去了,看人家不把你撵出来!他说这话时的幸灾乐祸让老人很难受。她想,就不该把村里的传言跟他说。这么多年来,李秉德只看得到窗外的院子里的一棵石榴树,石榴树上的一小片天。跟两个儿子分家后,家人为着他房里那股浓烈的混合着饭菜味、屎尿味、汗臭味的古怪气味,很少再进他的门,村里更少有人来。可家里村里的事他却无所不知。他天天向老人询问家长里短,在听老人诉说时,眼睛亮亮的仿佛饥饿的人看见大盘食物,耳朵上蓝色的血管跳动着。他耳朵特别灵,只要听见异常响动,必会向老人问清根源。这近在咫尺的哭声、阴阳先生的铙钹声,又怎么瞒得过他的耳朵呢。
吃下午饭,老人端来的是一盘青菜和两块卤豆腐。李秉德虎下脸,阴沉沉的目光追寻着老人的眼睛,老人不躲闪,也不迎接,平静着脸。肉呢?李秉德忍了忍,还是问道。家里的猪死光了,还吃什么肉?老人缓缓道,村里没几家还能吃上肉了。李秉德竭力忍着。他和媳妇都知道,他很快就会爆发,就会把碗筷摔在地上。他又问,去年的卤肉呢?那么两大缸!老人迎上他的目光,踢一脚身边的黄狗,黄狗叫唤一声,跑到门外去了。喂狗了!老人说,你就吃我吧,总有一天,我也得走她那条路。老人说这几句话时声音很低,目光锃亮。他们都在等待一场爆发。李秉德眼袋很大,随时哭过似的。眼袋颤动着,这是他发怒前的征兆。一会儿,那颤动平和下去了。他眼里似有泪水,端起饭碗,无声地吃饭。老人没想到这样,倒愣了一时,等他吃净两碗米饭,端了空碗空碟,刚一出门,鼻子莫名地有些酸。第二天的菜也没肉。李秉德也很顺从地吃了,脸上看不出高兴还是不高兴。
到发丧那天,老人也没去看看堂妹。去也看不到了,已经安棺了。中午时候,听到那边闹哄哄的,她站在门口,总算等到一个过路的女人。那边怎么了?老人也不晓得想知道什么,就这么笼统地问。女人撇了撇嘴,说,别提了,还不是老太太那没用的娘家人来了。
老太太那么个死法,虽然李秉义家没说明,但自己心知肚明,也怕老太太的娘家人来闹,恒山的好几个堂兄弟一早就在灵前等着,瞧那架势,是准备好和娘家人对着干。快吃早饭时,娘家人总算来了,一长一少,中年男人穿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小伙子则一身藏青色运动服,鞋倒是一模一样,都是黄胶鞋,都被厚厚的黄泥包裹着。不晓得村里哪个走漏的消息,一进门小伙子就嚷嚷,说他姑太怎么勒脖子死了?一句话出来犹如炮弹,在平地砸开一个大坑。不少人想,这下有戏看了。
恒山的几个堂兄弟一下子脸就绿了。他们看看彼此,下意识地挡在灵前。恒山的一个堂哥虎下脸,说,你们要做什么?不看小伙子,看着他身后的中年男人。中年男人不说话,自顾自走上石阶,探出一只脚在石阶边刮鞋底。小伙子感到被忽视了,大声说,我们要瞧瞧!径直往灵堂里走。恒山的堂哥们慌忙抱住他时,他一只脚已经踩进灵堂了。他挣扎着,还是被三个男人合力拽了出来。你们想毁尸灭迹?他大声嚷道。恒山一直跪在灵前,这时吮不住了,站起来,说小东子,你晓得什么叫毁尸灭迹?亏你还口口声声叫她姑太,安棺了你还不叫她安生!小东子满脸通红,嚷道,放开我!大家放开他,他整理着衣服,目光瞟向中年男人。中年男人并不看他,仍旧低着头在石阶边刮鞋底的泥。恒山冲中年男人喊,大表哥,你就不说句话?d00ef822e47406de75ee94033cbe0588b8d1b7f9ea2e28c78d1a51aaad44c5c4中年男人不答话,刮干净一只鞋底,抬起看看,接着刮另一只,刮了一半,觑一眼恒山,扭头望着院子里黑压压的人,领导似地说,有什么好说的?人眼不见天瞧着。恒山媳妇走到他面前,说是是,大表哥说得对,人眼不见天瞧着,我和恒山什么事不顺着妈?说着眼泪就下来了。又说,那边酒席摆好了,过去吧,看一眼他的鞋,说走了这么多路呀。
中年男人又耐心地刮干净剩下的一半黄泥,抬起头,目光在院子里一张张仰着的脸上扫过,鼻子里似乎哼了一声,随女人吃饭去了。小东子尴尬地站着,脸一阵红,一阵白。恒山说,你也过去吃吧。小东子瞪他一眼,说我姑公呢?我找我姑公。恒山犹豫了一下,说你又要做什么?你姑公在那呢,手朝院子东边角落一指。人群默默让开一条道,通道尽头,李秉义坐在小凳子上抽烟。小东子啪啪啪穿过人群,站在李秉义面前,忽然哽咽了,说,姑公,你说实话,我姑太是不是勒脖子死的?
……李秉义怎么说?老人瞅着女人的眼睛。
还能怎么说?
李秉义似乎肩膀抖了一下,仰起茶色的脸,呆滞着一双死鱼眼。似乎没听懂小东子说什么。小东子望着这张脸,又问了一遍,我姑太是勒脖子死的?不等他再说什么,恒山和几个堂兄弟从后面抱住他,拽走了。你姑公难过得不成人样了,你还刺激他?恒山大声骂着。
……那李秉义什么也没说?老人问。
他能说什么?他总不好当着全村人面,说老太太是勒脖子死的。女人摇摇头,说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平常看老太太和他,哪个不是乐呵呵的?听说啊,女人瞥一眼左右,嘴凑到老人耳朵边,压低声音说,老太太死前,李秉义打过她。老人说,不会吧?他们从来很好的。哪个晓得呢?女人撇撇嘴说。
当天晚上,老人给李秉德端进饭菜,菜里有三块核桃大小的卤肉。
肉不是都让狗吃了?李秉德气鼓鼓说。
又有了。老人淡然道。
李秉义媳妇下葬后两天,又落雨了,比前一阵子还要凶恶。河水刚刚落下一些,又很快漫溢,在桥洞口打着漩涡,漩涡里有没来得及掩埋的死猪浮上浮下。路边的厕所也灌满了水,秽物漂出,一堆堆挡在村路上。人们仰脸望天,一声声慨叹,老天爷!老天爷!有些人家的水稻熟得早,前两天晴开时,心想老天总算下够雨了,让太阳热热地晒上几天,等稻粒挂着的水收干了再割。不曾想雨又下来了。
李秉德老两口田里的水稻也黄熟了,被风一吹,一大半伏在水中。不尽早收回,一年的口粮真要“泡汤”了。两个儿子在外打工,二儿媳说身体不好,只大儿媳和老人一起冒雨去收割。村外一片白茫茫,大树被风扭着,不时在雨水中浮现,又湮没不见,仿佛钓鱼用的漂杆。在这样的大雨里,竟有不少人,都是出来抢收水稻的。田比路低矮,只是一片浑黄的大水。有几只小船摇进去,船上的人俯下身子,光割断稻穗,收到船里。老人和儿媳并无船只,试着趟水进去,呼隆一声,踩到沟里,老人差点没顶。被儿媳一把拽住,婆媳回到路上,瑟缩着再不敢进去,想只好等有船的人家收完后借船了。
还有老远一截,婆媳俩就听到李秉德的叫骂。死光了吗?全死光了?骂两声,又听得啪啪一阵响,是竹棍敲打床铺的声音。没有人回应,骂声又起。婆媳俩慌忙进去,院子里一个人没有,不晓得二儿媳到什么地方去了。大儿媳回自己屋换衣服。老人放下镰刀,从打开的窗户看到丈夫靠在躺椅上,挥舞着竹棍,做金刚怒目状,虚肿的眼袋可怕地颤抖着。他看到老人回来,忽然住了口,定定盯着她。老人推开门,一脚跨进,咣当响了一声,一大蓬灰白色的尿味腾起。李秉德瞅着她大笑不止。老^低头一看,踩了尿盆了。不知道他怎么能够把尿盆挪到这个位置。尿液溅湿了大半条裤子。老人木然立在门边,一手扶着门框。水和尿混合着,从裤脚嗒嗒滴落,湿了一大片泥地。
还以为你去找死了,不回来了。李秉德忍住笑,满脸孩子般的神态。
我是不想回来了。老人淡然道。
水!瓶里没水了。李秉德朝打翻的水瓶努努嘴说,好似小孩跟母亲索要东西。
自己打翻了自己去灶房倒。老人转身出去了。
李秉德手中的竹棍已脱手而出,幸亏老人转身快。老人在屋外靠板壁坐着,听凭丈夫在屋内大骂。没了竹棍,丈夫的气势减了许多。骂到后来,嗓子哑了,声音低了,终于不骂了。李秉德靠着躺椅,两手紧紧攥着躺椅的扶手,努力直起上身,努着嘴,死死盯着窗外的石榴树。隔一层板壁,老人也望着石榴树。李秉德的骂声像一条崎岖的山路,她要挑着重担翻过去,终于翻完,累得浑身骨架松散。在极度的疲乏中,她看到石榴树出现在山路尽头,从一片白雾中钻出一个碧绿的尖儿,在风中摇荡着,若一面小小的旗帜。她心里莫名地觉到了安慰。石榴树是她生下大儿子那年栽的,那是多少年前呵!如今树干虬结,似老人青筋暴露的手臂。果实已摘尽,叶子还绿着,往地上一看,已是落了许多黄叶。
那晚暴雨如注,雷声不时照亮村人发霉的梦境。他们在梦境中辗转反侧,鱼类一样吐出一连串发霉的叹息。猪瘟接连着水稻泡汤,他们不知道如何挨过一个个发霉的日子了。有人在梦里哭泣,哭声鼻涕虫一样顺着墙根爬出,浮萍一样漂在打着旋儿的水面。老人摸黑爬上二楼,手掌扶了墙,抹到大片大片凉沁沁的惨绿哭声。她把它们随手摔在脚下,踩着继续往上爬,哭声们便发出一地惨叫。她只装作听不见。
雷声闪过,她看到堂妹靠着柱子朝自己笑。堂妹好年轻,还是做姑娘时的样子。她笑了,说,你怎么不老啊,成心气我嘛。堂妹笑笑,说我不会老,你就不会老。不记得了?我们做什么总是一起,连嫁人都要嫁到同一个地方。老人淡淡一笑,说那你怎么先走了?还为分家产的事儿生气?堂妹呸一声,说你也太把我想得小肚鸡肠了,亏还说是姐妹。我这不是回来接你了?老人旺了一下,笑窝在脸上,说来接我了?算你有良心,是堂姐错怪你了。堂妹微笑着,朝老人伸出手,老人轻巧地迈着步子朝堂妹走去,远远地伸出手。雷声滚滚,四周白亮,硕大的雨点在光亮中如同一只只惊乱的眼睛。无数双眼睛看到老人向一道白光伸出手。手,连同人,一齐消逝在白光中。
第二场雨下到第六天,又一个老人死了。也可能是第七天,没人弄得清楚。
第二天一早,二儿媳妇上楼抱柴火,发现吊死在梁上的老人,老人平静地注视着她,她一屁股就坐地上了。尖叫声引来无数村人,陆陆续续站了一院子。隐瞒是不可能了,再说院子里的两妯娌都没胆量卸下老人,还得靠村里的男人。李秉义媳妇死时哭灵的灰白头发来了,一看见白布盖着的老人,哭声就咕嘟咕嘟从脖子里滚出。她伸出干瘪的手,抚摸着老人脖子上深深的红色印痕,想要将其抹平,从而唤回老人远去的魂灵。抚摸了好一阵,老人仍旧冷漠地僵硬着身子,她气急败坏,拍打着床板嚷道,你做的是什么事!什么事呀!难不成是李秉义媳妇来拉你?你们这两妯娌啊!说着大声哀哭。
哭声像锐利的小刀子,切割着听者的神经。老人的死丝毫没有遮掩,直白地袒露出惨烈的过程和结果,一时令人们难以承受。
老人停在堂屋,李秉德躺在隔壁,从得知她的死讯那一刻起,他就骂声不绝。算看清楚你了!他骂道,你就是不想服侍我!甩甩手就走了,告诉你,不要你照顾!我死了也不要你照顾,我堂堂一个男人,还受你威胁?!他用竹棍啪啪拍打着床,骂声高亢雄壮,老子是哪个?老子八岁没了爹妈,十岁学做生意,十五岁参加队伍,开过枪杀过土匪,老子怕过哪个?你威胁我!死了好,省得我耳根清净!老村长站在窗边劝他,说你少说两句吧,家里来了这么多人。你们过那么多年,怎么着也不容易,单是你瘫痪这四年,她也算尽心了,她人都死了,你就少说两句吧。他非但不听,反倒连老村长也一起骂了,打雷似的,似乎想要盖过堂屋里的哭声。便不再有人劝,任由他骂去。村人低低骂一句,老疯子XE/dt3KnXdB55scvYkNz5ZbixD66LN9stxEJPsF2x6Y=!
雨越下越大。来合棺材的木匠只好在院子里临时搭起的棚子里操作。家里现成的棺材是有,是李秉德瘫痪那年大儿子置下的,说好给李秉德的,都以为他要先她而去,不想反倒是她性子急。帮Yon4+HmIp2pCVZmdLB/Q8eppyVyvrfUNeaonTIlNJk8=忙操办的人打过注意,天气不好,诸事忙乱,棺材不如就用李秉德的,以后再给他置办。大儿媳妇不同意,说你们没看到他那个样子?对老太太恨之入骨,要是晓得拿他的棺材给了老太太,不喊破天才怪。大伙想想也是,只好匆忙找来木匠。两位木匠在院中操作,老人养的黄狗蹲在他们面前,目光凄凄地瞅着他们。
木匠到我家做什么?李秉德冲木匠哑声喊。——骂得久了,又没人给他送水,嗓子明显哑了。他说,水!没人理他,以为他说院子里的积水。喊了两遍,不喊了,眼睛瞪得远远地,努着嘴瞅着院子里哗哗流动的积水。一两位木匠停下手,纳闷地看看彼此。老村长说,还能做什么?好歹合一口老寿木,你总不至于要她光着下地吧?她再怎样,也把一辈子撂给你了。李秉德不言语了,低头沉思着,过了一阵,瞅着院中那些沾满黄泥的准备做棺材的木板,哑声说,都脏了,不好的。她爱干净,拿我的给她用吧。
你的东西她哪能用!老村长也有些执拗。
我说用我的就用我的!叫他们走!走!李秉德大声嚷嚷,朝木匠挥着竹棍。她怎么就走了这条路啊,他哑声说,要不是雷声那么响,我怎会听不见。
老村长看到,李秉德肥大的眼袋颤抖着,晃晃地如包着两袋热油。
雨第二次停歇,是十多天后了。村人不再如上次那般欣喜,怀疑地瞅瞅天,天蓝得发亮,分明浮动着暗影,是他们稻草一样弯曲着的发霉的影子。
水稻腐败后散发出的暗灰色霉味钻进村子,在每一条道路上游走,如龙如蛇,裹挟着村人,令他们脚步踉跄,跌跌撞撞。李秉义拄着一根松木棍子出现了。令村人震惊的是,他一下子就把腰弯下了,曲得像一只大虾。他大半身依靠着松木棍,让人不由得为棍子担心。他慢腾腾走,听到脚步声就停下,目光先落在对方脚面,一点点往上,爬到对方的胸口,很艰难了,必须使大力气,才能攀上对方的脸。村人也有礼貌地微微低下脸,对着他发霉的脸,看到两粒鱼类僵冷的眼珠子,鼻孔嘶嘶钻出发霉的荇草。村人从惊愕中回过神,礼节性地问道,大爹,哪儿去?老人灰暗的目光中跃出一丝光亮,说,到处走走。李秉义就这么在村里走了好几天。有人怀疑,他是不是神经不正常,又不见他有什么反常举止。虽说如此,大家心里有了避忌,觉得他脸带死相,怕是不久于人世。有人悄声说,说不准呀,他也会走两个老太太的老路!小孩子们远远看到他,总会慌忙躲闪开。
这一日黄昏,夕阳杏黄色的糖稀一般糊在灼热的屋顶,猪不叫,鸡也不叫,村子静着,若镜子里照出的幻境。李秉义拄着松木棍,在一片院子外停住了,他站在土门边,听到一个洪亮的声音:死光了?全家死光了?给我泡茶!然后是竹棍敲打床铺的啪啪声。有女人和孩子的声音,只听女人细细地说,爹,我们就来,你不要乱打我们。那声音更响亮了:不打你们打准?狗让良心拖了!拿冷水给我泡茶,我腿瘫了,舌头没瘫!没回应了。没人动。那声音又响起,还是洪亮着,却抱起了屈:要是她还在啊,哪会有这样的事!她那样事情不办得妥妥帖帖!还是那女人细细的声音,爹,妈那样好,还不是给你气死了?那声音停了一阵子,死寂,忽地,哐当当响了几声,一根灰色的竹棍三跳两跳蹦到院中央。
李秉义拄着松木棍,站在房门前,和房门前卧着的黄狗对视着,黄狗瞅了他几眼,默默站起,让到一边。李秉义推开门,恰巧和李秉德怒容未消,涂了泪水的脸相对。
从这一天起,李秉义从家里带饭,每天三顿送到李秉德床前。起初儿子恒山有过异议,被李秉义瞪了几眼,又被媳妇拉了拉袖子,不再说什么了。恒山媳妇还找来一个带饭用的盒子,吃饭前就装好饭菜,放在桌上,和李秉义说,爹就带着个给大爹吧,方便。李秉义也不说一句感激的话,理所当然接过饭盒,就走了。李秉德的两个儿媳只是诧异,记忆中从未记得李秉义进过家门,如今不单进家门,还每天三顿带吃的给老头子,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儿。但她们很快镇定下来,这事儿对她们绝无坏处。她们看见李秉义走进家门,就站起来打招呼,说,诶,大爹你来了?李秉义仰起脸,转向她们的方向,好一会儿,才淡淡点一下头,说,诶。回去时,她们又在他身后喊,大爹,你慢走呀。他头也不回,走了。
反应较大的是李秉德。一开始,他眼睛瞪得圆圆的,恼怒而又含着戒惧的目光追索着李秉义的一举一动。看到几十年没说过一句话的哥哥弓着腰,动作迟缓地泡茶,倒水,热热的茶水搁在眼前,袅袅地舞着一线白雾,他有了短暂的恍惚,恍隐妻子还在着。他不知道这杯茶是喝,还是不喝。
李秉义不看他,自己搬了一把椅子坐下。李秉德透过袅袅白雾,眼睛一瞬不瞬地盯着他。几十年没认真看过这张脸了,虽则变化剧烈,却发现这张脸仍是稔熟的,只是猜不透这张脸后面的意图。是来嘲笑自己?来看自己的热闹?看老太太死了自己怎么活下去?他分明感到蓬勃的怒气从四肢百骸聚拢,未经过思索,已经一把扫了桌子。茶杯撞飞到对面墙上,茶水酒了李秉义的脸。他努着嘴,眼睛亮亮的,挑衅地瞅着李秉义。你就装吧!瞧你怎么装!他这样子像极小时候和哥哥打闹,他就要气气他,看他怎么样。那时候哥哥总是先绷下脸,欲要发作,又忽地松弛了神经,反倒安慰他,把他当个不懂事的小孩子。他既感到哥哥小看了自己,又感到胸口氤氲着一派暖意。几十年后,他又在李秉义身上看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情形。李秉义先是瞪他一眼,碰到他挑衅的目光,即刻温软了,低下头想了想,艰难地扶着膝盖站起,走到墙角,蹲下拾起并未摔坏的杯子,冲洗干净,又倒上一杯,搁在他面前。
这杯茶,他真不知道是喝还是不喝了。
每天李秉义按时到来,拎一小盒子饭菜,鲜活生动的饭菜香味,在房间里浓浊的怪味中开辟出一片天地。自从媳妇死后,李秉德有一段时间没吃到这么合口的饭菜了。每次儿媳来送饭,总是匆匆搁下就走开,怕被他吃掉似的,饭菜也显得非常潦草,敷衍的意味毫不掩藏。李秉义把饭菜摆在李秉德面前,不说话,只看着他。李秉德迎住他的目光,嘴角有一丝挑衅的笑意。李秉义的目光一软,低下了头。一瞬间,他又在这双眼睛里看到了几十年前的哥哥。那时候粮食短缺,但凡有一点儿吃的,哥哥总是先让他吃。他的目光也软了,低下头,拿起筷子大吃起来。
一天中午,天气晴好,李秉德吃完后,李秉义刚收拾好,他的两个儿子媳妇就端进一大盆水,和李秉义对了一眼,喊了一声大爹,李秉义摆摆手,她们掩上门出去了。李秉德明白过来,脸一下子红了。老太太死后,他还没洗过澡,也没擦过身子,身上的味道一定很难闻。可他怎么能让李秉义给自己洗呢?他有一种本能的抵触。他努着嘴,瞪着李秉义。李秉义并不理会他,上去就脱他的衣服,他抗拒着,嘴巴却始终紧闭着。两兄弟像两个沉默的影子,扭打着,挣扎着。李秉德终究在床上躺得久了,不单脚动不了,手也没多大力气,不多时就被李秉义剥光了衣服,露出一副骨瘦如柴的躯体。他又急又气,嘴里呜噜着,两只眼睛如同烧红的石子儿。被李秉义抱起,接触到水的一刹那,他浑身抖了一下,静了。他还隐约记得,很小的时候,哥哥也给他洗过澡。李秉义用毛巾给他搓着身子,手伸到他的胯下那衰弱的地方时,他别过脑袋去,无声地哭了。他想忍住哭声,哭声越是汹涌,他使了大劲儿,导致浑身颤抖,心脏跳得像一只挨打的水老鼠。
我自己能洗,李秉德小声说。这么久以来他们总算说话了。
李秉义瞅了他一眼,默默地把毛巾递给他。艰难地站起,坐到对面椅子上。
我就想不通,他盯着李秉义说,你这么照顾我图什么?
你嫂子是上吊死的。李秉义说。她俩都是上吊死的。
死亡若一条隐秘的纽带,将兄弟俩牢牢捆在一起。他们从未如此靠近过。
久久沉默着。李秉德缓缓擦洗着身子,毛巾上的水滴落,溅起一片水声。他低头望着一圈圈扩散的肮脏的水纹,低声说,有一次,我还打过她。
那天晚上,李秉义没走。他坐在靠窗的椅子,李秉德躺在床上。他们兄弟俩几十年没这么聚在一起了。他们望着院子里月光下的那一株石榴树。月色凄迷,石榴叶已掉了大半,露出瘦瘦的疏朗的枝桠,黄狗静静睡在石榴树下。他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起一些过去的事。李秉义说的事儿,李秉德常常想不起,疑问道,是吗?李秉德说的事儿,有时李秉义也想不起,也会问一句,是吗?一旦谁说的事儿另一个也想起了,他们便会无声地笑上一阵子。
年前的一天,李秉德看到李秉义神色不对,问了几次,李秉义才说,兴菜回来了。兴菜是李秉义的孙子,三年前考到北京念书,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李秉义一家曾为此在村里风光过好一阵。李秉德不解,说哥呀你不是天天想着见他?李秉义叹了一口气,说怎么不想?只是,你晓得,他奶奶去了,他和她一直很亲,万一他晓得了……李秉义把脸对着兄弟,你说要不要和他说?李秉德瞪圆了眼,说什么?他知道了,还有心思好好读书?李秉义犯难道,我还不是这么想?只是我不说,村里怕也会有人和他说,别人和他说不如自家人说。李秉德想了想,说你放心,不会有人说的。李秉义说,不会有人说?李秉德说,不会。
过完年后的一天,李秉义一进门,李秉德就问,兴菜走了?李秉义说,走了。李秉德又低声问,他不知道吧?李秉义喝了一杯茶,说应该不知道。我没和他说,他爹妈也没和他说。村子里一不晓得有没人和他说。他晓得他奶奶过世后,感觉淡淡的,昨晚临时要走了,才说上后山瞧瞧坟。跪在坟堆前,手抓着红土,就哭了。瞧着他从小到大,还没那么哭过。李秉义长叹一口气,那时我就觉得,不告诉他,真是罪过。李秉德说,那罪过就由我们担着。李秉义看到弟弟的目光闪亮着,又回到了年轻时勇毅的样子。
转眼到了第二年雨季。李秉德由于长期卧床,肾脏病痛加重,身子日见消瘦。李秉义不但一日三餐送到,其余时间也很少离开,和黄狗一起陪着他。他已不能说话,目光倒还亮亮的,时而看看哥哥,时而看看黄狗,嘴角露出满意的笑。
眼看弟弟不行了,李秉义的心一点一点沉了下去,坠得腰骨也愈发弯塌了。他想起去年这时候做出的那个决定。他没有什么理由不那么做。没日没夜,他总听到她的声音,那声音就响在他的耳朵眼里。她说,看你能吧,一辈子不低头,现在怎么样?再强的弓也会折断,再快的箭也会落地。我们做了一世的冤家,还要接着做下去的。想不到好了一世,到老来你那么对我,我是忍不住了,先走一步,不过你不要得意,我可没打算离开你,我走了你随后也该到了。还有什么念头值得你那么赖着呢?又或者,在哪个拐角的地方,他看见眼前有一双熟悉的脚,努力抬起头,看到她正对自己笑呢。那笑里是嘲讽,意思是看你这副样子,还舍不下吗?他想想也是,是该舍下了,还有什么舍不下的?他只想再转一转住了七十来年的村子,就什么念想也没有了。不想那天在村里转悠,他听到了多年前那熟悉的声音。他忽然又有了活下去的念想。他对不停对他絮叨的老太太说,对不住了老婆子,你还得在那边等一等,我这边还有重要的事儿。他以为她会怪他,怨他,可她心平气和,说那你就去做吧,好歹你逃不掉的。他说,不逃,等事情做完了就来。自那以后,也怪,他耳朵里再也没她的声音,眼前再也没浮现过她的脸,时间久了,禁不住还有些想念。现在是时候了,等弟弟故去,找弟媳去了,他也差不多了。他们四个人竟然仇恨了一辈子,连带子女都跟着相互仇恨。他们该去那边和解了。他有些兴奋,想把这话和弟弟说说,也就说了。
他俯在弟弟耳边。说弟啊,一年多了,我们哥俩从没说过那件事,你还记得吧?不记得最好,记得你就原谅了哥,哥不该跟你争家产。李秉德眼里泛着泪花,摇了摇头。李秉义又说,不管你记不记得,哥有句话和你说,等你故去了,哥也就无牵无挂了,也不该再赖在这世上。到那边,我们四个人还是一家。李秉德眼中的泪花越积越多,又使劲儿摇了摇头。十来天没开口了,这时忽然开口说话了。
哥呀,李秉德眨了眨眼,艰难地说,等我走了,有一桩事还得托付你。眼睛斜向下,瞅着床边卧着的黄狗,说,黄狗是我瘫掉那年,她要来的,一天一天养到这么大。活着的时候,黄狗天天黏着她,她也喜欢它,我经常在夜里听到她和黄狗说话。等我去了,怕黄狗没人喂,就交给你了,说着滚下泪来。李秉义转过脸去,瞅着黄狗,黄狗两眼如晶亮的墨玉。
那一年雨季,李秉德死后,村人经常看到李秉义和黄狗一同出现。李秉义腰塌得更厉害了,若一张移动的凳子,和黄狗差不多一般高。黄狗时而在前,时而在后,不知道谁在引领谁,谁在跟随谁。黄昏朦胧的光晕里,目力不逮的人远远看去,一不小心,就误以为是两条狗走在荒凉的村路上。他们偶尔会停下手中的活儿,揣测一下,它们将走向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