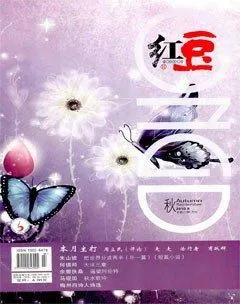有一些痛刻骨铭心(评论)
2010-12-31周立民
红豆 2010年9期
周立民,1973年出生于辽宁省庄河县。1996年大学毕业后曾任职机关、报社:2002年至2007年为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博士;2007年进入上海市作家协会工作,现为巴金故居(筹)常务副馆长、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评论工作,有多篇论文发表,并著有《另一个巴金》、《冯骥才周立民对谈录》、《巴金手册》、《精神探索与文学叙述》、《巴金画传》、《<随想录>论稿》等。编有“老上海期刊经典系列”《漫画生活》、《文学季刊》、《文季月刊》等文献资料,以及《月月小说》、《大家文选》等当代文学选本多种。
1
《说文》中把“痛”解释为“病也”,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痛”都是生理上的病,心里的痛更刻骨铭心,而且时间时常发酵着这些痛,让人心灵上的伤口难以愈合。
《白雨》的开篇是一个戏剧性的场面,这个场面我还看不出作者的高明之处,直到李秉德媳妇的出现,小说的走向因此而改变,也把一场戏引向了对人生和命运的关照。李秉德媳妇的痛有着很复杂的来源,堂妹的死使她彻底失去了彼此和解的机会是一个表面的原因。往昔的恩怨也罢,是非也罢,都抵不过时间,时间剥夺了她们的容颜、精力之后留给她们的只有孤独,生(出生)、老(衰老)、病(生病)、死(死亡)。佛家以为人生四苦,这是谁也逃避不了的,小说中的老人此时至少占了三苦,人在强大的时间下是那么渺小和无力,而此时他们更需要相互依存和关怀。人是一个群体动物,需要类的聚合,需要彼此诉说,对于李秉德媳妇而言,再没有比堂妹更适合倾听她的内心了:“她不由得想起堂妹来,如果和堂妹家没闹翻,好歹会有个人安慰一下。”甫跃辉写“痛”不会是撕心裂肺的,而总是小心翼翼、不动声色的,甚至把很多复杂的因素纠结进来。比如,她那么渴望诉说,但却有个巨大的心理障碍:丈夫带给她的痛——丈夫打过她,这可能让她在堂妹面前失去尊严;然而,当她听到堂妹也遭受过打的时候心里又有了另外的变化……
《白雨》的“痛”中有着太多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人是太奇怪的动物,需要相互温存,却彼此屡屡伤害。因为丈夫的态度,李秉德媳妇追随堂妹而去,然而丈夫不过拿她作为心理发泄的渠道,并非心里没有她,做棺材时的发脾气已将其内心暴露无遗。但这样的心为什么此时才有暴露,语言为什么常常不是最真实的内心的表达,而总是转向另外的方向使春风变成了利剑?如果李秉德早一点表达对妻子哪怕是一点的关爱,会是这个结局吗?兄弟间也是,一个瘫在床上,无力赌气了;两个人的媳妇都死了,才感到绝望的孤独,这才有了和解的可能。用小说里的话就是:“死亡若一条隐秘的纽带,将兄弟俩牢牢捆在一起。他们从未如此靠近过。”这难道是宿命,是人类自身无法破解的生存困局?唯有到了彻底无力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放弃(怨恨、争斗)?也就是说隔膜是永远拆不掉的墙,除非死亡,它从不坍塌。用死亡来解决问题是小说家偷懒的一种办法,但也是人间无法抵抗的法则和人们共同的归路,只有在这种共同的背景下,人才会有了迟到的理解。小说设计了逻辑严密的一套因果。如果推推,倘若兄弟二人不反目,妯娌俩哪怕遭了打受了罪,也可以用诉说来缓解,就不用到另一个世界去诉说了,一切的一切都会是现在相反的结果了,这并非是不可能,从结果讲,他们最后不都和解了吗?然而,结果永远无法取代过程,人生可以不断地重复一个结果却没有能力、时间去推翻过程,这就是命运,是人的困局,也是《白雨》让人读后唏嘘不已之处。
2
《疾病的隐喻》对于“痛”的表达比《白雨》直接多了。开篇就是主^公无法摆脱的头痛:“是的,常人很难想象,先是后脑勺下方左右两边中的一边开始隐隐作痛,如果这时忍住不吃止疼片,会慢慢线状一样辐射到斜上方。然后开始环状,在整个脑袋上方均匀地蔓延开来,这时再吃任何止疼片,吃再多都不管用了,那时人会很绝望的。”
小说中的“痛”至少提醒我们关注两点现实。一是主人公被抛弃、被忽略的处境。尤其体现在与母亲的关系上。母亲对于这种“痛”仅仅用“无病呻吟”这样一个词就打发了。“当年母亲从不相信她的疼痛。没有任何止疼片,没有阿咖酚散。有一晚。房间里都是人,没人会留意她的疼痛。噪音。她捶了捶墙(或是没捶?)。后来她从碗柜里拿出碗,朝地上砸去,那一刻,在场的人呆住了,很快,他们离开了。那晚母亲罚她在阁楼上睡,她蜷曲着身子抱着自己的脑袋,尽情地默默流泪。”这种被忽略的疼痛铸就了“我”今后的生活和对世界的感知。“我”缺乏温暖的感情,渴望它却又无比敌视它。这样的结果是对于周遭的世界和人的绝望和不信任。而且,我只有用“摔碗”的方式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我发现,注意所得来的并不是对她疼痛的关注,而只不过对她搅局的厌恶罢了,“我”仍然只得自己默默流泪。第二点是既然“我”无法与周遭世界建立起稳定的信任关系,“我”是孤独的——不是自我选择的孤独,而是被遗弃的孤独,那么证明“我”存在的,也只有这“痛”,“我”与“痛”其实已经有了相互依存的关系了。“对她的大多数时候而言,疼痛本身像是一个度假胜地,知道自己总会置身于此,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在疼痛这里,只有在疼痛这里,她好像站在了自己的内心深处。在疼痛面前,她歪斜着脑袋,迅速地寻找止疼片,把对抗的全部责任都交给那些粉、片、胶囊。”我对此的解决办法只有药片和畸形的情感——这也正是让人心痛的地方。
“作为隐喻的疾病”,曾经是苏珊·桑塔格一篇著名论文的题目。桑塔格反对把疾病道德化、隐喻化,她明确说:“我的观点是,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一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疾病的隐喻》第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12月版)但在走走的小说中,不可能摆脱隐喻性的思维,恰恰相反,在感受到作者所描述的那种疼痛的同时,我时时感受到隐喻的存在。
3
《遗嘱》讲述了一个古老的故事。这里也有一种“痛”,那是道德之痛。老扣面对着不孝的儿子,心中是何等的“痛”?我惊讶地发现这种痛最后是以喜剧的方式被消解,作者用民间正义战胜了道德的失衡。这真是一个让人痛快的结果,但它却最终葬送了这篇小说。在作者陶醉于他讲述了一个流畅的故事时,我不得不提醒作者,小说不是道德训诫,虽然,它有义务承担精神与道德的使命,但一位高明的作家不会以道德审判官的面目出现在小说中。因为这样,让小说失去了自身的生存基础,成为一种被人驱遣的工具。不,作者没有权利这样来蹂躏文字!
4
甫跃辉是一位年轻作家,我读他的作品并不多,但仅就《白雨》一篇而言,我认为他对于短篇小说的驾驭似乎不逊于任何一位成熟的知名作家。这是一篇标准的短篇小说,叙述节制、有力,不动声色、有条不紊地布局,起承转合都是那么工于心计,也做得行云流水。但我想说的小说中更为突出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一种对称技法的运用。兄弟俩、妯娌俩是对称,妯娌俩的命运是对称,兄弟俩从多年前的反目到后来的和解是对称,甚至连细节上都充满了这样的对称,比如妯娌俩都曾被丈夫打过……这种对称让小说有一种美学上的建筑美,年轻的小说家能够这么娴熟地搭建起他的小说世界实属难能可贵。限于篇幅,我不在这里仔细拆解这篇作品,但小说确实值得细细剖析,每一笔都有着它的值得玩味之处,细细品味,会觉得与内容水乳交融的技术是小说内在的魅力之一,特别对于短篇小说,如同修建一座园林,有限的空间中绝不容你随随便便乱放一块石头。
5
甫跃辉的小说有“根”,那些执拗的人背后是一片深厚的土地,作者是在发掘一种人的内心和性格,他走的是一种传统的正路。而走走的小说则走的旁门,她的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找不到背景和身份的,就这样站在你的面前剖白他们的内心和感受。我做这样的对比没有厚此薄彼的意思,不过说明他们两个人创作的特点。走走的小说让我看到了她所承袭的卫慧、棉棉的骨血。她的另外一篇小说《女心》(《上海文学》2009年第3期)哪怕遮上名字也一眼能看出是同一作者的作品。甚至冷漠、自私与女儿对立的母亲,还与主人公乱伦的继父,同性与异性恋,吸食麻醉品等都是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情节。说实话,我一直怀疑这么私人化的经验表述能否真正表达出一代人的生活状态,我甚至怀疑所谓私人化的经验都是些流俗的伪经验。除了无所事事、痛苦、做爱,似乎就写不出什么了的小说,它们除了相互拷贝和自我复制,实际上是产生不了任何新创作更不要说大作品来的。从这一点而言,青春期的卫慧、棉棉带给人的是锋利的冲击,然而小说需要成长,过了而立、不惑之年,还是这样表达,未免让人觉得做作和矫情了。但在极端的经验被完全平庸的生活复述所淹没和取代的今天文学界,我倒也有理由怀念卫慧、棉棉,也会用另外一种眼光看待走走的小说,至少她们的作品中有一种紧张、焦灼,不愿意放弃的抵抗,这些让疲塌的文学有了一点点向死而生的味道。
6
“痛”作为一种感觉,对当今中国文学也有着不能低估的意义。因为所有的好小说、大作家无不是能够打开人的感官,文字打开感官世界,这是一个好小说的第一个条件。那些所谓的大手笔,不是把思想弄成硬面包磕我们的牙的人,而是用一杯香浓的咖啡或牛奶,让我们先被这些文字融化,此时,读者的世界与作者的世界才没有了间隔,彼此才会共呼吸同命运。平庸的文字永远与读者的心没有对撞,“痛”却是深深的一击。
“哥呀,李秉德眨了眨眼,艰难地说,等我走了,有一桩事还得托付你。眼睛斜向下,瞅着床边卧着的黄狗,说,黄狗是我瘫掉那年,她要来的,一天一天养到这么大。活着时候,黄狗天天黏着她,她也喜欢它,我经常在夜里听到她和黄狗说话。等我去了,怕黄狗没人喂,就交给你了。说着滚下泪来。李秉义转过脸去,瞅着黄狗,黄狗两眼如晶亮的墨玉。
那一年雨季,李秉德死后,村人经常看到李秉义和黄狗一同出现。李秉义腰塌得更厉害了,若一张移动的凳子,和黄狗差不多一般高。黄狗时而在前,时而在后,不知道谁在引领谁,谁在跟随谁。黄昏朦胧的光晕里,目力不逮的人远远看去,一不小心,就误以为是两条狗走在荒凉的村路上。他们偶尔会停下手中的活儿,揣测一下,它们将走向何方。”
这是《白雨》最后一幅画面,它让我们痛并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