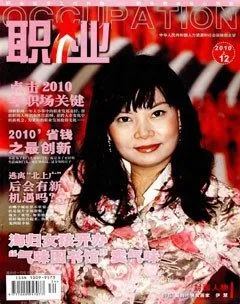“被”选择的职业角色
2010-12-31张正
职业 2010年12期
我们这一代人,大学毕业后是分配工作,没有吃过找工作的苦。靠分配得来的工作,因为身后有一份人事档案,像绳子一样牢牢地拴着,想重新选择、调整一份新工作,难上加难。即使这样,从青年到中年,一路走来,我先后在四个正科(局)级以上单位轮岗,在十个以上部门工作过,与职业性质相类似的大多数同龄人相比,不可谓经历不丰富。其中有的调动是我蓄谋已久、主动争取的;有的是服从组织安排、工作需要,时也、势也。时至今日,我经常问自己:到底哪一个职业更适合我?
“匠”
我最初的职业是乡村语文老师,先中学,后小学。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职业的,当初读师专的班上,我是唯一自愿选择读师范类而且如愿以偿读中文专业的。现实就是现实,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乡村教师,经济、社会地位太低,低得连找对象都成问题,我渐渐对这个职业失去了兴趣。我的性格也有致命的弱点:面对那群小毛孩,我传道授业、释疑解惑缺少最起码的耐心——我喜欢创新,不喜欢走重复的路。那个职业,只能允许我按部就班、年复一年地在三尺讲台上熬白头发。我不得不酝酿逃离、选择“跳槽”。若干年后,回头看看,我仍然希望自己有重返讲台的机会,但不是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而是大学的课堂。我非常希望自己退居“二线”后能找到一家民办高校,为一群生机勃勃的年轻人讲课。我有信心讲好的有两门课:写作和新闻采写。我曾经为这个职业努力过,希望通过考研的路直接从中小学的讲台走上大学的讲台,可惜我不是一个博闻强记的人,没有那个心智,不适合专门做学问,所以我不得不放弃。经过这些年的历练,我获得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在外发表了有关这两门课的一些论文,我想,也许可以一试了。
“家”
我最在意的头衔是作家。虽然我现在已挂着一个省级作家协会会员的称号,可我从来不敢真的把自己当作家看。作家是什么?他应该有才华、有学识、有思想,我呢,什么都没有,只有生活。我只是用文字在讲述自己的生活。这是层次很低的写作,与作家的名号是不相匹配的。如果才华是与生俱来的内在素质,我怕是这辈子都与才华无缘了。学识呢,学是学了一点,多是皮毛,不求甚解,还远没有到化为己有、成为“识”的地步。至于思想,更是无从谈起,我只有零碎的想法、念头,成系统的思想,从来不敢奢望。我渴望自己成为大作家、大文豪,这样的渴望连理想都不可能是,只能是梦想。我所能做的努力,是离那个遥远的梦想接近一点、再接近一点,最终相差多少距离,我想也不敢想。
“者”
我做过许多年的新闻记者,我获得的最高职称就是记者中级。如果说我最爱做梦的年龄献给了乡村中小学讲台,那么,中年之前的大部分宝贵时光,我是献给了新闻采访工作。这个工作我做得很好,得到的最高荣誉是大市级“十佳”新闻工作者,《人民日报》这样的中央级大报也多次用较大版面刊登我采写的人物通讯。尽管这样,我还是不能说这个职业最适合我。记者这个职业与现实靠得太近、平时太热闹,我不喜欢。累、有压力倒在其次,关键是辛苦之后很难收获想要的东西,连静下心来好好理一理思绪的时间和氛围都没有。有人干了一辈子记者,说自己到头来就像漂浮在水面的油花,表面风光无限,骨子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薄薄的一层,似有似无,从未真正溶于水。我喜欢这个比喻。话归这么说,记者这个职业还是让我获益颇丰。年轻人如果想在较短的时间内比较全面地认识这个社会,最好的职业无疑应该就是记者。
我先后还充当过机关秘书、部门管理者等角色,我心甘情愿、孜孜不倦去竭力干好的职业,似乎还是做一名文字工作者。做一个蹩脚的作家,我是文字工作者;做一个人在曹营心在汉的记者,我是文字工作者;做一个成天为领导写讲话稿、为活动制定方案的机关秘书,我是文字工作者……从事这些工作,我都在提醒自己:千万千万,不要把自己退化成为文字匠!家、者、匠,它们是不同层次的写作,前者追求心灵的自由,后者主要是谋生的手段,审视自己的天赋,我将自己的人生定位在中间。无论是我选择了职业,还是我被职业选择,我都有勇气说自己是一个兢兢业业的人。做一名文字工作者,或者再跳一跳,做一名优秀的文字工作者。这不是什么十分崇高的理想,也不是什么十分荣耀的职业,但对于我,已经十分满足。因为这个职业,既可以承载我个人的人生价值,也可以承载我为这个社会应尽的义务。做好这个职业,同样需要我付出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