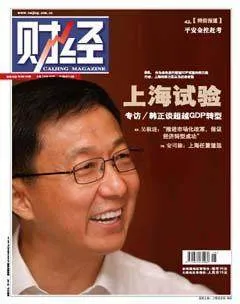人大代表专职化磋壁
2010-12-31左林徐凯
财经 2010年19期
李国喜骤然闲了下来。
这位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县御营镇的前综治办副主任,6月底辞去镇村两级的职务,成为“全国首批县专职人大代表”,接待着一轮轮的来访者,一度从早忙到晚。几天后,该县调元镇的刘圣会和蟠龙镇的罗刚模也先后出任县专职人大代表。
这是罗江县自发的一项人大代表制度改革:在驻镇的县人大代表中推选小组长,实行组长专职化,给予调研经费,将其生活补助纳入财政预算,确保其专门履职——上午在“专职人大代表工作室”接访,下午调研。
罗江县的改革被舆论评价为“民主宪政探索的一种有益尝试”。
“我喜欢有事忙。”李国喜说,但他忙碌的日子只持续了20天。7月17日,罗江县人大接到四川省人大新闻局传真,要求暂停专职人大代表试点,同时停止一切新闻宣传。7月19日,“罗江县专职人大代表工作室”被摘牌。
一个月后,一项国家层面的立法阐释了罗江县改革被叫停的深层背景。8月2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修正案(草案)》(下称代表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规定:代表不脱离各自的生产和工作岗位。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在对代表法修正案草案进行说明时表示,鉴于中国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办事机构、工作机构是代表履职的集体参谋助手和服务班子,代表不设个人工作室。
如果草案获得通过,基层推动多年,有尝试的“人大代表专职化”改革便告终结。
夭折的改革
9月2日,罗江县御营镇场镇中心,镇政府斜对面一处临街的门面房内,曾经的“罗江县专职人大代表工作室”换上了“御营镇幸福罗江促进室”的牌子。门庭冷落,大门紧锁,仅开一道侧门。屋内墙上专职人大代表职责、工作流程表已被揭去。
李国喜的名字依然挂在促进室的门口,他目前的身份是“幸福调解员”,每日工作仍是接待群众,但原先的自主调研已改成“受镇党委委托”进行调研,与其工作对接的机构,也从县人大常委会改成了县群工部。
“已经三天没人来了。”李国喜望了望门口。
罗江的人大代表专职化尝试,是一场当地官员和北京学者共同发动的改革,主要的推动者是罗江县委书记卢也和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
卢也年近半百,在当地主政七年多,先后任罗江县县长、县委书记,熟悉基层情况。而于建嵘持续关注县政改革,认为县级政权的体制改革“能真正改变中国”。他主张打造责任政府,使其既向上级负责,更向县域居民负责,他认为,基层人大代表职业化改革是现体制中具有操作性的突破口,可以实现人大“去官僚化”的特征,同时保持政府现有政策、人事的稳定性。
卢也与于建嵘结缘实属偶然,卢也在四川省的一份会议材料中,首次看到于建嵘关于县级政权改革的观点,产生共鸣,于是他通过作家野夫牵线,邀请于建嵘来罗江讲课。
2010年5月19日,于建嵘来到罗江,为全县400多名副科级以上干部讲课,主题是“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在此期司,于建嵘再次提出县级政权在现体制下的困境司题,以及他的“县级人大代表专职化改革”思路。 讲座之后,卢也与于建嵘一拍即合,决定在罗江将于建嵘的理论付诸实践。
6月12日,于建嵘将罗江县委数名常委请到了北京,组织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等人,对罗江县的改革方案进行全面论证。几天后,罗江县政法委书记张胜虎将《罗江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试行专职县人大代表的意见》(下称《意见》)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于建嵘,于在文字表述上做了修改,随后传回罗江再次修改。
《意见》对“专职县人大代表”和“县人大代表工作室”做出界定:前者指在县人代会闭会期司,专门在县人大代表工作室、履行定时接待所在镇选民的县人大代表。其职责为,重点收集、调研选民反映的问题,以批评、意见和建议的形式要求“一府两院”及其部门依法办理并答复。“专职县人大代表”由县人大代表自愿申请,经所在县人大代表小组选举产生,报县人大常委会备案;而“县人大代表工作室”,是县人大常委会设在各镇,供专职县人大代表接待选民的办事机构。其办公经费由县财政负担。
为不违背现行代表法的规定,罗江县专职人大代表的“工资”被称为“生活补助、误工补贴”。
据参加罗江改革论证的蔡霞称,在《意见》制定之初,罗江县便明确,专职人大代表遵循“不直接处理和解决问题”的原则,同时先选取一两个乡镇进行试验,待时机成熟再进行推广。
改革很快进人操作层面。御营镇被定为首批试点镇之一。该镇共有八名县人大代表,其中四人为县城的公务员,另外四人包括一名教师,一名镇财务中心的会计,一名村委会主任,以及李国喜。因李国喜当时的职务是御营镇环境综合整治办公室副主任兼太平村党支部副书记,相对属于“闲差”。6月中旬,罗江县政法委书记以及县人大一名官员找李国喜谈话,询问其是否愿意担任专职人大代表。“我觉得这是上级交代的任务,就答应了。”李国喜说。
6月23日,御营镇的八名县人大代表通过选举程序,一致推选李国喜担任县专职人大代表。五天公示期结束后,6月28日,李国喜辞去原职,走马上任。
此后,媒体峰拥而至,学界亦广泛关注,支持者多将罗江的探索视做未来人大代表制度改革的方向,异议者则指出其在立法、选举层面的制度障碍。卢也对于这些争议,已有心理准备,他曾对下属表示,如果罗江的改革给市人大、省人大带来风险,他将辞职。
不久,情势急,7月17日下午5时,罗江县人大办公室主任卢晓刚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接到了四川省人大新闻局的传真,传真的内容明确停止专职化试点。7月19日,“罗江县专职人大代表工作室”的牌子被摘了下来,罗江县的此次尝试就此画上句号。
代表法转向
就在罗江专职人大代表改革被叫停一个月后的8月23日,代表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初次审议。这是代表法自1992年开始实施后的首次修订。
草案规定代表不脱离各自的生产和工作岗位。代表出席本级人大会议,参加统一组织的闭会期司的活动,应当安排好本人的工作,优先执行代表职务。 总体而言,草案旨在抑制代表个人行为,人大代表要在组织的统一规定下活动,集体履行职责。
“专职代表”被叫停的同时,代表个人工作室亦未能幸免。草案规定县级以上的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是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集体服务机构,为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提供服务保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在对草案进行说明时表示,代表不设个人工作室。
罗江县改革被叫停、代表法修正案草案修订,两起事件被联系到了一起,引发舆论热议。有学者认为,这两起事件预示着对中国“人大代表专职化”改革路径的否定,这也使得发轫于1985年的人大代表尝试发挥个体作用的努力宣告结束。
1985年,经中央高层批示,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发布《关于改进全国人大代表视察办法的意见》,要求把集中统一组织代表视察逐步改为分散的经常的视察,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制发代表视察证,代表持证视察。
随后,经过一系列改革,人大代表个人视察成为一个常见现象。到2003年前后,大批具个性的人大代表涌现。如浙江义乌的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设立了个人办公室,他组织由退休老干部、大学教授等构成的志愿者队伍,大量倾听、整理、反映选民意见。随后,浙江、湖南、广东等省纷纷出现人大代表设立的个人工作室,被舆论认为是代表意识的一次觉醒。
这次觉醒很快就遭遇困境。2005年,中共中央辖发《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进一步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下称9号文件),其核心内容是代表在闭会期司,以集体活动为主,以代表小组活动为基本形式。蔡定剑认为,该文件实际上限制了当时活跃的代表个人工作室现象。
但即使在9号文件下发以后,各地有关设立“专职人大代表”和“人大代表工作室”的研讨以及实践,仍在进行。
2005年8月3日,深圳市人大代表杨剑昌设立了“杨剑昌接访室”,定时、定点接待市民,收集他们反映的问题,并呈送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再由其辖至相关部门。
2008年1月,王建民等代表向北京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建议,开展专职人大代表试点。
2008年8月,浙江省温岭市箬横镇贯庄村成立“江根德人大代表工作室”。
2008年9月,全国人大代表、农民工胡小燕主动通过媒体公开手机号码,接受农民工求助。
2010年6月30日,广东人大常委会主任欧广源在与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进行座谈时表示,“人大代表不能一年就只开一次会,不能开会‘是’代表,不开会就‘不是’代表。省人大可以接界别或者在某一个市先行试点专职人大代表工作。”
从制度层面而言,9号文件为党内文件,而此次代表法修正案草案则属于法律意志,但其中有关否定专职人大代表等条款,即由9号文件一脉相承而来。
“人大代表要不要专职化,这是值得讨论的,但是禁止代表专职化是不合适的。”蔡定剑认为,“代表法的立法思想应该是保障人大代表行使职权,而非对其进行管控。”
在蔡定剑看来,人大代表是由选民选出来,应对他的选区和选举单位负责。从这个性质出发,人大代表必须独立行使职权。因此,“代表活动以集体活动为主,小组活动为基本形式”的说法是不合适的。
更有学者指出,人大常委会无权修改代表法。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认为,各级人大是代表人民行使主权的“权力机关”,而人大常委会仅为人大的“常设机关”,由人大常委会修改代表法,是“下级给上级”“被监督者给监督者”立法。
此外,据蔡定剑介绍,1982年修改宪法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在进行修法说明时称,“我们要人大常委会尽量往专职化方面发展,就是为了脱离过去议行合一的体制”。人大常委专职制度由此而生。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表示,虽然这种专职化还不彻底,但全国人大常委必须辞去政府和司法职务才能任职,这在法律上和实践中均已确认。
较之人大常委专职化更进一步的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地方人大在完善人大制度的探索中,设立了人大常委会专职委员职务。其中,上海、广州、北京等地人大皆设立常委会专职委员。2010年6月3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李华楠也透露,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将在未来5年内设置专职委员。
在蔡霞看来,此次代表法修正案草案关于代表不脱离各自生产和工作岗位的条款,使得目前的人大常委会专职委员处于逻辑悖论中,“一旦修正草案关于人大代表禁止专职的建议规定通过,那么人大常委会设专职委员就是违法。因为人大常委会的专职委员,实际上就是部分人大代表专职化”。
对于外界的种种争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未做出回应,一位接近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人士则对《财经》记者表示,禁止代表专职化的事情,不像外界所说的那样,是阻碍改革。实际上,人大制度要改革的地方很多,全国人大正在逐步推进。
专职化路径
在一些学者看来,人大代表专职化改革,是真正发挥人大代表民意职能的现实突破口。
中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制度设计上,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就是行使人民主权的机关。张千帆表示,在理论上,几乎所有重要的政府官员都通过人大选举产生,而至少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人大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因而选民可以期望通过直接或可接选举基层人大代表来监督政府机构的运行。
然而,在实践中,尽管法律赋予人大权力机关的地位,但无论是全国人大,还是地方人大都远未能发挥出其所应有的重要职能。张千帆认为,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现实中的人大制度在代议制的两个关键——代表性和职业化层面,都存在着严重不足。 张千帆看来,造成代表性不足的原因,在于公民的选举权无法有效落实。根据法律规定,目前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其余人大代表由下级人大选举产生。一方面,直接选举的范围过于狭窄;另一方面,差额选举名额少,候选人推选资格往往受党政机关影响,选举往往流于形式。实践中,绝大多数人大代表另一重身份为各级官员。至于职业化不足,即人大代表业余化,代表缺乏政治和法律知识。根据现行规定,代表来自各行各业,草案强调代表不脱离各自的工作岗位,且在闭会期可以小组集体活动为主。这使得代表无法真正发挥代表民意的作用。
对此,作为罗江县改革主角的李国喜感受颇深,李国喜已是两届罗江县人大代表,他称自己此前九年的代表生涯中,鲜有民众找他反映,口]题。“农村百姓对人大代表没啥子概念,有事都是找领导、找书记,真是有司题的要么就上访。”在成为专职人大代表之前,李国喜履行代表职责,主要是参加县人大组织的视察活动,平均每月一次。而成为专职人大代表后的20天时司里,他接待了五六十名来访民众。
罗江县另一位专职人大代表刘圣会亦表示,14天的专职人大代表经历,和此前四年做代表的感觉十分不同,“现在很多是关于老百姓个人的,口]题,我从来没听到这么多意见。”
改革被叫停后,刘圣会曾表示,“虽然我还是人大代表,但是当我的以调解员的身份,把问题反映到镇上,比如水利局、信用社等部门,我去,口]他们这个事情办的怎么样,我可以监督,但是他们还会买我的账吗?而人大代表是有这个权利,可以约见他们。”
对此,蔡定剑认为,在目前的人大代表体制下,代表的主观能动性被抑制,“哑巴代表”等现象不可避免,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也无法真正发挥权力机关的作用。人大代表专职化改革属于地方人大的制度创新,应予鼓励。在抑制地方创新的同时,试图激励代表主动履职,无异于缘木求鱼。
于建嵘认为,罗江的实践,只是一个开端,不能指望它一蹴而就。实际上,于建嵘还为罗江设计了一整套的基层政改方案,包括预算监督、村级选举、发现社会矛盾的网格化制度等。在人大代表专职化改革被叫停后,这些政改方案只能停留在纸面了。
8月初,于建嵘再次来到罗江,他对罗江县人大办公室主任卢晓刚建议,县人大可以把这次代表专职化改革的资料作为史料保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