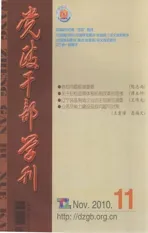民国初年制度意识缺失条件下制度破坏路径分析
——考察第一届国会存续期间民主共和制度存废
2010-12-26孙林
孙林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民国初年制度意识缺失条件下制度破坏路径分析
——考察第一届国会存续期间民主共和制度存废
孙林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民国初年(以下简称民初)中国民主共和制度初造,虽不完备但框架已立,相对于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然而由于国人制度意识缺失,使民初民主共和制度在“立——破——立——破”的路径上逐渐式微,在民初1912年至1914年第一届国会存续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本文试图祛除价值评价,依据史料力争客观地分析民初民主共和制度的破坏路径。需要指出的是,在民初民主共和制度的立与破中,政治精英制度意识缺失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本文拟从制度意识缺失立论,探寻分析第一届国会存续期间(1912—1914)年间民主共和制度破坏路径。
制度意识;民主共和制度;破坏路径
制度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是人们对现行制度及各种制度现象的观点、知识和心理态度的总称。它表现为尊重、信任、遵守和自觉维护制度规范的心态,以及遇事第一反应即依制度规范求解的主动意识和行为。在结构上,制度意识主要由执行制度的意识和维护制度的意识构成。制度意识事关制度生存,如果制度意识缺失,不仅难以制定出好的制度,即使有了好的制度也难以得到有效实行。笔者认为政治精英[1]制度意识缺失在民初表现得十分明显,民初政治精英遇事求解时要么神化制度解决问题能力、要么“以”而非“依”制度解决问题,甚至寻求制度外解决问题途径。这些都严重破坏民初民主共和制度的正常运行,本文拟以第一届国会存续期间民主共和制度破坏情况为例,分析制度意识缺失条件下制度破坏路径,探寻制度意识的功能、价值及培养方式。
一、从神化制度到工具化制度的嬗变
制度神话,就是过分迷信制度的自发作用,一种制度如果在理论上有优越性,人们就容易想当然地认为它在实践中也一定具有现实性,似乎不再需要制度主体的努力。[2]神化西方宪政制度是清末民初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共同政治倾向,似乎将西方的宪政制度引入到中国,就可以迅速改变中国贫弱的国势。
辛亥革命爆发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部分立宪派人士随即开始立规建制以期尽早践行奉若治国良药的西方宪政制度,1911年11月15日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迅速制订了临时政府的组织法,并完成了首都和国家元首的建置。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仍代行参议院职权,成为民国议政机关,直到1912年1月28日临时参议院正式开幕时自动解散。期间,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按照民主议事规则,基本搭建完成了民国民主共和制度框架。其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大纲》、《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一)是中国资产阶级在宪政领域奠基之作。“决不能轻估这一创试的意义……它给后来留下一个难得的好范例”[3]。其开创价值及所带来的制度神话持续了近十年之久。此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二次革命”、两次护法运动等一系列革命活动都是为了维护这套制度体系。
然而,民主共和制度也正是在民初这次法律化过程中开始走下了神坛,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及其后的临时参议院在创制和实施民主共和制度的过程中,却开始从神化制度向工具化制度蜕变,表现出典型的因人设法的工具主义倾向,其后北洋军阀更将倾向变成行动,具体表现为:
1.制度意识缺位,超越制度许勋允位。南北和谈期间,为了尽快实现“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革命目标,1912年1月22日,孙中山提出解决南北问题的具体办法:(1)清帝向中外宣布退位;(2)袁世凯同时宣布政见,绝对赞成共和主义;(3)孙中山辞职;(4)由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5)袁世凯宣誓遵守临时参议院所定之宪法。[4]在此解决南北问题的方案中,孙中山直接允诺让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这显然是将民主共和制度作为革命的工具,虽为革命的目的,却彰显出制度意识缺失下工具化制度的倾向。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接受南京临时政府议和条件迫清帝退位。2月13日,孙中山践行诺言,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并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越过副总统黎元洪荐举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从南京临时政府组织制度层面考察,孙中山推荐袁世凯在法理上显然违反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大纲》第七条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四十二条关于副总统之规定。根据1912年1月2日通过的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大纲》新增第七条:“临时副总统于大总统因故去职时,得升任之。如大总统有故不能视事时,得受大总统之委托,代行其职权”,[4]虽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施行之日废止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大纲》,但却继承了后者对临时副总统制度的规定。很显然,即使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无论怎样离职,临时大总统都应由临时副总统“升任或代行”,而非越过副总统举荐他人。
其实资产阶级革命派工具化民主共和制度的倾向,在南北议和之前就已经表现出来。袁世凯在武昌起义后复职组阁时曾向武昌发信倡和,黎元洪在回信中希望袁世凯投身革命,称“公果能来归,将来民国选总统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中猎取”[6],黄兴在赞同称“望建拿破仑、华盛顿之功,翻然速来”[7]。“猎取大总统”、“建华盛顿之功”即是先许勋允位,再用民主共和制度使之合法化,以完成革命任务。
2.根本大法因人重构,政体因人重置。南京临时参议院于1912年1月5日至25日推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一,因人立法,政体设置为总统制。2月7日推出的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三,于3月11日颁行,同时取代并废止《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大纲》。最后颁行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关于政体设计临时因人改弦易辙,既规定了总统的各项实际权力,又极尽可能地赋予参议院和国务院各种广泛的权力和实际的责任,以限制总统的权力,使得行政权力的划分极其混乱,成为一种介于总统制和内阁制之间的特殊的体制。
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在制订过程中修改固然无可非议,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一个月之内因人事变动而修改政体,这不仅大大削弱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范性和权威性,也肇始了民初“法随人而动”的制度破坏路径,这充分证明了民初政治精英制度意识淡薄乃至缺位。孙中山最有望担任首任大总统,最初也最力持总统制反对议会内阁,但随着袁世凯获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遂因人改法,采用责任内阁制。孙中山也改变态度表示“现在中国情形论之,以内阁制度为准,中国国民莫不主张政党内阁……内阁制是适合中国最好的政体”[8]孙中山主张责任内阁制为制衡袁世凯的革命策略,但从制度意识角度考量,民初政治精英对待国家制度的工具主义态度是形成民初制度破坏路径的滥觞。
3.制度外求解:“宋案”弃法律而用武力。1913年2月第一届国会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大获全胜,获得参议院870个席位的392个,共和、民主、统一党合计获得233席[9]。国民党组阁在即,力主政党内阁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踌躇满志,并草拟了《国民党之大政见》,俨然以内阁总理姿态出现。然而在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却在上海火车站遇刺身亡,这对中国宪政民主的发展是一个沉重打击,“它直接造成一个难得并可能继续良好发展的时代被扼杀了”[10]。
“宋案”发生后,国民党内就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产生分歧,黄兴等人主张法律倒袁,在制度框架内用法律和平解决“宋案”;孙中山等主张武力讨袁,用战争解决“宋案”。而袁世凯一直在做武力准备,并与五国银行团秘密签订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准备战争,随后又接连罢免了安徽、江西、广东三省国民党籍都督,派北洋军南下,南方国民党人仓促发起“二次革命”终归失败。
“宋案”称之为“案”即属于法律问题,然而却成了民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治内战的导火索。“宋案”发生后,民国初创的政治、法律制度被抛在一旁,双方用枪炮解决政见分歧和法律案件。这些政治、法律制度既是袁世凯政治合法性的制度基础,也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孜孜追求和维护的对象,双方却以内战的方式自毁之。从此,民主共和制度不但加速沦为武力的工具而且直至丧失工具价值而终被废弃。笔者较为赞同袁时伟教授对此问题的评价:“从历史发展的全局看,‘宋案’当然是袁世凯及其支持者犯下的罪行;但以此为由称兵进行所谓的‘革命’,也是民国史上的一个不明智和非常不幸的开端。此举给袁世凯之流提供了明目张胆堵塞军队国家化、不准干预政治的道路的借口,从而错过了逐步改造当时各种武装力量,使之向现代国家军队转化的机遇。”[11]“宋案”及随即的“二次革命”反映了当时主政的北洋军阀的制度意识缺失,也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制度意识的淡薄。更严重的是这一系列事件形成破坏民主共和制度的路径依赖。
4.以武力为后盾的因人改制,民主共和制度完全工具化。作为由军队起家的袁世凯惯用武力实现政治野心。“袁世凯把军队作为排斥政敌、挟制各党、操纵国会的法宝,时刻威胁着政党与国会的正常工作和存在。”[12]“二次革命”期间,袁世凯为使国会通过陆征祥内阁人选,鼓动北京军警称“议员不惜亡国,军人即不守法,必以铁血溅之”[13]。临时参议院第二次讨论陆征祥内阁人选时,袁再次鼓动北京军警称“如参议院再不通过,则请大总统解散”[14]。“二次革命”后,失去南方国民党武力制衡的袁世凯更屡屡操纵军警干涉行政、破坏立法、摧残民主共和,最终摧毁了民初民主共和制度的象征——国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政党制度。其具体过程为:(1)袁世凯违反程序正义,颠倒制度运作程序取得正式总统职位。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制宪程序,临时约法只能产生临时总统和临时政府,由临时总统根据临时参议院制订的国会选举法和组织法,并于10个月内完成正式国会的选举与召集,再由正式国会制订宪法,然后根据宪法产生正式总统和政府。这是临时政府赖以产生和行使职权的法律制度基础。[15]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武力压迫参众两院超越正常选举程序,提前进行正式总统选举。(2)驱逐国民党议员变相废止国会。袁世凯于1913年11月4日下令解散国民党,使国会达不到法定开会人数来变相废止国会。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正式要求熊希龄内阁全体阁员附署停止两院议员职务令,民国第一届国会被废止。(3)异化的制度——《袁记约法》。制度异化是将制度的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将制度的目的与手段颠倒过来,割裂制度的本意,扭曲制度的本质,最后将制度变成社会和人发展的桎梏。[2]
二、从移植到异化:民主共和制度破坏的路径依赖
民初民主共和制度移植非常迅速,成果显著。在具体制度移植的层面上,最显著的是西方宪政民主制度法律化成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大纲》、《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都是这一时期宪政法律化成果,而且在南京临时政府存续的3个月内,民主共和制度运行状况基本良好。大多数问题都在制度框架内解决,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进行了一次伟大尝试。[17]
但民初制度移植的最大问题在于制度意识的移植缺位。笔者在第一部分已经阐述了民初政治精英缺乏制度意识,造成民主共和制度屡遭破坏最后终被异化结局。笔者这里再从制度破坏路径依赖视角分析民初政治精英制度意识缺失。
民初民主共和制度破坏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所谓路径依赖 (path depengdence)是指今天的制度演化受到以往制度的影响,制度演化一旦在自我增强机制下选择了一条路径,它就会沿着这条路径走下去,即使一次或偶然的机会会导致一种解决办法,而一旦这种解决办法流行起来,它就会导致这种方法进入一定轨迹,此时要纠偏归正就变得十分困难。[2]民初民主共和制度的破坏有些虽出于“良好动机”之下偶然的解决办法,但很不幸这些解决办法形成了破坏路径依赖。
破坏路径依赖之一:宪政制度因人立法。民初民主共和制度因人立法肇始于南京临时参议院为制衡袁世凯,而将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循此路径到袁世凯为实现大权独揽,而以增修约法的形式制订了一部完全适合袁世凯专制独裁的《袁记约法》,将责任内阁改为总统独裁制。因人立法最大的隐患是国法附随人事,导致国家根本大法频被修改而动摇其权威性。宪法为一国立国之本,本固则邦宁,民初临时约法因人立法而引起的仿效最终摧毁了民国的民主共和制度。
破坏路径依赖之二:以武力突破制度框架。民初政治精英信任并依靠武力从事政治活动,忽视甚至无视制度规范。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依靠会党和新军取得革命胜利,而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更视军队和武力为“法宝”[15],这使得军队及武力始终是民主共和制度的心腹大患。民初民主共和制度下第一次以内战解决政治纠纷始于1913年“赣宁之役”,遂使民初内战频仍,都是循延内战解决政争的路径。“赣宁之役”缘起于“宋案”,“宋案”发生后,孙中山主张武力解决,虽然国民党大内多数人主张在法律框架内解决问题,但随着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和一系列人事和军事动作使制度框架内解决之路无望,最终武力冲破制度让内战遂起。其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更加滥用暴力或暴力威胁,在选举正式大总统、解散国民党、增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频频以军队或军警为后盾,暴力扭曲制度,甚至冲破制度框架行事。
破坏路径依赖之三:民初制度遵守采用反一报还一报模式,人们在遵守制度时多数时候会采用一报还一报模式,即第一步采取合作模式,若对方合作就继续合作,若对方背叛就也背叛。若不知道对方合作还是背叛时就采取合作立场。[2]但民初由于制度意识缺失,政治精英对制度的遵守往往采取反一报还一报模式,即在不明对方合作还是背叛时首先采取背叛立场,当对方合作时才合作,对方背叛时继续背叛。这一点在“二次革命”中有非常明显的表现,“宋案”发生后,南北双方都有做不遵守现存制度的武力准备,结果陷入“安全困境”之中,遂使“不可避免地要酿成内战”[17]。
三、制度意识培养:民初民主共和制度破坏路径反思
民初政治精英缺乏制度意识,游走于神化制度和工具化制度的两极。特别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推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大纲》规定的总统制而改为责任内阁制,是民初政治精英制度意识缺失的首次暴露。资产阶级革命派首先修改临时约法用作制袁工具,而后又将临时约法奉为“神明”,幻想用一纸约法所定制度即可统制袁世凯是注定要失败的。其后袁世凯及北洋军阀更变本加厉地工具化民主共和制度,随意操控制度规则最终异化了民元创试的民主共和制度。考察民初民主共和制度的破坏路径,笔者认为制度意识缺失特别是政治精英制度意识缺失是民初民主共和制度异化的主因。笔者亦就循此破坏路径反思制度意识培养。
制度合理性是制度意识培养的前提。制度合理性是指制度契合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内在保持逻辑上周延,外在促进社会发展、社会与人协调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2]制度合理性的最低要求是“即使在法律和制度不正义的情况下,前后一致地实行它们也还是要比反复无常好一些”[18]。从这个意义考量民初民主共和制度,笔者认为民初民主共和制度合理性充分,但也存在很大的问题。主要为制度内在逻辑上周延的问题:1.权力分立失衡,《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总章中,参议院、大总统、国务员三者权力关系中,参议院权力大得无边无际,国务员也负有“附署”权,唯有大总统权力受到各方面掣肘。参议院兼具立法、民意代表、宪法增修、弹劾、选举、财政、质问、建议等功能,这很大程度上远远超过保证实现真正责任内阁所必须的措施和规定,国家元首在参议院面前也完全成为“橡皮图章”。2.责任内阁制度低效率,临时约法规定每位国务员任命也必须经过参议院一一讨论通过,同时内阁在其他行政事务上更受参议院制衡。章太炎在1913年给黎元洪的信中评价责任内阁制度称“中国内阁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纷争。始以党见忌人,终以攻人利己;财政部官制议二月不成,六总长名单以众妒而反对;裁兵之案,延宕逾时,省制之文,蹉磨累月,以致政务停顿,人才淹滞,名为议员,实为奸府,形成千百议员皇帝专政”[19]。民初实行责任内阁制 16年,10易国家元首,组阁45次,总理更迭59人次,组成5届国会,颁布7部宪法。[20]3.对总统与总理划分权限不清,在实践中往往出现:总统如手中握有军队,绝不安于虚位,凡军国大事,一切由他敲定;如总理手中握有军队,总统必然处于虚位。当然民初民主共和制度在前后一致实行上也存在问题,如2年多时间里2次修改政体。
民元创试的民主共和制度存在以上缺陷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制度合理性,也导致了制度意识培养上的困难。对政体的政治共识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也不存在,制度意识培养需基于制度的普适性和主体在制度下获得预期收益的可能性,并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反复印证直至内化为制度意识。而民元的民主共和制度不具备提供这样资源的能力。
培养制度意识,需要破除制度神话和制度工具主义倾向。相对于神化制度,制度工具主义危险性更大,民初政治精英特别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对初创的民主共和制度缺乏应有的尊重,把制度作为一种为己所用、为己所改变的工具,合乎自己利益的时候就遵守,不合乎自己利益的时候就破坏。最终毁弃了民主共和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民初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在民主共和制度破坏问题上需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制度意识培养,需要保障制度普适性。民初,不同主体在民主共和制度选择和设计过程中的地位不同,有制度制定者,也有制度承受者,但只要不允许任何超越制度之上,游离制度之外的特殊主体存在,保持制度的普遍约束性,制度意识就可以培养出来,但不幸的是历史实践却走向了反面。
最后,制度意识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笔者这里引入制度意识概念只是提供一个分析变量和分析视角,并不是为假设历史或以今日标准苛求前人。民初结束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国家元首由封建制下的血缘继承,变为民主共和制下的投票选任,制度跨越很大,而且新制度的确立只反映在法律上和国家机构建置上,制度意识确立还需要国民长期的习得,具有滞后性。正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我国由五千年之专制一跃而进入共和,旧心态横亘脑中,新信条未尝熏受,欲求新政体之圆满难矣”[21]。因此,民初政治精英缺乏对民主共和制度的制度意识亦属正常,但制度意识缺失造成的破坏却令人扼腕,其破坏路径令人警醒。本文以制度意识为视角,考察第一届国会存续期间民主共和制度的破坏路径,意在见微知著提供借鉴。
[1]本文将民初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以及北洋军阀统称为政治精英,这里所谓的政治精英仅仅是从其功能上将其标签化,而非带有价值评价因素。
[2]辛鸣.制度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3]廖大伟.辛亥革命与民初政治转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4]孙中山全集.第2卷[M].上海:中华书局,1982.
[5]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1981.
[6]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M].北京:龙门联合书局,1958.
[7]刘泱泱.黄兴集[M].上海:中华书局,1981.
[8]孙中山全集(第1卷)[M].上海:中华书局.1985.
[9]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史稿(第4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1991.
[10]廖大伟.辛亥革命与民初政治转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1]袁时伟.政治策略与民初宪政的历史经验[J].战略与管理,2000,(6).
[12]杨绪盟.民国初年中国政党政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申报.[N]1912年7月22日.26日.31日.
[14]黄远庸.远生遗著(第2卷)[M].上海:商务出版社,1984.
[15]陶菊隐.武夫当国(第一辑)[M].海南:海南出版社,2006.
[16]廖大伟.辛亥革命与民初政治转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7][澳]骆惠敏.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下[M].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
[18][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1988.
[19]时报 [N]1912年7月25日.12月10日.
[20]郭剑林.民初北洋三大内战纪实[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2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M].上海:中华书局,1941.
责任编辑 宋桂祝
D693
A
1672-2426(2010)11-0015-04
孙林(1984- ),男,安徽阜阳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外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