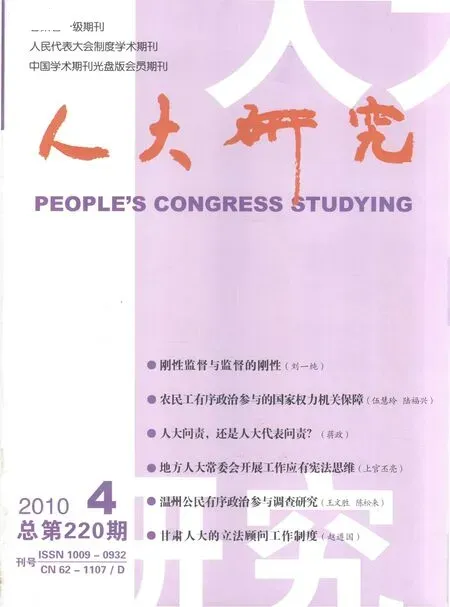地方人大常委会开展工作应有宪法思维
2010-12-26上官丕亮
□ 上官丕亮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一年只召开一次会议,难以发挥权力机关的作用。设立常委会,可以在人大闭会期间,开展经常性工作,真正使地方人大工作开展起来。可以说,这是1979年地方组织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的最大意义。在事实上,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30年来,地方各级人大的工作也主要是由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来组织和开展的。回顾30年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其中有一点,过去人们关注不多,笔者认为有必要予以强调,那就是地方人大常委会开展工作应当有宪法思维,充分考虑宪法,进行依宪解释,实施宪法。
一、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性质主要是执法
众所周知,人大的工作主要有立法和监督两大工作,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大多也不例外。然而,有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即地方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工作和监督工作在性质上都属于执法。
(一)地方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的性质属于执法
我国宪法第一百零四条对地方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权作了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七条等条款对地方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职权和监督程序等作了进一步的规定。2006年8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的监督法除总则和附则之外,设立了“听取和审议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决算,听取和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听取和审议审计工作报告”、“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询问和质询”、“特定问题调查”、“撤职案的审议和决定”等七章内容,对各级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权的内容、形式和程序作了详细的规定。
显然,目前地方人大常委会开展监督工作,必须依照地方组织法,特别是监督法进行。也就是说,地方人大常委会开展监督工作,就是去严格执行监督法等相关法律,严格执法、依法监督已经成为地方人大常委会开展监督工作的基本内容和要求。由此可见,地方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工作在性质上属于执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地方人大常委会既是监督机关,也是执法机关。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实践中人大工作的同志通常将人大的监督工作分为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两种,前者是对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后者是对“一府两院”的工作进行监督,给人感觉好像是后者与法律无关。其实,“一府两院”的工作本身就是执法(即行政执法和司法),对其进行监督就是一种执法监督,就是法律实施的监督。正如一位学者所言:“这种划分是很不科学的。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法律监督。人民代表大会监督的根本特点就在于它全面监督国家法律的实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就实质内容而言都是法律性质的监督,而不存在什么工作监督……人民代表大会主要并不是要监督它们的工作好坏,而是要监督它们工作是否违法和履行法律职责。”[1]可以说,所谓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这两种监督在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对执法的监督。人大开展这两种监督本身也必须依法进行,严格执法,严格执行监督法等监督方面的法律规定。
(二)地方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工作也是一种执法
根据我国宪法第一百条、地方组织法第四十三条和立法法第六十三条等的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而且,在实践中,较大的市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也将制定地方性法规作为其工作重点,由此我们通常也称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为“立法机关”。
其实,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也是一种执法。首先,立法法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限范围、制定程序等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工作必须依法进行,依法立法,要严格执行立法法,立法本身就是执法。其次,立法法在第六十四条明确规定,地方性法规主要就“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作出规定。也就是说,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执行法律和行政法规,即低层次的立法是为了执行高层次的法律。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说,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本身也是一种执法。
二、地方人大常委会在立法和监督工作中应当充分考虑宪法并开展依宪解释
(一)依宪解释是执行和适用法律的应有之义
执行和适用法律,首先必须理解和解释法律。而一般认为,法律解释的方法主要有: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比较解释、目的解释、合宪解释,以及偏重于社会效果的预测和社会目的的考量的社会学解释[2]。其中,合宪解释(笔者称之为“依宪解释”)是法律解释的基本方法,“合宪解释,系指以较高或宪法规范之意旨,而为解释位阶较低法规之方法而言。”[3]可见,执法者依照宪法来解释法律,间接地实施宪法,是执行和适用法律的应有之义和基本内容。
值得提及的是,国内有许多学者主张将理解与解释分开,认为执法者只能理解法律,而无权解释法律。其实,理解与解释是不可分的。正如著名的德国诠释学家伽达默尔所指出的:“解释不是一种在理解之后的偶尔附加的行为,正相反,理解总是解释,因而解释是理解的表现形式。”[4]马克思早在1842年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中就明确指出:“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5]
(二)地方人大常委会在开展立法和监督工作时也应解释法律并进行依宪解释
既然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执法机关,地方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工作和监督工作都要依法,都要执法,那么地方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工作和监督工作都要适用法律。其实,立法法第二条明确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修改和废止,适用本法。”监督法第二条第二款也明确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职权的程序,适用本法;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法律的规定。”
显然,地方人大常委会是通过执行和适用立法法和监督法等法律法规来开展立法和监督工作的,而立法法、监督法等法律法规是根据宪法制定的(例如立法法第一条明确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监督法第一条同样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所以地方人大常委会在开展立法和监督工作时理应开展依宪解释,根据宪法的有关规定和精神来理解、解释和适用立法法、监督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条款。
(三)地方人大常委会享有法律解释权与现行法律解释体制并不相悖
显然,地方人大常委会在立法和监督工作中开展依宪解释,依照宪法来解释立法法、监督法等法律,首先要承认地方人大常委会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享有解释权。这是否与我国现行宪法和立法法关于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解释的明文规定相矛盾呢?笔者认为,二者并不相悖。不能机械地理解和解释宪法的规定,否则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而至今仍在有效实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关于司法解释、行政解释和地方解释的规定以及人民法院组织法关于司法解释的规定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实践均有违宪之嫌。
我们可以认为,地方人大常委会在立法和监督工作中对法律的解释只是具体的、面向个案的应用性解释,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是抽象的、面向未来的立法性解释和最高解释。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律的应用性解释违背立法原意和精神,可以依法予以监督,并作出有关立法性解释。
(四)地方人大常委会进行依宪解释在我国有宪法依据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第五条第四款),“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序言)。显然,作为国家机关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和监督工作中执行和适用立法法和监督法等法律时也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进行依宪解释,根据宪法的基本精神来理解、解释和适用法律,保证宪法的实施。
三、在地方人大常委会工作的人员应该熟悉宪法并掌握依宪解释的基本方法
正因为地方人大常委会在立法和监督工作中应当充分考虑宪法并开展依宪解释,所以在地方人大常委会工作的人员首先应当熟悉宪法并掌握依宪解释的基本方法。2003年吴邦国委员长曾强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立法机关,在人大工作的同志,熟悉和精通宪法和法律知识至关重要。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也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的根本大法,大家务必模范遵守宪法,要成为熟悉宪法的专家。要先学习与工作直接有关的法律,熟悉议事规则和议事程序。立法也好,监督也好,熟悉宪法和有关法律是前提,不然的话,难以很好开展工作。”[6]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也不例外。
2008年12月,江苏省徐州市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徐州市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未经允许,提供或者公开他人的信息资料”,被网民们视为“禁止人肉搜索”,引起了很大争议。显然,立法者在立法时没有充分考虑并在条例中充分体现公民在宪法上的言论自由权和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这是引起争议的主要原因之一。
总之,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工作和监督工作(乃至人大及其常委会在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和人事任免权时)应有宪法思维,要充分考虑到宪法,开展依宪解释,依照宪法的规定和精神(特别是宪法中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以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精神)来理解、解释和适用相关法律条款,贯彻落实宪法的精神,实施宪法。这也要求在人大工作的人员不仅要熟悉和精通宪法和法律知识,而且还应懂得一些法律方法论,懂得法律适用的方法,掌握法律解释、依宪解释的基本方法。
注释:
[1]蔡定剑著:《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73、374、375页。
[2]参见杨仁寿著:《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3]杨仁寿著:《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页。
[4]【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著:《诠释学I:真理与方法》(修订译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18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6页。
[6]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2003年3月19日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