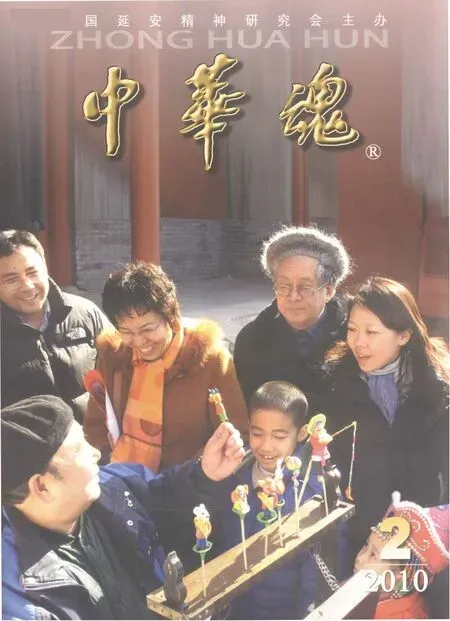我所知道的张鎏教授
2010-12-26李强
文/李强
我所知道的张鎏教授
张鎏教授是我国工业催化的先驱者和开拓者。他1920年生,1939年至1943年在西南联大化工系学习,1949年赴美留学,1950年获美国匹兹堡大学研究院化学工程硕士学位,后在美国堪萨斯大学任助教,同时攻读博士学位。朝鲜战争爆发后,他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和获得奖学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机遇,于1951年毅然乘船回国。回来后任唐山铁道学院副教授。1952年随着院系调整到天津大学化工系任教,直到2003年逝世。在5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张鎏教授成就斐然,除担任系和教研室的领导之外,主要精力都扑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上,开创性地编写了很多教材,亲自带领学生下厂实践,多年来带有多名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他1988年荣获天津大学金钥匙荣誉奖,1991年荣获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出版了由他主编的《英汉化工技术词典》这一化工行业的工具书。
张鎏教授桃李满天下,现在很多的工业催化界的名家都是他的弟子。我1981年入天津大学化工系催化专业读书,当然也就知道了我们这个专业的开山鼻祖张鎏教授。毕业两年后我又重返天津大学,有幸师从张鎏教授读硕士研究生,这就有了直接的接触。特别是进入写论文阶段后,由于泡在实验室的时间很多,跟其他老师在一起的时间也很多,对张鎏教授的事也就知道了一些。这其中,有亲闻的,也有亲历的。通过这一阶段的学习,张鎏教授的品德和作风深深地影响了我。他是对我的人生影响最深的人之一,也是第一个人。
淡泊名利
在对待金钱和物质待遇方面,张鎏教授的境界是极高的。在我上大学的那个时候,社会上还鲜有“先生”,不像现在“先生”满天飞,教师一般都被称为某老师,如王老师、李老师等,但是在天津大学里却有几位“先生”,那是对德高望重的名家的尊称。张鎏教授就被称为“张先生”。听说张先生好像是国家二级或者三级教授,工资很高,一般教师挣几十块钱的时候,他就能挣到200多了。有一次,教研室一位老师到天津大学附属的幼儿园(或学校)里去送孩子,回来跟我们说那里正在开一个会,见到张先生坐在主席台上,她觉得很奇怪,一打听,原来是张先生给幼儿园(或学校)捐了一笔款。她还说以前也经常有这样的事。
我的一位师兄写成一篇文章准备发表,在作者的位置留了白,拿来找张先生署名。由于论文是在张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中间又经过他亲自审阅和多次修改定稿,相当于两人合作完成,所以理当署他的名。这时我见张先生拿起笔,将自己的名字写在了后边。听这位师兄说,张先生总是这样,如果是多人合写的文章,他总是把自己的名字署在最后。
出于对老专家的爱护和尊敬,天津大学在校园里给“先生”们盖了一些独立的小楼,大约有十几套。其中就有张先生一套。但是听说他不要,还是住在筒子楼的两居室里,据说原因竟然是舍不得邻居们!住在简陋的筒子楼里,他自得其乐。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他家,他饶有兴味地展示自己的“宝贝”——几抽屉的音乐唱片和磁带。他甚至还跟年轻的教师比赛看谁烧蜂窝煤又好又省。当时他问一位年轻教师(我的师兄,当时正跟着张先生读博士),你一天烧几块煤,那位师兄很得意地说只烧四块,按说这已经是很不简单的了,结果张先生摇头说,你不行不行,我一天只烧三块!大家都乐了。笑声中充满对这位老专家的敬意。
严谨自律
张先生做事严谨,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听说他有一次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忘记带借阅证,坐下来才发现,他又要回去拿。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怎么忍心让这个谁都认识、每天在这里伏案的小老头再跑回去拿!所以坚持不让他回去。但张先生说不行。工作人员也没办法,只好由他。这样的事情只是偶尔发生,也可能就是这么一次,在学校就传开了。这不是沽名钓誉,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们的实验室在他家和图书馆之间,呈三角形。他每天去图书馆和从图书馆回家,都要先到实验室转一圈,看一看水、电、气的截门是否处于正常状态,检查实验进程,对正在做实验的学生叮嘱一番。几乎天天如此。这样做,一是为了安全,二是为了培养学生严谨的习惯和意识。对于实验室的财物状况,他全部装在心里。有一次,我做实验的过程中缺少一只热电偶,准备去领,需要导师签字。我就去图书馆找他。他说不用去领,咱们还有一个,我说没有了。他说有,应该就在哪个抽屉里呢。结果我回去仔细找,还真找到了!这件事让我很感羞愧。还有一次,为做实验我开列了一个需要用的物品清单,准备请他过目之后就去领或者买。他仔细看过,并一一询问这些物品我准备怎么用,然后告诉我哪些东西实验室还有,哪些东西可以用别的代替,哪些东西可以不用,而用其他的实验方法和技巧达到同样的目的。敲定之后他掏出自己的一个小本子,将准备领或者买的东西一一记在上面。原来,他有自己的一本账!在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同班有的同学活得是比较滋润的,往往能够用导师的科研经费为自己捞到好处,比如领或者买一些家庭用得上的东西,甚至以调研和采购的名义出去干私事或者出去玩,回来报销差旅费和补助。有的导师对此睁一眼闭一眼,甚至主动为学生提供机会。而这些,在张先生那里想都不要想!在我们进入写论文阶段后,记得是学生们每周都要跟张先生交流一次,学生汇报自己对于实验的想法和设计,张先生要针对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给出指导意见。他所给出的意见都写在一张纸上。可这是怎样的一张纸啊!密密麻麻地从天写到地,两边不留空白,字写到哪里,纸就止于哪里!所以这简直不能称其为纸,最多算是纸头!其“吝啬”竟至于此!可惜我现在一个这样的纸头都没有留下!否则我可以让我的孩子好好看看。
惜时如金
张先生惜时如金。他个子不高,是个白头发小老头,但精神矍铄,脊背挺得笔直,步履极快且有力。每天低头沉思快步走在去图书馆的路上。他每天早八点会准时到图书馆查阅资料、写书。有一次我在去图书馆的路上碰到他,向他请教一点问题。我们边走边谈,一直走到图书馆的三楼,结果上楼时我竟有点跟不上他的步伐!须知,那时他已经是接近70岁的人了!要毕业的时候,我们班里很多同学都请这位和蔼的、德高望重的小老头作答辩委员会主席,给自己的学业“长脸”。张先生都很高兴地答应下来。他问其中一位同学答辩时间是几点到几点。同学说是九点到十一点。张先生马上摇头,连说不行。他说,你们是九点到十一点,那么九点之前我做什么,十一点之后我又做什么?我八点到图书馆,屁股还没坐稳,你这里时间就到了;十一点后我到图书馆,刚看到一点东西马上又到吃饭时间了,这不行!改,要么八点到十点,要么十点到十二点!这段话我至今记忆深刻,不敢忘记。当时在场的同学个个都啧啧称叹。
关心青年的成长
2000年,天津大学召开“新世纪的化工与催化”专题讨论会,庆祝张鎏教授执教50周年暨工业催化学科创立30周年。这时张先生已经80岁。由于我无暇抽身赴会,于是在3月份给张先生写了封信。没想到,他竟然回复了,而且是工工整整、密密麻麻写了四页之多!过了大约一个月,我在反复研读张先生的信后,又给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他于当年6月初又给我回了一封信。现在这两封信成为我珍贵的纪念品。
在第一封信里,他说到90年代初,他要求自己所招的研究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给几个博士生开会讨论名利问题,说“名利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工作勤勤恳恳,不断进步创新,必有成果,多了就有名,利也会有,但不要去争名夺利。发表论文谁排第一、第二,不必争论。谁做的工作多,执笔撰写,就排第一。我既不动手去做实验,也不写文章,我的名字就排在最后。应该鼓励年轻人争上游。有人说很多主意、想法是我出的,可这是导师的责任。”信中他非常详细地介绍了他的一位在职博士生的情况。这位同学特别想像其他有的导师的学生一样,不付出很大努力就获得博士学位,对张先生多次的真诚帮助和严格要求非常不满,张先生为此十分苦恼,觉得这个学生“一晃就耽误了两年,太可惜了”,却又无可奈何。他把这些告诉我这个在高校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教师,想和我“讨论一下”。
在第二封信里,他在知道我准备去作科技副县长后,给我提出了极为详细的六点建议,叮嘱我要“将科学技术这一实实在在、摸得着看得见的实际东西在全县普及、推广,并见之于发展生产力,使老百姓得到实惠。”“首先要亲自下去做调查研究,摸清现状,思考和研究切实可行的实现‘科技兴县’的方案和措施,提出规划,有短期和长期的。”还要公之于众、统一认识和行动以取得成果。他告诫我,制订规划前要深入研究第一手材料,包括“全县各乡镇的历史、沿革,原有计划和存在的问题,还要现场亲自察看实情,走家串户,访问穷富老百姓,做记录。”要发动干部一起来做,“限期写出报告及建议。然后整理、分类、排队,根据上、中、下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合理化建议。”规划要通过集体讨论形成共识,要下发请大家提出意见,报批前还要反复。规划在实现过程中,要做好宣传工作,打通思想;分类指导,试点突破,切忌一刀切;不能强迫命令;要到一线蹲点,遇事与群众商量;遇重大问题和新情况,要及时总结,不能拖延,尤其农业生产,“错过农时,就很难挽回”。我在给他的信中曾提到由于不合领导胃口而在院校调整中被闲置的情况,对此,张先生批评了我,认为是我的工作方式和方法不当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