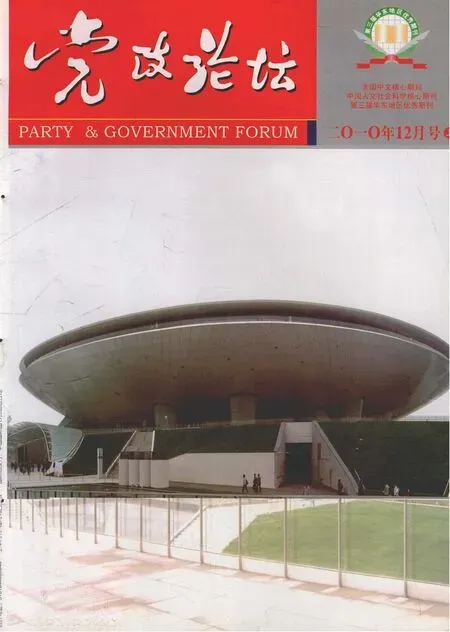在资本、国家与社会之间
——《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读后
2010-12-05严国萍
○严国萍
在资本、国家与社会之间
——《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读后
○严国萍
近来,深圳企业富士康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继19岁的马向前跳楼身亡后,另外10名 20岁上下的员工先后跳楼。短短时间内,富士康“十一连跳”,身陷跳楼门,舆论一时哗然:这到底只是偶然、孤立的事件,还是富士康这一“血汗工厂”的必然结果,责任到底在谁?
围绕上述事件,公众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既有冷静、理性的思考,也不乏简单化、情绪化的反应。
或许,争辩富士康的“十连跳”到底只是偶然、孤立的事件,还是富士康这一“血汗工厂”之必然结果,以及争论到底由谁来承担责任,其实意义不大。在当代中国,富士康事件并不是一个特例,偶尔浏览网络新闻,有关“血汗工厂”的劳工问题事件比比皆是,富士康事件不过是此类事件的一个缩影;在网络日益发达和开放的今天,也可以说富士康事件不过是此类事件的一个放大而已。或许,重要的是通过富士康事件,我们必须再次正面中国工人严酷的生态环境,进一步反思劳工问题,并真正找到解决中国劳工问题的办法。
不过,认真对待劳工问题,不能仅仅满足于一种简单化、情绪化的反应,而是需要我们把这一问题作为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来加以关注,并认真对待国内外学者的相关思考和研究。也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玛丽·E·加拉格尔(Mary Elizabeth Gallagher)的《全球化与与中国的劳工政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是一份需要我们仔细加以领会的思想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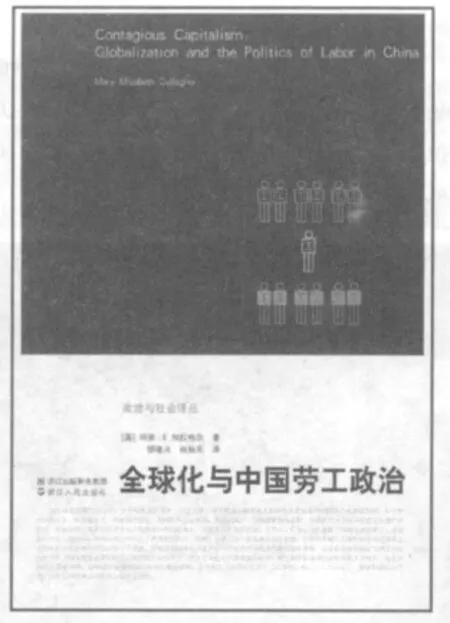
玛丽·E·加拉格尔(Mary Elizabeth Gallagher)2001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密歇根大学政治系。《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一书是她的博士论文的修订和扩展,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出版后获得了西方学术界的极高评价,其中,美刊《政治观察》(Perspectives on Politics)第6卷第1期(2008年3月号)玛格丽特?M.皮尔森的书评文章指出,玛丽·E·加拉格尔在全球化对中国的劳工阶层的影响方面作出了新的理解。玛丽·E·加拉格尔重新强调了劳工阶层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认为它是当前中国稳定和发展的关键,这改变了之前十多年研究中强调劳工阶层的社会地位降低导致其在国家的重要性下降的观点。
玛丽·E·加拉格尔对中国劳工政治的考察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一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在此期间,中国通过创办经济特区(1979—1984)、确立沿海发展战略(1984—1992)、发动国企改制(1992—)等改革开放措施,逐步消解了传统的经济体制遗产,确立了竞争自由化逻辑。在这个过程中,外国直接投资悄然而入、茁壮成长,外国企业的劳动实践也因此不断扩展到中国经济的其他部门。这大概就是她的原书名“传染的资本主义(Contagious Capitalism)”所要传达的意思吧。巧合的是,1978年改革开放的启动和实施,中国经由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全球化不断加速,中国不断融入全球化的过程,所以作者说,“在我实地调研期间,竞争、碎片化和全球化这样一些观念反复出现在不同的人当中”。这表明全球化的普及以及当代中国对全球化观念的分享和认同。
在上述背景下,玛丽·E·加拉格尔考察了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所造成的中国劳动关系的改变。在玛丽·E·加拉格尔看来,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施加于各地区和各公司的竞争压力,通过学习和示范效应,促使国有企业接受了资本主义的劳动实践;其次,外资企业还为较难开展的、政治上敏感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实验场所,并扩展到经济的其他部分;最后,外国投资部门的存在还导致了意识形态的重构,模糊了国内现有的私有制和公有制企业之间的区分,使它们都成为了民族主义框架中具有竞争力的中国产业。在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影响下,劳动实践在企业层面成功地实现了向资本主义劳动实践的转型,然而,对这一转型所急需的解毒剂量,也即缓解资本主义劳动实践过渡性的国家规制和法律制度,以及代表工人的有效组织,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
不过,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劳工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故事,并不是一个市场战胜社会主义,以及通过资本主义解放中国工人的传说。中国国家继续抵制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自由化。试图通过强大的国家主导的发展和对劳工的威权主义的控制,结合对外国直接投资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依赖,来创造发展奇迹。在这一制度下,法律制度并没有很好的保护工人的权利,工会组织也没有有效地履行代表劳工利益的职责。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劳工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故事,也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奴役中国劳工的故事。通过为弱者立法,市场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和基于契约的法律框架对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关系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
接下来的故事主要围绕“资本-劳动-国家”这一三重结构展开,故事似乎也很清楚:外国直接投资代表资本逻辑,它以利润最大化追求为最高目的,为此,它无视工人的健康、生命和安全,无情地推进它的事业(其具体表现即管理方一味强调管理自主和劳动实践的灵活性),以至工人斥责其“无人性、肮脏”。而“劳动”显然也不会束手就擒,英国经济史家卡尔·波兰尼指出,市场的无情扩张必然会引发保护性的反向运动。③因此,劳工必定会通过抗议、罢工等形式来反抗市场暴政,以避免劳工沉陷于无情的利润法则。当然,“磨坊中的撒旦”还得依靠国家的力量来驯服,为此,国家必须制定法律法规来确保劳工的基本权利,并通过工会组织提升工人的组织化利益,以此规制市场,保护劳工(如颁布劳动法,要求企业成立工会等)。
当然,故事可能要比这复杂和精彩得多。在我看来,玛丽·E·加拉格尔著作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她对“资本-劳动-国家”三者之间复杂关系的把握和揭示。在玛丽·E·加拉格尔的笔下,国家显然并非铁板一快。国家包含着数量庞大的机构和人员,交织着中央和地方的博弈,改革派与保守派的较量。所以,玛丽·E·加拉格尔写道,由于政商之间的和谐关系,持有发展主义观的地方政府缺乏管理意愿,企业管理层或老板完全决定着劳动实践。而由于保守力量的阻碍,劳动改革进展缓慢,改革前进两步,然后退后一步。而“资本”对“国家”、“劳动”的抵制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就成立工会而言,由于社会主义的历史遗产,国有企业建立工会的比率最高,合资企业和非华侨企业主的外资企业也愿意建立工会,华侨投资者则不愿意建立工会。(P99)可以说,“资本-劳动-国家”内部都存在缝隙,且与任何其他一方的关系都是复杂的,充满变数的。
回到前述关于富士康事件的讨论。从根本上来说,富士康事件以及类似事件的发生,其根源在于中国的发展主义,一如玛丽·E·加拉格尔所说,在发展主义模式下,国家主导经济的发展,以经济增长作为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在这一发展模式下,法律制度并没有很好地保护工人的权利,工会组织也没有有效地履行代表劳工利益的职责。因此,要真正解决劳工问题,政府必须转型,从以经济增长作为政治合法性主要来源的政府模式,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不过,发展主义模式恐难在一夜之间进行转变,在通往政府转型的漫长过程中,中国劳工的命运恐怕还得在“资本-劳动-国家”三者之间的鏖战中缓慢前行,社会的保卫战必将是一场漫长的战斗!
(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浙江省科学发展观与浙江发展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谭 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