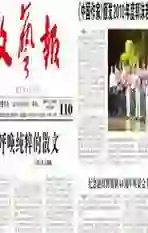商务印书馆与儿童文学——中国儿童文化产业早期实践的启示
2010-11-25陈恩黎
陈恩黎
随着文化产业日益被经济发达国家视为21世纪的“黄金产业”,儿童文化产业更是被寄予了巨大的期望:“北美的孩子每年要花费1150亿美元……在孩子们身上有着无限商机。如果忽略了儿童对经济的影响,我们失去的不仅是对这个上升最快的消费市场的把握,还包括未来数十年商业发展的判断。”(安妮·萨瑟兰 贝思·汤普森,《儿童经济》)于是,从“天线宝宝”到“哈利·波特”,从“变形金刚”到“哆啦A梦”,一个又一个席卷全球的儿童产业富矿被成功开发出来。这对正在蓄势待发又尚显薄弱的中国儿童文化产业来说,既提供了一个令人遐想的远景又构成了一种必须超越的压力。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创建富有生命力的本土儿童文化产业?这个命题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操作层面都值得我们长久关注。
由于中国百年现代化历程的曲折与断续性,当代的诸多文化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需要我们回到上个世纪的历史现场才能理清其内在的演进思路、困境以及可能的解决途径,中国儿童文化产业也同样具有某种历史的积淀和经验。
1904年,商务印书馆以一套在中国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小学教科书为基点实现了从印刷业到出版业的飞越,并由此成为近现代中国影响最深广的图书出版企业。商务的运作思路和它的成功正应和了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观点,“启蒙同时也是一项利润巨大的生意”(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这家深度介入20世纪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民营出版机构在其起步之初敏锐把握了新兴的商业缺口——学校和儿童市场,这一历史记忆可以说为今天的中国儿童文化产业研究提供了值得借鉴与深入思考的早期实践。
商业利益与现代性诉求
虽然中国早在11世纪就发明了活字印刷,但一直到19世纪前叶,中国使用最为广泛的依旧是已有一千多年历史的雕版印刷,导致传统中国的书籍阅读和思想传播只能局限于士大夫阶层,而不能扩展到经济能力和阅读能力均贫弱的平民阶层。
1897年,四个中国基督徒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和高凤池带着他们从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所创办的“美华书馆”(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Holy Classic Book Establishment)所学来的印刷技术在上海租界内创立了自己的印刷厂,取名为“商务印书馆”(Commercial Press)。第四年,他们又购入日资“修文书馆”的印刷机器,令印书馆的印刷力量得到及时扩充,成为当时上海拥有最先进设备的国人印刷所。
无论是器物层面还是精神层面,商务印书馆的诞生都可以被视为晚清社会近半个世纪以来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一个典型结果。同时,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以及投资者之间或血缘或姻亲的联结纽带则呈现了传统中国源远流长的家族文化力量。因此,更确切地说,透过商务的诞生,我们似乎看到晚清中国在经历“西学东渐”的洗礼之后开始寻找本土文化现代化的出路,而其背后的直接推动力则源自世俗的经济诉求。
虽然已经具备当时编撰教科书的诸多有利条件,但是商务依旧经历了在“启蒙与生意”、“引导与迎合”、“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等一系列彼此依赖又彼此对抗的因素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的艰难磨合来确立自己的文化理念与商业品牌。
从商务诞生到初期的发展,外来技术、资金乃至文化一直是其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当年的日本元素为《最新教科书》的高质量铺垫了扎实的基础,而商务其怀抱世界又不失自我的格局则别有一番勇气和承担。日本的小谷和长尾提出,“教科书插图极为重要,须请第一流画家绘制。这意见受到商务印书馆当局高度重视。”(王益,《中日出版印刷文化的交流和商务印书馆》)虽然日本的出版技术与理念在总体上均领先于中国许多,但商务编译所的中国学者并不曾失去自信与独立,正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双向交流为商务的《最新教科书》带来富有生命力的本土气息。
商务教科书编撰工作的推动力之一是1902年清廷颁布的学堂章程,但是1904年1月(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清政府颁布的“癸卯学制”却给这项工作的前景抹上浓重的阴影。在面对外部压力时,商务内部的不同意见颇能反映出版社这一文化实体其本质的矛盾性,如果经济利益与文化责任不能兼而得之,孰为先?幸运的是,当时孱弱的清政府已失去对民间的掌控,商务冒险按照自己教育理念出版的第一本《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获得学校与读者的热烈回应,“未及五六日而已销完四千部。现拟再版矣”(汪家熔选注,《蒋维乔日记选》)。随着商务国文教科书的行销全国,政府的癸卯学制居然在无形之中被废弃。而不久以前商务所面临的那种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内在紧张戏剧性地成为一种鼓舞人心的双赢。
一间民间出版机构成功对抗了政府意志,开创出中国教育的现代气象,这不能不说是在特殊时代语境下商务印书馆所创造的一个很难复制的文化与商业奇迹。
强烈的“产业”意识
1904年伊始,商务创办了《东方杂志》。在创刊号上,《初等小学堂国文教科书》的广告赫然在目,预示了商务将以改造成人教养儿童的方式为中介全面塑造新都市儿童文化的雄心,而其实践的策略便是对教育的多层次、全方位的深度介入。
1905年7月,商务设立小学师范讲习所;同年底,续办第二届小学师范讲习所,两届讲习所共毕业小学教师80名;1910年7月,创立师范讲习社,编印师范讲义13种;1918年,第三届师范讲习社毕业,人数为580余人……无疑,不断增多的从讲习所毕业的小学教师将成为商务《最新教科书》的有力传播者和使用者。与此同时,商务致力于创办一系列教育实体来扩大和提升社会影响力。创办于1905年的尚公小学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所学校。
除了自上而下拓展教科书的受众群体外,商务还在1909年创办《教育杂志》,成功营造出多元教育思潮并争的大众言论空间。如,1913年第5卷第5号刊发了《编辑小学教科书商榷书》,就如何改进教科书中的宗旨、程度、形式、时间分配和教授书等五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向社会各界征询意见。这种向大众打开专业门户、鼓励不同意见的编辑思路,不但赋予了商务各种教育实践、实验的理论合法性,而且最大程度吸引了新兴都市文化阶层对商务以及它所推行的文化产品的关注与认同。
以教科书为起点,商务对儿童的关注从课堂教学延伸到日常生活中,出版了许多在当时中国均极具开创性的儿童课外读物:1906年创刊《儿童教育画》;从1909年开始,共出版《童话》丛书102种; 1911年创办《少年杂志》;1914年创办《学生杂志》;1922年创办《儿童世界》《儿童画报》;1923年出版百科小丛书;1937年出版《幼童文库》和《小学生文库》……在出版时,编辑们既重视儿童的年龄、学科的分类、阅读的目的、图书的价格等因素构成儿童读物的差异性,同时也始终与教科书的内容、进度以及精神主旨等各方面保持紧密的衔接,呈现出市场细分与整合的专业策略。
对商务而言,儿童文化市场的空间有着多种向度的延展区域,它不仅意味着精神启蒙还意味着提供一系列有益或无害的娱乐。除了在《儿童世界》《少年杂志》等各种刊物上开辟笑话、漫画、游戏等栏目外,商务还出版了《活动影戏》二辑12种、《活动变形人》《儿童游戏丛书》《儿童游艺丛书》等读物。随着图书的出版,商务还适时跟进儿童玩具、教学器具等物品的制作,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也正是这种敏感使得商务在1917年开始进入电影业,成立“活动影戏部”。不久,商务拍摄了《盲童教育》《慈善教育》《养真幼稚园》《女子体育观》《技击大观》《驱灭蚊蝇》《养蚕》等一系列教育片,进一步呼应了教科书的内容与商务的新教育理念;1919年,商务制造了第一台中文打字机,并同时拍摄了中国第一部动画广告片《舒震东华文打字机》……通过电影这一新型媒介再次实践了启蒙、生意、娱乐之间的互动与互补。
成人是必经“通道”
所有这些围绕着教科书而展开的文化产业活动“既抓住都市市场的新部分——孩子(以及他们的母亲),同时教程外的出版物也早就超越了学校体系的局限,进入了因为谋生而失学的都市成人世界中”(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商务以新教育为核心所建造的现代性景观成功打破了儿童-成人之间某种天然的文化隔阂,这正是商务定位儿童文化的独特之处。
商务在成人文化领域内的专业与前沿地位对它所从事的儿童文化产业以多层面的丰厚回报。首先是商务的儿童文化产业始终获得深广的文化底蕴的支撑,其标志之一便是商务从事儿童文化产业的编辑人员的学养背景以及抱负,如:“编写教科书的一批人像庄俞等,就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杜亚泉可以与陈独秀进行中西文化的论战,也是当时学者型的编辑和思想型的学者。”(王建辉,《出版与近代文明》)“童话丛书”的开创者孙毓修是目录版本学家、翻译家和藏书家;《儿童世界》的创办者郑振铎后成为中国著名学者、文学史家;“儿童教育画”丛刊创办者伍联德在1926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大型综合性画报——《良友》;《儿童世界》美术编辑万籁鸣依托商务提供的平台开创了中国动画电影;青年茅盾曾担任孙毓修的助手,撰写了《大槐国》《千匹绢》等17本童话……
可以这么说,所有在商务从事与儿童文化产业相关的人员都不是固守“儿童”这一领地的“专业”人员,他们之所以加入这项工作也怀有不同的目标或抱负:对张元济、高梦旦、杜亚泉等知识分子而言,投身儿童文化产业不仅仅是为了开拓一个全新的市场,更是晚清民初中国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启蒙诉求;对郑振铎、茅盾等年轻人来说,在商务编辑儿童读物不但解决了自身的谋生需要而且获得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上述从业人员的非“儿童”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商务的儿童文化产业始终具有成人-儿童的运作思路和精神气质。为了让成人在最短时间里成为《儿童世界》的积极订阅者和推荐者,主编郑振铎还充分利用商务多元化的杂志平台,分别向《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学生杂志》等订户赠送非卖品《儿童世界》创刊号。在这种有效运用成人-儿童的广告策略中,《儿童世界》以其最大可能性获得了成人世界的关注。
通过成人向儿童传达商务新教育的理想可以说是《儿童世界》一个非常关键的思路。在《〈儿童世界〉宣言》一文中,郑振铎向父母和教师们全面陈述了刊物的宗旨、内容分类、资料来源、处理资料的方法以及适宜的儿童读者年龄,并且还援引西方儿童文学、儿童心理学的观点来消除普遍存在于当时中国父母和教师们心中对童话的疑虑,实现了对成人的儿童观乃至儿童文学观的启蒙。《儿童世界》大规模发行后,编辑与成人教育者之间的互动联系则以刊登读者来信和编辑回复的方式得以不断加强。
在《儿童世界》第二卷第十三期上的《第三卷本志》中,郑振铎写道:“一方面固是力求适应我们的儿童的一切需要,在别一方面却决不迎合现在社会的——儿童的与儿童父母的——心理。我们深觉得我们的工作,决不应该‘迎合儿童的劣等嗜好,与一般家庭的旧习惯,而应当本着我们的理想,种下新的形象,新的儿童生活的种子,在儿童乃至儿童父母的心里……”而在第三卷第十二期上,郑振铎更是直接回应了一个叫周得寿的读者的意见:“至于神秘一层,更不必故意避免。儿童是充满了幻想的。儿童文学中决不能——也不必——完全除掉一切神秘的原始气味。” 就如他在1925年发表于《小说月报》上的《〈列那狐的历史〉译序》中写道的那样:“编译儿童书而处处要顾全‘道德,是要失掉许多文学的趣味的。” 可见,成人-儿童模式不但在扩大儿童文化产品的影响力、提升儿童文化产品的质量等方面均有重要作用外,而且还使儿童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泛道德化”的僵硬面具,获得了一种美学上的自由。
虽然由于时代的变迁,商务印书馆在1958年以后退出儿童图书出版领域,但是它在20世纪前半期所进行的儿童文化产业实践所达到的高度与产生的影响力可以说至今没有被超越。当时间进入21世纪,中国儿童文化产业所置身的环境与上个世纪初有着某种相似性:西方化与本土化、教育与娱乐、儿童与成人,这些因素之间的天然对抗性依旧存在。所不同的是,一个新的媒介时代正在来临,它所产生的“娱乐至死”的文化令人忧虑。今天的中国出版业有没有像上个世纪的商务那样在危机中创造出西方化与本土化、教育与娱乐、儿童与成人等因素之间既对立又保持独立、张力及互补性的儿童文化产业的可能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