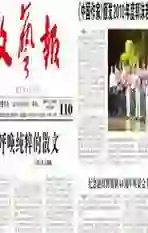现实的确立与命名的真实——评贾兴安长篇小说《县长们》
2010-11-25刘向东
刘向东
“不是现实中发生了、我们看见了,再高明的小说家编造出来都非常困难”,长篇小说《县长们》的作者贾兴安如是说。《县长们》表面并不复杂,内里绝不简单,汇聚了复杂的经验和情感,有着丰富的层次,反映出不同的关注点,以伦理的高度和响当当的风骨、富有弹性的肌质,呈现出超乎一般的能量;它看似乡土,却是现代艺术,具有特立的结构、新颖的叙述、鲜明的形式个性。其伦理的高度和文体试验的成果,其感动的能力和关怀的能力,均不可多得。
贾兴安在谈论《县长们》的来龙去脉时,提及他到县里挂职的经历:“我当时并不是冲着写作去挂职的,而是跟着一批年轻副处级干部去当县长的,‘挂好了可以留在县里‘当官。所以我必须把‘作家的身份忘了,便一门心思当起了县长,实实在在当了个‘县官儿……天天跟县委、县政府一帮领导们‘泡在一起。”由此可见,《县长们》是有真实写作背景的,或者说,是有生活“原型”的,起码作者与作品中的挂职副县长角色重叠,或感同身受。一旦真的有人把这部长篇当做写实作品看,关心起“县长们”的原型是怎样的,那就大体意味着,与其说是作家塑造了“县长们”的形象,不如说是主人公塑造了自身。作品中的“县长们”是被创造的人物,不再等同于任何人。原型是一个起因,一个线索,最初可能帮助了作家,当作家写作时,逐渐把当过“县长”的身份忘了,作品完成了,原型就没了。《县长们》触及高度复杂的县官生活的各个方面,人物各有各的内心和面孔,经过命名,如同星宿,一一对应着人的命运,这时,命名的真实成为最高的真实,它超越了具体的某个县域而存在,是语言中的现实,是作家笔下确立的现实。
贾兴安对“县长们”极其真实、生动的叙述,尤其是把那些“本来很难摆到桌面上”但又“不得不那样做”的事情摆到我们面前,令人为之会心,有时心里也有“咯噔咯噔”的感觉。“黄副县长(对新来的县长)认真地说:这里的老百姓没见过大官,你握一下他们的手,他们会激动好几天,会舍不得洗你握过的手,他们会用你握过的手,再去村里握别人的手,说这是县长握过的手,握了他的手,就等于握了你县长的手。”因为大多数百姓对“县长们”的经验是间接的、有限的,《县长们》对“县长们”的零距离才有了意义。
贾兴安以挂职副县长的身份广泛地参与到“县长们”的工作、生活里,深入到排解重大事件等应变操作之中,拥有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知识领域。他用第一手资料构筑了自己的经验,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有虚构,但不是乔装或伪装的世界;他在细节和经验中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真实感,令作品推进过程中的逻辑性、可信度、经验的真实性,都不容置疑,作品的血肉、精神和它的外衣非常合身,整体精气神儿就自然而然。
但在从生活向艺术转化的过程中,更重要的还在于心灵质地。如果说,筑造心灵世界的材料确是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给贾兴安的心灵注入了力量和勇气的是活生生的“县长们”,那么反过来,对“县长们”的把握却是依靠了作家的灵魂,而不是由“县长们”本身型塑了我们的理解。我们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彩、多变、多元的时代。历史性的变动、社会构成的庞杂,令人应接不暇,难以把握和理解,并不是身处其中想“看见”就能看见,“怎样看见”,更有赖深深扎根于自己的时代,认真研究、调查这个时代,并深刻地见证人心万象及其细微的变化。
在从生活向艺术的转化过程中,贾兴安的文体试验,其对形式追求的信心和能力,同样值得格外称道。他顽强地保持了他的劲头,艺术地、成功地驾驭了“县长们”。小说家的三个基本可能,或讲述一个故事,或描写一个故事,或思考一个故事,贾兴安在《县长们》中都尝试了,却并不显得繁缛、冗长。因为有要紧的话说,就不必不停地罗嗦,故事简练而饱满,利索却又充实。
全书呈收缩结构—— “春、夏、秋、冬”四章,每章框定在一个季节里的某一天,每一天又由AB两条线索呈S形交叉递进。会看戏的人当能看出,犹如当年梅兰芳在小小舞台上走S形线路以扩展运动空间。两条线扭结着穿过了《县长们》:一条是县长们(还有书记们)的生存状态,为结构主体,形成基本格局;另一条是主人公、挂职副县长乔志青的所见所闻、所做所为,先是在主体之外,最终进入了主体。如此结构方式,既是生活的启示,更是层次的需要。窃以为启示直接来自作家的挂职,他既是在场者,是主角,有时又是“旁观者”、“局外人”。把故事收缩到极点,不是贾兴安的发现,把四季压缩为四天,却是新的发明。故事收缩至极,衍生出更大的放射性,变成了自由出入的基地。四季为年,在冷暖轮回之中,日复一日,每一个日子又都是新的。“县长们”到底经历、经受着什么?有着怎样的担当、作为以及怎样的困惑与危机?贾兴安给出的是变量,是乘法而不是减法、除法。
《县长们》中一再出现了“筷子”:“再直的筷子,插到水里也会变弯的!”这是短命冯县长的口头禅,在他成为植物人之后,还以短信的方式鬼使神差地发到了乔志青的手机上,令乔县长恍兮惚兮。筷子的隐喻,连同特立的点线结构方式,可能远远超出了贾兴安最初的意图。但愿筷子还是筷子,弯曲的只是它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