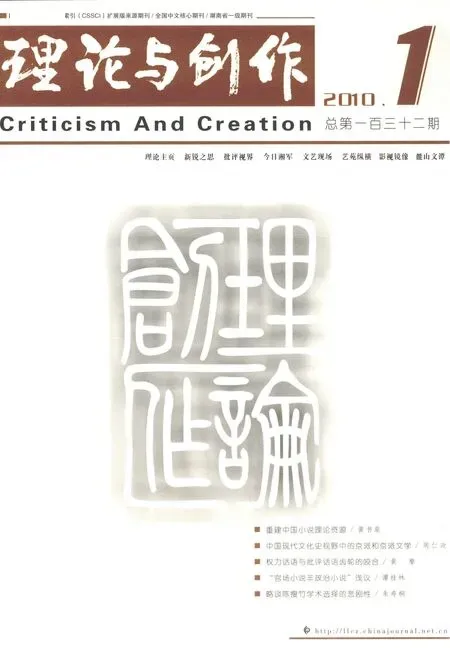媒介化环境的形成与小说创作空间
2010-11-25刘茂华
■ 刘茂华
传统媒介的不断改革和完善、新兴媒介的兴起,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正如尼葛洛庞帝所言:“人类的学习方式、工作方式、娱乐方式,一句话,人类的生存方式都变成了数字化”。①数字化时代,文化领域中呈现出日益明显的全球一体化趋势,个体的能动性、参与性大大提高。数字技术以其强大的科技力量使得新媒介将人们包围在信息世界之中,人们可接受的信息资源大为拓宽。媒介的改革与转型在1990年代中期取得了成功,中国各类形式的媒体因此高度发展,为媒介化环境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和思想上的基础。媒介化环境,换一种说法又称为现代媒介语境,这种全新的媒介语境已经深刻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思维。媒介化环境如何形成,形成之后的现代媒介语境又怎样渗入到小说作家的创作思维,需要从理论与创作实际两个层面作一番论述。
一、新的媒介语境渗入小说创作思维
马克思描述过:“电报已经把整个欧洲变成了一个证券交易所;铁路和轮船已经把交通和交换扩大了一百倍。”②这个描述形象传神,生动地说明了科技的发展不仅仅影响经济,同时影响到文化,给人类的相互交往也带来了重大变革,可称之为“交往革命”。因媒介发生了革命式的改变,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和速度等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需要强调的是,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使信息资源在经济、文化、生产中占有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许多国家已经进入了信息社会。这是现代社会交往与革新的物质基础,以高科技为物质基础的传播媒介填补了人类的许多缺陷,让人类具有了最为完善的获取信息的手段。所以,麦克卢汉说,在机械时代,我们完成了身体在空间范围内的延伸。今天,经过了一个世纪的电力技术发展之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了延伸,以至于能拥抱全球。……创造性的认识过程将会在群体中和总体上得到延伸,并进入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正像我们的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凭借各种媒介而得以延伸一样。③尤其要看到电子媒介的巨大能量,电子媒介大大拓展了人类的视野,为人类获取信息提供了最为方便的通道和工具。互联网因此而诞生,全球化的趋势出现,人类可以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领略世界各地的人情风俗、信息。所以,人们现在对于麦克卢汉“媒介即人的延伸”理论深有感触。当媒介作为工具被人们使用时,人们发现了媒介沟通人类信息的巨大作用,同时还发现了媒介有推动经济发展的功能。媒介把人们团结在周围时,人们也开始离不开媒介了,一种依赖关系在人和媒介之间形成了。人们离不开媒介,一方面是需要获取信息,还需要从媒介那里得到娱乐,得到经济利益等等。人们获取信息的感观在迅速延伸的同时也跟着媒介变化,人们甚至认为媒介用信息构造的世界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世界,人与媒介形成了无法脱离的依赖关系时也被媒介牵着鼻子走。媒介信息所组成的世界已经从客观世界中分了出来,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空间,这个空间可以称之为媒介化环境的一个部分,这个空间的独立自主性还体现为一套自行运行的机制。媒介会按照自己的运行方式去影响世界,包括作家的创作,这也是一种为己所需的原则。
从现在人们的生活现状来看,媒介化社会里,信息传播所构成的环境越来越成为了人们生活其中的必要环境,以至于人们就认为这是现实中真实环境,传播学将这种环境称之为信息环境。信息环境已从现实世界或客观环境中独立出来,按照为己所需的原则运作,对人们起着提示功能,“通过不断的信息流,构筑现代信息环境,作用于人们的认识,引导舆论。现代人已日益浸润在媒介信息的汪洋大海中,人们眼中的现实,是媒介有意无意地营造出来的媒介现实。”④这也就是传播学研究中美国的新闻工作者李普曼所提出的“拟态环境”。他说:“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到一个共同的因素,这就是在人与他的环境之间插入了一个拟态环境。他的行为是对拟态环境的反应。但是,正因为这种反应是实际的行为,所以它的结果并不作用于刺激引发了行为的拟态环境,而是作用于行为实际发生的现实环境。”⑤李普曼较早意识到了“信息环境”的存在问题,他的着眼点是现代社会日益复杂,人所能经过的地方或者说接触到的地方总归是有限的。要了解外界信息就要通过传播媒介。人们已经习惯了媒介所提供的信息,至于信息的来源如何,信息背后还隐藏着什么,人们对于这些则懒得去管,渐渐的把这种“拟态环境”当成了现实生活中的真真切切的环境。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论”也具体讨论过“信息环境”的相关问题。他认为,媒介所造成的信息环境同人们表现自己行为时所处的自然环境同样重要,当媒介发生变化时,它所构造的世界也会发生变化,人们因依赖媒介,就会跟着信息世界的变化而变化,深受媒介构造的一种生活中的“情景”,人其实就生活在这种情境之中,无法脱身。⑥日本学者藤竹晓沿着李普曼的思路提出了“信息环境的环境化”问题,意思是说拟态的环境具有一种让人们难以分清楚真实与否的障碍作用,人们过于依赖信息的存在,过于相信媒介无所不能的力量,这种拟态环境会影响到人们对于客观真实世界的看法,甚至于主导人们的思想观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信息环境也会被环境化。⑦传播学者的理论观点发展到了波德里亚这里又出现了新的内容,波德里亚认为,后现代社会就是一个大众传媒进行符号过剩的生产的时代,由媒介信息所构造的社会图景是一个符号的图景,这个符号图景也就是上文所提到的传播学者所称呼的信息环境。波德里亚说:“大众传媒的真相就是:它们的功能是对世界的特殊、唯一、只叙述事件的特性进行中性化,代之以一个配备了多种相互同质、互为意义并互相参照的传媒的宇宙。在此范围内,它们互相成为内容——而这便是消费社会的总体‘信息’。”在这一过程中,媒介通过它的运作程序“窃取”现实代之以虚拟的“新现实”,“在大众传播中,这种程序攫取了现实的力量:后者因为由媒介本身物化了的这种范例的新现实而被取消、被窃取。”⑧
我们再将上述的传播学理论用于分析文学现象。从信息生产的流程来看,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组成现实世界,还有一个由信息组成的信息世界,现实世界与信息世界之间通过媒介——信息的符号进行信息的传递和反馈。媒介以新闻选择原则从现实世界中取材经过解码和汇编,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描述的:“由大众传播形成的拷贝世界信息环境,是现代社会中人们无法逃避的生活世界,它同感性世界并驾齐驱,成为决定人们生活情感、生活欲望、期待、认知和态度的两大环境世界。”⑨很显然,作为现代社会成员的作家或写作者同样无法逃脱这种存在现实。可见,无论是现实存在还是理论研究都在提醒我们:文学活动中的“世界”和“作家”两大要素的关系和“世界-作家”的过程已不再像传统理论描述的那么简单了,而需要通过当今的事实进行重释。媒介化环境中,作家面对两个世界并且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即现实世界和信息世界,这使文学活动的“世界”、“作家”两大要素之间形成了既各自独立又相互交织的两种关系。务必理解这么一个现实:现代社会中的一些作家越来越多地通过媒介直接面对信息世界,就如同很多小说家每天起床所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电脑,察看新闻网站,看看这个世界昨天和今天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或者稀奇古怪的小事,这个信息世界以前是附着于现实世界之上的,而现在依附于媒介。媒介按照媒介场的规则进行符号生产,使信息世界独立出来,并将包括作家在内的现代人包围其中。作家往往通过媒介了解客观世界,对世界的认知活动直接作用于信息环境,与信息世界中的事物形成直接体验关系,而且主要与客观世界形成间接体验关系。这里需要辨析的是,关于历史题材等的文学创作在历史上很久以前就出现了,这些题材的创作都是作家间接体验世界后的产物。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时期的作家会像现在媒介化时代的作家这样依赖于间接体验的方式,历史上的作家也从未像今天的作家这样生活在一个复杂化和信息爆炸的时代。正如李普曼说的那样,今天人的实际活动范围和精力又是有限的,人们不可能与如此复杂和信息纷繁的外部世界保持完全的经验性接触。这样,如果不通过媒介间接了解和体验外部世界,久而久之就会与外部世界拉开距离,产生隔膜。与此同时,报刊、影视、网络等媒介又为作家创造了足不出户就能掌握天下事的条件。因此,在媒介化时代以间接体验的方式进行文学创作已不仅是可能的问题,而且更是必然的问题。这里的以间接体验的方式进行文学创作大体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作家通过传媒了解过去,体验历史,这就是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二是作家通过传媒了解超越直接感知范围之外的世界,间接体验当下的现实生活。随着现代传媒影响的进一步增加,从信息世界中获取材料、获得创作灵感的现象将会越来越普遍。这样,另外一种意想不到的情形产生了:从我们所处的现实生活来看,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已经被信息环境包围,在不知不觉中与现实环境拉开了距离,作家单纯直接从现实世界中获取创作材料、直接体验生活的传统方式被打破,许多作家更多的是依赖于各类媒体提供的信息。这种过于绝对化的看法虽然有些偏颇,但能够说明当下许多作家的生活体验状况。当然,现实中很多作家仍很看重对现实世界的直接体验,并试图努力穿越大众媒体的包围,走向现实世界。
从精神、思想层面来看,媒介对客观世界的报道不断更新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及其意识形态,包括对文学写作内部的渗透和影响。陈平原认为:“在文学创作中,报章等大众传媒不仅仅是工具,而是已深深嵌入写作者的思维与表达。”⑩从技术层面看,媒介在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手段和更广泛空间的同时,对文学创作方式和思维方式产生了革命性变化。比如,电脑和互联网的出现使文学创作和研究发生重大甚至革命性的变化。电脑写作不仅是作者的书写方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方式和思维方式。事实上,媒介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不仅影响文学媒介、体裁等外在形式,更在深入到写作思维、写作动机等文学的里层之中。写作信息载体和写作工具的转变带来写作思维的转变。麦克卢汉曾重点研究了广播电视等电子传播工具对人的“篡改”及人类的社会作用,他得出结论,媒介并非工具,“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地、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现代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正在改变文明人受视觉支配的状况,电视不仅扩张了人类的视觉和听觉,而且由于强烈的现场感和接触感而扩展了人类的触觉。传播样式的变化改变了人们的感觉,同时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在麦克卢汉看来,媒介对于人类社会的最大意义,主要不是它作为载体所承载的具体信息,而是它本身作为“人体的延伸”所带来的人类感知世界、认识世界、把握世界方式的改变以及由于这种改变而带来的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一种新媒介的产生,无疑会引起社会结构及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变化。[11]传播载体和表达手段的不同,其写作规律和要求也相应发生变化。以传统的三大媒体报纸、广播和电视为例,报纸以纸张为载体,主要技术是印刷,以文字、图片、版面设计、色彩为表达手段,是供人们阅读的,其写作完全是“为读而写”,要求经得起细读和反复琢磨;广播以电波为载体,表达手段是音响,由自然界的声音、人为的声音,主要是供人听的,其写作是“为听而写”;电视以电波为载体,以声像、文字为表达手段,主要是供人看和听的,其写作就是“为看和听而写”。先锋小说在1990年代中后期和新世纪有图像转向的趋势,就是影视媒体对于作家的创作思维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消费已经越来越城市化,作为文化消费之一的文学消费,其消费群体主要生活在城市,他们生活在媒介全天候的“轰炸”之中,看到的、听到的几乎全是消费性的商品、消费性的广告。这些东西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也改变了他们的审美趣味。有学者认为:“他们更喜欢在都市的奇异故事与刺激的场面中寻求感觉与情感的通道;他们更倾向于欣赏节奏欢快,情节突变,充满荒诞、惊险场面的‘艺术品’。”[12]
先锋小说、晚生代小说以及1990年代以来女性写的小说都有图像叙事的倾向,这种倾向也是新世纪文学发展的一种倾向。图像叙事不仅是一种手段,一种视角,而且它所呈现出来的视觉思维也越来越多地影响了传统文学的思维模式。正如电影、电视、网络视频的银幕、荧屏、界面中的镜头是对情景的视觉切割和组合,小说中由文字构成的叙述场景也成为文字符号所构建出来的视觉意象,它们在读者的想象、联想下重新生成一连串清晰的画面形象,而这正是图像叙事的思维模式。
现代社会读者的阅读、审美习惯会对作家提出要求,其中表现技巧的视觉化,也就是图像化趋势成为“后新时期”文学的重要特征。高行健很早就从读者欣赏习惯的角度对当代小说视觉化提出了意见,“他们对冗长的环境描写和静态的叙述感到烦腻,希望文学作品多提供活的画面,也就是一个个相互连接的镜头。他们对无止境的、烦琐的心理分析也不耐烦,要求作者更为准确地抓住人物瞬间的精神活动。”[13]比如卫慧《我的禅》,主要描述主人公CoCo与美国男子Muju的异国恋情,其中夹杂着CoCo与女友朱纱的友情。严格说,小说并没有故事情节,小说中有主人公活动的场所、风景、生活的片段,阅读起来给人感觉像似在电影院里看电影一般,读到的全是不断转换的画面,至于小说所叙述的内容没有留下深刻印象。潘军的《对门·对面》用英文字母来命名小说人物,突出画面感,对话推动情节发展。小说显然就充分运用了电影镜头的表现手段。朱文的《傍晚光线下的一百二十个人物》,与电影剧本相差无几,正文分为七个部分,分别由场景一、场景二组成。每一个场景又全部由人物的对话、动作组成。七个部分全有人物、动作、对话、场景,基本上就是电影一般的画面。当然,朱文后来做了导演,这不是偶然的现象,媒介化时代,文学的空间越来越狭窄,对于“后新时期”文学的探索、文学的出路必须做认真的思考,图像化趋势就是这种思考的结果。
与图像化趋势相应的是小说呈现出空间化叙事的倾向,这主要表现为情节的断裂、破碎,阅读小说感觉不到小说的时间感,时间的顺序已经没有了,留下的是空间,故事就在某个空间展开。空间小说暗合了当代视觉文化的特征,小说追求动感、节奏、张力,空间的位置移动和转换推动了情节的发展,“空间小说的出现,并不是想导致小说的解体,让人对它失去兴趣而抛弃小说,而是试图建立一种新的、从某种意义上看更有弹性的情节段组合方式,以更吻合于当代人的思维模式,更适应于生活本身的小说形态,让读者感知、理解我们生存于其中的这个世界。”[14]正如上文提到过的,这当然不是偶然现象,无论是图像化趋向,还是空间化叙事趋向,都是时代的必然,也是文学史发展的必然。
二、新闻与小说的相互改造
新闻与文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文学界和新闻界经常探讨的课题。就目前能收集到的的材料来看,大家比较认同两者之间既有差异也有很大的共通性。文学是人学,新闻则为事件报道的学问,即事学。人学表现人的情感,性格特征,表现人与人的关系、与环境的关系;事学注重表现事物的发展变化、事物的本质特征。人的活动只有通过事才能得到体现,所有的事必须依靠人做,两者因此紧密联系而彼此不分家。文学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新闻亦会通过一定的方式表现出来,新闻和文学体现出某种天然的相似性。概括来看,新时期以来,新闻与文学在内容与形式上均表现出相似性,一是社会关注点的相似性,二是叙事方法的相似性。新时期新闻走过的道路除了与国家政治生活息息相关之外,与文学现象的发展历程相一致。1990年代,变革与历史转型期给文学带来了多元的价值观,崇尚理想精神的传统模式不再是统一模式,甚至不占有主导地位,文学开始有意的消解崇高。文学的娱乐功能被提到重要地位,因此文学注重于写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即使是在写重大历史事件,也从日常生活状态来展示历史的本色。[15]1990年代的新闻观念不再以鼓舞人、教育人为主导思想,功能由宣传转为报到信息。晚报和都市报进入大多数平常百姓家,新闻把眼光投向了普通百姓和百姓生活,报道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关于宣传的内容大大减少,普通百姓希望得到的各类信息报道得到了加强且占据主要地位。新闻报道讲求娱乐性、信息性、服务性。报道的文体,报道的语言以及版面语言都发生了变化。新闻从形式到内容实现了平民化的回归。[16]《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与文学关注的兴奋点如出一辙,《冰点》的主编李大同说:“我反复强调的是要关注人群的命运和生存状态。”[17]1990年代的文学走向平民化,写普通人的“为生存”,这样一来文学在表述中讲求故事性,讲求情节的悬念和趣味;在细节的详述中表达作者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这一时期的新闻叙事理念也是以平民生活为本,讲究故事性,“缺乏情节悬念的、琐碎的、不能提供感悟和共鸣空间的、大体在受众经验范围之内的(看了开头就知道了什么结尾)过分‘普通’的生活,决不是新闻的‘摇篮’。”[18]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类新闻的叙事方法。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的《百姓故事》板块,其名称就说明了其叙事的模式。1990年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大众化报纸,叙事的理念和具体方法与传统报纸相比较,发生了质的变化,抽象化概念化的长篇大论逐步消失,信息的告知是其突出的特点,趣味性、故事性表述是这类媒体的新闻手段的主要工具。这些可以说是文学对于新闻的影响或者说不动声色的“改造”,这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为新闻报道形式的多样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由新闻而到文学的转化在“后新时期”的创作领域也表现出来。读者所熟悉的报刊体实录中的一种主要文体——口述实录,其文体性质一直存在争议,可以说是新闻与文学相互改造的典型例子。口述实录诞生于1980年代中期,关于它是否属于文学的问题,在当时热衷于新潮探索和制造热点的文坛引起了较大争议。[19]争议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日常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分歧,以及日常语言能否进入文学。就现在的学术背景来看,这已经不是问题,口述实录是文学,且可以按照媒介和读者的需求生产出非常好的纯文学文本,林白的小说《妇女闲聊录》等就是较优秀的代表作品。现在有三种说法:一是新闻体[20],理由为口述实录已在广播、电视及报刊中广泛运用。口述实录,使小版面上有了大容量,做足做活了新闻。口述实录是忠实记录,原汁原味地讲述故事本身。口述实录讲故事、说新闻,由口述人,而不是记者个人,用语言把目击的新闻和发生过的故事讲出来,与读者共享和互动。口述实录是“继大特写之后的又一被各媒体普遍看好的新闻体裁”。二是散文体[21],理由是从结构上来看,口述实录大多比较松散,具有散文“形散”的特征。口述实录的主旨一般都很明确,是以反映情感问题为主的,恰恰合乎了散文的“情感”特征。在写作方法上,口述实录形成了散文的“意境”。三是小说[22],均从叙述模式、真实性、文学性等方面对口述实录的小说因素加以揭示。本文倾向于把口述实录作为情感类小说看待。安顿作为作品中实录者,除了无可非议地起到连贯故事的作用之外,还为读者做着通俗小说般的描写,如在《绝对隐私》的《纯真是一份易逝的·情怀》中对主人公,即口述人松雨的描写:“松雨的声音咬住了一会儿”、“松雨把脸转向一边”、“松雨的嘴角抖着,有些嘲讽又有些无奈地笑了一下”、“松雨笑出了声音,空空洞洞的笑声,眼泪无声地顺着面颊流下来,一滴一滴地落在胸前”。而且,实录中的描写大多指表情、身体的小动作,好像人物都是演员似的,总在做一些意味深长的小动作。比如,“她笑,粉红色的小毛巾又在眼前一挥”、“周安点燃一只烟,不抽,眼睛盯着红色的烟头”,这样的描写在书中经常出现,如果从文字上来看,这些描述真实可信,但让人怀疑的是,谁能见证当时的口述者的形象和言行?而且,口述实录中的人物,其行为举止已经不太像现实中的人物了,倒像是通俗小说中的人物,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读到许多通俗小说的细节。实录者在口述者叙述时经常插进去自己的判断,如《惧怕婚姻的女人》中,实录者插入这么几段:“我没有想到我会脱口而出:‘你真可爱’。无论魏私的这种做法在大多数人眼里是不是正确,她的那种充满了牺牲精神的理想主义的确令我感动。女人在爱一个男人的时候往往是这样的,勇敢、凄美而又不可理喻地超凡脱俗。”“这样的感情注定是脆弱的,他不可能给她任何承诺……”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实录者经常在主导着口述者的叙述,无论是情节的叙述还是价值、道德的评判,我们在作品中都能够看到实录者的身影,与其说是口述者的叙述,倒不如说是由实录者引导的答问录。还需要提出来的是,口述者均以第一人称出现在作品中,所叙述的全部都是“我”的故事,按照安顿的说法,多个“我”的故事就构成了“当代中国人情感”故事,这无疑带有强烈的作者个人的主观色彩。就现在已经刊发出来的安顿的口述实录作品以及其他报社的类似作品来看,很多批评家就指出,绝对隐私并不就是绝对真实,其真实性值得怀疑,因而必须作为小说来看待,阅读的收获才有可能多一些。安顿五年连续出版了九本情感实录类作品,结集出版的书中所讲述的每一个情感都显得似乎是小说中才可能发生的“完美无缺”的“故事”。许多读者和批评家由此开始对安顿的作品的所谓真实性表示怀疑,安顿也不敢明确表态说明自己实录的绝对真实性,她在以后的作品如《欲望碎片》、《焚心之恋》、《因为爱你才害你》等明确标明“小说”字样。毫无疑问,口述实录一直是作为媒体商业化和市场运作的手段和卖点,有一个问题必须注意,大众媒体还有一种更为隐蔽和强大的作用,借口述实录这样的大众化形式召唤大众的审美阅读惯习,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弥合现有的文体分野——缝合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口述实录是对1990年代以来“个人化写作”主题的一种延续,比如,对女性情感的关注,对隐私的揭密,对家的书写,对两性关系的剖析等等。
无论怎么说,在“后新时期”,从整体上来看,新闻的话语力量占据了优势,新闻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改造并不是平衡的。新闻的小说化挤压了小说的空间,使得自身本来具有的一些优势逐步丧失。新闻没有局限于自身的便捷、框架,主动打破既有的陈规,广泛影响到其他文体的写作,小说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变得游移不定。受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影响,一些小说开始放弃了宏大的叙事和审美理想而倾向于仿照在受众中间影响力强的新闻。1990年代以后,小说的目光更关注实录性内容和当下体验,倾向于炫耀激情并追求时髦,紧跟时代的变化,一些纪实性、个人化、教育性的小说成了时尚。小说的写法技巧也向新闻逐渐靠拢,凸现现场感、大量使用流行语。小说的创作讲求时效性、可读性、服务性等只有新闻才具备的独特性质,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小说的文学性。
文学思潮自新时期来就一直处于活跃状态,形态各异的文学理论不断被介绍进来,不同的文学现象不断产生,形成一波又一波文学思潮。文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一类,而社会思潮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文学思潮通过文学的传播,其辐射力影响力是广泛的和深刻的。不同学科领域的互相借鉴是常有的,而文学与新闻在人学与事学的关注点上又存在着诸多交叉的部分。新闻一方面借助于文学对社会触发的兴奋点,另一方面借鉴文学叙事方法来使自己的传播更易为社会接受,产生更大的影响力。研究受众兴趣、如何进行有效的传播是新闻传播的经常性工作。“信息发出者自然希望得到接受者的回应,这就要熟悉不同接受者群体的认识模式或先验图式,以及特有的经验和观念。”[23]新闻界借助文学思潮的影响形成自己的新闻现象是新闻界对传播技巧的熟练运用的表现。我们在研讨新闻现象时,还有一个问题是不应忽视的,那就是新闻从业人员的学科背景。据统计,目前全国55万新闻从业人员中学新闻出身的只占1/3,而2/3的从业人员中大部分以中文学科为知识背景,而此前这个比例更大。因此文学与新闻的相互影响,文学思潮对新闻的辐射是在所难免的。[24]当然,反过来文学思潮的兴起又对新闻现象的产生和发展注入活力。新时期以来,文学思潮和种种文学现象一个接一个,身处新闻界的有文学修养的记者,或多或多少接受这些思潮的冲击和新的观念,然后在新闻工作中建议运用文学的手段来观照社会现实,这就使得新闻现象与文学现象有了相似的地方。作为报纸,一些软新闻、娱乐花边、服务咨询等等所占有的版面越来越多,甚至根据读者的需求被放到头版头条。同样的情况在电视改革中也表现明显,电视开始走向娱乐化,新闻也走向娱乐化,与此相反,娱乐也走向新闻化,这些共同影响着文学与媒介。
小说界的运作方式与新闻界也趋向一致,很多小说家、评论家不再关注写作或作品本身,而喜欢使用、制造各种各样的新名词来掩饰作品的缺陷和批评本身的“无能”,制造轰动效应以期在公众眼前频频亮相。余华的《兄弟》深受新闻媒介的影响,可以说是新闻传播改造的产物,“太过追求‘与时俱进’,一方面想竭力讨好读者,尤其是已然进入网络时代的读者们,至少可以显示自己不‘落伍’。另一方面要讨好出版社,要主动为重出江湖的销量做贡献。这种‘努力’使《兄弟》增加了很多时尚的语言和情节,比如上半部宋平凡的扣篮及其后对李兰的当众拥抱,下半部李光头举办处美人大赛及宋钢跟随周天游兜售人造处女膜丰乳霜等,无不努力学习时下网络及媒体吸引读者眼球的种种手法。”[25]
新闻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强势是不可逆转的,借用话语理论来说,新闻话语占领了主导地位迫使文学话语做出让步采取屈服的姿态。尽管新闻具有了绝对的优势,但新闻毕竟是以现实和当下事件为中心,新闻的时效性容易令人淡忘历史,新闻叙事的具象性容易令人失去世界的完整,新闻表现手段的故事化、视觉化容易使人陶醉于纷杂的感官刺激而仅仅获得虚假的心理满足。新闻信息大量复制和“海量”传播,信息轰炸将人的思想炸成碎片,信息洪流将人的意识淹没其中并且让人不知所措。所以,新闻在受众的记忆中转瞬即逝,在文化上也枯竭得更快,看似形式繁多的新闻其实在内核上往往呈现出思维向度的单一。新闻的“缺陷”恰为小说发挥文学艺术的特长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小说应有接受宏大叙事考验的勇气,应有追寻生活或生命本质的无畏精神,应有完整观察理解人生社会的能力,应能写出真正的人、健康全面的人,塑造出不可重复的艺术形象。与新闻产业化、商业化相比,小说是高层次的精神创造而非产品生产,是一种内心秩序而非外在描写。小说要经过精神的艰辛的孕育,必须对人生基本状况做出新的、独到的阐释,必须具备独立自主的品质。新闻的扩张整体上提升了大众的文化知识水平,拓展了文化消费的自由的空间,使大众文化更具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的发展也为小说的复兴提供了更广泛的读者基础。
三、新的互动空间的形成与拓展
刁斗接受访谈时就坦言:“有时候在故事性相对弱的情况下,便在文本形式上做一点尝试。很多人说我对故事感兴趣。事实上,我对故事的兴趣不大。每一篇作品动笔之始,都不知道往哪儿写。但我对能否写下去一点儿不担心,最大的担心倒是市场与读者。”[26]晚生代小说作家群、美女作家群等由文学期刊和出版社共同推出,这也是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的成功运作,创造了较好的市场业绩,文学刊物和出版社也从中获得了实惠,提高了刊物的发行量和图书的市场占有率。于是,媒介同晚生代作家等群体建立了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继续加大对这这些作家作品的关注力度。因有了展示的舞台和可观的经济收入,可谓名利双收,这些作家的创作热情更加高昂了。出版社还以和加盟作家签合约、召开作品策划选题会议等形式与作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一系列的行动使得文学期刊、出版社在市场竞争之中夺得了经济利益。而利益又是人们不得不去追求的目标,是衡量价值的重要杠杆,这也意味着媒介在市场之中拥有了更多的“商品阅听人”[27]。这些所谓的“商品阅听人”对文学期刊和出版社来说至关重要,媒介有了他们才能有进一步发展的资本,所以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后,在保持稳定的作家资源和读者资源的同时,与晚生代、美女作家群等建立起了良好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和以前的那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生产体制的关系有了很大程度上的不同。晚生代、美女作家群体为了表达自己对于纯文学的理想的追寻,在纯文学、精英文学日益边缘化的当下,力求为精英文学找到自己言说的空间,找到自己在当前文学界的准确的位置,迫不得已地和文学传播媒介达成一致,而文学刊物和出版社等文学生产机制也可以通过这种运作,获得丰厚的经济利益。“出版企业根据读者对知识和信息的需求,而设计出选题方向,然后联系到能较好地满足这方面需求的作者,对其编辑加工和印制并提供给消费者。可以说,期刊、出版社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桥梁,类似于买者和卖者之间的一个中介机构,但在这个市场中,并不是一对一的交换,而是批量交换。”[28]可以这么说,媒介和晚生代小说等作家群体的“互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共赢”的关系,两者之中的每一方都有自己的内在的目的,通过这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彼此都能从中得到实惠,一种经济和个人名声等等方面的实惠。
媒介已经成为制约甚至是主导当代文化市场的重要力量,在当代文学的生产机制这个层面上,媒介改变了文学的外部环境,文学日益变成了“产业化”运作的事业,某些时候是“车间式”生产的工序。进入1990年代以后,文学艺术也随着社会的全面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初步确立,其市场化、商业化特征日益呈现出来。身处一个“消费”控制整个社会生活的情境之中,人们更多地关注商品的符号价值、文化精神特性与形象价值。在消费社会,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即“生活的文学化”[29],这种“生活的文学化”描述指的是文学对生活的“进入和现实化”,力求达到一种生活类似文学的人生境界。在文学“产业化”、“市场化”的情境之下,文学写作活动成为一种生产活动。文学作品也就成为了一种商品,它要服从市场行情与商业原则的束缚、限制,在带给作家诱惑的同时,也给作家带来了焦躁不安等等心理、艺术上的负面作用。在这种文学作品的商业化生产之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作家审美创造的个性受到限制,作家写作行为演变成商业性活动。根据市场规律,文学作品要直接面向广大的文学受众,因此在文学写作活动中就要顾及到受众的阅读接受心理习惯及其审美期待。因考虑到能否获得商业利润,作家在大多数情况之下会权衡于审美价值与经济效益之间,在经历过痛苦的抉择之后,最终会忍痛让位于经济效益。在一定程度上,媒介确实影响到了文学写作的独立性和创新。
新兴的互动空间的形成,用余华为例来做说明可以论述得更为清晰一些。在1989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的文章中余华曾这样说:“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我的这个真实,不是生活里的真实。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一种真假参半的、鱼目混珠的事物。我觉得真实是对个人而言的。”在随后发表于《上海文论》的《虚伪的作品》中,余华再一次强调了自己对“真实”的认识,表达了他对“现实生活的常识”的推重。余华的这些解释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前期先锋写作的总结,同时也可以看作他“真实”观的确切表达。无论是接受记者采访还是接受文学界人士的专访,余华在很多场合强调动笔写小说之前他首先考虑的是读者是否喜欢阅读,出版社是否认为有阅读轰动效应,各类媒体是否关注。有人将这种行为概括为:“传播上对出版商和媒体的倚重;创作上对大众趣味的的趋同。”[30]在《兄弟》的销售上,余华从未有过的大力配合媒体宣传,频繁曝光、演讲、签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今娱乐圈,众明星为新片、新专辑发行的卖力宣传。近年作家的媒体炒作已屡见不鲜,尤其是名人出书,知名度、宣传力度与销售商之间的关系已不言自明。熟悉中国文坛的余华有自己的苦衷:“要不一家也没有,要不就全照顾到。所以我只能这样,否则人家说你太势利。”在这似乎矛盾的叙述中不难看出:能够对批评家不在意的余华,这一次对出版商和媒体却无法说不。在媒介功能日益强大、丰富的经济时代,文学对于媒介、商业的借助已无法回避,即使如余华般优秀、有号召力的作家为更好传播自己的作品,也不得不服从或者借助于商业运作,商业利益随传播环节进入到文学体系中,并成为重要因素改变文学的生存环境。与传播商业化相对应,创作表现出大众趣味化倾向。《兄弟》还未创作完毕,作为出版单位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就开始大做广告,按照广告学中的“整合营销传播”[31]的理论,《兄弟》未成型时就已经开始了营销,并且将“产品”、“广告”、“营销”整合到了一起,完全按照现代商品的生产营销运作方式来做的。事实上也是如此,余华充分考虑到大众阅读曲味与接受能力,把故事讲得通俗、精彩。
作家与媒介之间的互动并非新现象,本文之所以专门提出来,是出于这样的思考: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十七年、新时期文学发展中,媒介与作家之间的互动关系更多的富有精英式的倾向。新时期及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所处于的媒介环境或者说信息环境并非全由大众化媒体组成,许多媒体发行对象主要限于知识分子,而“后新时期”的媒介环境主要由大众化媒体组成,或者说大众化媒体的声音占据“主旋律”的地位。在此基础之上,作家与媒介之间的互动、作家与大众之间的沟通交流几乎处于“零距离”,作家通过这种互动更能清楚了解到读者、市场的需求,从而能以最快的反应速度满足大众的阅读口味和审美需求。
注 释
①尼葛洛庞帝著,胡泳译:《数字化时代》,译林出版社1995年版,转引自喻国明:《解读新媒体的几个关键词》,《媒介方法》2006年第5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央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53页。
③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0页。
④李良荣:《新闻学概论》(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
⑤Walter Lippmann,Public O Pinion,Macmillan,New York,1956.P15.
⑥参见吴文虎主编:《传播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201页。
⑦参见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页。
⑧波德利亚著,刘成富、全志刚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136页。
⑨沙莲香:《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页。
⑩陈平原:《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以北大诸君的学术思路为中心》,《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562页。
[11]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149页。
[12]胡沛萍:《消失的景物》,《当代文坛》2006年第2期。
[13]爱德华·茂莱著,邵牧君译:《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14]朱水涌:《中国文学:世纪初与世纪末》,.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321页。
[15]张韧:《新时期文学现象》,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80-194页。
[16]杨卫平:《极目楚天舒》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0-82页。
[17][18]单波:《20世纪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9页。
[19]参见1985年的《当代文坛》关于“口述实录”的讨论。张跃生:《口述实录是不是文学——读〈北京人〉有感》;李运抟:《当代文学中艺术方式的跃进——关于〈北京人〉“口述实录”文学的初探》;李昌华:《远非为〈北京人〉争文学一席地》;李墨:《也谈“口述实录”是不是文学——兼与李运抟同志商榷》;袁基亮:《关于口述实录文学的思考》。
[20]参见王瑶:《“口述实录”:一道耐人寻味的菜》,《当代传播》2001年第l期;李苹:《口述新闻在专题新闻报道中的优势》,《传媒》2006年第7期。
[21]参见吴荣娜:《“口述实录”不是新闻体裁》,《采写编》2004年第1期;梁志林等:《“口述实录”的体裁归属》,《中国记者》2004年第7期。
[22]参见欧阳小显等:《安顿小说精神意义的阐如》,《中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刘肖厂:《解读口述实录的几个问题》,《新闻爱好者》2004年第10期。
[23]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页。
[24]曹维劲、魏承思:《中国80年代人文思潮》,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406页。
[25]周松芳:《新传播风潮下的当代文学创作——从余华的〈兄弟〉谈起》,《太原日报》2006年5月15日。
[26]参见姜广平:《典型的时代已经过去——与刁斗对话》,《与当代作家对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7]美国学者斯梅塞认为:“阅听人包含一般阅听人和商品阅听人,媒体能够打包出卖的是商品阅听人,商品阅听人是由市场创造出来的,是应市场工业的竞争需要而生的。”参见金元浦:《谁在出售商品阅听人》,《读书》1999年第7期。
[28]齐宏亮:《浅析出版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编辑学刊》2003年第5期。
[29]此种说法参照张永清:《消费社会的文学现象》,《文艺报》2003年8月26日;宁逸:《消费社会的文学走向》,《文艺报》2003年10月14日;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陶东风:《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新文化媒介人的兴起》,《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王德胜:《视像与快感——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快感》,《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黄应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中西不同的“美学返化”》,《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
[30]郝江波、赵蕾:《从〈兄弟〉及“兄弟热”看当代文学的商业化倾向》,《山东文学》2007年第4期。
[31]参见苗杰主编:《现代广告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6-2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