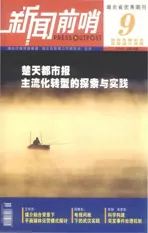虚拟网络社团中社会资本的构建
2010-11-24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博士生430072
◎张 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博士生 430072)
“社会资本”是继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之后,一个新的被广泛关注并认可的资本形式。1977年,它第一次由经济学家格林·洛瑞(Glenn Loury)提出,不过当时它仅是作为与 “个人资本”相对应的一个经济名词出现。随着对它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它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20世纪80年代,法国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尔迪厄 (P·Bourdieu)首次把社会资本概念引入社会学领域,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 “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些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网络,这一网络是同某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其核心主张即:关系网络创造了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有价值的资源,并向成员提供集体所有的资本。这一理论的提出,引起了极大关注,并被广泛地用来解释许多经济、社会现象乃至一个区域或国家的经济繁荣。哈佛大学教授普特南指出,社会资本对一个社会经济繁荣和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社团组织较多的国家一般民主制度绩效高,反之则低。
20世纪80年代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先后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伴此而生,社会出现了如罗伯特·普特南所言的 “独自打保龄球”、弗朗西斯·福山所言的“大分裂”现象,其中最为典型的问题是社会资本的流失问题,主要表现在政府的权威不断流失、公民参与社团的积极性大为降低、公民花费在志愿事情上的时间不断减少、关心公共事务的责任心不断下降、公民彼此之间的信任度严重下降、机构与团体之间的协作与合作精神缺乏等等,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社团公共事务丧失兴趣。但是,寻找团体、寻找组织是人的社会本能。进入数字时代后,越来越多的大众将这一腔热情投入了细化、无边界、虚拟的网络团体,并逐渐对之倾注高于现实生活中的信任度,各种公民自发的网络团体发展一路升温。在以网上社区、论坛、博客等非正式团体生活为主的网络中,人们通过倾诉遭遇、交换经验、共同针对具体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达到彼此信任,形成互惠。社团活动的参与从公共领域转移到网络空间,网络团体中社会资本的力量开始凸显。
网络营造出人们熟悉的社团空间,给予人们经济、应用以及娱乐方面的满足,但由于网络本身的特点,它所构建的社会资本区别于现实社会中的社团。普南特曾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三要素的结合——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及由此产生的可信任性。这三点,在虚拟网络社团中似乎都有了新的形态,为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意义。
一、虚拟社团社会网络的构建
社会资本是嵌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网络中的行动者因此在行动时能方便得到并利用这种资源。网络普及前,人们的社会网络一般来自于三个方面:血缘、地缘与业缘,包括亲戚、朋友、同学、邻居、同事、业务往来伙伴等等。在现代社会,人际交往以及依托于此的信息交换已构成人的发展最重要因素之一,同样也是人的发展最重要指标之一。因此,现代社会,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团体,精心经营各自社会网络成为一大生活重心,它决定着个人或团体的发展潜力及速度,有时甚至决定其生死。然而,这种关系网络的构建并非没有成本的,它需要行动主体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感情甚至金钱,并且,层次越高的社会网络,网络规模越大(拥有较多关系、信息和桥梁)、网顶越高(网络内拥有权利大、地位高、财富多、声名显赫的关系人多)、网差越大(网络成员从事不同的职业,处于不同的职位,资源及影响有互补性)、网络构成越合理(与资源丰富的社会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其投入要求也越多。
进入21世纪,网络技术飞速发展,人类迈入信息社会,地球成了“一个村子”,人们视野变得空前开阔,活动领域空前宽广,遭遇问题也大大超出原有社会网络资源范围——人们对社会网络的规模要求迅速膨胀。为了充分享受“信息”带来的“利益”,它需要人们加速扩大自己的社会网络。然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让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更加冷漠,长期作为一个社会“部件”的生活方式,逐步减弱了现代人构建生活中社会网络的能力;同时,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也让现代人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扩大、完善自己的社会网络,维持已有社会网络已显得筋疲力尽。即使少数精力充足者,能重新寻找合适的资源,但构建相应社会网络需要大量时间,而信息获取速度带来的利益差异是巨大的,当网络构建完毕,它所带来的价值已大打折扣。
由于地域、时间、精力、财力等方面的限制,人们越来越发现现实生活中社会网络的构建相对于人的需要,总是显得速度过慢、范围过窄、信息过少。此外,由于现实社会网络资源利用的有限、有偿性,对于琐碎、次重要或目的不明确的事情,人们不愿轻易动用社会网络的资源。现实社会网络的不便凸显出来。这种不便迅速推动人们在21世纪逐步普及的网络中找到了替代品——虚拟网络社团的社会资源。
同样是社群的集合,但由于网络的虚拟性,人们只需要坐在电脑前,链接网络,打开搜索页,输入需要群体关键字符,即可进入相应社区,并获得所需资源。匿名式的参与,让人们关系网络的构建少了面对面情感的试探、寒暄、必要的应酬交际、个人背景的打探以及路途的奔波,只要进入共同的“社区”,大家就已具有一致性与认同感。少了现实社会网络关系的羁绊,自发的社区中人们说话更自由,没有利益的考虑,大家都自发地愿意提供一定资源与众分享。社群网络的构建变得简洁、迅速,构建成本的投入大大精减。
此外,不同于现实社会网络资源使用的排他性,网络社团组建的随机性与无界性,让个体的发展不再局限于其所属的狭隘地域性和民族性的背景、资源之中,网络以自身所固有的虚拟性、交互性、广泛性和超时空性,使得网民可以通过网络发生丰富多样的社会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种类的网络交往群体。个体能从整个人类、整个世界中吸收自我发展的养料,从而实现人的本质、需要、个性的发展,以及人的发展阶段的提升。
总之,相对于现实社会资本的构建,网络社团中社会资本构建的优势是明显的:它范围广、速度快、投入成本较小,面对琐碎的问题更是方便快捷。当然,其劣势也是突出的:由于网络社团的虚拟性及网络成员的偶然性,导致网络社团社会资本的构建以低层次社会网络为主,若没有现实社会网络构建的加入,较难建立高层次社会网络。
二、网络虚拟社团互惠性的形成
普特南曾把“互惠”分为均衡的互惠和普遍的互惠,前者指人们同时交换价值相等的东西,后者指在特定的时间无报酬或不均衡的付出,即“现在己予人,将来人予己”,是一种短期的利他主义和长期的自我利益的结合。[2]不过,普特南的这种分类主要是针对现实社会社团而言,即相对身份明示、结构稳定的现实社团。网络的开放性、流动性与匿名性,决定了网络虚拟社团的互惠性在没有现实交往介入的情况下,只能以“普遍的互惠”为主。一方面,网络社团之所以能生存,在于广大网民自觉自愿不计报酬付出;另一方面,网络自身的特点让网络社团的“利他”不可能带有任何针对性,只能是“普遍的互惠”。但即使都是“普遍的互惠”,虚拟网络社团也有其自身的特点。
首先,现实社团的“普遍互惠”是基于网络结构中“互惠预期”的推动下行动者的行为,所谓“现在己予人,将来人予己”,含有回报的期望。网络虚拟社团中,除少数需要资源交换的社区外,多数网民的共享资源行为是不求回报的,至少不是在“互惠预期”的本意下发布信息的,其动力似乎更多来自于一种“自我满足”——提供的资料如果为人所肯定,会带来为人师的成就感;如果为他人所否定,会激发行动者的反抗,带来一种参与竞争的满足感;抑或仅仅满足行动者进入社交的需求。不管缘于何种动机,行动者主观的“非功利性”带来的客观结果却是全体社区网民的“互惠”,并且这种“互惠”的普及更为广阔。
其次,“互惠”作为人们精心经营各自社会网络的核心动力,其效益也有层次之分:有关于社会地位获得、职业流动、财力资助等较高层次的社会资源;也有仅限于一般性的资源共享。互惠效益越高,需要行动者的投入也相应要求越高,网络成员对资源的控制也越加严格,不会轻易转让。因此,能在网络虚拟社区中轻易获得的共享资源,大多属于低层次社会资源,主要表现信息资源的共享。它一般不能带来直接的实惠,仅能为行动者提供追求实际实惠的信息支持,这种信息支持的维度和广度远远大于现实社团。
三、网络虚拟社团信任的产生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要素,也是互惠交易的关键组成部分。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说,“所谓信任,是在一个社团之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基础是社团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隶属于那个社团的角色”。[3]网络结构中不同成员之间的信任有强弱之分,一般对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以及密切交往的朋友圈信任度最强;对与自己有合作关系的公司领导、同事和邻居等的信任度居中;而对包括生产商、销售商以及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度最弱。网络虚拟社团中成员的信任属于信任度最弱的一种,但它特殊的形成方式对社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传统社会中,现实社团关系网带有相当的封闭性和排他性,信任仅限于关系网内部,“陌生人”之间难以给予信任,因而也难以发生频繁交易或交往。而已步入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需要交往的多元化,即交易主体的多元化。无数交易者以陌生人的身份进入市场,但依赖传统关系网的信任无法覆盖“陌生人”,市场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于是,为了弥补由传统关系网对陌生人排斥带来的经济发展障碍,“契约”应运而生。通过契约的外在强制力——法,“信任”产生,陌生人第一次强行进入传统关系网,进而逐步成为关系网的一员,新的关系网得以形成。契约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关系网的不足,但它主要限于经济交往领域,并且多用于大型、重要的经济项目,对于小型、微型经济项目或非经济领域,契约在社会交往中显得繁琐、累赘,并消耗大量社会资源,造成资源浪费。
虚拟网络社团中交往虽同样以陌生人为主,但其信任产生的特殊方式避免了这种资源消耗。网络匿名性带来的安全感让人放松了现实交往中的警惕,虚拟网络社团中传递信息的无指向性以及社团中交往主体无利益冲突性,让网络成员排除了现实社团中大量由利益权衡带来的不信任,怀疑多限于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不再以对信源主体的怀疑为主(而这在现实社团中是不信任的主要原因),基本信任已然产生。此外,虚拟网络社团不同于现实社团的是相同信息具有高度选择性,即同一疑问会有多个成员回应并提供信息,求助者可以在多个信息中比较分析,最终确定认可的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减轻了人们对信息客观真实性的怀疑。与此同时,现实交往中暴露过多可能会带给自身一定的危险,但虚拟交往中不存在现实的危险,保留过多反而会妨碍交流,因此网络社团中“自我暴露”会更多,共享信息相应更加丰厚。不过,虚拟网络社团中的信任多限于网络之中,如果脱离网络进入现实交往中则需要重新适应现实社团运转逻辑规则,信任需要重新构建。但无论如何,在信息资源共享层面,虚拟网络社团信任产生的特殊方式,节约了大量成本,创造了丰富的社会资本财富。
总之,社团进入虚拟网络,其社会资本的构建无论在网络的形成还是互惠性、信任的产生中都有明显的特点,这些特点让虚拟网络社团在普遍性的信息资源共享上拥有现实社团无可比拟的优势,也必将为社会的发展注入新的力量。
注释:
[1]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2]胡荣:《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地域性自主参与》,《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3]弗兰西斯·福山:《信任》,湖南出版社,2001
[1](美)罗伯特·普特南著,王列、海榕译:《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2]帕萨·达斯古普特、伊斯梅尔·撒拉格尔丁:《社会资本——一个多角度的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张其仔:《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4]顾新等:《社会资本及其在知识链中的作用》,《科研管理》2003年第2期
[5](美)弗朗西斯·福山著,曹义烜译:《社会资本、公民社会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2期
[6]秦琴:《社会资本研究中的二元困境及其出路》,《长江论坛 》2006年第5期
[7](美)林南著,张磊译,《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8]寇东亮:《社会资本的伦理意义》,西北大学学报,2004
[9]郭毅、朱扬帆、朱熹:《人际关系互动与社会结构网络化——社会资本理论的建构基础》,《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10]李维安:《网络组织:组织发展新趋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1]Bourdieu P,The Forms of Capital,Handbook of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1986
[12]Bourdieu&L.Wacquant,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Chicago, 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