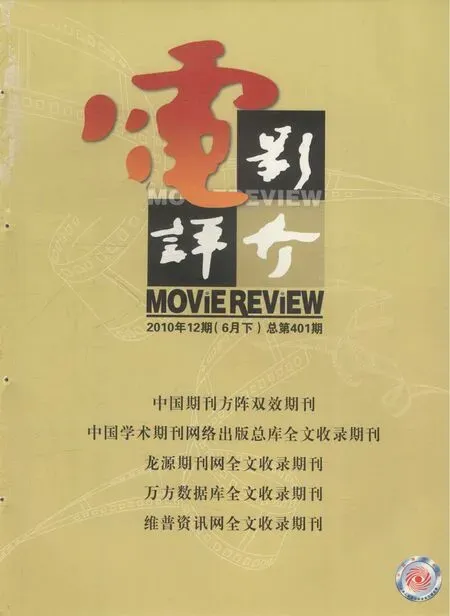影视作品对经典的毁灭性解构——谈1996版的《罗密欧+朱丽叶》
2010-11-16丁菲菲
莎士比亚(1564-1616)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们常说,没有《圣经》和莎士比亚作品集的家庭,就算不上是完整的家庭。他的作品是西方文学(诗和戏剧)的顶峰,也是西方文化的代表,代表了基督教、希腊罗马、意大利文艺复兴和英国本土文化的一种综合结晶。作为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留给世界的39个经典剧本(新增添的是《爱德华三世》和《两个高贵的亲戚》)。这些剧本涵盖了悲剧、喜剧、历史剧、传奇剧(或悲喜剧)等诸多戏剧形式。在文字为主宰的世界里,他是历史上读者最多的作家,他的作品被译成100多种文字;在音像为载体的社会中,他的剧本也是历史上拍成电影最多的,从1899年第一部《约翰王》拍摄以来,已拍摄成300多部电影。他的戏剧、以及以他的作品为基础而改编的现代作品,继续吸引大量观众拥入世界各地的剧场,证明了他的作品所具有的永恒魅力和现实意义,那就是对世界普遍性主题的关注。
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1936年,乔治•库克导演了黑白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1954年意大利导演卡斯特拉尼将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搬上银幕。1968年,弗兰克•泽费拉再次将它搬上银幕。然而,巴兹•鲁尔曼于1996年推出《罗密欧+朱丽叶》(后现代激情版),却让观众大大体验了一把什么叫做后现代,什么叫做激情版。
看完1996的现代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心中突然听到一声清脆的声音,一如珍爱的瓷器啪嗒碎了,一地碎片。曾经幻化万千的朱丽叶,定格了。心中没有涌起熟悉的美感和心灵净化的享受,所谓的后现代原来竟是很现代。
兰姆C. Lamb在“论莎士比亚的悲剧是否适宜于舞台演出”(1811)中曾极力反对将莎式的悲剧搬到舞台上,他指出虽然演出能够将作品的思想具象地体现出来,但是:“为了获得这种幼稚的快乐,这种明确之感,却要付出终生的代价。一旦新鲜感过去,我们就会发现得不偿失,思想其实并没有被体现出来,相反它们实际上只是把一个美好的梦幻物质化了,把它降低到了有血有肉的水平。我们为了追求得不到的实体,放弃了梦幻(C. Lamb:161)。今天我们看到的这部激情版,恰恰为兰姆的这段话作了很好的注脚。这种演出摧残了我们的头脑,我们看到的只是丰满的躯体和躯体的行动,人物不再向我们呈现丰满的内心和灿烂的内心活动。
在一个浑身上下充满肉欲的母亲的身教下,你会指望看到什么样的朱丽叶,那个曾经羞涩的、受着严格礼教约束但青春萌动的纯情少女,被人暗中偷听到内心独白也会羞红了脸的女孩在哪里呢?眼前这个风情无限的风月老手,这个显然受了性自由教育的成熟女人(14岁?),与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个纯情的姑娘有多少相似?你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感觉,这样的一个女人在这样的场合,她的吻应该不是第一次,或是第二次,第三次?只是习惯的猎艳吧。阅读时在头脑里产生的崇高形象、诗意的画面在影视镜头前通通消失了。还有多少悲剧的意义在这样的画面里这样的镜头下?剧作家写作的意义难道仅仅是描述一个低级的追求性对象的女性么?
这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悲剧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西欧古典悲剧的理想,是要通过“怜悯与恐惧”使感情升华到净化的境界。德国评论家莱辛说:“这是我们看见不幸事件落在这个人物身上时,唯恐自己也遭到这种不幸事件的恐惧;这是我们唯恐自己变成怜悯对象的恐惧。总而言之,这种恐惧是我们对自己的怜悯。”戏剧家将主人公的牺牲仪式当作戏剧的高潮处理,以使观众生命庄严和死亡崇高的情感体验。在这部电影里,有的是恐惧,但没有紧随而来的怜悯。你永远没有被净化的感觉。从场景从头拉开时就是一连串视觉冲击。
好莱坞的拿手好戏:酷枪酷弹、美女调情,在这里展露无遗。随着太保尔特的一句“我痛恨讲和,就如同我痛恨地狱”,所有的枪支一哄而上,一场街头火拼闹剧拉开,人们期待的温情浪漫被盖上一层层火光与血腥,一切都只是在发泄,没来由的宣泄空虚的精神、消耗过剩的体能和欲望,体现同样好莱坞式的空虚。但是酷枪还是要有美女配的,所以朱丽叶也变得脾气火爆,从小就见惯使惯枪的人,难怪到最后自杀时也能如此驾轻就熟地将枪支扣在自己的头上。
影片无处不在、随时随地渲染暴力倾向。这也是好莱坞的拿手好戏。虽然几百年前父权社会中,子女是家长的附属品,无论在《仲夏夜之梦》、《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还是在《罗密欧与朱丽叶》、《奥赛罗》中,都体现出女儿是父亲的私有财产,作家长的可以依靠法律,随意处置叛逆不孝的孩子。朱丽叶的父亲凯普莱特虽然脾气暴躁,还是爱自己的女儿的,否则他也不会在女儿大婚前的晚上忙上忙下地张罗婚宴。而影片中的凯普莱特面对朱丽叶的反对,疾风暴雨式的爆骂和着暴打,镜头在父亲的极端暴力和女儿的无助哀求之间不断切换,令人心生恐怖。
结婚的仪式在剧本中原本是神圣的,在神圣的教堂没有把年轻的心合法化地结合在一起前,过多的接触都是要受到上帝的轻视。这是基本的礼法,也使他们在神父面前的结合更加神圣、庄严。然而,后现代的朱丽叶心中有贞洁感么,隔着金鱼缸的大胆的露肩挑逗,游泳池里迫不及待的肌肤相贴,已使人丧失对仪式庄重的期待,床上戏的功夫表演,硬将观众逼到墙角,或许导演以为所有人都和他一样有偷窥癖。
原剧中的宗教意识也荡然无存。剧作家试图通过宗教献祭的方式赎清两家的罪,用青年男女纯真青春的血液洗涤众人心中的手中的罪,使世界重新恢复和平与秩序。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救赎的行为是由这对恋人的牺牲完成的。正是由于他们的牺牲,蒙太古和凯普莱特两大家族才能够消除宿怨,达到和解,喧哗和骚乱才能转变成和睦相处。凯普莱特看着这对死去的情侣,心里明白他们是“我们互相仇恨的可怜的牺牲品”(第五幕第三场)。这是原剧带给我们的精神升华。
然而后现代拒绝大众的向往,主人公的死亡没有引起观众的同情与怜悯,相反,金光闪闪的华丽的墓室、喧闹的场景、没完没了的热吻、罗密欧的粗心,冲淡了人们的悲悯情怀。作品的赎罪意识被解构了,成了支离破碎的一具具陈尸腐肉,一堆堆难平的欲望沟壑。“所有人都受到了惩罚”,是影片的结语,男女主人公的献祭行为完全失去了作用与意义,矛盾没有消解,仇恨依然存在。当朱丽叶朝自己的脑袋娴熟地扣动扳机的时候,人们更关心的是美国枪支崇拜、枪支泛滥、性自由的问题。悲情在这里跑了调。一场血腥的闹剧落幕了。
歌德说“说不尽的莎士比亚”,果然如此,美国现代版罗密欧与朱丽叶,让我们见证了莎士比亚“属于所有世纪”的预言。导演不是拿旧瓶装新酒吗?百年前让人一再感动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今天不是同样可以拿来解释美国当下的社会现状吗:枪支崇拜与泛滥、家族利益纷争、性自由教育?厄普代克不是也解构了哈姆雷特吗?它不再次印证莎士比亚的经典地位吗?所谓莎士比亚的作品的经典,一是其中关于生存与死亡的话题是永恒的,为生活在每一个时代的人们所熟悉,容易产生共鸣。二是他的剧本具有无限的包容性,他的作品特点在于集中反映了文艺复兴时代对人和人的个性的重视,突破封建时代对人的自由发展的禁锢。文艺复兴强调的个性张扬在茂邱西奥的身上体现的多么精彩,“在第四场中,我们看到茂邱西奥上场了。啊,叫我怎么来形容他那种年轻的生命的非常沸腾和充溢的状态,他的快乐和幸福的笑浪向前浮动着……总在惊醒中的机智、繁忙而有生殖力的像一个昆虫一样的幻想、勇敢、一颗自由自在的心,无忧无虑,立刻也想把别人的烦恼付之一笑,然而,又对别人的烦恼感兴趣;——这一切以及所有与此相同的性质,溶于它们所有这些的共同的“结合肌”中,有地位的人和绅士,具有他全部的优点和弱点,组成了茂邱西奥的性格。” (P145,柯尔律治 S. T. Coleridge, 关于莎士比亚的演讲,1818)当现代版的茂邱西奥掀起裙子,从裤裆里掏出请柬时,他已经不再是那个热情的有着无限鲜活生命力的青春偶像。我的心又一次听到碎裂的声音。
永恒的话题、无限的包容,这两点在后现代中不是得到延续么?
然而,我们需要知道,经典的意义是要人们得到精神上的洗礼、人文精神的情怀,而不是表层感官的刺激,物欲、肉欲的冲击。我痛苦的是,我在阅读中获得的自由想像和美好印象被颠覆了,美丽、含蓄、羞涩、坚贞、勇敢的朱丽叶曾经在心中引起许多美好记忆,却在一刻间灰飞烟灭,眼前晃动着的是一个肉欲无边的后现代女郎。钱钟书老先生说过:拙劣的翻译是对原著毁灭性的打击,那么拙劣的解构是否对原著同样具有毁灭性的破坏呢?
一如两百年前的兰姆站在演员伽立克雕像前面痛苦无比,我拔掉电源,没有以往的神清气爽,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凄美真情而感动、而敬畏生命的魅力,我感到的是碎了梦砸在冷冰冰的水泥地上。没有想像,感觉是惨白的;没有涤荡,精神是压抑的;没有真情,心灵是空虚的。
[1]杨周翰.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下)〔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2]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5)〔Z〕. 朱生豪,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3]辜正坤.中西文化比较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4]歌德等.莎剧解读〔Z〕.张可、元化, 译.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5][美]迪克•瑞利, 帕姆•麦克阿里斯特.开演莎士比亚〔M〕.刘军平等译.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5.
[6]方平. 欧美文学研究十论〔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7]M. M. Reese, Shakespeare, his world and his work〔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0.
[8]John Kerrigan, On Shakespeare and early modern literatur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