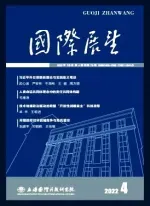关于英国对华外交的几点思考
2010-08-15赵怀普
赵怀普
关于英国对华外交的几点思考
赵怀普
英国外交素来讲究“现实主义”,追求利益目标。二战后英国奉行了较为务实的对华政策,采取了意识形态分歧下经济利益优先的外交策略,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美国因素的干扰和制约,从而较好地维护和发展了其在华利益,同时也促进了中英双边关系相对稳定的发展。今后英国仍会坚持基于利益目标的务实对华外交路线。
英国外交 对华政策 务实 利益目标 中英关系
1997年香港问题解决后,中英关系驶入全面发展的快车道。1998年两国发表《联合声明》,确立了中英“全面伙伴关系”的发展框架;2004年,两国决定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领导人会晤机制;2008年,中英关系进一步被定性为“面向未来的有活力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前中英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并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应当说,在近年来中欧关系出现波折、中法和中德关系陷入低潮的逆境中,中英关系能够保持这一稳定发展的势头殊为不易。这首先应归功于双方领导人高瞻远瞩、始终把握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同时也是两国政府和人民共同为之奋斗的结果;进一步来分析,亦与英国奉行较为务实的对华政策密切相关。本文以英国对华外交的历程为主线,通过考察不同时期的英国对华政策,发现和总结其对华外交的主要特点。
一、奉行较为务实的对华政策
英国外交素来讲究“现实主义”,表现为审时度势,努力使自己不处于过分被动、尴尬的境地。知所进退,往往能更好地保住自己的利益,①陈乐民主编:《战后英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2页。这是陈乐民先生对英国外交的实质及特点的精辟概括。
作为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强国和殖民大国,英国在数百年的国际交往和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国际政治经验,铸就了底蕴深厚的外交传统和高超的外交技巧,这些无形的外交资产对其在国际事务中保有一定的影响力有所助益。虽然二战后国力急剧衰落,外交空间大为缩小,但英国外交的总势依然是在被动中争取尽可能多的主动,从不放弃表现主动性的任何机会。②参阅陈乐民主编:《战后英国外交史》,第11页。战后初期确立的“三环外交”方针和策略,就是基于现实而作出的战略性选择,目的是要在外交上争取尽可能多的主动,以有助于维持和恢复英国的大国地位。从实施效果来看,该战略总体上也是较为成功的,在战后的国际政治中最大限度地维护了英国的利益和尊严。一言以蔽之,英国外交立足于现实,讲究务实性,追求利益目标。
战后英国除了在“三环”和美苏间纵横捭阖外,其对华外交也颇具特色,表现出较为务实的一面。这可以透过几个大的历史节点进行观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英国对新中国的政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由于战后自身力量衰退、对美国依赖加深,英国在许多国际事务上支持和追随美国的立场,对新中国的政策总体上同美国一致,即力图防止中国在亚非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影响的扩大,并积极配合美国图谋阻挠台湾回归祖国,以达其维持远东现状和保住香港的目的。另一方面,在中国问题上英国又没有完全按美国意志行事,并不顾美国的反对于1950年1月承认了新中国。主要原因有三点:其一,英国在旧中国有着比任何别国都多的投资,③英国当时在华投资达10.3亿多美元,见吴承明著:《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2页。另根据建国初期各地军管会统计资料测算,在当时所有西方国家在华投资中,英国占48%,美国占43%,其他各国总计不到9%。转引自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1995》,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9页。它希望以承认新中国的姿态来保住其在华投资;其二,英国担心中英关系过度恶化会导致中国以武力收复香港,因而希望尽早与中国新政府建立对话机制;第三,英国希望利用美国因扶蒋反共、日本因侵华战败被排挤出中国的时机拓展在华市场。④参阅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1995》,第9页。承认新中国体现了英国外交的“现实主义”,英当政者敏锐地意识到了新中国是一支上升的力量,要想维护英在华权益将难以回避同中国共产党打交道。应当说,在东西方意识形态严重对立和冷战形势紧张的当口,英国在西方大国中率先承认新中国是需要一定的政治勇气的,也正由于此,英国这一理性的外交举动给中国政府和人民留下了务实与友好的印象,为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也为对外关系的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英国垂涎于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欲重新打开因二战被迫退出的中国市场。然而,横亘在两国之间的香港问题对双方关系形成了制约,英国一度为香港问题的解决设置种种障碍,企图阻挠香港的回归。但终究形势比人强,在双方力量格局业已改变和中方在原则立场上毫不动摇的现实面前,务实主义在英对华外交中再次占据了上风。1997年上台的布莱尔政府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试图以香港回归为契机改善中英关系,加强两国合作。香港问题的最终解决,使中英两国摆脱了历史的包袱,双边关系驶入全面发展的快车道,半年之内即实现了两国高层领导人的互访,这在中英关系史上前所未有。更重要的是双方通过高层互访加深了相互了解,增进了彼此间的信任,促进了两国关系朝着更加稳定务实的方向前进。
进入21世纪后,在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推动下,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大提升。对此国外有分析指出,中国日益强大的经济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地区性,并正在转化为国际政治上的优势,甚至有可能彻底改变冷战后的国际战略格局。①关于这种观点,请参阅“中国崛起对世界格局的影响”,http://www.china.com.cn/chinese/EC-c/666789.htm。虽然这一看法带有某种夸大的成分,但也不必讳言中国的发展对现存国际格局的影响,重要的是对中国实现发展的方式和目标作出合理的、正确的判断。应当肯定地指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是以“建设者”而非“改革者”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的,其发展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目的是促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民主和均衡的方向发展,从而有助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根本上是由其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也顺应了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
中国和平发展的愿望和政策是明确的、真诚的,得到了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和赞赏,却仍不能完全消除西方社会的疑虑和偏见。一些西方国家囿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成见,对中国的发展疑虑重重,鼓吹和散布“中国威胁论”,甚至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加以干涉和限制。尽管如此,在充满着更多智慧和理性的人类世界里,即使西方社会也不是铁板一块,讲究实际的英国人意识到中国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对英国来说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英国对中国发展的看法主要有这样几点:1、中国的发展不可避免,其发展势头也是不可遏制的;2、中国的发展已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之一;3、中国发展会对英国形成挑战,但不是威胁;4、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了巨大的机遇,希望英国企业能够抓住机遇,乘上中国发展的快车;5、中国现在已不仅是吸引外资的国家,也开始向外投资。英国很重视和欢迎中国来英国投资,希望中国把英国视为走向欧洲的优选点;6、随着力量的增长,中国在国际上的作用和影响明显上升,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很多全球性问题离开中国的参与很难解决。①中国驻英大使谈中英关系:“英积极面对中国发展:它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3831166.html。总之,对于中国的发展,英国总的态度是理性、务实和积极的,由于深谙务实外交的利处,故而在对华外交上更强调因势利导、化挑战为机遇的重要性。
布莱尔在任时一再强调,西方有些人把中国的发展看作威胁,但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它不仅有利于中国13亿人民生活的改善,同样也有利于世界,它为世界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对于中国发展的“挑战”,英国的认知角度也有别于美国等国,后者倾向于夸大中国的发展所可能引发的地缘政治后果,而英国则更多地关注其对世界环境、能源和资源带来的影响,并希望与中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战。2007年5月,英国外交大臣玛格丽特·贝克特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的一篇题为《构建和谐世界:英中关系及其应对国际性挑战的贡献》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在英国把中国看作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持续的经济繁荣也关乎英国及欧洲的利益。我想引用中国领导人所用的一个概念,英中两国不仅是战略合作伙伴,也是科学发展的合作伙伴”。她还说,“在各国相互依存的全球化世界里,中国的成功对全世界都有益,而中国的失败则会损害所有人”。②http://www.britainusa.com/sections/articles_show_nt1.asp?d=0&i=41020&L1=41002&L2=41020&a=46442.贝克特的这段话很好地诠释了布莱尔政府因应中国发展所采取的化挑战为机遇的务实外交策略。
2007年布朗政府上台后,在对华外交上继续奉行务实路线。布朗曾在布莱尔政府中任财政大臣,多次访问过中国,支持发展对华友好合作关系。他曾在公开演说中表示,中国的和平崛起并不会成为一种威胁,并指出“英国外交政策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与中国密切合作”。2008年1月访华前夕,布朗在接受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联合采访时强调,“对英国来说,与中国在国际问题上进行建设性的合作,是我们外交政策的重点之一”。①“专访英国首相布朗:我对科学发展观非常感兴趣”,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1/18/content_7444257.htm。访华期间他又进一步表示,中国倡导的“和谐世界”和“科学发展观”有利于世界人民,有利于全球化进程。布朗政府的新任外交大臣米利班德2007年底撰文称,英国已为更进一步的中英合作伙伴关系作好准备,他指出,“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间奇迹般的经济增长及不断对外开放已经为中国人民及世界其他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英国政府欢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对国际社会的不断融入。我们希望中国获得成功,因为这不仅符合贵国的利益,也符合英国的利益。”②“英国已为更进一步的中英合作伙伴关系作好准备”,http://www.cycnet.com/cms/2006/2006youth/xw/gjnews/200712/t20071207_619559.htm。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前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布朗政府非常重视并积极评价中国的作用,支持中国等发展中大国在国际机构中发挥更大作用。在应对其他全球性挑战和国际体系改革问题上,布朗政府也较为重视中国的作用和诉求,主张国际社会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支持在气候、环境领域的技术转让与资金合作。可以说,布朗政府的对华政策延续了布莱尔时期的务实友好,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
二、意识形态分歧下经济利益优先的外交策略
外交为经济服务是当代国际外交的一个新信条,这一外交目标的实现要求超越国家间社会制度的差异和摆脱意识形态分歧的束缚。中英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存在分歧,但这并没有妨碍英国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其原因就在于英国强调外交为经济服务,并为此采取了意识形态分歧下经济利益优先的策略。要之,英国的对华务实外交主要是受经济利益的驱动。
从一开始,英国的对华政策就带有强烈的经济动机。如前所述,英国承认新中国的重要考虑之一,就是为了保持其在华投资和拓展其在华市场。据有关统计,1949年中英贸易进出口额为2300万美元,英国承认新中国后,1950年中英直接贸易和中国大陆同香港贸易都有了显著的恢复和发展,贸易额约为1949年的3倍。①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314页。从这些数字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对华务实外交给英国带来了显著的经济上的好处。经济考虑在促使英国最终在香港问题上作出理性决策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布莱尔政府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看到了巨大的机会,希望与中国开展务实合作以谋取经济上的利益。1998年布莱尔首次访华便与中国领导人发表了《联合声明》,确立了中英“全面伙伴关系”的发展框架,为中英经济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2003年再次访华后,布莱尔又与中方商定成立双边关系互动小组,该小组汇聚了社会各界的智慧,在贸易与投资、金融、能源、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环境包括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提出了新的建议。而当中欧发生贸易纠纷时,布莱尔也不忘提醒欧盟采取务实立场。例如2005年中欧纺织品贸易谈判举步维艰之际,布莱尔就强调欧盟应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这背后当然有着本国利益的算计,因为从贸易和经济的角度,英国将从开发中国市场中获益良多。布莱尔成功地利用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历史契机,为英国谋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他在任期间中英两国贸易额逐年上升就说明了这一点。
布莱尔的接班人布朗熟谙经济财政事务,他对中国的发展给英国带来的机遇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2005年2月,时任财政大臣的布朗在中国社科院发表的演讲中说,“有些人或许把中国和全球一体化看作一个威胁。我认为中国的崛起和全球一体化的深化不是威胁而是一个机遇。之所以是一个机遇,因为中国是一个对英国公司来说具有巨大机会的巨大市场;一个富有活力的市场,它促使英国准备着面对新世界的挑战并做出回应。之所以是一个机遇,因为中国的发展帮助我们了解变化之所需,并促使英国民众寻求改变。”②http://www.cass.net.cn/file/2005030143645.html。布朗政府上台后尤其重视对华经济外交,英对华贸易和投资稳步增长。2007年中英双边贸易额达394.4亿美元,增长28.6%,其中中国出口316.6亿美元,增长31%,进口77.8亿美元,增长19.5%。截至2007年底,英在华累计投资项目5834个,协议金额285.8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147.8亿美元。①“中国同英国的关系”,http://www.eeloves.com/garden/article-show/gid/523/id/887。另据中国英国商会近日透露,截至目前英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已经超过160亿美元,见“英国在华投资超过160亿美元”,《北京青年报》,2009年7月3日,B4版。近年来中欧经贸争端有所增加,但布朗政府坚持认为中国的发展对中英经贸关系利大于弊,英国工商界也日益感受到与中国合作的利益所在。目前英国是欧盟最大对华投资国和第三大对华贸易伙伴,中英双方还有志于到2010年实现6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
布朗政府在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的同时还运用多元化的手段,争取扩大与中国的共同利益,促使两国合作的制度化和机制化水平跃上了一个新台阶。2008年,两国首次举行了副总理级的中英经济财金对话,该机制的建立有利于双方在经贸、金融、气候等问题上深入探讨与合作。在当前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阴霾下,该机制尤突显出其意义和价值。一方面,英国经济因受到金融危机的拖累而陷入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预测数据显示,英国经济今年将收缩2.8%,承受着发达国家中最严重的衰退,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更加体会到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性,希望利用中英贸易来提振本国停滞的经济。另一方面,受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影响,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有抬头之势,而中英两国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和反对贸易保护方面既有共识,更有共同利益交集,故上述机制为深化双方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2008年3月,英国外交部亚太司司长伍德在英中贸易协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表示,英国需要中国保持稳定和发展,中国是英国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伙伴。中国也需要英国的合作,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化解一些外交挑战,推进海外投资和贸易。②“英国外交部官员积极评价英中关系”,http://www.fmprc.gov.cn/ce/ceuk/chn/xnyfgk/t415014.htm。2009年5月在伦敦举行了第二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双方就金融、贸易、投资、能源、环境等领域合作达成许多重要共识。英国财政大臣达林积极评价了中国为推动落实二十国集团(G20)伦敦金融峰会共识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称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改革国际金融体制以反映当今世界现状方面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他还特别强调在当前形势下中英两国携手合作的重要性,称英方期待进一步密切与中国的合作。
19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有一句名言:“我们没有永久的盟友和永久的敌人,我们只有经常的、永久的利益,我们应当以这种利益为指针。”①http://hi.baidu.com/alittlefox/blog/item/caa589cb80f63efd52664fc9.html。正是追求经常的、永久的利益的这一信念决定了英国外交的“现实主义”取向,也深刻地影响了英国的对华外交。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分歧是导致近年来中欧关系出现波折的最大症结,但与中法、中德关系出现某种程度的倒退形成对比的是,中英关系总体上保持稳定并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其缘由就在于英国较好地处理了政治分歧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并采取了意识形态分歧下经济利益优先的务实策略。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英关系将会更加紧密,经济因素在英国对华外交中的作用会进一步增强。当然,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新时期的中英经济关系是建立在平等、合作和互利基础上的,这与旧中国时期英国单方面对华经济掠夺和剥削有着本质的不同。
三、灵活处理对华外交中的美国因素
战后英国外交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受到了美国因素,也就是“英美特殊关系”的显著影响。保持英美特殊关系、“通过影响美国来影响世界”被认为是英国外交的一项重要方针和谋略。②阿尔弗雷德·格罗塞:《战后欧美关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395页。“英美特殊关系”对英国外交的深刻影响已为大量事实所证明,无须赘述,这里所要指出的是,美国因素的影响同样也渗透到了英国的对华外交中。
分析美国因素对战后英国对华外交的影响,首先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特点,即总体影响有限,但在不同时期影响的程度有差异。冷战期间特别是初期阶段,英国对华外交受美国的影响和制约比较明显,主要表现是:英国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采取了两面态度,即一方面表示愿与中国建交,另一方面又在美国压力下不愿接受中国提出的合理的建交条件;此后一个时期,英国在其他一些涉华事务中也支持和追随美国的立场,如反对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配合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以及限制同中国的贸易和技术合作等。虽然与多数西方国家相比,英国这一时期在处理与新中国关系时表现出了一定的务实性,但其对华政策受美国因素的影响仍较为明显。
冷战后,伴随着世界多极化进程的推进,英国外交的自主性增强、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这无疑有利于中英关系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对英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而香港问题的解决进一步为两国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英美特殊关系”对英国对华外交的影响总体上趋于弱化。布莱尔虽然强调维系和加强“英美特殊关系”,但也越来越重视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2006年8月,布莱尔在洛杉矶发表的一篇专题演讲中表示,英国外交“天平”应移向崛起的中国与印度。他特别指出,未来的20到30年,中国将成为新的超级强国,英国及美国必须调整政策。布朗上任后明确提出“新多边主义”,主张对“英美特殊关系”进行微调。他积极评价中国的国际作用,指出“英国外交政策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与中国密切合作”。英国在对华外交上主动和自主意识的增强,表明美国因素的制约作用在减弱,英国对中国的发展采取了较美国更为务实的态度和立场即是一个证明。
除了上述特点,英国在处理美国因素的影响方面还表现出某种两面性:一方面,在北约和欧盟等一些西方多边机构中,或因美国居于主导地位或拥有较大影响力,英国在涉华事务上多与美国协调,例如在是否取消欧盟对华军售禁令问题上受美国立场的影响较大,态度较为消极,在北约内部讨论某些涉华问题时也倾向于附和美国的立场;另一方面,在中英双边框架内则是务实主义占上风,强调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避免多边机构内存有争议的涉华议题影响和干扰中英双边关系的发展。这种多边谨慎消极与双边务实积极之间的反差,或可以被批评为“机会主义外交”,但这也正体现出英国外交成熟、圆滑和灵活的特点。当然,英国并非在所有国际多边机构以及在任何时候都唯美国马首是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以及作为八国集团、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的一个重要成员,英国有时在某些国际问题上也保持一定程度上的“中立”,这对中国来说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英国在处理某些涉华事务时明显同美国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保持了一定距离。在一些人以中国解决达尔富尔问题不力为由掀起“抵制北京奥运”之时,布朗政府对中国进行了坚决的支持。外交大臣米利班德明言,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不能单靠中国解决,须全世界携手合作。他同时表示,人权与奥运这两个问题不应该混为一谈,不应借奥运之机向中国施压。在美国等一些国家忧虑和质疑“中国模式”时,英国却已开始思考“中国模式”是否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英国在制定非洲政策时就参考了中国的经验。①郑永年:“西方模式无戏可唱 却为何惧怕‘中国模式’”http://news.ifeng.com/mil/4/200804/0410_342_484277.shtml。还有,在应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布朗政府对中国的立场和政策也给予了较多的理解和支持。
保持“英美特殊关系”是战后英国外交的一项根深蒂固的传统,英国内各主要政党至今仍把与美国的密切关系视为英国外交和防务政策的重要基础,因此其对华外交也难免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但英国的优势在于它一直站在美国身后,作为美国的忠实盟友,英国在西方多边场合有时要默认甚至配合美国的行为,但同时又在双边框架内积极发展同中国各方面的友好往来,最大限度地谋求自身利益。一句话,英国在处理美国因素方面与美有协调又有分歧,通过采取务实灵活手段基本上避免了“英美特殊关系”成为其对华外交的负资产。英国这方面的一些做法或许对其他西方国家处理对华关系具有某种启示意义。
四、结 语
在国际政治中,实力是一个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本,不仅决定着其影响力、话语权,也决定着其对外政策。面对战后国力衰退的现实,讲究实际的英国人在外交上知所进退,表现出了更多的务实与理性,通过运用外交“软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硬实力的不足,从而较好地维护了自己的利益和尊严。其经验的背后反映了支撑英国外交的某种特殊力量,正如英国前首相希思1971年所说,“···我们的特殊力量在于我们深刻理解历史,知道在恰当的时候做恰当的事”。②转引自陈乐民主编:《战后英国外交史》,第14页。陈乐民先生也总结指出,既善于适应环境的变化,又善于在变化了的环境里不与传统的利益观决绝,这是一种应变的“天赋”。③陈乐民主编:《战后英国外交史》,第14页。此论虽主要是针对英国的总体外交而言,却同样适用于理解英国的对华外交。
总结英国对华外交的经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英国奉行了基于利益目标的务实政策,采取了意识形态分歧下经济利益优先的灵活策略,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美国因素的制约和干扰,其结果是不仅有利于中英双边关系的发展,英国也谋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论及当下英国的对华政策,须要提及其近期采取的两个涉华外交举措:一是2008年10月明确承认了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100多年来英国政府首次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二是2009年1月发表了《英国与中国:合作框架》文件,称发展对华全面关系将是英国政府今后数年外交工作的“重大优先目标”,这是英方首次公开发表对华关系文件。这两个举措体现了英国对华务实外交的延续性,前者显示了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西藏问题上对中国的尊重,后者则因为文件的平等性和战略性而受到了中国方面的欢迎和肯定。
中英关系目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这是两国领导人高度一致的共识。展望未来,发展“面向未来的有活力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仍是中英双方共同努力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是对两国外交政策的考验。就英国对华政策来说,虽不能断言今后不会出现任何问题,而事实上英国社会在对华关系上一直都存在着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和主张,但这些都不是主流,它们过去没能今后也不可能主导和改变英国对华外交的主航向。因为归根结底,坚持务实对华外交既符合英国一贯的“现实主义”外交传统,更是维护和拓展其在华利益的必由之路,同样也是保持中英关系可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
Observations on Britain’s Diplomacy towards China
ZHAO Huaipu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博导
British diplomacy always stresses “realism”, and pursues goals of national interests. In the post-WWII period Britain followed a relatively pragmatic policy towards China, adopted the strategy of giving priority to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interests under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and contained the effects of America factor on its China policy to a certain extent, which protects and develops its interests in China and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Sino-British relations. In the future Britain is likely to maintain its interest-driven pragmatic diplomacy towards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