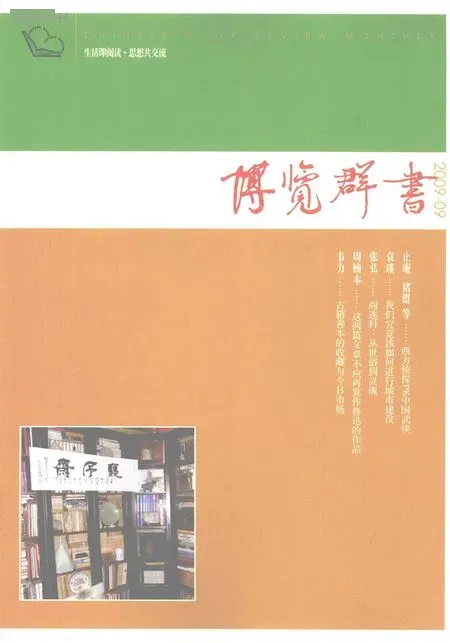许君远二题
2010-08-06○眉睫
○眉 睫
许君远(1902-1962),河北安国人。现代作家、著名报人、翻译家。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与废名、梁遇春、石民、张友松等同学。二三十年代,在北平文艺界较为活跃,经常在《现代评论》、《新月》、《北平晨报》、《华北日报》等发表小说、散文、文艺杂谈,深得丁西林、陈西滢、杨振声、沈从文等人赏识,被一些文学史家称为“京派代表人物”。后转入报界,深得张琴南、陈博生、张季鸾、胡政之等赏识、提携,先后在《北平晨报》、《天津庸报》、《大公报》、《文汇报》、《中央日报》担任编辑、编辑主任、副总编辑,为《大公报》第二代中高层决策者之一,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一度在北平中国大学、上海新闻学校、暨南大学担任讲师、教授。1945年曾以《益世报》特派员身份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1946年至1953年,担任上海《大公报》编辑主任、资料组长。1953年后在上海四联出版社、文化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工作。著有小说集《消逝的春光》、散文集《美游心影》,译有《斯托沙里农庄》、《老古玩店》等。主要作品后人辑为《许君远文集》(许杏林、许乃玲编)、《许君远译文集》(许乃玲编)、《许君远文存》(眉睫、许乃玲编)。
笔者在整理《许君远文存》一书时,发现许君远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可贵的精神品格。他的一些回忆和经历,可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史料,特辑为《许君远二题》,望方家有以教我。
王芸生转变谜题
3年解放战争期间,王芸生为《大公报》总编辑,许君远为上海版《大公报》编辑主任。1949年6月17日(《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逝世后两月),王芸生在上海版《大公报》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这彻底表明《大公报》放弃自由主义立场,甚至在宣言中自称“《大公报》基本是官僚资产阶级的”。那么,《大公报》是怎样从1948年的中间立场突然转变了呢?目前的学者普遍承认,这与王芸生的转变有极大关系。
吴廷俊先生在《新记大公报史稿》一书中有过细致的剖析。基本观点是:1948年夏之后,王芸生遭受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双面夹击,“坐卧不安,陷入了深深的苦闷、犹豫和彷徨之中”,旋经本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大公报》骨干人员杨刚、李纯青的“交谈”,“王芸生听后,十分感动,他感谢共产党不计前嫌,随即表示:‘甘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包括我本人和我能代表的《大公报》。’”一个著名的自由主义报人,就这样在短短的几次“交流”中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和立场。很快地,《大公报》董事长吴鼎昌在当年年底宣布辞去董事长一职,而王芸生则于当年11月5日悄悄离开上海。半年后,《大公报》就宣布了“新生”,这也说明此时的《大公报》已经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了。
那么,王芸生是否真的有过“苦闷、犹豫和彷徨”?他又为何选择悄悄地离开《大公报》、借助共产党的力量的方式促成《大公报》新生呢?为什么没有采用鼓动大家共同转变立场的方式?许君远在他的《自传》(现已收入《读书与怀人——许君远文存》)中对王芸生其人和《大公报》新生的情况有过回忆,或许能为以上谜题添加点材料。他说: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制造的北塔山事件,全国各报都登在要闻版第一条,我既未受到国民党新闻机关的暗示,也不曾嗅到它有什么重要,就当作一件普通消息处理。第二天国民党特务包围《大公报》编辑部,辱骂了半天,还在墙壁上写了斗大的“大公不公,正义不存”八个字,王芸生把我找去,痛责我失职。这本是我无心造成的“错误”,却替《大公报》增加了一个“罪状”。王芸生政治嗅觉比我灵敏,因此他的顾虑也比我多。他一心向上爬,我也没有这一套想法。一九四八年,上海形势不稳,国民党加紧统治,王芸生、萧乾、潘际坰等都投机逃往香港,把报馆的编辑交给我,我就当作无啥希奇地承担下来。等到上海解放,王芸生一班都以接收大员的姿态返沪,占据了极重要的地位,而把我贬入“冷宫”(资料室),我自然忿忿不平。因为我觉得在思想上,我和他们没有什么不一致,甚至有些问题,我比王芸生还要“自由”。

《许君远文存》简体版封面
以上短短的一段回忆,说明了“王芸生政治嗅觉灵敏”,能够洞察时代走向,那么他真的“苦闷、犹豫和彷徨”了吗?在《读书与怀人——许君远文存》一书中,许君远对大多数大公报人都有正面的回忆,而唯独王芸生除以上一处之外,并无提及,这是耐人寻味的。
许君远怎样成为右派
许君远成为“右派”的经历,或许能为“反右”的研究提供一些个案的信息;何况他与民国著名报人徐铸成、陆诒被定为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三大右派”,应该有研究的必要。
许君远在1957年5月21日的《文汇报》上发表《报纸应该这样干下去吗》一文中说:
去年秋天,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几位同志到上海搜集教材,和我谈了一些有关新闻业务的问题。我把过去的经历讲了一些,又把当时我与新华社上海分社一位记者会见的情形谈了谈。他们叫我把那次会见写成短文,送《新闻与出版》刊登。文章的题目是《我受了一次审》。我的主要意图是想说明记者培养之难,一个记者要常识丰富,要熟悉业务,要具备采访风度。不久我就接到人民大学来信,说我的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他们预备一一发表。
可见,许君远在1956年秋以后,就开始在报刊上“鸣放”。次年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全国开始“大鸣大放”。短短两三个月,许多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鸣放”,或发言,或受访,或写杂文,或者以其他活跃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百家争鸣”的气象一时在全国成为潮流。
这年的4月25日、5月21日,许君远分别在上海出版系统座谈会、上海市委宣传部会议上公开表达表达了对新闻管制、不受重视等问题的不满。他说:
编辑人员都是调来的,不是考的。出版处调来,出版社领导没有权考虑没有时间考虑能不能用。就是考虑亦只是政治上的问题,对专业知识方面不了解。……上海出版通俗读物的“野草闲花”这对群众没有害处,亦是精神食粮,是人民需要的。……编辑部与经理部有矛盾。多插了图,排得稀一点是浪费,《明清故事选》一书翻开来,上面是内容提要,下面是目录,行距那么密,多难看,这叫节约吗?……为什么我们这班有专业知识的出版工作者就应该不受社会重视,不受作家尊敬,也不蒙政府垂青呢?长此以往,势必造成人人视编辑为畏途,不敢问津尝试。其结果出版社徒存空名,出版物的质量将大受影响。……有一些编辑同志还是硬搬教条,强调政治意义,一碰到男女关系就不敢大胆放手,对于一夫多妻的故事,总是设法删改,使之符合‘婚姻法’的原则。对于谈情说爱的描写,更是畏之如蛇蝎,好象男女不应该恋爱,只凭领导安排就是。这对读者起什么教育作用呢?……我们这个出版社没有宗派主义倾向,倒是向作家开着大门,不像作协对我们大门禁闭。
同时,许君远还在《报纸应该这样干下去吗》中说:“毛主席的报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阅报看见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四日邀请本市各报社、电台和通讯社编辑,座谈当前新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心中极为感奋。就算是‘外行’的话吧,觉得‘鸣’出来还是比闷在肚里好些。……解放后的报纸只愿说教,忽视趣味,而趣味正是中国报纸的一种优良传统。……大部分的党报还在摆着‘党员面孔’,没有笑容,难道这就是党报必备的风格吗?……凭我局外人的看法,我感到解放后报馆机关化,新闻从业员与一般机关干部没有什么差别。大家例行公事一番,消息不必竞赛,版面不必改进。”
让“感奋”的知识分子意想不到的是,“大鸣大放”戛然而止。1957年7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右派急先锋许君远诡计多端,妄图篡夺新闻出版事业的领导权》一文。很快地,许君远与徐铸成、陆诒被定为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三大右派”,全国对他们开始了“围剿”,并尽力将他们与胡风分子挂钩。同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汇编出版了《批判出版界右派言论的参考资料》一书,便收入了许君远以上的许多言论。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于1956年秋鼓励他“鸣放”呢?
可悲的是,许君远之女许乃妍教授最近在《报人、作家、翻译家许君远》(原载《新民晚报》2010年6月13日)一文中回忆说:“在‘反右’前,他曾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邀请担当系主任与授课,只是‘反右斗争’风云骤起,未能成行而作罢。”五十多年过去了,还记得许君远“曾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邀请担当系主任与授课”,并为之未能成行深感遗憾——天真到这个地步,真有些“可笑”复“可悲”了。
被打成右派后,许君远的命运如何呢?许乃妍在文中回忆说:“父亲因此被发配到青浦饲养场劳动改造(据有关材料显示,1960年九月许君远还在青浦饲养场劳改),并受到降职降薪处分,工资降八级,后改为降七级,才60元。一家数口,日子十分难过。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父亲他老人家除了精神压力外,困苦的生活也十分难奈,有时只能靠变卖所存书籍度日。”1962年6月,许君远全身瘫痪,并患肺炎,不久于当年9月9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