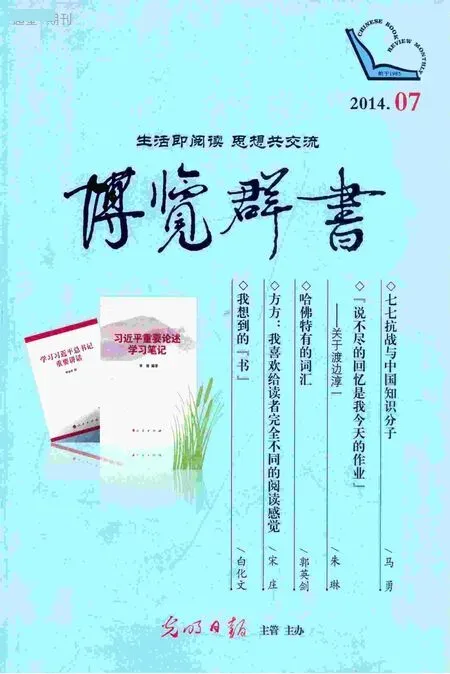谁应该感谢谁——从赵作海被要求感谢说起
2010-07-15张绪山
○张绪山
河南农民赵作海蒙冤身陷囹圄11年,由于原来的“被害人”偶然“复活”,才使冤情得以大白于天下。据报道,赵作海出狱后,有“法院带来的记者”问他“要感谢谁”,他说感谢法院,感谢党。记者再问还要感谢谁,赵作海一时僵住了。众人散去后,他坐立不安,反复躺下又起身,最后喃喃自语:“为什么要感谢?我不感谢。”
对于记者追问赵作海“要感谢谁”,以及赵本人被动地表达“感谢”,有人评论说,赵作海被那个记者“诓”出了一个感谢,因为这样的感谢未及深思,所以后来又被他自己否定了;记者的提问有倾向性,即在提出的问题中悄悄地置入自己的倾向、结论,在逻辑学中属于一种谬误,叫作“复杂问题谬误”。易中天也同意这一见解,并做了更通俗的解说,认为记者的提问方式应叫做“陷阱问题”和“诱供方式”,乃是强者对付弱者的方式。还有人认为,记者既是“法院带来的”,那么他的发问不过是完成上级交代的“差事”而已。
对这一细节,如果我们的认识仅及于此,恐怕就过于肤浅了,因为它背后的丰富的文化意义并未得到深刻剖析。类似的例子是,在有关矿难事故的报道中,被埋在井下的挖煤工人获救后,几乎毫无例外地会有记者追问“有何感受”,而获救工人也几乎毫无例外地表示“感谢”党和政府。赵作海被追问“要感谢谁”的情形并非孤例,而是司空见惯、国人早已习以为常的“经典”画面。
这种被要求感谢的现象绝非现在才有,相反,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存在至少两千年之久了,乃是一种恒常现象。我们且从大家熟悉的著名的岳飞冤案说起。岳飞被冤杀后20年,宋孝宗为他平反。这本来是一件理应做的事,宋孝宗应该为其祖上冤杀岳飞表达歉意才对,未料他却对岳飞后人说:“前世流人,亦有父子兄弟死则追褒,生则宠秩,如今日者乎?国家雨露之恩,与天通矣。……尔之一门将何以报朕哉?”很显然,宋孝宗不仅要求岳飞后人表示“感谢”,而且要以实际行动“报答”他的“与天比高”的“雨露之恩”。在这里,为蒙受冤屈的臣下平反竟成了可以要求回报的“大恩德”。可以想见,彼时的岳飞后人除了口呼万岁、感激涕零外,不可能有其他的表示。实际上,即使口含天宪的“天子”没有追问到这份上,想那饱受“精忠报国”政治思想教育的岳飞后人,也一定会五体投地,敬谢浩荡皇恩,并信誓旦旦地表示,愿为朝廷的利益而赴汤蹈火,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岳飞冤案平反事件与赵作海冤案昭雪事件可谓如出一辙:第一,被要求感谢的一方都蒙受了不白之冤;第二,要求他人表示感谢者似乎都对自己的要求理直气壮,认为蒙冤者表示感谢乃是理固当然;第三,蒙冤者都是弱者,除了表示感谢外并无其他选择。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曾频繁出现,所反映的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传统文化心态的具体表象。
这种民族心态,直接导源于支配中国亘两千余年的政治伦理,即以“天道”为权力基础的“权力神圣观”。在这种前现代的政治伦理中,皇帝是“受命于天”的天子,是人间神,代表天意对民众进行统治,其权力具有无可怀疑的“神圣性”;皇帝权力的“神圣性”使代表皇帝行使权力的整个权力集团也具有“神圣性”。所以,权力机关对民众所做的一切都体现着“受命于天”的皇帝对民众的恩赐,所谓“皇恩浩荡”表达的正是这种含义。由于有“天意”的存在,小民对“神圣权力”时刻怀有敬畏和“感谢”之情就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了。
代表“天意”的“神圣权力”,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体现的是“神圣的正义”,所以“神圣权力”对破坏既定“神圣”秩序的“犯上作乱”者实施的惩罚就是“恭行天罚”。儒家虽有“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说法,将“民心”与“天意”联系起来,但“民”这个整体概念之下的无数具体的个人,绝不可能被权力当局视为“天”,如果不被视为“刁民”,而只是被视为“斗筲之人”、“野人”就算烧高香了。在“神圣权力”集团看来,“恭行天罚”落实到罪有应得的犯罪者头上,是其本身“神圣性”的表现;而冤枉了无辜者,为蒙受冤屈者平反昭雪,“过而能改”,更是其“圣明”、“神圣”的表现。换言之,以“受命于天”自居的权力控制者,将自己的任何行为视为理所当然的神圣行为,不管“神圣权力”是否犯错或犯罪,它的神圣性都是不能怀疑的。这就是旧政治伦理要人“感谢”乃至”回报”的潜在伦理基础。
这套政治伦理经权力集团长期灌输,已经浸透到整个民族的思想深层,积淀为一种思维定势。1983年有一报道:一位在“文革”中蒙冤的农村教师在获得平反后,感激之情不能自抑,于是付诸实际行动:在家里办了个图书馆,并在门上贴了一幅对联:“历十载寒窗,经廿年冶炼,多亏三中全会精神,喜有今日;订几份报纸,购百册图书,提供四邻子弟学习,敬报党恩。”这位农村教师为家乡教育事业做贡献的行为无疑是高尚的,但其心态却是旧传统的,它向人们展现了一幅传统臣民形象图:“神圣权力”虽是冤案的制造者,但仍然是居高临下、皇恩浩荡,而小民虽无辜蒙冤受屈,历经磨难,却仍对“神圣权力”的正义性不敢有丝毫的怀疑,相反,极尽谦卑、忠顺之状,感恩涕零地表示“感谢”。这场景曾千万次地出现中国的史册上,我们读历史时常常遇到。
与此相对应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反思“文革”浩劫时流行的一个很著名的理论:权力集团错整了人,被说成是“母亲打儿子”;既然是母亲打了儿子,所以受到迫害的数以千万计的儿子们就不必计较了。于是一切都涣然冰释,事情好像没发生过似的,再没有人去反思那可怕的悲剧,剩下的就是感谢权力集团将人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并以至诚之心歌颂“过而能改”的权力集团的英明与伟大。时至今日,这种心态还没有得到改变。不久前,一位运动员在国际比赛获奖后,在获奖感言中将“感谢”首先献给了“父母”,遭到体育官员强烈批评,认为应该首先感谢党、国家、政府和领导,然后再感谢父母。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权力神圣观”之下的“君臣礼制秩序”意识是何等根深蒂固!
“神圣权力”的去魅化是现代公民社会建立的重要前提之一。只要“神圣权力”观念存在一日,“皇恩情结”就不可能消除;只要“皇恩情结”存在一日,“谢主隆恩”就是必须履行的行为礼仪准则。所以,记者对赵作海提出“感谢”要求,并非刻意为之,乃是传统政治伦理下的“臣民心态”使然,是下意识的行为。有报道描写赵作海获释后的一些习惯性的“身体反应”:对前来表示歉意的领导“深躬”。这一行动就如同前面所说的农村教师在获得平反以后表达的“报恩”行动一样,都是传统政治伦理塑造的结果。
不过,令人稍感欣慰的是,赵作海出乎本能的喃喃自问“为什么要感谢”,最后得出结论“我不感谢”。这个行为细节在二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它使人们看到了历史进步的影子,以及新时代来临的一缕曙光。在“人民主权”的现代社会中,大权在握的所有官员(包括总统),都不是“受命于天”的“神圣物”,相反,权力导致的欲望扩张,使他们时刻都有可能犯错乃至犯罪,因此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公共权力对民众犯下错误、改正错误,并对蒙冤者作出赔偿,无关乎权力集团的“伟大”与“圣明”,相反,乃是天经地义、理固当然,公民无须感恩涕零;对公民犯下错误乃至罪行的权力机关,如果固守传统的“权力神圣”旧政治伦理拒绝认错,乃至居高临下地要求人民以屈服的“感激”姿态无条件地承认其神圣性,乃是双重的犯罪。在赵作海冤案中,应该表达感谢的,应是那些被人民授权的权力机关,它们应该感谢人民对其错误行为的“宽容”,并引以为戒,力避重蹈覆辙,冤案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