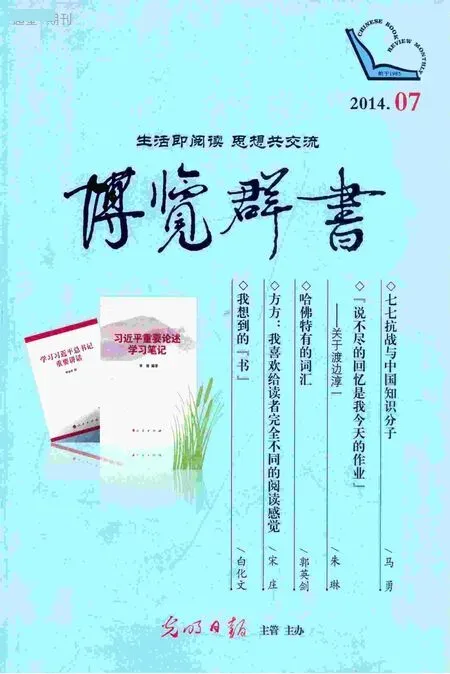关于轻性论文、学术随笔的通信
2010-07-15陈学勇
○顾 农 陈学勇
学勇兄足下:
上次你在电话里说看到我在《博览群书》以及南北几家报纸副刊上发表的学术随笔,谬加赞许,鼓励多写,这后一点甚合我意。致力于此,慢慢争取形成规模,乃是我退休后的野心之一;可惜不容易写得自己满意,总有些学院派的流毒没有彻底肃清——腰肢尚板,面肌仍硬,许多就题发挥的话没有说透,总之,犹抱琵琶。什么时候能把身段彻底改造过来,胜利完成老派书画家之所谓“衰年变法”,那就好了。
还有一个野心是大写轻性论文,也争取慢慢形成规模。近年来在《文史知识》、《古典文学知识》、《鲁迅研究月刊》、《新文学史料》等处发表的一些长长短短的零星文章属于此类。我看你不少关于现代女作家的考辨论述且已成书数种者,也属于此类。篇幅不甚长,不安排什么参考文献和边注,单刀直入地来讲自己的研究心得,文字也比较自由——但不能自由到随笔的份儿上,这就是我心目中的轻性论文。
区分学术随笔与轻性论文,是根据鲁迅的意见。现在人们往往将鲁迅的文学创作(《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编》)和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以外的文章统统称之为“杂文”。其实这个办法未必妥当,可惜积非成是,恐怕已经不容易改变了。鲁迅本人曾经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过“杂文”一词。从广义来说,“杂文”是编年体文集中的各种文章,不管其文体如何,夹杂地编在一起。在这样的意义上,“杂文”是一个集合的概念,而非文体的一种,也不能用来指某一篇具体的作品。二是文体意义上的“杂文”,其中又可以细分为杂感、随笔和轻性论文三种小的类别。由于这三者之中杂感最为多见,有时也就直接称之为“杂文”——这是狭义的“杂文”。
在文体的意义上,现在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是鲁迅的随笔(其中自然包括学术随笔)和轻性论文。鲁迅在提到《坟》这本集子的时候,自称其中是“论文和随笔”(《三闲集·鲁迅译著书目》);他又说《二心集》中也有论文——这些就是所谓“轻性论文”,亦即比较灵动、可读性比较好、有别于学院派(或称学报体)的那种论文;而《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等,他自称为杂感集。《三闲集·序言》写道:“我的第四本杂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来已在四年之前了。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编此后的杂感。”这种提法,就是把《坟》那种纳收轻性论文和随笔的集子排除在外的。
所谓“轻性论文”正是鲁迅自己的说法,他在1933年11月12日致杜衡的信中说:“轻性的论文实在比做引经据典的论文难,我于评论素无修养,又因病而被医生禁多看书者已半年,实在怕敢动笔。”学院派论文是非要引经据典不可的,有些甚至全靠各路引文支撑着,从中可以见学问,却未必就有思想,也未必有意思。从当下的风气看去,此种不大有个性的论文如想抄袭,比较容易,如果懂得上网下载,更是只要费一点吹灰之力即可。学术界反抄袭如果没有体育界反兴奋剂那样的力度,“文章一大抄”的歪风只怕要愈刮愈烈。
现在不少高校专以此种学院派论文来考核教师,凡此种成果以外的东西,一概不予承认,更厉害的则凡不在所谓核心期刊上发表的一概不予承认。在这种严厉的二不主义笼罩下,路子愈走愈窄,而真正高明的学院派论文却不甚多见,不少高校学报里垃圾成堆。
真正的学院派论文当然是重要的,学者也应当写这样的论文。鲁迅就写过《〈嵇康集〉考》等正儿八经的论文。你我先前亦多年干这种活儿,不免厌倦,所以现在多来点轻性论文正合适。
轻性论文不大引经据典,引文虽然免不了也得要有一点,但很有控制。所谓“轻性”,实为举重若轻,写此种文章必须胸有成竹,对所论的问题有深刻的观察和透彻的把握,思维活跃,发表有意思的分析和评论,而且还要讲究一点文采和意趣。
写轻性论文同样要有学问,要多看书,但绝不仅以材料取胜,倒是义理、考据、辞章全要在行,其中一、三两条尤为重要,而考证也不能是迂夫子式的纯述证,而往往多作点到即止的辩证,容易引人入胜。鲁迅写过不少轻性论文,如论社会问题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论“他妈的”》,论思想问题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从“别字”说开去》,论文学问题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论讽刺》,论文学史问题的《破〈唐人说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如此等等。与杂感、随笔相比,轻性论文总是要略为长一点。
杂感一般来说都相当短,所以鲁迅又称为“短评”。除了《热风》等五本以外,《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也都是杂感集短评集。在这些书中,也可能有少数例外,如《三闲集》中有两篇“夜记”——《怎么写》和《在钟楼上》,应当算是随笔。鲁迅在《三闲集·序言》中说:从写作时间上来说,两篇“夜记”本应收入《而已集》,但当时想“另成一书”,所以没有编入,而后来那样的随笔未及多写,现在就将它们收在这里了。可见鲁迅在编集子的时候,很有些文体方面的考虑,只是因为形势不容许他太多地顾及文体,只好采用编年的方法,“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起”(《且介亭杂文·序言》),所以此后的《二心集》、《南腔北调集》和晚年的三本且介亭集,全都是这样编成的,其中包含了若干杂感或曰短评,也有不少随笔。我将来如果编新的集子,拟只取学术随笔和轻性论文。
杂感自然是鲁迅杂文的主要构件,瞿秋白编选鲁迅杂文,书名就叫做《鲁迅杂感选集》。近人对鲁迅杂文进行艺术上的分析,也往往多以杂感作为讨论的对象。学鲁迅的路子写文章的人,也多半写杂感,亦即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某种艺术性的短篇评论。而随笔和轻性论文,则大抵被忽略了。
随笔在《坟》、《三闲集》、《二心集》中已有若干,到《南腔北调集》和三本且介亭集里,就更多一些。所谓随笔,一方面来源于中国古代的笔记,另一方面更多受英国的Essay的影响,写法极其自由,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可以叙事,可以议论,可以抒情,篇幅长短不拘,当然一般来说要比短评长一点,结构松散一点也无妨,大可随便谈谈,慢慢道来。鲁迅的随笔大抵以议论为多,富有学术内涵,写法雍容,在侃侃而谈中让读者增长知识,提高认识,得到启发、教益和愉悦。《拿来主义》是鲁迅随笔的代表作之一,几篇“夜记”和“题未定草”写法更是典型,文章平易生动,联想丰富,比喻杂出,而且像不少外国随笔那样,在从容议论之中,“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话,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容易疲倦”(《华盖集·忽然想到(二)》)。鲁迅晚年尤喜作读史随笔,对史事作意味深长的分析和评议,行文委婉老辣,无学究气,亦无火气,谈言微中,令人想起眼前的现实,像《且介亭杂文》中的《儒术》、《隔膜》、《买〈小学大全〉记》等篇都是。我最想学习的正是这一路随笔,可惜学不到手。当然我们也可以我用我法,不必完全像鲁迅。
随笔包括学术随笔在鲁迅晚年所作杂文中比重增加,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新动向,这应当是表明他晚年与时俱进,为文之道更上层楼。《且介亭杂文》中的《看图识字》、《阿金》、《病后杂谈》诸篇是鲁迅本人明确指为随笔的,准此以推,他的《拿来主义》、《说面子》、《脸谱臆测》以及上面提到的评史诸文也应当算随笔。同鲁迅的轻性论文一样,他的学术随笔如今似乎也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继承。你我当就这一方面多做点事情。
明天是劳动节,最近搞什么劳动?匆匆,再谈。
颂安!
弟 顾农再拜
2010年4月30日
顾农兄:
来示诵悉。平时我们电话里断断续续交谈的话题,经兄一写,显豁得多了。
兄依据鲁迅提出轻性论文概念,呼吁多写轻性论文、学术随笔,甚好。不过,写这类文字并不容易。文化环境是个大掣肘,学术评价机制掌握在不懂学术或不懂文科学术特点的官员手里,这个环境不作大改变的话,庶几乎难矣。即使有开明的领导,他也无奈当下钢铁般的评价机制。好几年前我们领导读到我在《文汇读书周报》“专稿”版一篇长文,他是懂行的,看出文章的学术性。可是碍于政策明文规定,凡不在指定的几种大报上发表一律不得以学术成果上报。他觉得可惜,建议再到哪个学报登一次。我心领了好意,却不想粘“两投”的腥气。现在更要求所谓的“核心期刊”,真是形而上学到家了,也正是官员们郑人买履式的偷懒。核心刊物的文字,未必篇篇都有多强的学术性,非核心刊物有时也能读到很具学术见识的文章。本来这是显而易见的事,他们偏偏不看文章,只问标签。记得有一阵我常常将研究中的边角料写成普及性文章登在南京的《民国春秋》杂志,这是一种很普及的刊物。然而不知怎么的,它竟然归属核心期刊。同事们奇怪我,从来不作成果上报它们。按标签似乎名正言顺,可哪里好意思冒充羊肉。你我不必再为职称为项目为其他什么去写那类学报论文了,而需要炮制它的同行们比比皆是,他们难以超脱的,不必苛责。
我说难矣,作者自身素养也是重要的原因。作轻性论文或学术随笔,义理之外尚需辞章。听一位杂志编辑叹苦,办刊既要保持学术品位,又要赢得众多读者,谈何容易!稀缺的是作者。别看到处有教授,他们干瘪的八股文章令读者敬而远之;文字漂亮的中青年作者也算济济,而且不乏快手,可是学术含量就很有限了,多的是二传手。兄说到鲁迅兼擅论文和随笔,我想,其缘由乃集作家、学者于一身。何止鲁迅呢,沈从文的《新诗的旧账》《性与政治》也是此类的漂亮文章;还可以举出朱自清的《新诗杂话》,谈诗的感觉,诗的哲理,诗的幽默,诗的朗读,十多篇成一系列。郁达夫、闻一多、梁实秋、施蛰存、朱光潜、李健吾,无不有漂亮的轻性论文、学术随笔。举不胜举,一个时代形成的风尚。到80年代,健在的老作家笔下仍余韵悠悠,施蛰存《丁玲的“傲气”》就是。我在学生时代读过一本刘大杰关于《红楼梦》的小册子(书名忘记了),虽不能识得其学术价值,但十分喜爱它的文采,阅读的喜悦美好的回忆至今犹在。这些作家,也都在大学里教书或教过书。王蒙针对作家的学养欠缺曾经提出过作家学者化的命题,那么针对今日的文学研究人员,是否也可以希望他们作家化?当然,难处在于文学创作不算成果,他们岂敢分散精力。考核中文系教师排斥文学作品,是由来已久却不大高明的规则。
文学评论文章正襟危坐起来,好像起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那时一切学习前苏联老大哥,文学更得努力地学。日丹诺夫们的观点、思维,乃至文风一股脑儿影响我们的作者,文章里性情没有了,特色没有了,仿佛一个模子铸的标准件。再加上火药味儿,便造就了批评家姚文元这个样板,面目可憎。初写文学评论的青年不辨良莠,多争相仿效姚的路子,一代文风大变。其实前苏联除正统的日丹诺夫,另外还有不像他们那么写的人,例如帕乌斯托夫斯基。其《金蔷薇》翻译到中国很受文学青年欢迎,也是我学生时代喜爱过的一本书。前些年重新出版了这本书,听说依旧很受欢迎。80年代一批新锐引进西方概念,其中还夹杂了自然科学的概念、术语。运用于文学评论,它的贡献这里不论,那种诘屈聱牙的文字竟也赢得追赶时髦的青年学者热衷,很有几位新秀以文字生涩著称。然而终究太为过头,不能在学界生根,只作今日谈资罢了。
文学评论,尤其是作家、作品的评论,应该写得漂亮,“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它终究不是思想评论、社会评论、经济评论。诚然,探讨学理的文章,讲究全面、周密、深邃,就不宜苛求它文字的可读与否。有的论题,必须繁复论证才行,不然殊难阐释透彻,不足以说服人,亦难见其“重”。例外也是有的,记得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厚厚一大本,印象里文采斐然,读得不累。兄是治汉魏晋那段文学的,《文赋》《文心雕龙》皆杰出的例子。“神思”、“风骨”、“情采”诸篇,所涉都是不易说清楚的文学道理,而刘勰条分缕析,词采飞扬。以形在江海心存魏阙的比喻解释“神思”题目,已经成了经典。古代文论里不少名篇,曹丕的《典论·论文》,韩愈的《答李翊书》,即轻性论文或随笔。有的短小文字集腋成裘,成为传世名著,如谢榛的《四溟诗话》、王夫之的斋诗话》。说到诗话,宋以降蔚然成风,它和后起的词话,酿成颇具中国特色的批评文体。这两年举国上下大讲“国学”,讲得内涵和外延越来越叫人糊涂了。古代文论的传统是否包含其内呢?即使不用国学的旗号,我们也应该发扬诗话、词话的这个传统,它们虽短小,却脍炙人口,且多隽永语句。
从轻性论文、学术随笔写作本身,兄说了与正格论文的差异,这差异还取决于读者对象不同。同行专家,自可拿高头讲章,慢慢与之穷究其理。若一般文学爱好者,对正格论文是没有兴趣和耐心的。学问不应该总关在学院里,研究的提升、发展,少不得专家做些普及文字,水涨才能船高。但是这文字要做得一般读者喜爱看,专家读来也不无启迪,所谓雅俗共赏,实非常不易的事,学养和才气缺一不可。兄宜担此重任,弟翘首以待。
打住了。正如我们时常感叹的,有些本来是基础常识的东西,如今还得费舌去絮叨。看来,再怎么絮叨它,效果如何是不太敢乐观的,就像天天指斥学术腐败,它照样地腐败,并无收敛之势。文风尚不至于如此吧。
犬子回来看望病中母亲,我岂能不围着她母子劳动?为此信迟复了几日,见谅。谨颂
衰年变法成功!
弟学勇
201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