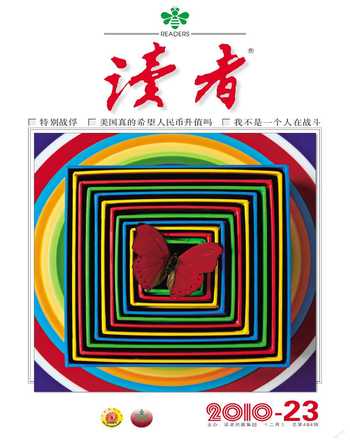景福阁的月
2010-07-04叶广芩
叶广芩
儿时,我住在颐和园大戏台东侧的小院里,那里有我的三哥和三嫂,他们都在园内工作。我真正的家是在城里,那里有父母亲。三哥轻易不回城里的家,母亲偶尔来送些东西,也是搁下就走,三哥不是她的孩子。父亲也来,比母亲来得少,与母亲不同的是,他往往要在园子里住些日子,以慰藉我这个终日孤寂的小人儿。每逢这时,我便感到快活无比。
晚上,父亲和我睡在外间的北炕上,炕是宫廷中常见的式样,长度与屋宽相等,整个儿嵌在北墙上。雕花的炕架,低垂的炕帘,那帘像戏台的幕布,一放下,内里便黑咕隆咚,外面天亮了也不知道。父亲与我睡了两日,便说这炕“不干净”,使他净做噩梦,说这炕自砌成以来,上面不知睡过多少恩恩怨怨的人,百年前的事全到梦里来了。为此三哥借了玉澜堂门首西边的一间小屋让父亲去睡。那里是值班室,有两张木板床,没有古老的炕。父亲只住了一天,又回来了,他对我说玉澜堂里怨气太重,戊戌政变后,慈禧在霞芬室和藕香榭殿内砌了高墙,专做关押光绪皇帝之所,不宜人住。接着他就玉澜堂的夜晚而发挥,编出一个与光绪品茗谈论古今的故事,内中自然还会有猪八戒和黄天霸出现,甚至连拖着大辫子的自尽于昆明湖的一代文豪王国维也由水中踏月而来,加入清谈之列。于是,出自父亲口中的玉澜堂之夜,人鬼妖聚集,热闹非凡,实实地让人向往了。如今看来,父亲以其艺术家的丰富想象力,深入浅出地为他的女儿编出一个又一个与“大灰狼”“小红帽”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的故事,多少深厚的历史文化知识,就这样由玉澜堂之夜溢出,潜入一个孩子的心田。
一年中秋,父亲恰住园中,便携了我与三哥、三嫂同去景福阁观月。景福阁原名昙花阁,位于万寿山脊之东端,是听雨赏月的绝佳之地,最受乾隆喜爱,后来被慈禧重修改建成厅堂,赐名景福阁。年少的我无赏月雅致,为三嫂所携之糕饼吸引,一门心思只在吃上。当时我口啃糕饼,偎依在父亲怀抱,举目望月。居亭台楼阁与亲情的维护之中,此情此景竟令我这顽劣小儿也深深感动了。长大后读了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更觉那逝去光阴的可贵,以至每每见月,便想起景福阁。那美妙绝伦的景致当还存在,而那恬静温馨的亲情却是再不会有了。
那夜的月似乎给了我某种启示。父亲第二日返回,说是要去河北彭城。我从内心生出难以割舍的依恋,这种依恋的深重超出了一个六岁孩子的经历。我执意要与父亲同归,置三哥三嫂的阻拦于不顾,后来索性以号啕大哭来达到目的。三哥说:“今儿这孩子是邪了。”
那晚我终于与父亲手拉着手向颐和园东门走去。天上的月亮又圆又亮,照着我和父亲以及我们身后那些金碧辉煌的殿宇。父亲穿着春绸长袍,我穿着三嫂给临时加上的小大衣,一老一小的影子映在回家的路上。我把父亲的手攥得紧紧的,一刻也不松开,直至在车上睡熟。第三日父亲离家去外地,我和母亲将他送至大门外,母亲怀中还抱着两岁的小妹妹。父亲一步一回身地走了。我当时却突发奇想,赶上去陪着父亲走了很长一段路,一直将父亲送到北新桥,送上开往前门火车站的黄牌有轨电车。父亲站在车尾向我挥手,示意我快些回家,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那颗小小的心里充满了悲哀。
那一别,竟成了生死的诀别。我是父亲的孩子们当中最后见到他的一个。不久,父亲因突发心脏病,卒于彭城峰峰矿区。噩耗传来,全家惊呆。此事谁都知晓,唯独瞒着多病的母亲。母亲系一毫无主见的家庭妇女,所恃以为活者,唯指父亲,如今生机已绝,待哺何来?我欲哭不敢哭,欲言不能言,含酸自咽,仰望中天,一轮月依然是朗朗地照着,让人不解。人的长大是突然间的事,经此变故,我稚嫩的肩开始分担了家庭的忧愁。因无直系血亲奔丧,全凭在彭城的一位堂兄做主,将父亲的棺木丘封在峰峰矿区滏阳河岸。年年寒食,我都与母亲在路口烧些纸钱,祭奠父亲的亡魂;岁岁中秋,奠香茶一盅、月饼数块,徒做相聚之梦。随着岁月变迁,年龄增长,内心负疚愈深。对父亲,我生未尽其欢,殁未尽其礼,实是个与豚犬无异的不孝孩子。
“文革”期间,京畿之地的祖坟被夷为平地,祖先骨殖荡然无存。父亲坟茔远在峰峰,幸然得以存留。后来,当地发来急电,因要征地建楼,父亲的棺木需要迁移,逾期不迁,将按无主坟墓处理,就地深埋。父亲有过三位妻子,子女也着实不少,然而众子女当时均是被揪斗、关牛棚、进学习班的对象,几乎找不出一个“干净”之人,无人能办此事。我虽年轻,亦顶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帽子,在荒凉的黄河滩充任猪倌。与兄长们相比,我毕竟有活动自由,便请假迁坟。队长出自恻隐之心,听了我的陈述,又念及我父乃一社会文人,非“地富反坏右”之类,慨然应允。我至今仍感念此君,他完全可以举出一百条理由不准我假,如若那样,我今日将去何处寻觅亲爱的父亲。
我和由汉中而来的妹妹前后脚到达彭城。陌生的地域,陌生的语言,粗硬的饭食,我在简陋的小土屋里便想见父亲昔日的艰难。不是出于对事业百折不挠的追求,他不会来这里。因事情急迫,那位堂兄已代尽子孝,做了艰巨的启坟捡骨工作,我们到达时,父亲的骨殖已被分别用纸包了,装在一口纸箱中。追念前欢,想到二十年前给我编玉澜堂故事、在景福阁拥我赏月又在电车上挥手作别的父亲,现已变做大大小小的纸包,我不禁悲从中来,泪如雨下。父亲去世后,我又是孩子们当中第一个见到他的。是我将父亲送出京城,又是我将父亲接回家乡,送归母亲身边。似乎是冥冥中命运的安排,是我与父亲不解的缘分,命该如此,无人替代。
峰峰矿区有响堂寺石窟,料理完父亲的事,我漫步上山,去寻找父亲的履痕。是夜,夜凉如水,月光如银,衰草寒烟中那些北齐时代的艺术珍品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我料定,这必是父亲长久驻足之处;也料定,父亲猝然倒在四千余尊精美的石佛之中,虽无子女在身边,亦当含笑而去了……山间腾起的烟轻轻向我拢来,那其中有父亲的气息。头顶圆月,与昔日无异。我感觉到了,父亲就在我身边。遥望北天,不知月照景福阁的此刻,廊下可坐着我与父亲?
(王迪摘自《文艺报》2010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