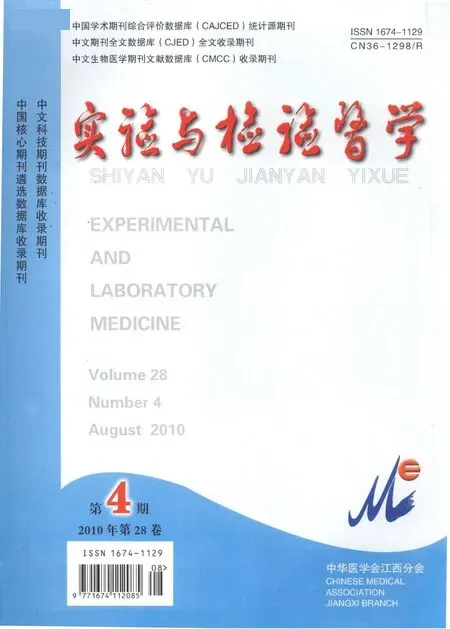广州管圆线虫病的传播与流行研究进展
2010-04-12荟综述仇锦波审校
王 荟综述,仇 昊,仇锦波审校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广州圆线虫病(Angiostrongyliasis cantonensis)是一种人畜共患寄生虫病,由广州管圆线虫(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引起,主要分布于热带、亚热带地区;其终末宿主是鼠类,中间宿主为软体动物。该虫在人体内一般不能发育为成虫,其幼虫和童虫侵害中枢神经系统,从而引起嗜酸性粒细胞增多性脑膜炎或脑膜脑炎,还可损害肺、眼和鼻等器官组织;然而在特殊情况下也能在人体内发育为成虫[1-3]。1933年,我国学者陈心陶在广州家鼠及褐家鼠肺内首先发现本虫,并命名为广州肺线虫 (Pulmonema cantonensis)。1937年,日本学者Matsumoto在台湾鼠体内发现,故报道为鼠血圆线虫(Haemostrongylus ratii)。直至1946年,才由 Doughery最终定名为广州管圆线虫。1944年,Nomura和Lin在台湾发现首例人体广州管圆线虫病;而大陆的首例广州管圆线虫病则是由我国学者何竞智于1984报道的[4-8]。
1 广州管圆线虫的形态特征与发育过程
广州管圆线虫白色,雌虫长约30mm,宽约0.5mm;雄虫较小,长约20mm,宽约0.3mm。虫卵椭圆形,大小约为75×41μm。虫卵随血循环到肺动脉血管内发育。孵出的第一期幼虫穿过肺毛细血管壁进入肺泡,沿支气管、气管上行到咽喉部,被吞入消化道后,随粪便排出体外。排出体外的第一期幼虫在潮湿或有水的环境中可存活3周左右,被软体动物(螺类和蛞蝓)吞食或主动钻入其体内。1周后,蜕皮为第二期幼虫;再经1周发育后,即蜕皮为第三期幼虫(感染期幼虫)。当终宿主鼠吞食含感染期幼虫的软体动物或饮用了被污染的水后,幼虫即可在鼠胃内蜕鞘,并进入肠壁的小血管,经肝(腔静脉)或淋巴管、胸导管至右心,再经肺循环至左心,进一步到达全身各器官组织。但多数幼虫均沿颈总动脉到达脑部,并穿过血管壁,在脑组织表面窜行。广州管圆线虫在人体内的移行、发育过程大致与在鼠类体内的相同[1、2]。
2 广州管圆线虫侵入人体的途径及其感染方式
福寿螺是广州管圆线虫的主要中间宿主,该螺原产于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通过巴西华侨引进台湾,于20世纪 80年代后期传人我国广东。它的适应性和繁殖力极强,既可以生长于流动的水域,也可以在污水、田园里孳生繁殖。该螺营两栖生活,夜间活动频繁,雌螺于晚间爬上水生植物的茎、叶、池塘壁等处产卵,每个卵块约含1 000多个卵,呈粉红色。由于产卵量大,故很容易扩散、流行。广州管圆线虫的其他中间宿主还有褐云玛瑙螺、蛞蝓、皱疤坚螺、短梨巴蜗牛、中国圆田螺和方形环棱螺。同时,黑眶蟾蜍、虎皮蛙、金线蛙、蜗虫及淡水鱼、虾和蟹等则可作为该虫的转续宿主。
人体是广州管圆线虫的非正常宿主。主要因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广州管圆线虫第3期幼虫的淡水螺、鱼、虾或被幼虫污染的蔬菜、瓜果和生饮被污染的水而经口感染。此外,用蛙、蟾蜍肉敷贴疮疡疾患等也可感染。当人食用含有这种寄生虫幼体活体的食物后,幼体便可穿过人体消化道壁进入血管,随血流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并继续生长、发育,引起中枢神经系的损害和炎症反应。若虫体在皮下移行,便可引起局部触痛和感觉异常;若移行到眼部,则可致视力下降等眼部病症。在临床上,广州管圆线虫病患者多表现为以中枢神经系统损害为主的脑膜炎症状。广州管圆线虫引起的炎症反应有3大特点:①脑血管扩张。尤以蛛网膜下腔的静脉为甚,有时可引起脑血管栓塞;②虫体周围常有大量嗜酸性粒细胞浸润。有时,还可形成嗜酸性肉芽肿或脓肿;③死虫周围有很多单核细胞、巨噬细胞侵润。在受损部位,还可有淋巴细胞、粒细胞及浆细胞浸润,甚至形成肉芽肿[1-4]。
3 广州管圆线虫病的传播与流行现状
广州管圆线虫引起的嗜酸性粒细胞增多性脑膜炎在东南亚及太平洋岛域、非洲、加勒比海地区较为常见;在其他地区也有散在病例发生[5-8]。2004年,在欧洲国家瑞士也报道了该病[9]。迄今,全世界报告的病例超过3 000例;尤其是泰国,估计年发病例逾数千之多。在我国,广州、香港、温州、上海、北京、天津、黑龙江、辽宁、海南、云南、福建等10多个省(市)也均有本病的报道。例如,浙江温州于1997年就有42人在饭店因食用福寿螺而集体出现头痛、伴躯体多处游走性疼痛等症状;2002年,在福建长乐市有8名中、小学生因食用烘烤的福寿螺而出现发热、肢体疼痛、头痛、头晕、嗜睡、恶心和呕吐等症状;同年,福州市某单位职工在酒楼食用褐云玛瑙螺(俗称“东风螺”),其中有20多人出现以头痛、四肢无力和皮肤触痛等为主要特征的“脑膜炎”病症。最后,以上病例均被诊断为广州管圆线虫病。2006年8月,北京爆发的广州管圆线虫病也是由于食用了未熟透的福寿螺所致[10-13]。
全球气候变暖对本病的传播与流行可能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4,15]。21世纪以来,广州管圆线虫病的流行及其防治问题已经引起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关注;我国卫生部门和世界卫生组织均给予了高度的重视。2003年,国家卫生部已将广州管圆线虫病列为我国的新发传染病;2005年,又进一步告戒人们:要高度警惕包括广州管圆线虫病在内的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食源性寄生虫病的传播与流行。
4 防治对策
目前,本病尚无特效治疗药物,故主张采用对症治疗和支持疗法。但黄晓红等证实:阿苯哒唑和甲苯咪唑不失为治疗广州管圆线虫病的较好药物,与皮质类固醇(corticosteroid)联合应用则疗效更佳[10~11]。本病的预后多良好,死亡率较低(<0.5%)。预防该病的关键在于加强卫生宣传,提高国民的自我保健意识,不吃生的或半生的螺类、蟹、蛤蝓及蛙类、淡水虾等,严防病从口入。另外,被螺类污染的蔬菜也有可能传播之,所以也不宜生吃。因为鼠类是重要的保虫宿主,故灭鼠对预防本病有重要意义[16~20]。具体防治措施如下:
4.1 提倡良好的饮食习惯,严防病从口入 预防本虫感染并不困难,只要不生食淡水螺和易感染这种寄生虫幼体的淡水产品、不喝生水、不生吃未达到生食标准的蔬菜,并注意在加工、保存食物的过程中避免交叉污染等,就可能杜绝广州管圆线虫感染。
4.2 改善水产品养殖环境,切断传播途径 由于淡水螺类和鼠类分别是广州管圆线虫的中间宿主和终宿主,所以在放养鱼、虾前要清除池塘底层的杂螺,并进行消毒处理。同时,对于池塘周边的环境也要彻底整治,以防止鼠类粪便污染水源,切断传播途径,保障水产品的质量和食用安全。
4.3 加强监测力度,做好防控工作 为防控广州管圆线虫病,必须加大对广州管圆线虫等水生动物食源性寄生虫的监控力度,从“池塘到餐桌”全程把好水产品质量、安全关。为此,有必要尽快出台相关法规,加快建立、健全水产品检验检疫机构及其队伍,加大财政专项投入,加强卫生、工商、水产等相关部门的信息沟通,联手做好对该寄生虫病的监控和防治工作。积极开展食源性水生动物寄生虫病防治科研。
4.4 目前,国内对广州管圆线虫中间宿主适生范围的预测、宿主传播能量的评价、宿主易感性的监测和研究仍比较滞后,有的甚至还是空白,与国内外市场对水产食品质量、安全的要求很不相适应。所以,一定要积极开展广州管圆线虫病的流行病学调查、虫害快速检测、动物宿主扑杀等相关技术的研究;深入开展对食源性水生动物寄生虫病的风险评估,大力培养、培训各级水生动物防疫检疫技术人员,加强班子和队伍建设,尽快使广州管圆线虫病在我国得到更有效的控制。
[1]仇锦波主编.寄生虫学检验[M].第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40-41.
[2]詹希美主编.人体寄生虫学[M].第5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232-233.
[3]Pien FD,Pien BC.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 eosinophilic meningitis[J].Int J Infect Dis,1999,3(3):161-163.
[4]Chen HT.A preliminary report on a survey of animal parasites of Canton China rats[J].Lingnan Sci J,1933,12(1):65-74.
[5]Alto W.Human infections with 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J].Pac Health Dialog,2001,8(1):176-182.
[6]Pipitgool V,Sithithaworn P,Pongmuttasaya P,et al.Angiostrongylus infections in rats and snails in northeast Thailand[J]. Southeast Asian JTrop Med Pub Health,1997,28:190-193.
[7]安春丽,郑兰艳,王雪莲.从患者脑脊液中检出广州管圆线虫发育期雄性和雌性成虫[J].中国人兽共患病杂志,2000,16(4):53-55.
[8]何竞智,朱师晦,杨思齐,等.广州管圆线虫在我国大陆人群病例的脑脊髓液中首次发现和证实[J].广州医学院学报,1984,12(3):56-61.
[9]Bartschi E,Bordmann G,Blum J,el al.Eosinophilicmeningitis due to 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 in Switzerland[J].Infection,2004,32:116-118.
[10]潘长旺,梁韶晖,黄慧聪,等.温州地区广州管圆线虫病的研究[J].温州医学院学报,2002,44(6):3-5.
[11]王小同,黄汉津,林 燕,等.广州管圆线虫病所致的嗜酸粒细胞性脊神经根脑膜炎[J].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1998,24(5):306.
[12]丁步兰,何竞智,朱天成,等.广州地区广州血管圆线虫的调查研究[J].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1984,2(1):34~37
[13]李富华,周晓梅,李彦忠.云南河口的广州血管圆线虫调查[J].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1988,6(1):90-94.
[14]Ishii Al.Effects of temperature on the larval development of in the 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 intermediae host[J].Biomphalariaglabrata Z Parasitenkd,1984,70(3):375-379.
[15]吕 山,周晓农.全球气候变暖对广州管圆线虫病流行的潜在影响[J].国外医学寄生虫病分册,2005,32(5):195-199.
[16]王 莉,侯启春,王 岩,等.一起群发食源性广州管圆线虫病流行病学调查与分析[J].中国预防医学杂志,2007,8(4):430-432.
[17]张鸿满,陶甲芬,胡文庆.南宁市广州管圆线虫中间宿主感染情况的调查研究[J].广西预防医学,1996,2(2):78-83.
[18]黄晓红,杨发柱,屠昭平,等.广州管圆线虫病治疗药物筛报告[J].海峡预防医学杂志,2000,6(1):15-16.
[19]杨发柱,许龙善,黄晓红,等.两种药物治疗广州管圆线虫病的效果观察[J].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杂志,2002,15(6):346-348.
[20]Chotmongkol V,Wongjitrat C,Sawadpanit K,et al.Treatment of eosinophilicmeningitiswith a combination of albendazole and corticosteroid[J].Southeast Asian JTrop Med Pub Health,2004,35:172-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