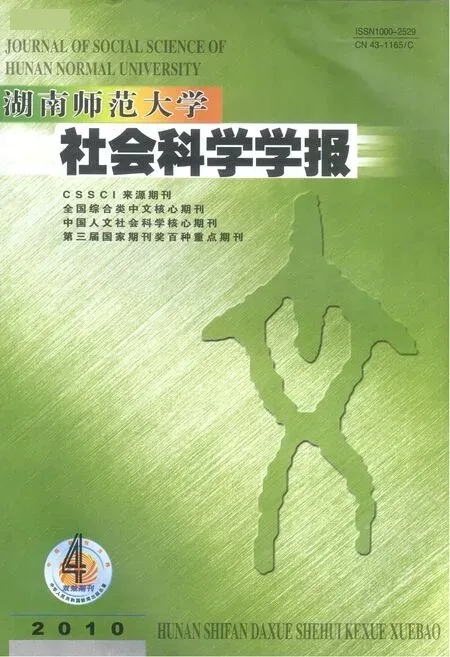自我分裂与主体间性:《宠儿》中的主体建构
2010-04-11熊海英李长亭
熊海英,李长亭
(1.湖南理工学院 大学英语教学部,湖南 岳阳 414006;2.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外语系,河南 平顶山 467001)
自我分裂与主体间性:《宠儿》中的主体建构
熊海英1,李长亭2
(1.湖南理工学院 大学英语教学部,湖南 岳阳 414006;2.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外语系,河南 平顶山 467001)
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在小说《宠儿》中着重塑造了塞丝和宠儿两个人物形象。作品的情节和涉及的其他人物形象大都是围绕这两个人物间的关系展开的。塞丝和宠儿互为主体,共同建构并结构着对方的主体性。因此,二者的主体间性是贯穿小说《宠儿》的一条主线。
托尼·莫里森;《宠儿》;主体间性;塞丝;宠儿
小说《宠儿》是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第五部作品,她因此而获得1988年普利策奖。小说讲述了塞丝等黑人挣脱奴隶制的压迫和以“学校老师”为代表的奴隶主惨无人道的掠夺、迫害而成为真正自由人的复杂而曲折的心路历程。塞丝和宠儿是作品中的主人公,按照拉康的观点,在各自的主体建构中,她们互为镜像,形成主体成长过程中的象征界,同时又互相解构,造成各自的主体分裂。
作品中的“甜蜜之家”是对《圣经》中伊甸园的戏仿。庄园主加纳夫妇实行一种特殊的奴隶制,待黑奴们很和善,从不打骂他们,教他们写写算算,让他们拿枪,还允许黑尔在周末外出打工挣钱赎买母亲的自由。一直到加纳先生死去、“学校老师”接管庄园,庄园里的黑奴们都好像伊甸园里的亚当夏娃一样,懵懂自得地生活在田园牧歌式的环境中。塞丝这些黑奴们并没有意识到周围的环境对他们的主体人格养成与白人奴隶主有何不同。他们都处于“诗意的栖居”状态。因为在形成自我意识的镜像阶段,他们认识到的自我就是与庄园主加纳夫妇这些白人他者对比而形成的自我,即视奴隶身份为当然的自我,他们如其所是地生活、繁衍。拉康主体理论中的象征界是符号的世界,通过语言同整个文化体系相连,个体只有依靠象征界接触文化环境,才开始作为主体而存在。而想象界中相对完整的自我是象征界中主体确立的前提,象征界的主体只有通过想象界的自我才得以自为地客观化。与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的情节相对应,塞丝由想象界进入象征界来源于一次偶然的偷听:她无意间撞见“学校老师”给两个侄子上课,他正指导他们对黑奴进行研究,要求他们把塞丝人的属性放在左边,动物的属性放在右边,然后把它们连起来[1](P164)。得知自己在“学校老师”这些他者心目中的形象后,她在想像界建构的主体身份轰然倒塌,带着分裂的自我进入由“学校老师”等构建的法严森森的象征界。拉康指出,“事实上,在任何自恋关系中,自我就是他人,而他人就是自我。”[2](P120)塞丝通过“学校老师”这些他者构建了客观的“自我”,与自己原先的主观想象性认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造成了主体形成过程中的分裂。因此,被认为是个体最本己部分的自我实际上是通过与自身之外的他者认同而构建的。得知了自己在白人心目中的动物属性,塞丝深受震动,并发誓不让自己的孩子的属性再被放到动物一边。当塞丝的丈夫黑尔和西克索策划的集体逃亡失败后,她毅然决定只身逃亡并获得了成功,而当时她尚有六个月的身孕,且刚刚遭到“学校老师”两个侄子的毒打,后背被划开,伤势严重。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纯属被动行为,而塞丝的出逃则是主动出击,它以对乐园的否定和拒斥展现了重建自我的决心和勇气,而塞丝的杀婴行为正是对客观“自我”的反叛。塞丝受够了白人奴隶主的折磨,她再也不想让孩子们过那非人的生活,她心中所谓安全的地方无非是“天国”,所以她毫不犹豫地为孩子们选择了死亡。作为母亲,她要不得不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女,毁灭自己生命中最美好的部分,这是最令人痛心的事。然而塞丝杀死自己的亲生女儿不仅仅是出于对奴隶主的反抗,更是出于一种浓厚的母爱。保罗·D说:“你的爱太浓了。”“太浓了?”她回答道,“要么是爱,要么不是。淡的爱根本就不是爱。”[1](P164)正是因为那浓厚的母爱,才有此暴力行为,暴力缘于母爱。至此,一个长期在“优秀人种”压制下“失语”的人种却在一个失去理智的弱女子身上获得了自己的声音和性格,对失乐园神话的戏仿也升华为主体人格在本己文化和精神复苏中的重构。所以,“人类的主体性问题与语言的运作直接相关。正是语言本身的分裂导致语言的主体,即言语的分裂,而主体性即是主体之分裂。”[3]
出现在蓝石路124号的神秘少女宠儿是一个魔幻化的人物,莫里森为她编织了扑朔迷离的多重身份。从魔幻层面上看,她既是塞丝18年前亲手杀死的女儿,也是消失在塞丝记忆深处的母亲,她是一代又一代生活在奴隶制中的黑人的化身;从现实层面上看,她既是自小就被白人囚禁并虐待的小女孩,也是经历了运奴船上非人折磨的非洲姑娘,她是现在仍承受奴隶制肆虐的黑人的形象。她是美国黑人痛苦经历的结晶,是奴隶制罪恶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见证人。正是宠儿的这种多重身份使她与书中主要人物各自的历史联系起来,迫使他们得以历史性地重现,从而推动了各自的自我构建进程。尽管小说开放性的结尾并未对书中人物的结局有明确交代,但故事情节的推进过程已充分反映了主体意识的觉醒。
当宠儿进入蓝石路124号这个封闭的环境之后,这一环境就成了塞丝、丹芙和保罗·D觉醒的“想象”空间,塞丝一家以宠儿为他者开始了主体重塑的过程;而蓝石路124号之外的黑人社区场景则是塞丝一家与现实中其他人交往并逐步确立主体的象征界。《宠儿》反映了第一代在法律上获得自由的黑人,由自我空白的奴隶向拥有自我主体的自由人迈进的艰难历程。黑人们的生活是残缺不全的,多数人生来就没有父母和兄弟姐妹,成年后没有固定的丈夫或妻子,也无权拥有自己的子女,甚至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正是由于生命中这些他者的缺失,使得他们留在了一种可怕的自我空白之中,无法形成他者镜像。在小说中,宠儿神秘地出现在自我空白的塞丝一家面前,因其身份的多样性分别充当了塞丝、丹芙和保罗·D想象界中的他者,从而使他们得以填补自我的空白,得到了想象界中完整的自我——这是他们建立象征界的主体的前提。但想象界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以及自我设计都是想象性的,个体终究要实现象征界中的健康主体。宠儿在小说中表现出一种破坏性,间接地推动了塞丝一家进入象征界,成为真正自由自主的自由人。她引诱保罗·D、控制塞丝的情感和生活,她像一个巨大的漩涡,企图把别人吸入历史的深渊。她的这种破坏性表明,人应该面对过去,但不能停留在历史和想象界中。正是这种破坏性驱使丹芙和保罗·D走出了封闭的环境去与外界接触,使社区中的黑人邻居重新走近塞丝,最终使塞丝结束了多年孤立的状态,回到现实,从而能够确立象征界中的健康主体。
宠儿是被塞丝杀死的女婴的化身,“人人都知道怎么称呼她,却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她被人遗忘,来历不明,却永远不会失踪,因为没有人在寻找她;即使有人在寻找,他们不知道她的名字,又怎么唤她呢?虽然她有所要求,但是没有人要求她。”[1](P274)所以,不管宠儿是以鬼魂的形象萦绕在世人周围,或是以肉身出现在大家面前,其自我身份都是以他者的态度和目光而得以确定下来。面对不同的他者和环境时,宠儿的自我身份建构随之改变。换言之,宠儿的主体建构是受他者支配的,其自我是分裂的。
米歇尔·福柯在《事物的秩序》中宣称,人这一概念“就像画在海边沙滩上的面孔一样会被擦掉”。[4](P387)这是尼采在19世纪末宣告“上帝死了”以后,福柯振聋发聩的声音在概念层面上宣告了“人的死亡”。标志着近一个世纪以来,人文学科领域质疑西方传统视“人”为一个统一的、先验的、理性的认识主体的观念达到了顶峰。拉康对主体实施去中心化,指出“自我”不再是通过理性掌握世界的统一自足主体,而是深陷于文化中并被文化构造和颠覆的分裂欠缺的主体,其行为动因不再是理性而是无意识的欲望。一般而论,拉康关注的是主体如何在“他者”中形成,以及主体身份如何总是由主体被置于外在世界中而建立起来,即主体身份是由外界构建而成的。在拉康看来,作为融摄他性的结构是任何主体的先决条件,并不存在任何“自我”之起源的先在形式,甚至无意识,因为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主体是通过历史建构起来的,而历史是一个渐次分裂的过程。
在“学校老师”带人抓捕塞丝等人时,为了使孩子避免成为第二个塞丝,不受奴隶主的欺凌,她极端地、近似疯狂地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她的这一疯狂举动蕴含了她和被杀孩子的主体间性。她把孩子视为另一个自我,为了不使这一自我重蹈被奴役的命运,只有使其在这万恶的世界上消失。出现在蓝石路124号的神秘少女所带来的都是塞丝企图忘掉的过去,她的出现是“压抑的回归”[1](P73)。塞丝的家人都在回避18年前的杀婴事件,但它却一直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塞丝的两个儿子离家出走,婆婆死于精神崩溃,丹芙养成了孤僻幽闭的性格,而塞丝每天最严肃的工作也是“击退过去”(Morrison,2005:73)。宠儿的出现使他们无法再回避过去,她是他们想象界中的他者,反映出他们个人历史和心理上的残缺不全。塞丝和婆婆贝比·萨格斯早已达成共识,过去是苦不堪言的,即便是面对丹芙和保罗·D,塞丝不愿也无法用语言表达那种真实的心理。宠儿是18年前杀婴悲剧的目击者和受害者,因此她成为塞丝唯一的倾诉者和听众,她使塞丝回忆起自己的母亲和母语,也迫使塞丝第一次开始对18年前杀婴事件进行回望。
自我是在与另一个完整的对象的认同过程中构成的,自我的构成离不开想象的他者的存在,宠儿就是塞丝的他者,宠儿既是母亲又是女儿,她使塞丝有可能得到为人女和为人母的统一的自我感。但宠儿只是塞丝渴望拥有母亲和女儿的想象性投射,想象关系所表达的认同没有进入现实层面,而追求自我、重塑主体的希望在于既能面对历史,更能直面现实。宠儿已经使塞丝恢复了个体历史的记忆,但宠儿对塞丝感情的贪婪占有却逐步割断了塞丝与现实的联系,塞丝必须恢复现实生活。当社区里的黑人邻居们得知塞丝的困境,她们克服了对塞丝的成见,并最终集合到塞丝家的院落里去帮助她时,宠儿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了,这标志着在经历了多年的孤立后,塞丝重新融入到现实生活,而保罗·D的归来更是预示了一个乐观的未来。
因为母亲的原因,丹芙也间接地逃避过去。杀婴事件后,蓝石路124号成了黑人社区的一个孤岛。在没有与外界的交往和没有他者注视的情况下,丹芙一直生活在孤独和虚无空白之中。宠儿出现后丹芙全身心地照料她,宠儿给了她被需要的感觉,这为她最终走出蓝石路124号这座孤岛,恢复与外界的联系作了准备。作为塞丝最小的孩子,丹芙出生在塞丝只身逃亡的过程中。借助宠儿聆听的渴望,丹芙一遍遍重构自己也参与其中的逃亡经历,讲述的过程也就是丹芙借助他者构建自我历史的过程。宠儿作为丹芙的他者,加固了丹芙作为塞丝女儿的自我感,无形中密切了她们之间的母女亲情,而塞丝对宠儿所作的解释也促进了丹芙对母亲的过去的了解。在蓝石路124号这个封闭环境中,宠儿帮助丹芙摆脱了空白虚无,获得了想象界的自我。同时,由于宠儿对塞丝掠夺性的占有,使这个家庭的生活陷于困顿,这迫使丹芙走出蓝石路124号,到现实世界中去寻找工作并养家糊口,她进入了象征界,成为能进行正常社会交往的健康的主体。在宠儿出现之前,保罗·D和塞丝通过互为他者构建的自我,是建立在对不可言说的噩梦予以回避的基础上的,他们幻想着以这个虚幻的、不完整的自我来开始新的生活。但是,建立在虚幻的、不完整的自我基础上的保罗·D很快引起了丹芙的排斥,和塞丝的交流也产生了障碍,建立家庭的幻想破灭了。这证明黑人们无法通过抛开历史来获得新生,他们必须面对过去。宠儿的存在提醒着每一个试图遗忘过去的黑人,使他们努力回避的曾经为奴的经历不断浮上意识的层面,这是他们重塑自我的一个必要条件。宠儿对保罗·D的引诱就是拒绝被忘记的往事向他频频招手,她唤醒了保罗·D压抑在无意识深处的有关奴隶屈辱遭遇的回忆,使他回到了能理解塞丝的历史状态。因为宠儿这个他者的存在,保罗·D才丢弃了那个不完整的、虚幻的自我,找到一个完整真实、背负沉重历史的自我,这个自我是保罗·D和塞丝可以共同生活在一起、共同面对未来的重要条件。最终保罗·D回到塞丝身边,他渴望彼此成为“精神上的朋友”,因为“我们拥有的昨天比谁都多。我们需要一种明天”[1](P275)。
宠儿和塞丝之间的恩怨情仇构成了特定社会、特定时期黑人主体身份的建构。就像《麦琪的礼物》一样,她们都是在牺牲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来表达对对方最真挚的爱,尽管这爱浸淫着心酸和残酷。它是对社会有力的揭露和泣血的呼唤,它的功能已超越了恢复黑人记忆的范畴,而成为唤醒整个社会回归本真的介质。
[1]Morrison,Toni.Beloved.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5.
[2]Lacan,Jacques.Ecrits:A Selection.trans.Alan Sheridan.New York:Norton,1977.
[3]严泽胜.拉康与分裂的主体[J].外国文学评论,2001,(4):128-134.
[4]Foucault,Michel.The Order of Things.New York:Vintage,1970.
The Disintergrated Self and Intersubjectivity:Subjective Construction inBeloved
XIONG Hai-ying,LI Chang-ting
(Department of College English,Hu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Yueyang,Hunan 414006,China)
Belovedwritten by Toni Morrison,a famous black writer in America,mainly presents the characters of Sethe and Beloved.The plot and other characters involved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protagonists.They mutually exist for each other and construct the intersubjectivity.Therefore,the intersubjectivity is the main line through the fiction.
Toni Morrison;Beloved;intersubjectivity;Sethe;Beloved
B00
A
1000-2529(2010)04-0120-03
2010-01-05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艾略特《荒原》的陌生化研究”[08YBB241]
熊海英(1974-),女,湖南湘潭人,湖南理工学院大学英语部讲师,硕士;李长亭(1972-),男,河南叶县人,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外语系讲师,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校:谭容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