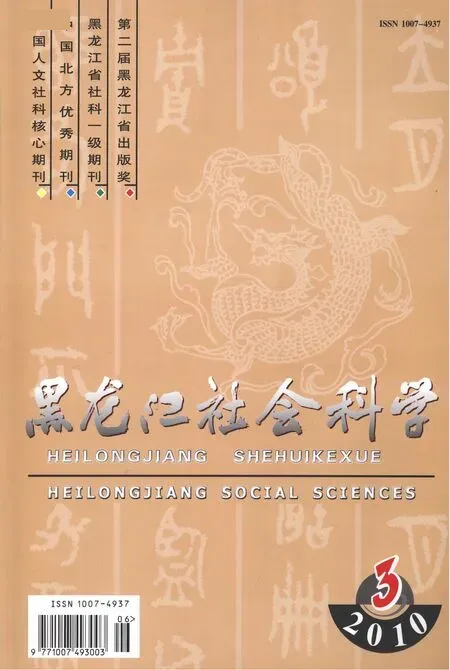从历史角度看科学划界
2010-04-10程晓皎孙玉忠
程晓皎,孙玉忠
(哈尔滨师范大学科学技术教育系,哈尔滨 150025)
从历史角度看科学划界
程晓皎,孙玉忠
(哈尔滨师范大学科学技术教育系,哈尔滨 150025)
划界问题是西方科学哲学最基本的问题,划界行为具有社会和政治后果。不考虑历史维度的纯逻辑研究割断了科学的完整历史,在理论上造成缺憾,并导致现实的困惑。西方科学哲学在划界问题中走不出片面和困境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混同了标准与判据。划界标准立足于科学的本质,据此形成划界的充分必要条件,但不能对此提出“足够精确,便于操作”的要求。划界的判据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判定依据,在整体上体现出科学与非科学认识论意义上的差别。
科学划界;科学判据;科学哲学
科学划界问题是西方科学哲学最基本的问题。波普尔认为,科学划界是“认识论的中心问题”,英国科学哲学家吉勒斯把划界问题列为 20世纪科学哲学的四大主题之一。时至今日,划界问题已不单单是科学认识领域的问题,划界本身往往蕴涵着更为广泛的问题,用吉勒斯的话说,划界问题关系到超出科学王国之外的普遍知识的论题。逻辑经验主义把划界作为排除形而上学的手段,然而更多的是作为怀疑的手段。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划界显然更具有社会和政治后果。
一、划界问题的历史维度
1936年,一批“不具科学价值”的牛顿手稿被拍卖。随着这些文件的曝光,作为科学家的牛顿的形象遭到质疑。这些文件显示,牛顿在 1667年进入炼金术领域,1669年底开始炼金实验。其后近三十年的时间中,牛顿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从事炼金术的研究与实验。他的收藏中有 169册关于化学及炼金术的书籍,而他留下的有关炼金术的资料超过了 100万字。有关炼金术,现代科学史上所认可的正面意义是,它催生了现代化学。而炼金术在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之后,由于其本身的非科学性也已成为科学史上的遗迹。然而,炼金术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只是一些江湖术士的招摇撞骗,它在一定程度上与科学有着密切的关系。牛顿时代的炼金术包含三个领域,首先,炼金术聚集了大量的技术,包括颜料和染料的制造、无机酸的制造和水的蒸馏等,这些产品在当时已经有了商业用途。其次,作为早期科学的新领域之一的医学曾是炼金术的分支。第三,从物质中制造黄金。就牛顿而言,他所从事的炼金术和物理学研究就其出发点和研究手段来说并无实质性的差别,他沉迷于炼金术的原因也不排除发现宇宙的真理。这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与牛顿同时代的科学家摩耳、巴宾顿、巴罗、波义耳等人均痴迷于炼金术的原因。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如下理由:一是可重复的实验结果。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布卢明顿分校一个普通的化学实验室,两位化学家威廉姆·纽曼和凯瑟琳·里克“复制”了牛顿用于做实验的仪器,依据牛顿手稿所描述的实验,力图在与牛顿相同的条件下重做炼金术实验。按照牛顿的实验方法,他们制出了被牛顿称为“网”(net)的一种球状物质。他们还利用牛顿的笔记重新制造了树状金属结构,制造出这种结构对牛顿的炼金术研究有重要的作用。二是可解读的符号体系。像其他炼金术士一样,牛顿发明了自己的符号体系来描述他的实验。他用行星符号来表示已知的金属,用标准符号来代表一些普通的物质。除此之外,牛顿还创造了大量的非常个性化的象形符号。这些符号虽不正统,但均有明确的代表性。用来代表金属矿石的符号比较容易对译,今天的人们已经能够知道其含义,但还有一些人们至今不知其含义。尽管如此,用符号来表示物质表明牛顿的研究在形式上已接近科学形态。
现有的划界标准无法对炼金术进行结构上的分析,根据现有的标准我们会把这一时期的研究整体上判定为非科学,因为按照历史主义的划界标准,这一时期尚未形成科学范式。逻辑主义的划界标准也对此无能为力。可检验性是逻辑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提出划界的一元逻辑标准,标准虽然是一元的,但结构是二元的,即经验—理论的二元结构。因为可检验性虽然是经验的可检验性,但所检验的结论却是来自理论。可检验性是指命题具有如下性质:可以从命题中推演出一个可与观察、实验结果相比较的推断。因此,当我们面对炼金术并对其进行分析时会发现,虽然炼金术是非科学的结论,但将其宣判为非科学的理由却掩盖了有价值的思考,暴露出不考虑历史维度的纯逻辑标准的局限性,忽视了划界带来的社会后果。
此外,我们还必须对划界问题进行历史维度的思考。“所谓科学认识,其区分有两个等级:整体的和个体的”[1]。科学划界既针对科学的整体,也包括科学的个体。就科学的个体而言,其广义的发展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发生,即科学理论从无到有,从非科学领域进入科学领域。第二种情况是科学范围内的发展,此时的科学活动表现为一种在现有的理论框架内解决问题的活动,用库恩的话来说,即常规科学阶段科学家在范式的范围内从事解难题的活动。第三种情况与第一种情况刚好相反,科学个体的发展从科学领域走向非科学领域,进入到诸如哲学、神学以及其他的非科学领域。我们现有的科学划界问题的研究不仅割断了科学的完整历史,而且对前科学时期分析的缺失也造成了理论上的缺憾,更给今天的现实分析带来了思想上的不一致。如果我们对过去的历史做事后分析,科学实践的成功会决定我们作出的判断。而在牛顿时代,科学与哲学、科学与神秘学的界限十分模糊,科学研究的探索本性更决定了他不可能在一个已经圈定好了的能够通向成功的领域内去从事研究。科学研究的探索本性注定了研究道路的不可预知性,人们不会预先知道哪条道路能通向成功。
如果对当下的历史进行分析,我们将如何对尚无法预测能否成功的实践行为进行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呢?按照现有的划界标准,不具备系统知识形态(范式)的就是非科学,可在今天的现实中,一项有价值的探索性研究一旦被宣布为非科学或伪科学,就会彻底丧失社会的支持,这势必会阻断前科学通向常规科学的必由之路。
二、不能消解的划界问题
目前,划界问题的研究首先需要面对的是后现代主义颇具破坏性的冲击。从实证主义正式提出划界问题到社会历史学派及其后来的发展,划界问题经历了三个转变:从静态标准向动态标准的转变、从一元标准向多元标准的转变、从有标准向无标准的消解。历史主义准确地抓住了逻辑主义的要害,指出,无论是证实标准还是证伪标准都严重脱离和歪曲了实际科学,因而不可能对科学与非科学作出正确的区分。历史主义虽然准确地揭示了逻辑主义的错误,但不能够给出正确的解决方案,反而使划界问题走向消失。
历史主义之后对划界问题的消解基于两个前提:一是彻底否认现有划界标准的合理性。二是拒绝承认科学与非科学的本质区别。劳丹就认为,自实证主义提出划界问题以来,没有一个划界标准满足了他所提出的三点要求,“不管人们如何区分科学与非科学 (例如根据进步性、合理性、经验性、可证伪性),这些区分都经不起仔细推敲。”[2]196因此,也就不可能有效地分清科学与非科学。他还进一步指出,科学本身是异质的,它们不都是从认识中获得的。科学本身的异质性决定了我们寻找划界标准只能是徒劳之举,因为“非科学与科学完全一样,也有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二者均能表明在其历史演化的某个阶段取得了重大进步。”[2]196劳丹之后,罗蒂也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重申了划界问题的消逝。
科学哲学作为对科学的反思和超越,其所研究的主要问题来自于科学理论和科学实践中最普遍的问题,划界问题也同样如此。任何事物都是肯定与否定矛盾的统一体,异质不能替代本质,更不能消除差别。划界标准的不成功不会迫使我们消解划界问题。只要我们承认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那么合逻辑的结论必然是承认科学划界的存在,进而寻找划界标准。理想的科学划界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划界标准的合理性和划界判据的可操作性。
西方科学哲学在科学划界问题的研究中走不出片面和困境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混同了标准与判据。他们无法在最大的普遍性和现实的可操作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结果是这两方面都不令人满意。以劳丹为例,劳丹认为划界标准应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能够表明科学的认识论根据或证据基础比非科学更加确定;二是能够对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方式作出明确的解释,并从认识论意义上表明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三是足够精确,便于操作[3]。从逻辑经验主义到社会历史学派以及后来的发展,没有哪一个划界理论不受质疑,更没看到哪一个划界理论在科学实践中取得了压倒式的成功。
科学的划界意在把科学与非科学或反科学区分开来,其划界标准显示出科学与非科学或反科学的本质区别。在科学领域进行的划界是人们运用一定的标准对知识领域进行的用以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科学与伪科学的一项活动。就其目的而言,科学划界就是确定一个边界,从而把科学与其他知识形式区分开来。这种区分关乎科学的本质规定,对“什么是科学”进行追问,据此形成划界的充分必要条件。因此,不能对标准提出“足够精确,便于操作”的要求。划界的判据是依据划界标准,并结合具体的科学实践,判定科学行为和科学成果是否符合科学标准的具体的、可操作的判定依据。各种判据结合在一起,会在整体上体现出科学与非科学在认识论意义上的差别。每一条具体的判据都蕴涵着这种意义,但不能期待它来回答科学的认识论何以比非科学更加确定。
划界的标准与划界的判定不能混为一谈。划界标准与科学的本质相关,即提供一种界定,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而判定是一种实践行为,与科学具体的行为和结果直接发生关系。标准是抽象的,而判据是具体的。划界标准不能替代判据,如果仅仅抽象地谈论标准,而没有在此基础上形成与这个标准相对应的方法论判据,就会使划界标准找不到实现的可靠途径,使划界标准无法用于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科学与伪科学的判定,就会使后现代主义消解科学划界的各种观点有机可乘。同样,判据也不能离开标准,标准对判据有指导和规范作用,标准是形成判据的前提和根据,任何判据都不能离开划界标准这个前提而独立存在。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两位加拿大哲学家萨伽德 (P.Thagard)和邦格 (M.Bunge)的划界思想。萨伽德的划界理论有两个部分:其一,提出了科学划界的三个元哲学问题:(1)为什么科学划界是重要的,从何处划分?(2)什么是科学划界标准的逻辑形式?(3)作为科学或伪科学的单元是什么?其二,提出了划界的具体评判单元,包括:(1)科学使用相互关联的思维方式,伪科学使用相似性思维。(2)科学追求经验确证和否证,伪科学忽视经验因素。(3)科学研究者关心与竞争有关的理论评价,伪科学研究者不关心竞争理论。(4)科学采用一致并简单的理论,伪科学则是非简单理论和许多特设性假说。(5)科学随时间而进步,伪科学在文本和应用中停滞不前,保守等[4]。尽管这些评判单元还十分模糊,尚不能构成划界的充分必要条件,但仍然可视为是划界研究的进步,它代表了理论未来努力的方向。
历史分析使我们认识到,现有的划界问题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不能令人满意,而且距现实的需要相差甚远。要想把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除了理论思考之外,还要依赖科学实践的推动。科学划界的标准是从成功的科学历史中总结出来的,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其必将随着科学的发展被继续总结,进而丰富和发展。
[1] 舒炜光.科学认识论:第 4卷[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4.
[2] [美 ]拉瑞·劳丹.进步及其问题[M].刘新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3] Laudan.The Dem ise of theDem arcation Problem[A]//in R.S.Cohen and L.Laudan(eds),Physics,Philosophy and Psychoanalysis[C].D.Reidel Pub lishing Company,1983:8.
[4] 陈健.科学划界的多元标准[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3):1-2.
〔责任编辑:王雅莉〕
B2
A
1007-4937(2010)03-0158-03
2010-03-15
程晓皎 (1985-),女,黑龙江哈尔滨人,硕士研究生,从事科学哲学及科学史研究;孙玉忠 (1964-),男,黑龙江哈尔滨人,教授,科技哲学博士,从事科学哲学及科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