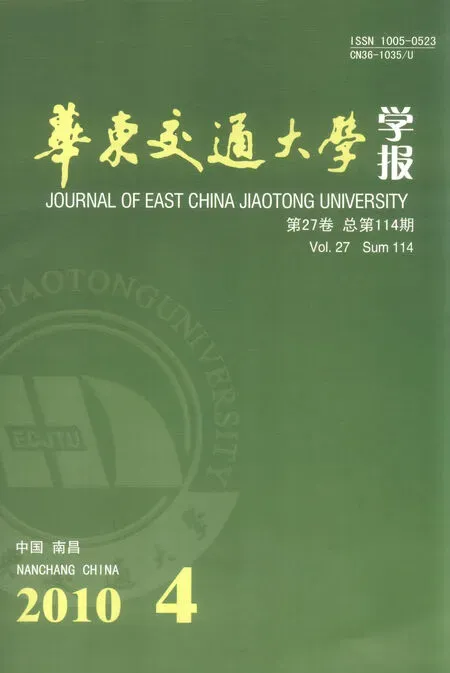批判与重建:论克沃尔的生态社会主义
2010-04-08余维海
余维海
(华东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克沃尔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2000年美国绿党的前总统候选人,也是当代生态社会主义的重要倡导者之一,其代表作《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终结?》被认为是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阐释。近年来,克沃尔积极参与生态运动,二度起草了《生态社会主义宣言》,筹建了生态社会主义网站(EIN)。克沃尔从资本主义交换价值至上主义和资本无限扩张的逻辑中发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因此他断然指出任何不涉及资本主义制度更替的生态主义思潮都无法根本解决生态问题。克沃尔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对各种生态主义思潮的批判基础上,针对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和传统社会主义的生态缺陷而提出的关于未来社会的一整套替代方案。这套关于未来社会的替代方案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它对于人们理解并应对当代生态危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并有助于人们理解社会主义的真正内涵。然而,由于它存在较大的理论缺陷,它所构建的生态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绝非药到病除的灵丹妙药。
1 批判与超越:克沃尔对生态危机根源的分析
克沃尔认为生态危机是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人类历史到了最紧要的关头,如果不创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以拯救生态危机,文明和历史进程将终结,人类将面临灭顶之灾。”[1]22克沃尔把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指认资本主义是引发这场危机的根源和幕后推动力,资本主义天然的反生态性侵犯、扰乱了文明的自然基础,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首先,为了论证资本主义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性,克沃尔借鉴了马克思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相互矛盾的经典理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价值从属于交换价值,具体劳动从属于抽象劳动,商品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是为了交换金钱和其他的商品。人们为了不断地买进其他商品,就必需不断地卖出更多的商品。这样,商品生产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销售以维持购买其他商品的能力,商品只保留了交换价值却淹没并丧失了使用价值。因此,“资本主义的增长不是物质生产要素或产品的增长,甚至也不是经济总量的增长,而是交换价值的增长。”[2]123在克沃尔看来,资本主义是千年来一种发展方式的巅峰,它的特点就是把经济高高置于一切之上,把人类的一切存在都转换成金钱关系,以至于“资本变成了一种存在方式,要克服资本,就必需探究和克服发展本身。”[1]22
其次,克沃尔从资本的扩张本性中分析了生态系统破坏的根源。他认为,“扩张或死亡”,是资本的逻辑和内在规定性,资本主义必须以经济的不断增长方式来制造利润以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国家或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无法解决危机,因为要解决危机,必须对积累进行限制,这是增长型的体制所不可接受的。“资本主义无法限制增长,就像人无法停止呼吸一样。任何关于资本主义是可以任意管理和转变的经济排列的幻想都是大错特错的。”[1]22交换价值至上主义的逻辑致使自然中的一切变成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且被私有占有的商品,资本积累和资本的无限扩张成了整个社会的内在逻辑。事实上,‘万能的'资本驱使国家、军队、市民社会、学校、媒体、文化产业——马克思所谓的我们社会的‘摩西和先知者'——来完成资本积累。”“控制自然的不是别的东西,正是无处不在的资本主义。”[3]120因此,资本的无限扩张和增长对生态系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资本不但无休止地创造财富,也制造贫困、不安全和浪费,分裂生态系统。
再次,克沃尔断然否定了靠技术革新来挽救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可能性。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是增长的必要条件,即使在能源免费的世界,汽车生产成本的降低也会造成大量汽车的生产过剩,引发基础设施的崩溃,资源的逐渐耗竭。为了加以说明,克沃尔重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新技术的使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例如,氢燃料电池是最新的无污染的科技成果,但是为了进行分子分裂——从甲烷或水分子中分离出氢,须要耗费大量的能源。因此,他警告“环境自由主义者”不要过分贩卖他们所谓的可再生能源,因为这始终无法满足大众的能源消费需求。他认为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比技术形式更加重要,在仅仅依靠再生能源技术之前,更重要的依然是重建社会以减少对能源的使用。
最后,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还表现在其生态帝国主义行径上。克沃尔和洛韦在《生态社会主义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在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全球化的扩张中产生了生态帝国主义行径,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失范。[4]1-6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污染了生态系统,破坏了动植物的栖息地,耗尽了自然资源。在南半球,越来越多的森林被砍伐殆尽,土地被圈起以种植经济作物,人们被迫背井离乡,贫困现象更加恶化。克沃尔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为资本扩张扫除了各种障碍,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回归到纯资本的运行方式,便利了资本对人类和自然进行赤裸裸地剥削。西方强国和美国霸权领导下的国际组织打压不同意见者,在经济和军事上压制边缘国家。资本主义国家须要掌控住能源资源,特别是石油资源,因为这是确保工业持续增长所不可或缺的。
2 克沃尔对各种生态主义思潮的批判
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乃至全世界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各种生态主义思潮试图开出诊治的药方。克沃尔认为这些思潮的兴起的确可以唤醒生态意识,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绿色运动的主流极易被强力的社会政治力量拉拢和利用,使之从市民运动转变成沉闷的、谋求席位的官僚混战。他批评生态主义没有积极地反资本主义,而是维护现存资本主义,寻求技术的完善和修补,是一种“体制内的方法”,解决的只是表面的外在症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因此,生态主义思潮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
第一,对绿色经济学的批判。克沃尔指出绿色经济学的逻辑前提是资本主义具有吸收生态危机的能力和自我恢复的功能,因而他们对社会变革不感兴趣,应对生态问题的主要措施是建立以奖励为基础的规章制度、生态关税、自然资源损耗税以及对制造污染者的强制性惩罚等。如以大卫◦科登为代表的新亚当◦斯密学派崇尚“资本主义小型生产”,认为自由交换具有自我约束的功能且更具竞争力,他们主张应该由政府和市民社会共同阻止资本企业的扩张和集中以建设生态社会。克沃尔批驳他们没有指出资本扩张本性的缺陷,忽视阶级、性别和其他控制等问题。总体而言,克沃尔一方面赞赏绿色经济的小规模改造,认为小规模的生产单位是通向生态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他认为它们并不是目的和终点。在他看来,小企业在其配置上可以是资本主义的,也可以是社会主义的,要真正解决生态问题,必须始终如一地通过解放劳动、辩证地看待一切事务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第二,对深生态学的批判。虽然深生态学也认同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但是克沃尔认为深生态学像其他绿色政治或绿色经济学一样“徒具道德的灵魂,却不批判资本主义,不主张解放劳动”,远离现实社会的斗争,他们主张“非左非右,向前走”。[5]171克沃尔指出深生态学家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为了努力保持自然的原始状态,他们“走得太远了”,他们竟然赞成“把(哪怕是从有史以来就居住在那里的)闲杂人员清理出去”。克沃尔认为,事实上深生态学已经演变成为资本主义精英们霸占自然资源的战略哲学,为精英主义哲学增加了合法性。
第三,对生物区域主义的批判。生物区域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柯克帕特里克◦塞尔(Kirkpatrick Sale)。该理论主张“适当的生态区域保护主义”下的自给自足,其本质就是强调生态系统在地域上的统一性。生物区域主义以可持续原则、生态技术和生态经济为其特征。克沃尔担心区域的边界不清会导致社区之间的冲突和互相限制,因此在现实中根本无法建立所谓的生物区域。“资本主义要求土地私有化,而印第安人却顽强地拒绝私有化。资本主义并没有改变私有的本质,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土地被看成商品,被少数外来者集中占有、出租和剥夺。因此,生物区域主义不可能在这里得到贯彻实施。”[5]174生物区域主义没有解释如何进行社会转型,也没有解释建设生物区域时人们对资本主义国家将会有哪些不可避免的反应。此外,克沃尔也批评了自给自足的问题。柯克帕特里克坚信自给自足的区域能够使每个地区按照自身特殊的生态开发能源,像美国西北部开发木材一样。克沃尔认为这远远无法满足本地区的需求,指出西雅图的环境破坏使之成了一个森林破坏严重、木材燃烧、烟熏弥漫的城市。
第四,对社会生态学的批判。社会生态学是绿色生态主义中的激进派,其创始人是美国著名的生态学家默瑞◦布克钦(Murray Bookchin)。该学派把生态问题视为社会问题,提出社会生态学要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和改造,把社会政治改革方案和无政府主义联系起来,反对国家政权,维护地方社区。他们把特权阶级本身看成是生态破坏的根源,克沃尔则强调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性别和阶级统治,认为社会生态学继承了无政府主义的非暴力行动传统,并认为该传统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因为它没有论及建设超越资本主义的生态社会。此外,社会生态学家和无政府主义者习惯于强调国家本身,忽视国家统治背后的阶级关系。克沃尔指出,这种来源于无政府主义和宗派主义敌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政治倾向是默瑞◦布克钦顽固的错误,最终将陷入空洞化而丧失具体性。
3 社会重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蓝图
尽管社会主义在20世纪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克沃尔仍然使用社会主义一词,因为“社会主义代表对资本的废弃”。和传统社会主义截然不同的是,他力图建立的是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生态社会主义”一词的前缀“eco-”昭示着需要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范式,体现“生态中心主义”的一系列价值;词干“socialism”指取代资本主义的悠久传统。[1]23生态社会主义为何要有所不同呢?加上“eco”前缀的社会主义又是如何改变传统社会主义、增加成功的机会呢?克沃尔在评价生态社会主义和绿色政治的区别时指出,二者最根本的区别在于绿色政治不诉求劳动的解放,不诉求终结生产者和生产方式之间的分离,“生态社会主义”是一个能充分达到这一标准的社会形态。
首先,向生态社会主义的转变意味着从一般的商品生产向生态系统生产的转变。农场、社区信用社、车间、反对世界银行的各种团体等可以视为人类的生态系统[5]225。人们在那里只要沿着生态完整性的路径就会挖掘出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潜力,使该系统更加繁荣,相反只要沿着资本积累的路径就会使之更加恶化。在商品生产模式中,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商品生产的不断扩张使资本成了破坏地球的癌症,这是资本再生产的唯一路径。在向生态系统生产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具有生态社会主义潜力的生态系统会被点点滴滴地挖掘出来,然后以点带面,最终全面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生态系统的生产在理论上将使生产远离商品,创建繁盛完整的生态系统;在实践中将恢复生产的使用价值,贬低交换价值,并实现使用价值之外的内在价值。完整的生态系统和道德经济分不开,人应该是积极参与自然的改造者,而不是笼罩在沉默的自然之上的造物主。在生态系统的生产中,生产过程将优越于产品,各主体之间的联系将会加强,将会更加重视审美诉求,也将更加强调共同义务、团结和团队精神,尊重自然的极限。这些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经济中贪婪的占有欲和支配欲。
其次,重新定义财富。克沃尔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尽力实现商品的使用价值,通过使用价值的实现,实现其内在价值。重新摆正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位置,意味着要克服资本积累的逻辑。克服积累不是导致人类的普遍贫穷,而是须要重新定义财富。这包括多个相互关联的转变:[1]25(1)生产目的从交换价值到使用价值的转变,社会关系从量化规范到以质为取向,即生产的目的是其使用价值,而不是扩大交换价值、金钱和资本。(2)社会从普遍疏远和拜物教的支配到人们之间的相互重视,也即从利己主义到团结的转变。(3)从世界是由许多各不相干、彼此孤立的事件组成转变为世界是一个有差别的有机整体的概念转换。自然不再被认为是和人相分离的,而被视为人类身体的扩展。这又须要更新使用价值的概念(包括交换价值):让质量、真实需求、美学和真实生活进入生产过程,杜绝交换价值和抽象劳动至上主义。[6]1(4)从疯狂追求商品消费的社会到自觉生产的转变。消费至上主义反映了无力的、孤立的精神绝望,它既是资本主义异化的结果,又是产生生态破坏的条件,表现为废物的不断增多、生命的不断浪费。由于异化和生产者与劳动产品的分离相关,生态社会主义就和社会主义一样将通过实现财产的公共使用权和公共所有权来加以避免。这是“生态”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节点。
再次,解放劳动力,实现劳动者的自由联合,最终恢复自然的完整性。生态社会主义是从以劳动力的解放扩张到恢复自然的完整性的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就是通过解放劳动以克服生态危机,重新发掘自然的内在价值,解放人类的创造能力以解放人类本身。[3]120尽管生态社会主义坚决支持合适的技术并对生态恶化进行直接干预,其首要关注的还是如何使人在自然中生存以及劳动如何改变自然。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劳动的异化导致自然的异化,自然恶化最终导致生态危机,它将断裂人类历史。因此,生态理性的社会需要自由,自由不是定义为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特许,而是包括自身在内的永续发展。生态社会主义必须保持并扩张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必须让人类在其社会劳动中实现自觉自由。这就意味着必须克服生产方式和劳动者的分离,“我们需要和平和正义,和平意味着生态健全,正义意味着消灭靠剥削他人积累财富的制度,真正公正的社会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7]2克沃尔援引《共产党宣言》中的话语——《共产党宣言》至今仍是社会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检验标准,“每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8]294总之,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自由的联合劳动选择生态中心价值来愈合地球并使之重新繁荣的生产模式。
最后,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与奥康纳的改良型生态社会主义不同,克沃尔的生态社会主义属于革命的生态社会主义。[9]84克沃尔在《自然的敌人》中阐述了进行生态社会主义革命的三阶段:革命前期的准备阶段、冲突与实现革命对象的制度并存阶段、改变旧社会秩序并进行新社会建设的革命转型阶段。[5]200-206其中,克沃尔特别强调第一阶段的酝酿和先决条件的重要性,认为革命的先决条件成熟与否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生态社会主义是一条可预见的道路,它是面对全球各个角落的生态危机的挑战而采取的“逐步的”斗争。生态社会主义就像生命一样,不是立刻就能形成的。它是一种预示,现存的社会系统总是蕴含着潜在的生态社会主义的胚胎。从预示中看到了未来的雏形,越往前发展,就和其他生态社会主义因素一起越趋向于一个生态社会主义的轮廓。换句话说,生态完整的世界不是通过某一蓝图或特定道路来实现的,而是在一系列实践中产生。
4 对克沃尔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评析
总而观之,克沃尔在构建自己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时不是设法还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生态向度,而是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分析当代的社会问题,因而其理论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践性。他将生态破坏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联系起来,从交换价值与资本的视角分析生态危机的根源,这对于我们认识生态危机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克沃尔在“生态学”与“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完成了对社会主义的生态学重建,向世人展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美好蓝图,这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其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
首先,克沃尔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明确了生态社会重建的社会主义向度,主张绿色社会应该是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克沃尔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生态现代化,在理论上展示了社会主义与生态问题上的内在联系,把生态危机的彻底解决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结合起来思考。这能帮助人们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也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与完善。
其次,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系统阐释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蓝图,为世界各国改善环境的努力和环保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持。在生态危机面前,生态运动风起云涌,各种思潮和理论献计献策,为消解生态危机的困境提出了版本各异的方案,其中,生态中心主义就精心构建了没有生态危机的世外桃源。众说纷纭的生态理论极易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使人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就曾深受生态中心主义的影响,主张经济的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否定现代化。但是克沃尔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从绿色政治中分化出来,对各种生态主义思潮进行了系统批判。此后,他的生态社会主义逐渐从理论走向实践,对环保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最后,克沃尔生态社会主义倡导了生态化生产的理念与对劳动者的关照思想,不但能帮助我们进一步澄清社会主义理念,从苏联模式中吸取教训,也能帮助我们吸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生态社会主义和当前我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也有许多契合之处。这对于树立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对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也具有直接的借鉴作用。
然而,克沃尔的生态社会主义虽然生动展示了消解生态危机的美好图景,但是由于其理论设计上在马克思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现代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之间左右徘徊,因而依然存在许多理论缺陷和不足。事实上,克沃尔本人也把生态社会主义当成一种积极的理想追求,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被视为通往理想通途中渐进实现的过程。生态社会主义从生态学出发建构其理论,企图抛弃社会形态更替的客观规律而转向价值伦理的批判。这种既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又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精神的生态社会主义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这也再一次证明生态社会主义是从生态原则基础延展出来的理论构想,而不是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这样,他的理论从思潮的起源到最终实现都注定了具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
[1]JOEL K.What is ecosocialism[J].Canadian Dimension,2007,41(6):53-56.
[2]DOUG B,DAVID S,JANEZ,et al.Another look at the end of the world[J].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2003,14(3):123-136.
[3]DAVID J,JOEL K,MICHAEL L.Has ecosocialism passed on the tough questions[J].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2003,14(2):120-128.
[4]JOEL K,MICHAEL L.An ecosocialist manifesto[J].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2002,13(1):1-3.
[5]JOEL K.The enemy of nature:The end of capitalism or the end of the world[M].New York:Zed Books,2002.
[6]JIN O C,JOEL K.House organ[J].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2004,15(4):1-3.
[7]JOEL K.The Ecofeminist ground of ecosocialism[J].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2005,16(2):1-7.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刘仁胜.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10]GEOR GE S.The enemy of nature:The end of capitalism or the end of the world[J].Science&Society,2004,67(3):511-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