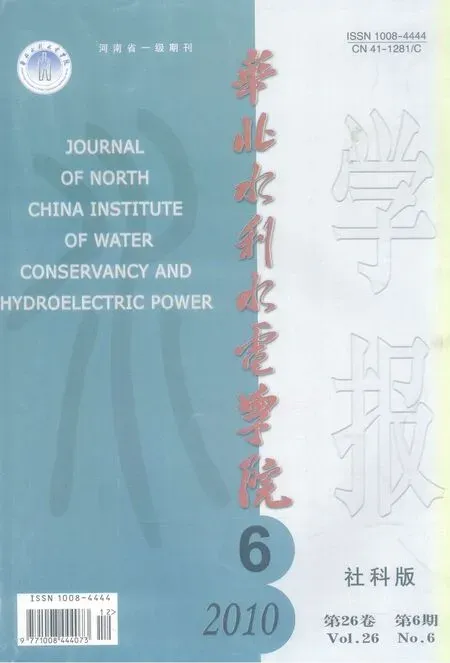马克斯·韦伯的比较法律制度研究
2010-04-07李强
李强
(华侨大学,福建泉州362021)
马克斯·韦伯的比较法律制度研究
李强
(华侨大学,福建泉州362021)
韦伯在其法律类型学分析的基础上对西方现代与传统法律制度以及西方现代与中国传统法律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然而,当理想类型方法被运用于比较法律制度研究时却可能存在着认识论上的局限性,即有可能导致以西方人的认识视角来专断地解释其它社会的法律制度,最终无法实现对不同社会的法律文化现象进行客观认识的目的。
比较法律制度;理想类型;类型学分析
一、西方现代法律制度与传统法律制度的比较
(一)西方现代与传统的法律制度比较
韦伯认为西方法律理性化过程的最高成就就是形成了现代西方欧陆的形式理性式的法律制度。借用19世纪德国法学研究中的几项假定,可以说明这种形式理性式的法律制度的一些基本特征:第一,现代意义上的形式理性的法律制度是一种专门法律家的法律,这些专门法律家所作出的各项知识努力构成了法创制与法发现的主要动力。第二,从现代法律制度中的司法裁判上看,法律的实际运作都是由专门的法律人来执行,其中任何的法律决定都是由于抽象的法命题“适用”于具体“事实”上的结果。而且,对于任何具体事实,必须都能够通过法律逻辑分析的手段从现行的抽象法命题中得出决定。第三,现代法律制度中现行的客观法律,必然是法命题的一个“毫无漏洞的”体系,或者潜在内含着这样一个体系,或者至少为了法律适用的目的而被当作是这样的一个体系。凡是未能在法学上被理性地“建构”者,即被视为与法律无关。此外,人类共同体中的全部行动都必须被解释为法命题的“适用”或“实现”,或者反之,解释成对法命题的“违犯”。因为,相应于法律体系的“天衣无缝”,“在法律的规制之下”也理应是所有的社会现象的一个基本范畴[1](P29)。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西方历史上各种传统的法律制度则全都不具有这种高度的形式理性的性格。由于韦伯对法律制度的比较散见于其多部著作中,这里仅就其中的一些主要的对比做出说明。例如在原始的、借由法的启示这种巫术手段而达成的决定里,其中形式非理性的性格表现得极为显著。其中,一般性的“法规范”既不适用于个案,也不会成为那种一旦被“确认”,将来就可遵循此一决定作出“判定”的标准规范。此外,举凡个案是以占签(犹太人的)、决斗或其他任何诉诸神明或具体的神谕来下决定之处,其中无法找到任何下决定的“规则取向”——无论是就规则的适用或就规则的创造而言。例如古代的政务官法和法务官法的诉讼手段、法兰克诸王的敕令法、教会的审讯诉讼程序等等,由于教权制支配或者家产制君主支配的影响,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实质理性的倾向。在这种法律制度中,所追求的不在于获得形式上的与法学上的精确性以及法律规范上的体系化,其目标只在于能够找出一种最能符合其权威的、功利的、伦理的目的的法律制度类型。此外,例如雅典直接民主制里的人民裁判、英国治安法官处理大众日常交易和犯罪的裁判等则是一种罕见于欧陆的非形式性的“卡地裁判”①来源于回教国家的一种裁判制度。“卡地”是回教国家的法官,特别负责有关宗教案件的审判。韦伯将重视实质的公道、平等和某些功利主义的目的,而无视于法律与行政的形式合理性的审判,称为“卡地审判”。参见[德]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Ⅸ——法律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0页,注释○35。这些裁判都不是基于抽象的法律规则体系做出,而是基于感情、伦理的关怀或者是基于政治的或者社会政策的关注而做出的[1](P223)。
(二)西方法律理性化过程中的政治影响力
韦伯在对西方现代法律与传统法律进行比较的过程中以及在对西方法律理性化过程的论述中,对于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在西方现代法律制度的形成中所发挥的影响力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从一定意义上说,法律与政治、经济、宗教之间的关系可以看作是韦伯考察西方法律理性化过程的另外一个极为重要的维度。其实,在韦伯的社会理论中,对于各种社会领域之间的关系(如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等等社会领域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着某个单一的、最终的决定性力量,在各个领域之间也并不存在单向度的影响力,各个领域之间存在着一种“有择亲和性”[2](P49-50)的关系。然而,在法律社会学中,相对于法律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韦伯更强调了法律与政治秩序之间的亲和性,尤其是在具体论述中不断地强调了政治因素在法律的理性化过程中的巨大影响力。
就法律秩序与政治秩序之间的关系而言,韦伯强调了政治因素对法律制度的影响。在西方法律之理性化发展的各个阶段上,几乎都可以发现政治秩序对法律秩序的影响力。第一,韦伯认为,法律领域里为我们所熟知的各种基本概念,在区分的方式上高度取决于法律的技术以及政治团体的结构,而经济的因素仅占有间接的地位。[1](P25)例如公法与私法的区分、“请求权赋予法”与“行政法规”之间的区分、“刑法”与“民法”之间的区分、“侵权”与“犯罪”之间的区分等等。第二,在论及由利害关系者所创制的“特别法”的技术形式可以发生改变的动力时,韦伯指出:将特别法当作是切事的特殊法规而统合到一般法里去,这一统合倾向能否真正实现几乎全赖政治的情况而定。[1](P91)例如越来越被强化的国家机构里的支配者和官僚的权力欲等,就可能对特别法向一般法律的转化起到推动作用。第三,在经由公权力的介入而导致世俗或宗教权威的强制法的情形中,政治秩序对法律秩序的影响体现得最为明显。这种经由公权力的介入而形成的法律制度的内涵和形态,主要是依据政治上的支配性格的不同而各有特色的。韦伯指出:“公权力——特别是来自君主的——之介入法生活,无论何处皆有助于法律的统一化与体系化,亦即促成‘法典编纂’,而且公权力越是强化、越是持续发挥此种走势的力道就越发强劲。”[2](P274)第四,韦伯虽然就法律的理性化的各个发展阶段在理论上进行了一般发展趋向上的概括,但在历史现实里各个地区的发展会有各种不同的可能。在这里,韦伯认为,各处的发展之所以会有很大的不同,基本上取决于政治因素的不同,这些政治因素包括:政治权力关系的不同(亦即公权力所拥有的力量强弱的不同)、神权政治的权力相对于世俗权力的权力关系不同以及法律名家之结构上的不同(这种结构上的不同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的状况)[1](P320)。
二、西方现代法律制度与非西方法律制度的比较
对西方(尤其是欧陆地区)与非西方的各种社会制度进行比较,是贯穿于韦伯社会理论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尽管韦伯对于西方现代法律制度与非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并没有做出专门的、集中的讨论,但却始终贯穿于韦伯有关法律社会学、宗教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的讨论之中。由于篇幅所限,在这里本文仅以韦伯就西方现代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法律制度所进行的比较为例,来说明韦伯法律社会学中的比较法律制度研究。这里首先需要指出的是,韦伯对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与西方现代法律制度进行比较,依然是从韦伯自始至终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出发的:即为何资本主义出现在西方现代社会而不是其他文明中?为何形式理性的法律制度出现在西方现代社会而不是其他文明社会之中?正是从这些问题出发,韦伯将其它非西方社会的法律制度(包括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作为西方现代形式理性法律制度的对比类型。也就是说,在这里韦伯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比较本身,而是为了使西方现代法律制度的特征在这种对比之中更加突出,并最终对形式理性法律之所以在西方社会(而不是其他社会)出现的原因做出解释。
韦伯认为,自秦汉以来中国一直处于一种典型的家产官僚制的政治支配形式之中。在这种家产制支配之下,行政与法发现(即司法)之间在实际上并未分离。政府官员以家产制的方式,自费雇佣仆役来担任治安与细琐的公事。帝王具有绝对的自由裁量权,整个帝国行政处于一种以传统为取向的由士人官府所控制的状态之下,西方资本主义中产业发展所必须的理性的、可计算的行政与法律并不存在。在这种帝王行政之下,大量的制定法皆为公法范围内的法令,而西方人认为极为重要的私法规定却几乎完全没有,真正受到保障的个人自由权根本不存在。在韦伯看来,传统中国的行政与司法裁判大致上停留于“卡地裁判”或者“王室裁判”的程度上,亦即停留在一种实质非理性的状态之下。由于以伦理为取向的家产制所追求的总是实质的公道而不是形式法律,因此在行政司法裁判中始终拒斥法律的形式主义。皇帝所颁布的行政法令并不是法律的规范,而是法典化的伦理规范[3](P156-160)。无论是民间的家长制裁判还是官方的家产制裁判,所强调的始终是实质的伦理上的考量,而非形式上的法律[4](P7)。因此,在法学教育与法律思想上,韦伯认为传统中国不存在类似于西方的自然法思想和形式的法学思想。
除了上述对传统中国具体的法律制度状况与西方法律制度进行了比较之外,韦伯还就中国法律制度之所以(较之西方形式理性法律)呈现出一种实质非理性的特征,进行了原因上的探究。韦伯指出,西方近代法律的理性化是由两种力量的共同运作所造成的:一方面,资本主义关心严格的形式法与司法程序,它倾向于使法律在一种可以预计的方式下运作,最好就像一具机器一样运作;另一方面,集权国家的公务系统所具有的理性化特征,要求法典系统必须交由一个追求公平之升迁机会的、受过合理训练的官僚体系来掌握,而这种理性化的官僚体系在形式上所关注的是法的一致性,特别是政府的律令具有高于传统的最高主导性。韦伯认为,只要这两股力量缺乏其一,就无法产生近代的法律体系。然而,中国的家产制整体并没有面对强而有力的资本主义利益,也不必顾虑一个自主的司法人员阶层,它所顾虑的是如何保证其正当性的传统的神圣地位,亦即行政组织力量的局限。因此,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不仅形式的法学未能发展,并且也从未设想要有一套系统的、实质的、彻底理性化的法律;一般而言,司法的本质也仍然维持着神权政治的福利公道的特色[3](P216-217)。
三、韦伯比较法律制度研究的限度
韦伯是通过运用理想类型方法将其对法律制度的类型学划分运用于其比较法律制度研究中的。也就是说,韦伯对西方现代与传统法律制度的比较以及对西方现代与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比较,都是以“法律实务之技术手段的类型划分”、“以法律担纲者为核心关注的法律类型划分”以及“法律教育和法律思维类型划分”这三种类型建构为根据来展开的。此外,韦伯的比较法律制度研究始终是把西方现代的形式理性法当成一种纯粹的理想类型,并以此为参照将其与西方传统法律制度和非西方法律制度进行对比。在这里,理想类型方法的比较功能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研究者通过在经验现实与理想类型之间进行比较来试图达到对被研究对象的客观认识;另一方面是指研究者通过在不同的理想类型(其中包含着客观上可能的因果关联)之间进行比较来试图达到对不同社会的文化现象加以客观认识。然而,由于韦伯在建构有关法律制度的理想类型时,完全是基于西方历史的经验材料,因此,当其把这种法律制度的类型划分运用于比较那些具有完全不同历史经验之社会的法律制度时,极有可能导致以西方人的认识视角来专断地解释非西方法律制度的经验。因此,当理想类型方法被运用于比较法律制度研究时可能存在着认识论上的局限性,最终使得理想类型的比较功能无法实现对不同社会的法律文化现象进行客观认识的目的。
[1][德]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Ⅸ——法律社会学[M].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郑戈.韦伯论西方法律的独特性[A].李猛.韦伯:法律与价值[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3][德]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Ⅴ——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M].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林端.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韦伯比较社会学的批判[M].台北:三民书局,2003.
Max Weber’s Comparative Research of Legal System
LI Qiang
(Huaqiao University,Quanzhou 362021,China)
Max Weber compared west modern legal system with western traditional legal system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legal system on the base of his typological analysis of law.However,there might be some issues of epistemology when Weber made research on comparative legal system with his ideal-type method.That is to say,it may results in explanation of other legal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st people,and it can’t explain different legal cultures in an objective manner.
Comparative legal system;Ideal-type;Typological analysis
D903
A
1008—4444(2010)06—0102—03
2010-09-25
李强(1978—),女,辽宁辽阳人,华侨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宋孝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