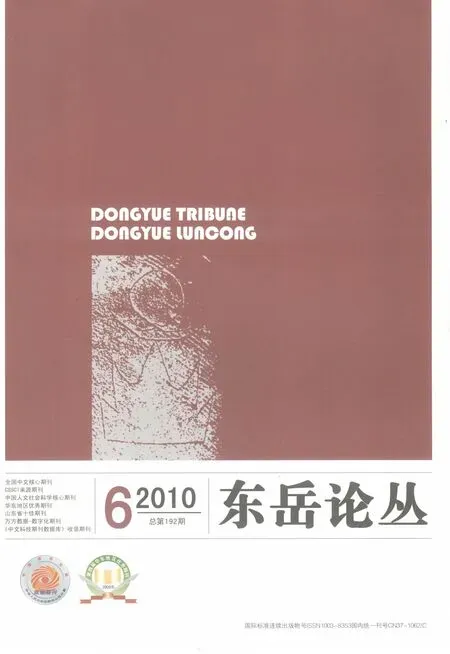近代文学对中西文化资源的选择与融合——以民主主义思想与国民意识为例
2010-04-05季桂起
季桂起
(德州学院,山东德州 253023)
近代文学对中西文化资源的选择与融合
——以民主主义思想与国民意识为例
季桂起
(德州学院,山东德州 253023)
中国近代文学的独特性,在于其对中西文化资源的选择与融合。西方文化带来了中国近代以来文化资源的变化,也带来了近代文学精神内涵的变化,但近代文学对西方文化资源的吸收并非简单的移植,而是注意到与本土文化资源的融合。其中对民主主义思想和国民意识的吸收具有很大典型性。民主主义思想和国民意识进入近代文学,得到了“民本”思想与族群意识等本土文化资源的支持,在保持其现代性内涵的基础上,体现了相当大的民族特征。这种外来文化资源与本土文化资源的选择与融合,成为中国文学从古典走向现代的一条重要途径。
近代文学;中西文化资源;民主主义;国民意识;本土文化支持;过滤整合
与中国传统的文学相比,近代以来文学在精神内涵上的变化是十分巨大的。尽管这种变化还没有从总体上脱离传统文化的精神框架,但西学东渐所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强大影响,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开始具有了我们通常所谓的“现代性”气息。以至于仅从这一点上看,就可以把近代以来的文学看作是中国文学脱离古典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的过渡。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对西方文化资源的接受与借鉴上,并非采用简单的移植,而是根据中国文化变革的实际情况,有选择地进行甄别、梳理和吸收,使其能够与自己的本土文化资源更好地融合在一起。因此,在对西方文化资源的选择上,他们尽量借鉴那些可以与本土文化资源具有结合点的文化元素,并注意用中国自己的文化资源对其加以改造,企图使其转化为建构新的中国文化的重要成分。这是近代文学之区别于古典文学,又区别于“五四”之后现代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在这一点上,对民主主义思想和国民意识引进与吸收具有很大典型性。
民主主义思想与国民意识有着很大的相关性。民主主义思想是国民意识产生的基础,国民意识反过来又促成了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与拓展。作为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理念,必以国民意识的普及为前提。因此,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变革运动中,民主主义和国民意识是作为一对相辅相成的思想观念被引进、借鉴、吸收和创生的。在引进、借鉴、吸收和创生的过程中,它们一方面保留了一些在西方文化中的原初涵义,但同时也经过了中国文化资源的过滤与整合,逐渐成为中国近代文学精神内涵的组成部分。
对中国人来说,民主主义思想并非本土文化的固有资源,而是从西方输入的。尽管自先秦时代起中国就有着“民本”思想的资源,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明代末期黄宗羲也阐发过具有强烈民主倾向的“民本”思想,他曾宣称天下应为“民”之天下,“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①。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与文化结构的特殊性,这一思想并没有自然发育成近代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从实质内容来看,中国近代以来的民主主义思想无疑是“西学东渐”后的产物。民主主义思想的文化源头是古希腊文化。在古代希腊的城邦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基础上,产生了最初的民主政体及运行机制,并形成了相应的思想体系。此后随着古罗马帝国的解体,西方社会陷入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和基督教会的专制统治,民主主义传统随之式微。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后,伴随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兴起,西方文化重新吸收古希腊文化资源进行文化变革,民主主义传统得以恢复并根据资本主义的需要进一步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文化。作为对中世纪封建专制统治和基督教神学意识形态的反动,自文艺复兴后经过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在恢复古希腊民主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同时吸收了基督教、近代科学的某些思想资源,形成了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价值观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其主要成分是民主主义的政治观、进化论的历史观、人道主义的伦理观、个性主义的人生观。这些思想观念构成了人们认识世界、认识历史、认识社会与人生的新的价值系统。在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过程中,这些民主思想被传播到中国,引起中国人政治、伦理、生活观念及其价值准则的重大变化。尽管对中国文化中是否有民主主义的思想传统,学术界还有争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也就是影响中国人近代以来民主精神和“国民”意识的思想资源,主要不是来自于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是西方文化输入的结果,或者说民主精神和“国民”意识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大交流的产物。
仔细考察近代以来的文学创作,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西方的民主精神 (包括“国民”意识)的比重在作品中日渐增加。在龚自珍等早期改革者们的作品中,尽管有一定的民主思想的表述,如龚自珍的《尊隐》篇,但当时的民主思想在形态上还属于儒家“民本”思想的范畴,还没有同西方输入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相结合,更没有“国民”意识的自觉。在这里应该特别指出,“民主”思想与“民主主义”思想是不可混为一谈的两个概念,前者表现的是一种民众对自身权利的普泛要求,后者则是一种包括了价值观念、政治理论、伦理主张、社会理想在内的完整的思想体系。以西方民主主义思想体系为摹本的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始自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主义维新派。包括具有近代意义的“国民”概念的提出,也是最早出自于康、梁二人。当然,康、梁等人的民主思想中也包含着传统儒家“民本”思想的成分,但其主要内涵,应是西方民主主义的思想范畴,如立宪思想、国民意识、平权观念、分政于民、妇女解放、伸张民权等等。
从现有资料来看,可以说从康、梁的改良主义维新派开始,中国文学中的民主精神就基本更换为西方色彩,完成了由“民本”思想到民主主义思想的转换。康有为曾有诗云:“从知天下为公产,应合民权救我疆”(《胶旅隔后各国索地,吾与各省志士开保国会》),可以看作是这一转换的一种表白。相比较“民本”思想,民主主义更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和个体权利,尤其是人的生存权利、生命价值及社会权利。例如同样是对民生问题的关注,“民本”思想主要着眼于人的“生存”问题,强调老百姓的“生存”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其文学作品大多以“悯农”、“哀民”为关注点,甚至从维护统治者的立场出发,阐发“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而民主主义思想则更注重从维护人的基本权利的立场来看待民生,强调权利对人之存在的意义。严复以西方启蒙思想的“天赋人权”论为依据,认为民众有获得自由的权利,包括生命的自由和生活的自由。自由乃是一种基本人权。“民之自由,天之所畀”,“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盗人财物者,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②在这里,对“自由”的强调超过了对“生存”的强调,这成为中国文学“民生”主题的一大变化。
从这样的思想出发,近代以来的许多作品大多不再只是延续传统的“悯农”、“哀民”的主题,而是更多强调了人性关怀、人权解放的要求。《老残游记》着重表现了封建专制官僚用“清官”的名义随意践踏民众权利的现象,表现出对这种无视人的生命权和生存权之罪行的强烈谴责。其中,刘鹗对曹州府毓贤草菅人命激起民变和齐河县刚弼对十三条命案武断处理这两起事件的描写,其主要关注点并不在传统的“哀民生之多艰”上,而是特别强调了普通百姓生命权利被“清官”所谓政绩抹杀、践踏的残酷性、危害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从人与人平等的权利意识出发,谴责那种漠视个人权利特别是妇女权利的家族制度及其伦理规约。小说从维护人性及人的正当权利出发,对旧伦理中贞操观念提出愤怒批判:“此刻她家庭出了变故,遇了这种没廉耻,没人伦的人,叫她往哪里守?”《官场现形记》写道:“中国的官,大大小小,何止几千百个;至于他们的坏处,很像是一个先生教出来的。”这样的思想同以前揭露官场黑暗的作品很不相同,不再把吏治的腐败归咎于某些昏君、奸臣、贪官,而是矛头直指造成这种黑暗现象的专制主义的文化模式,强调了文化反思的必要性。《黑籍冤魂》从人性关怀的角度,写鸦片流行给中国人所带来的惨祸,表现出对中外奸商包括一部分腐败官吏从事毒品交易,危害、剥夺人的生命权利的强烈愤慨。陈景韩的短篇小说《路毙》,揭露长期受封建意识熏染的民众对人的生命淡漠及缺乏同情心的精神状态,从改造国民性的角度呼吁提高整个社会的权利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蒋智由在他的《有感》诗中更是大声疾呼:“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从人权的角度对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历史提出了质疑。
以上这些作品虽然对民主主义思想的理解、认识还没有达到“五四”文学那种普遍自觉的高度,但也比较充分显示了随着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文学作品思想观念的重要变化。它们所传达出的信息,一是表现了中国人生存意识的改变,不再甘心成为某一王朝的顺民奴隶,而是要成为有尊严的生命者;二是表现了中国人权利意识的自觉,不再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外在的威权,而是要拥有自主自决的权利。应该说这些都是现代民主意识的必要内容。这种具有了“近代性”内涵的民主意识在当时极大地启发了中国人的国民意识、权利要求、自由精神,形成近代以来中国人精神世界巨大变化的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结我团结,振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纪,雄飞宇内畴无伦。可爱哉我国民!可爱哉我国民!”(梁启超《爱国歌四章》)“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秋瑾《勉女权歌》)“我想人生在世,就是这个自由要紧。若不能自由,便偷生在世有什么好?若是为自由而死,九泉之下也觉得值得!”(雨尘子《洪水祸》)在这些作品中,人性的“国民”意识取代了奴性的“臣民”意识,自由精神取代了对皇帝威权的盲从,男女平等的思想取代了男尊女卑的观念,对自由的追求取代了对礼教规范的顶礼膜拜。这种思想观念的改变,尽管主要发生在一部分知识分子阶层中,还没有融入到大多数国民的意识中,但却具有相当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它预示着一个民族精神大变革时代的到来。
民主主义思想对中国的输入,为中国人带来了改造或变革社会制度及生活方式的新的理念和思路,造成了中国人对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权利要求的重新认知,由此而形成了“国民”意识产生的社会与文化背景。
对于这一点,梁启超曾有过专门论述,他说:中国的改革应以制度的改革为关键,其所走的道路是引入民主的制度。而制度的改革则需以观念的改革为前提,在民众中造成民主的精神,即所谓“新民”。这就需要在民众中树立以民主主义思想为主导的“国民”意识,以取代以往的“臣民”意识。他认为,“国民”的涵义为:一是要有独立的人格意识,二是要有合法的权利意识,三是要有有机的团体意识,四是要有民主的国家意识。只有民众普遍由“臣民”转变为“国民”,国家才有真正的竞争力,民族才有复兴的希望。“有国家之竞争,有国民之竞争。国家竞争者,国君糜烂其民以与他国争者也;国民竞争者,一国之人各自为其性命财产之关系而与他国争者也。……国家竞争其力薄,国民竞争其力强;国家竞争其时短,国民竞争其时长。”③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将“国家”与“国民”作为对立统一的概念加以阐发,认为国家是封建专制社会中皇权至上的产物,“国家即朕,朕即国家”,国家一直被视为帝王个人家的私产,是家族制度“化家为国”的结果。“国家者,以国为一家私产之称也。古者国之起原,必自家族。一族之长者,若其勇者,统率其族以与他族相角,久之而化家为国。其权无限,奴畜群族,鞭笞叱咤。一家失势,他家代之,以暴易暴,无有已时,是之谓国家。”④“国家”既为一家之私有,就与“国民”相分离,从而导致“国土云者,一家之私产也;国际云者,一家之私事也;国难云者,一家之私祸也;国耻云者,一家之私辱也。民不知有国,国不知有民。”⑤而“国民”恰恰不同,梁启超认为“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⑥他进而得出结论:国家只有进而为国民之国家,而非家族之国家,才能够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摆脱内受奴役外受欺侮的命运,走上富强之路。
梁启超的这些观点,代表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国民”意识的觉醒。很显然,他对“国民”概念的阐发和界定,不是源自于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而是基于他对西方以民主主义为核心的近代思想资源的吸取。在中国古代的文献中,虽然也有个别“国民”的词语出现,但并不具备现代“国民”概念的内涵。如《左传》“先神命之,国民信之”,但此“国民”强调的是地域概念,意指本国人,并不涉及权利内容。统观整个封建专制时代,“国民”一词很少使用,诚如梁氏所言:“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⑦在中国古代,人们更多熟悉的是“臣民”、“顺民”、“庶民”、“黎民”等反映社会上下等级关系的措辞。“国民”一词的现代含义,实是从接受西方思想资源开始。关于“国民意识”与民主主义思想之间的关系,梁启超在 1901年《清议报》上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也做了明确地说明,他说:“国家者,本于人性,成于人为”,乃“同一之国民,自然发生之团体也”,“国家为人民而立者也”。从主权归属看,“国家与人民一体”,其主权在民。“人民之盛衰,与国家之盛衰,如影随形”,“有治人者,有治于人者,而无其级。全国民皆为治人者,亦皆为治于人者。一人之身,同时为治人者,亦同时即为治于人者。”⑧这些思想与西方十八世纪启蒙主义运动以来的民主主义思想同出一辙。
但是,应该看到,无论是来自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还是在这种思想催生下的“国民”意识,都不是简单的文化移植,而是经历了一个与中国的本土文化与社会实际相融合的过程。民主主义思想及“国民”意识在当时之所以能够顺利进入中国人的精神领域,主要在于它们得到了中国本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呼应。“民本”思想虽然与外来的民主主义思想并非同源文化的产物,但它产生的思想基础却有着相似的文化基因。“民本”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中国尚未被专制主义完全笼罩。在礼崩乐坏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家天下的思想基础开始动摇,而专制的皇权意识与奴化的臣民意识还未真正形成。以儒家、墨家思想为代表的显学占据了意识形态的主流,“民本”思想得以盛行。这种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保留下来,虽历经专制皇权的一再践踏、蹂躏,而火种仍未熄灭。在近代中西文化碰撞的背景下,民主主义思想与“民本”思想的接触,使得中国固有的“民本”思想的文化资源在外来思想的促动下,有了一个历史性的升华,而民主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也得益于“民本”思想的帮助。自先秦时代起中国就有的“民本”思想的资源,如儒家思想中“天下为公”、“民惟邦本”、“民贵君轻”的观念,墨家思想中“尚同”、平等的意识等,对中国人接受民主主义思想以及“国民”意识的形成都是不无裨益的。这些资源虽然与民主主义思想有着实质上的差别,但却为民主主义思想的输入提供了本土文化资源的支持,使得来自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有了一定的本土文化的依托。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中国人对民主精神的理解,一方面是对中国文化固有的“民本”思想的继承,另一方面也是用民主主义的新的思想内涵改造和升华了原有的“民本”思想,使其获得了与时俱进的素质。
事实上,民主主义思想进入中国后,一直在寻找着本土文化资源的支持。无论是严复、梁启超、孙中山,在论述民主主义思想涵义的时候,都经常引用中国“民本”思想的内容。而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在反抗满清专制统治时对“民本”思想的阐发,在晚清知识分子中也大行其道。这说明,民主主义思想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资源,如果要被中国人所接受,必须与本土的文化资源相结合,来寻找自己的合法性支撑。如陈天华在小说《狮子吼》中就曾经特意用中国的古史来印证民主主义在中国实行的合法性,他说:
自夏、商、周全是贵族时代,民权也很发达。无论天子、诸侯、大夫、陪臣,要想争权的,都要巴结民党。民心所归,大事可成;民心所离,立见灭亡。所以当时的学说以民为天。如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话,皆言民之尊重。有得罪民党的,比什么罪恶都大些,不曰“独夫”,即曰“民贼”,诗书记载,以警后世。
这虽然是对中国古史有意的误读,但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民主主义思想的输入是需要一个中国本土文化的立足点的。因此,尽管民主意识、自由观念是从西方文化资源中引进的,如黄兴诗所言:“太平洋上一孤舟,饱载民权与自由。愧我旅中无长物,好风吹送返神州。”(《自美洲归国途中口占》)但当时的中国人却并非盲目的引入,而是结合中国自己的文化资源和社会变革的实际要求,把这些思想同中国的现实条件与文化土壤进行了必要的整合,使“民权”、“自由”的内涵有了特定的历史性与民族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主主义思想在同中国本土文化资源结合的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的过滤与整合,其原初内涵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同西方文化的民主主义主要关注于人的个体权利、个体价值不同,中国近代以来的民主主义更重视群体权利、群体价值。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的文学家们更多关注的是一种以个体解放为方向的民族的和民众的群体解放,这就使得他们的个性解放要求同西方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在这一时期改良或革命志士们的作品中,个性意识以一种新的群体意识的姿态得到了大量表现,这就是觉醒的“国民”意识。应该说,中国近代文学中的“国民”意识,是一种个性意识与群体意识互相包容的意识,它既具有西方文化的影响,又有着中国文化的印记。其中虽然包含着个性解放的要求,但更主要是对群体权利的争取。在这中间,中国传统的“族群”意识显然对“国民”意识的产生也起了一定的影响作用。尽管“国民”意识在引进之初,人们也竭力区别它与中国人传统的“族群”意识的不同,如梁启超曾说:“群族而居,自成风俗者,谓之部民;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⑨但“国民”意识进入中国,还是得到了本土“族群”意识的支持与改造,使其与西方的“公民”意识有了很大区别。“族群”意识促使“国民”意识在引进之时,更偏重于“群”即民族之义,而非“个”即个人之义。这正如许纪霖先生在针对梁启超有关“国民”论述时所指出的:“特别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国民,并非公民(citizen),它不是像后者那样是一个具有独立身份的个体,而常常指国民的总体而言,是一个集合概念。”⑩也就是说“国民”主要不是一个个体意识的概念,而是一个群体意识的概念,在这其中它过滤了西方文化的一些内涵,而加入了中国文化的一些元素。这说明,中国人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是不能回避本土文化影响的。
而且,“国民”意识在中国的产生,经过了日本文化的转手。明治维新后,日本对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的接受,结合了日本文化重群体而轻个体的特点,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的同时,文化上倡导国民主义。被称为日本近代思想之父的福泽谕吉曾强调:他所奉行的“主义”,虽然在于使日本由东方文明转向西方文明,脱亚入欧,但其“重国家”和奉天皇为最高权威的观念不变。这种“主义”强调的是一种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的“国民”意识,而非西方风行的个人主义。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同源,有着极为相近之处,其近代的国民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中国的“国民”意识。
当然,“国民”意识在中国的出现,更应该看作是当时中国人政治伦理观念的一大跃进,它标志着人们开始从“臣民”的奴隶意识中挣脱出来,以一种主人公的觉醒态度要求应有的社会权利。“国民”——这是受西风东渐影响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自我确认。流传在当时的《国民歌》、《军国民歌》、《女国民歌》表达着“国民”们的自豪感和庄严感,也表达出一个民族的现代意识的觉醒。不能因为“国民”意识是一种群体意识,就否定它所包含的个性解放的意义及其现代性内涵。有的研究者从单纯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出发,批评这一时期文学中的“国民”意识是个性意识的退化或对个性意识的遮蔽,这是不准确的。实际上,“民权”、“自由”在当时并不是单纯西方化的概念,它包含着实在的合乎中国现实需要的内容: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只有先推翻专制帝制,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实现政治的自由,才能够普遍实现人们生活中的自由。诚如梁启超所言:“我中国今日所最缺而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何也?必先铸部民使成国民,然后国民之幸福,乃可得言也。”[11]邹容所说,只有先“拔去奴隶之根性,以进为中国之国民”,然后才能争取人人“天赋之权利”[12]。应该说,在当时这些改革志士们的心里,“国民”意识之所以作为群体意识的改造被放在首要地位,对外部世界的政治责任之所以掩盖了对“自我”个体意义的体悟,主要是因为他们感受到这样一种时代使命,促使他们不得不先牺牲个人的自由而去争取民族的自由,不得不先放弃个人的权利而去争取群体的权利。这种选择从心态上仍然是自由的。因此,相比较西方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中国近代以来的启蒙主义更重视“国民”意识的启迪,而相对弱化个性意识的培养,这应该说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革及发展的逻辑进程的自然结果。对此,我们不应以今天的社会标准和学术视角去过份地苛求前人。
“国民”意识的产生是近代以来在中西文化大交流的背景下,中国人自我意识的一个巨大的转变,是中国人思想境界向现代化方向的一次重要的提升。它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时代精神与文化语境,从而对文学产生了深深的影响。“国民”意识进入到中国的文学,促使文学内容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变化,从此中国人看待历史和现实的眼光产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一种以平等、自由为主要价值追求的评判生活的准则得以形成,并重新建构了作家的文化心理。作家的创作由一般的关注民生向更加关注下层民众的生存状态及人生命运发展。由此出发,平民主义、人道主义的文学思想开始在文学创作中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这一倾向是促使中国的文学在精神内涵上走向“现代性”的关键动力,同时也是启发“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的思想背景和文化语境。
[注释]
①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转引自《中国哲学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 189页。
②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 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 3页。
③④⑤⑥⑦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 116—117页,第 116页,第 200页,第 116页,第 116页。
⑧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梁启超选集》,第 184—187页。
⑨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梁启超选集》,第 217页。
⑩许纪霖:《政治美德与国民共同体——梁启超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 1期。
[11]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梁启超全集》(第 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 1066页。
[12]邹容:《革命军》,《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散文集》(第 4册),上海:上海书店,1993年版,第 752页。
季桂起(1957-),男,德州学院副院长,教授,文学博士。
I206.5
A
1003-8353(2010)06-0027-05
[责任编辑:曹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