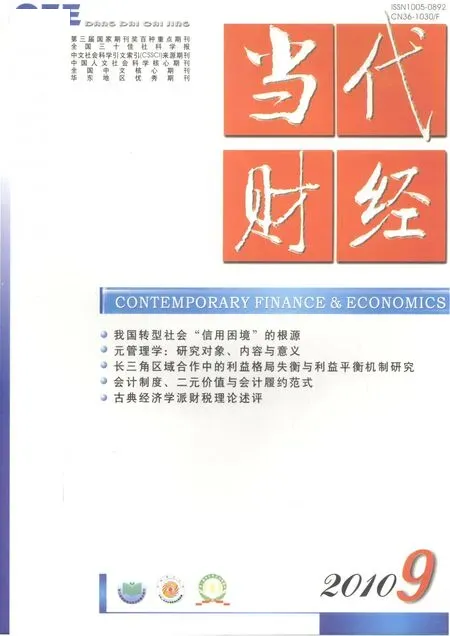元管理学:研究对象、内容与意义
2010-04-05吕力
吕 力
(武汉工程大学 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元管理学:研究对象、内容与意义
吕 力
(武汉工程大学 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各种各样的管理学属性之争中,管理学知识中的“科学与人文”是否能统一、如何统一等问题从来都没有得到最终解决,元管理学围绕此一问题展开研究。元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管理现象或管理实践,而是全部管理学知识;元管理学研究管理学知识的性质、来源和产生的机制,以及对管理学知识的可靠性和客观有效性进行检验。元管理学的研究必对中国本土管理学有所裨益——因为所有有关本土管理研究方法论的争论都直接间接地与管理学学科性质、体系结构等相关。
管理学;学科属性;元管理学;认识论
一、“管理学学科属性”的世纪争论
(一) 问题的缘起
2007年《管理学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试问管理学——管理学在中国侧议》,文中提出了“有没有普适的管理学?”的疑问,考证了一些长期以来模糊不清的名词如“管理学与管理科学”、“管理学与一般管理学”、“指导性与实践性”、“管理文化与管理组织”、“管理哲学与管理学”,结果发现这些关乎管理学学科结构的基础性概念几乎都没有定论。[1]在文章的结语部分,作者指出,这些疑惑对于综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管理学,其学科结构会有什么特点?管理学的学科结构与“创建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是怎样的关系?在“创建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的历史进程中,学科结构值得研究吗?教育部科技委管理学部刘人怀院士(2009)对于管理学理论的基本架构也提出了19个具有普遍性问题,包括:“为什么要对管理、科学和管理科学等基本概念做一番正本清源的探讨”、“什么是管理科学,管理科学与管理学是什么关系”、“什么是管理,什么是管理活动什么是管理工作什么是管理者”等。
事实上,关于管理学的学科属性之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有的学派强调管理学的科学属性,有的学派强调管理学的人文艺术属性。泰勒认为,管理学主要研究如何通过科学的手段来提高生产效率。泰勒由此创立了科学管理理论。较早明确提出对“管理科学”持不同意见的是利昂·普拉特·奥尔福德(1877-1942)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丘奇。奥尔福德和丘奇(1912) 认为,泰勒方法的缺点是“以精心设计的机制或制度”取代了领导艺术,他们认为泰勒的所谓“科学管理”过于机械,他们对“科学管理”一词表示遗憾,因为它意味着“一种科学,而不是管理的艺术”。[3]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认为管理学是科学与艺术的综合,他指出“我们对已取得的成就感到振奋……正在朝着创造活力的管理科学和基于科学的艺术迈进”。[3]
不仅如此,有关管理学学科属性之争的另一个主要议题是:管理学究竟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或者管理学是否具有普适性?丹宁布灵(Dannenbring) (1981)等认为,管理学需要应用自然科学方法对管理者面临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案,尽管管理科学可能不如物理学那样精确,但这并不构成管理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性区别,管理学应追求其普适性,能够运用数学语言是学科成熟的标志。[4]管理学知识体系目前缺乏统一性,这只表明管理学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每一学科的初始阶段都会表现出这种特征。惠特利(Whitely)(1984)则认为,管理学与自然科学有本质上的不同,管理学是一门实践导向的社会科学,社会实在不同于自然现象,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包含着更多的价值判断和选择。[5]管理学应重视文化、价值观和习俗的作用,应走出过分数学化的误区。林羲(2006)认为,自然科学注重的是发现研究客体的因果律,因此自然科学具有很强的预测性与普遍适用性;而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这使得社会科学不仅很难在严格意义上重复进行,更使其结论的普遍适用性受到挑战。[6]彭贺(2009)和郭毅(2010) 认为,管理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7-8]其必然包括普适性知识体系与地方性知识体系,显然这一论断也是基于管理学的社会科学属性的。一般认为,在自然科学领域不存在地方性知识。
自泰勒1881年开始著名的“工时研究”创立现代管理学,有关管理学学科属性的定义与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管理学学科属性问题成为跨越三个世纪的难题。
(二)对“管理学学科属性”研究的传统路径——从“管理现象”到“管理学”
考察以上争论,我们可以发现,在上述“管理学”学科属性之争中,对于“管理”或“管理活动”的定义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对于管理活动的本质也不存在太大的疑义。美国管理协会对管理活动的定义是:通过他人的努力来达到目标。这一简明扼要的定义给出了管理活动的本质,或者说给出了“管理活动”区别于人类其他活动的根本特点。谭力文(2009)认为,管理活动产生的原因主要应归结为人类为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与凶险的内外势力,为维护自我生存与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特有的“群聚”现象,并指出人类协作而产生的“群”就是管理理论中的“组织”。[9]在组织这一概念的基础上,谭力文继而援引马克思的话,“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谭力文认为,这种协调活动的本质就是管理。上述对管理活动的本质的认识不仅得到主流管理学派的认同,在复旦大学苏东水教授所创立“东方管理”、黄如金教授所创立的“和合管理”、南开大学齐善鸿所创立的“道本管理”中均有类似的描述。例如,东方管理学认为,“管理就是组织人力与物力以实现正式组织的目标与过程”;[10]齐善鸿(2009)的“道本管理”认为,管理的基本目的就是解决组织中人群冲突和建构目标效率秩序。[11]就对“管理”或“管理活动”的定义而言,韩巍(2009)认为,组织管理的基本要素及其关联,已经被泰勒、法约尔、韦伯、巴纳德,包括德鲁克等西方学者确立起来了,这些基本问题(即对管理活动的界定)已经轮不到无论是哪一国的当代学者置喙了。[12]由此可见,尽管学术界对于管理或管理活动的定义存在表述上的区别,但其核心与本质“组织”、“协调”、“目标”等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别,对“管理活动”的看法基本上是统一的。
然而,大量的争论从何而来,这正是本文要讨论的关键问题。在笔者看来,这一争论来自于从“管理活动”到“管理学”这“惊人一跳”。或者说,“管理活动”并不能必定推导出“管理学”应如何进行研究,在这“惊人一跳”过程中,绝大多数观点持一种“应然”的判断。我国著名管理学者席酉民(2010)持论应属公允。席酉民认为,管理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探索和寻找相对确定、有效地实现管理的目标方法、技术和思维方式等。[13]然而,即使从这一持论相对公允的判断来看,其中亦包括“应然成分”。例如,为何将“管理学”限定在“相对确定”的范围内?这种限定一定会将某种出于直觉的管理艺术性思维排除在管理学研究的范围之外。此外,如何把握“相对”的“度”?从对席酉民教授上述定义的深入分析可以得知,无论“度”在何处,总会将一些“相对不确定的、然而却是真实”的管理思想排除在外。可以肯定的是,这种限定对于席酉民教授创立的和谐管理理论没有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管理学的某一具体学科,这种限定甚至是必须的。然而,对于以“管理学自身”为研究对象的元管理学,这种限定就是主观和有害的了。
在《论管理学的普适性及其构建》一文中,谭力文教授(2009)在对管理活动的概念进行了详细的探讨之后,得出管理学“可以得到具有普适性的管理理论”。[9]这一表述没有问题,但关键在于“可以”二字,管理学可以得出普适性的结论,不等于说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必然是普适的,作为一个总体,管理学究竟是不是普适的,的确是一个问题。谭力文教授在该文末尾所认为的,“管理学的普适性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可以达成基本的共识”似乎过于乐观。我们前面所列举的关于管理学学科属性的种种争论,它们大多也属于“应然”的判断。例如,泰罗认为“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使雇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是一种应然判断;奥尔福德和丘奇认为管理学“应该”包括艺术的成分,[3]丹宁布灵等认为,管理学应该需要应用自然科学方法对管理者面临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案。[4]惠特利则认为,管理学应重视文化、价值观和习俗的作用,走出过分数学化的误区等。[5]
事实上,学术界大多还是注意到管理活动中存在的社会的、人文的、直觉的、艺术的成分,这些成分无法包含在“管理科学”或“普适性的管理学”之中。例如,在国内学术界引用较多的林曦的《管理学的学科属性与学科定位》一文中,林曦(2006)认为,管理活动及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管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关注人的尊严与价值的,管理活动所涉及的对象、场合、时间和地点是具体的,或者不具备更强的一般性,因此似乎将管理学完全定位于“普适性的科学”并不合理。[6]因此,对于大多数管理学者而言,不得不承认“管理学既是科学,又是技术和艺术”或者“管理学既有人文的属性,又具有自然科学的属性”。
对于“应然”这一路径而言,“管理学是科学和艺术”或者“管理学既具有人文的特质,又具有科学的特质”是一个终极判断。这一判断实际上早就被诺贝尔奖获得者赫尔伯特·西蒙甚至更早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丘奇所提出,[4]丘奇提出的这一观点的时间几乎与泰勒创立管理学这一门学科的时间一样久远。然而,这一终极判断并未结束这一跨越了三个世纪的争论,《管理学报》特约评论员就敏锐地指出,“对于综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的管理学,其学科结构会有什么特点吗?”[1]换言之,管理学知识中的“科学与人文”是如何统一起来的,这对于“管理学属性”的传统研究进路而言,是一个真正的难题。
二、元管理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上述目前没有定论的争论使我们可以宣称存在“元管理学”这样一个研究领域。韵江(2007)、罗珉(2005)、杨栋(2009)都曾提到过“管理学的元研究”。[14-16]韵江在《管理学合法性的反思——基于跨学科的视角》一文中提出了管理学“元研究”的必要性。罗珉认为管理学范式理论是以管理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具有元管理学的性质。杨栋认为,管理学科学属性是管理学元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吕力(2009)认为,元管理学是对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学科性质、体系结构进行系统反思和研究的学科。[17]Haridimos Tsoukas(1984)认为,元管理学将重新定义管理的本质以及明确各类管理学知识的应用范围。[18]
(一)种种“元理论”及其学科性质
“元”的西文为“meta-”,意即“在…之后”或“超越”。“元”在与某学科名相连所构成的名词中的含义是:这种更高一级的形式,将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来审视原来学科的性质、结构和其他种种表现。“meta”起源于“metaphysics”一词,后人在整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将其《物理学》之后的著作称为拉丁文的“metaphysica”,直译为“物理学之后”,它探讨的是世界本体的原理,其含义与我国古代关于“道”的学问相近。《易·系辞》有“形而上者谓之道”的说法,于是“metaphysics”就被译为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回答的是世界的本原等问题,代表了一种整体性反思。
在“metaphysics”之后,很多具有整体性反思性质的学科都被冠以前缀“meta”。例如,德国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Hilbert,D.)提出的元数学概念就是希望用有穷的方法来证明无穷的数学系统的协调性,它把整个数学理论完全形式化为无内容的符号体系,其中包括作为符号的基本概念、作为符号系列的公理以及作为符号系列变形规则的基本推理规则;然后把这种符号体系作为研究对象,用另一套理论来研究它的协调性。这种用于研究数学理论的理论便是数学的元理论。
元逻辑学是在希尔伯特的元数学概念和形式化思想的启发下发展起来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元逻辑学是指对逻辑理论整体性质的研究,而对某个具体的逻辑法则并不感兴趣;广义的元逻辑学是指对于一般形式系统的研究。换言之,元理论意味着用一种理论——元理论——来审视另一种理论,这是元理论独立性的一种体现。
1951年,沃尔什(Walsh.W.)率先提出了“分析的历史哲学”一词,[19]实际上就是历史学的元理论。
1925年,波兰社会学家兹纳涅兹基(Znaniecki.F.)首先创造了具有元科学性质的“科学学”一词,它不仅将全部科学知识作为研究对象,而且还涉及了科学家的学术活动、科学的社会作用等知识与社会交叉的问题,从而使科学的自我反思从科学自身扩展到了与社会的关系上。在科学元理论的启示下,1970年,古尔德纳(Gouldner.A.)将元社会学定义为“社会学的社会学”,即把社会学看成一种社会活动加以研究。
从数学到哲学、科学、乃至不少具体学科,各种以元理论为标题的研究逐渐诞生并发展起来,这些不同的元理论构成了一个元理论家族,从中可以看出元理论体现了整个学术领域“自我意识”的萌动。当某一学科尝试建立元理论时,它就是在对本学科进行反思、探索,而其中隐藏着变革。[20]
(二)元管理学的研究对象
元管理学对管理学自身的研究,因此元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管理现象或管理实践,而是现有的全部管理学认识,元管理学本质上是一种认识论。借鉴刘人怀院士(2009)的说法,管理学是研究管理现象与管理实践的全部知识的总和,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知识体系,[2]元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这个知识体系。
管理知识里既包含科学的成分,也包含人文的、艺术的成分,甚至包括只能体验得到、不可言传的技能(或者说所谓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元管理学既然是对管理学自身的研究,就应全面涵盖上述不同类型的知识。在研究对象方面的模糊不清,必然导致研究结论的根本性错误。例如,认为“管理学是一门普适性科学”的观点,大多忽略了管理知识中人文的、艺术的、直觉的成分;而认为“中国管理学应建立全新体系”的观点又忽略了管理知识中科学的、普适的成分,这两种观点之所以经不起反驳,其错误的源头均在于片面地界定了研究对象。
管理学知识中既存在明确的、普适的科学性知识,也存在不明确的、地方性的、体验性的、感性的、直觉的知识,在“明确”与“不明确”之间存在大量“相对明确”,同时也“相对不明确”的管理学知识。如何确定“相对明确”的“度”?在本文看来,不如事先搁置这一争议,而就全部管理学知识做一番考察,不论它是明确的还是几乎完全不明确的。
在管理活动领域,存在着大量的“普适性”之外的管理知识,这些知识同样对于人类的管理活动非常重要。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人敢于宣称,只要掌握了现今主流管理学教材中的理论就完全能胜任实际的管理工作——这是因为还存在着大量的实用的、不可言传的直觉性知识,还存在着大量的有关管理实践的艺术。管理学的一门常规分支,可以宣称只研究其中的一部分,但以管理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元管理学”就不能不以全部的管理学知识为研究对象。
究其源头,求知的最终目的是求得人类更好的生存。既然直觉的、不明确的、艺术性的知识在管理领域中具有相当的实践价值,管理学就不应将研究视角总是固定在可以重复、可以验证、可以明确表达的知识上,作为对管理学自身进行反思的“元管理学”更应将研究范围扩展到全部的管理学知识领域,惟其如此,才能实现反思,才有可能在反思的基础上发展管理学自身。
(三)元管理学的研究内容
如前所述,认为“管理学是研究管理实践中普适规律”的观点实际上是对管理学研究的一种“应然”规定,它限制了管理学知识的来源,同时决定了对管理学知识真实性的检验手段——这种检验手段就是基于大样本的所谓实证主义方法。这样一种观点显然不为管理学界大部分学者所接受,管理学的全部知识域中无疑包含着人文、艺术的成分,那么这部分知识的来源是哪里?它产生的机制如何?这部分知识和所谓普适性规律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上述问题正是元管理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它本质上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元管理学研究管理学知识的性质、来源和产生的机制,以及对管理学知识的可靠性和客观有效性进行检验。
哲学上传统认识论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21]一是关于认识的性质、前提和基础等问题,近代哲学对这类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具有本体论哲学的特点;二是认识的来源、过程和机制即认识的发生学方面的问题;三是认识的可靠性、真理性、确证性和客观有效性等知识论问题。
具有本体论哲学特点的认识论以洛克的经验论、休谟的怀疑论以及康德哲学为代表。洛克的经验论以承认对象的客观实在为前提,而休谟则质疑对象的实在性,他认为,“我们所确实知道的唯一存在就是知觉……除了知觉之外,既然从来没有其他存在物呈现于心中,因此我们永不能由知觉的存在或其任何性质,形成关于对象存在的结论”。[22]康德认为,一个具有先天认知能力和形式的先验主体是认识的中心,康德以此来解决认识的本性和来源问题,从主体的认知能力来划定认识的范围和可靠性,认识就是主体运用先验的感性直观形式和知性范畴对感性材料、表象进行综合整理而得来的。
在现代科学和哲学看来,由于传统认识论中的命题不能被经验所证实或证伪,因此这一研究思路逐渐被淡忘,关于认识的来源、机制等认识发生学问题被逐渐经验科学化。[21]20世纪重视认识论研究的哲学家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使认识论问题经验科学化的倾向。现代西方哲学大多把科学发现和认识发生问题看做经验心理学问题。当代认知心理学、脑科学与人工智能、神经生理学等新兴学科也都体现了认识发生问题的经验科学化倾向。
与此同时,哲学认识论发展的另一条进路是科学哲学,即将科学作为研究对象,关注科学发现和发展的方法和逻辑、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知识的检验及其标准、科学知识的演进和模型方面的内容,把认识论转向对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21]
基于以上考察,本文将以上认识论研究的两种思路应用于管理学,将对以管理学全部知识为对象的元管理学研究划分为以下两大部分:
(1)从管理学认识的心理学发生机制上研究管理学知识的性质、来源和产生机制。现代的认知神经科学已经可以从自然科学的角度部分揭示认识的来源、过程、机制与结构问题。认知神经科学是在脑神经科学(Neuroscience)和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的基础上发展而来。[23]
在认知神经科学产生之后,一些社会科学家试图使用认知神经科学的手段研究社会科学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00年12月,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研讨会(Princeton workshop on Neural Economic)首次使用了神经经济学(Neural Economic)名称,并在以后的时间内逐步被广泛认可。与神经经济学相对应,中国学者马庆国提出了神经管理学的概念。[23]
显然,认知神经科学作为一种有效的手段,既然可以研究被管理者的神经心理因素,也就毫无疑问地可以研究管理者的认识来源、产生机制和结构,后一研究就是元管理学所关注的。因此,借助于认知神经科学,我们就可能回答管理学知识中的直觉、意会性知识的来源,及其在管理实践中被应用的情况。这就是从管理学心理学发生机制上研究管理学科的性质、来源和产生机制。
(2)从对管理学知识的检验与确证方面来研究全部管理学知识的体系结构。在知识问题上,当代哲学思潮的特点是“不考虑心灵怎样或是否可以真正认识外部世界的问题,而是一开始就预先假定,我们已经以各种方式获得了知识,并且在任何情况下能去认识这个世界”,[24]从而问题就变成了这种知识的发现和证明的逻辑的问题。
这一观念影响到各种元理论,具体到元管理学,它的基本问题就不是我们能否获得管理学知识,而是预先假设我们能够认识管理实践,管理学知识可能存在或已经存在,而无论它们以什么知识形式存在。我们的任务是通过描述这种既包含普适性规律又包括特殊的人文艺术因素的知识,是如何在实践中被检验、确证与应用的,从而探查这些不同类型的管理学知识是怎样在管理实践的过程中被逻辑地组合成一个有机的管理学知识体系的。
众所周知,当前的主流实证管理学早就确定了知识的“检验标准”,这就是形成假设、获取数据、检验假设的一致性等一系列规范的步骤,毫无疑问,如果遵循如此严谨的操作,得到的将是“真知识”。然而,这一套操作可能是获得“真知识”的充分条件,但不一定是“真知识”的必要条件。在管理知识领域,相当多的意会性知识也是“真”的,或者说在一定条件、一定的范围内是“真”的,但是这些“真知识”很难通过如此一套标准。例如,意会性知识在这套操作的起始阶段,即“形成假设阶段”就会有很大的麻烦,意会性知识在很多情况下难以形成表述清晰、逻辑严明的假设。主流西方管理学因为这些意会性知识的麻烦,断然将其排除在主流管理学研究范围之外。主流管理学尽管“主流”,但也只属于管理学研究的一个流派,这样做无可厚非,但如果一定要坚持“主流帝国主义”,将其作为一种通行标准强加到其他研究范式上,则欠妥当。元管理学既然以全部管理学知识为研究对象,就还需要考虑普适性之外的地方性、本土性、个性化的管理知识,根据其在管理实践中被应用的情况,为各类管理学知识确定“真”的标准。
三、元管理学对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意义
如果管理学是一门纯粹的自然科学,就不会存在本土管理学——本土管理学之所以存在,正在于它是普适与特殊、科学与人文艺术的混合体。假如丹宁布灵(Dannenbring)的观点正确,管理学研究的目标如果是追求单一的普适性的理论体系,则本土管理学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错误的命题。因此,本土管理学所以存在、如何存在及其研究方法论正与管理学的学科属性、学科结构等密切相关,而这正是元管理学的研究主题。
在2009年第二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论坛上,北京大学巩见刚(2009)提出,管理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因此管理学研究中发现的规律很难保证有普适性和重复性。[25]华南理工大学张树旺(2009)在《普适性与民族性的真正对话的开始——“管理学在中国”论争的方法论意蕴》中认为,科学主义管理是以实证研究为研究底色,其研究特点是严格的科学性、普适性和逻辑性;人本主义管理学以解决实际管理问题为研究底色,其研究特点是艺术性、民族性和有效性。此双方近20年来(实际上为100多年来——本文注)互为诟病,难以对话,这一学术对立源于“管理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或者“管理学的普适性与非普适性”的经典命题。[25]
情境化是著名管理学者徐淑英教授(2008)所首倡的一个概念,徐教授对情境化的定义非常简明: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是指将研究置于一定的情境中。徐淑英认为,情境化在管理研究中越来越重要,它是在中国进行本土研究的关键要素。徐淑英教授指出了情境化的4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决定研究什么,即研究者不仅应该关注已有的(西方化)主题,而且要问一些中国的公司,管理者和员工所特有的或重要的正确的问题。第二种方法是理论的情境化,即将西方理论和假设进行适当的修改使之适用于中国的环境。第三种方法是测量工具的情境化,使在西方环境下开发的构念在中国情境下仍然是有意义的。第四种是方法论的情境化,就是在中国情境下使用新的方法论来观察、记录和分析数据。[26]
按照学术界的理解,情境化研究有2种典型的范式:情境敏锐性研究(情境嵌入式研究)以及情境特定性研究。显而易见,情境化同时包含了对情境的普适性理解和对情境的特殊性的理解,这两种理解实际上与管理学知识来源的心理发生机制有关,它们又分别决定了本土管理学中的普适属性与人文艺术属性。正如李平教授(2010)所指出的那样,任何本土现象都有共同普适性元素,也有独特新颖元素,而关键在于研究者是否关注到它,如果关注独特新颖性元素,就是本土研究,如果不关注,就是普适性研究,然而“关注”只是一个起点,从“关注”到管理学知识产生的全过程如何?——这是从过程来看本土管理学的产生。[27]从结果来看,这两种研究的结果是截然相区别的吗?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这实际上也是管理学学科体系结构在本土研究中的反映,或者说,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元管理学问题。
[1]本刊特约评论员.试问管理学——管理学在中国侧议[J].管理学报,2007,(9):549-555.
[2]刘人怀.大平台、聚义厅及其它——四谈创建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若干问题[J].管理学报,2009,(9):1137-1142.
[3]雷恩·D·A.管理思想的演变[M].李柱流,赵睿,肖聿,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4]Dannenbring.Management Science:An Introduction[M].New York:McGraw Hill,1981.
[5]Whitely R.The Scientific Status of Management Research as a Practically-Oriented Social Science[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1984,21(4):369-390.
[6]林 曦.管理学的学科属性与学科定位[J].管理世界,2006,(3):88-96.
[7]彭 贺.也从批判性和建设性的视角看“管理学在中国”[J].管理学报,2009,(2):160-164.
[8]郭 毅.地方性知识:通往学术自主性的自由之路[J].管理学报,2010,(4):475-489.
[9]谭力文.论管理学的普适性及其构建[J].管理学报,2009,(3):285-290.
[10]胡祖光.东方管理学及其在管理理论连续谱中的地位[J].浙江社会科学,1995,(5):14-21.
[11]齐善鸿.道本管理论:中西方管理哲学融合的视角[J].管理学报,2009,(10):1279-1290.
[12]韩 巍.“管理学在中国”——本土化学科构建几个关键问题的探讨[J].管理学报,2009,(6):711-717.
[13]席酉民.从不确定性看管理研究逻辑及和谐管理理论的启示[J].管理学报,2010,(1):1-6.
[14]韵 江.管理学合法性的反思:基于跨学科研究的视角[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3):143-145.
[15]罗 珉.管理学范式理论的发展[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16]杨 栋.科学观之演进与管理学科学属性之争[J].管理世界,2009,(6):124-134.
[17]吕 力.元管理学及其主要研究取向[J].管理观察,2009,(3):18-19.
[18]Haridimos Tsoukas.What is Management?An Outline of a Metatheory[J].British Academy of Management,1984,(5):289-301.
[19]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M].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
[20]唐 莹.元教育学[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21]林默彪.认识论问题域的现代转向[J].哲学研究,2005,(8):69-74.
[22]休 谟.人性论(第1卷) [M].商务印书馆,1981.
[23]马庆国.认知神经科学、神经经济学与神经管理学[J].管理世界,2006,(10):139-149.
[24]穆尼茨·M.K.当代分析哲学[M].吴牟人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25]曹振杰,王学秀.“管理学在中国”研究的理论反思与实践探索——第二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J].管理学报,2010,(2):159-170.
[26]陈晓萍,徐淑英,樊景立,等.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7]李 平.中国管理本土研究:理念定义及范式设计[J].管理学报,2010,(5):633-641.
F270
A
1005-0892(2010)09-0052-07
2010-05-0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09YJC630180)
吕 力,武汉工程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本土管理、管理研究方法论研究。
责任编校:齐 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