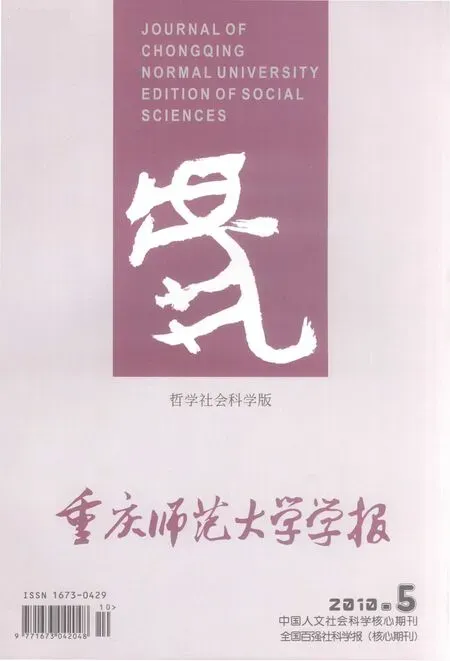幻美旅者的批评之旅
——唐湜 1940年代作家论研究
2010-04-04谢丽
谢 丽
(重庆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重庆 400047)
幻美旅者的批评之旅
——唐湜 1940年代作家论研究
谢 丽
(重庆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重庆 400047)
在 1940年代以政治批评为主体的作家批评氛围里,执着于探寻艺术之美的唐湜,以“人”为主题兼及现实关怀的批评实践和形象诗化的抒情性言说,实践着自己作家批评的幻美追求。显然,正是用这种深情歌吟自己美学追求的批评文字,唐湜在把握时代与艺术的跳动脉搏中,为 1940年代的作家论舞台留下了一位幻美诗人绚烂而璀璨的探索足迹。
唐湜;作家论;幻美之旅
1940年代,当青睐文学社会功能的作家批评感应着时局和政局的需要逐渐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一翼之时,仍有少数的现代作家论写作者立足于文学的立场向时代文学和创作主体提出了要求。作为一种有悖于时代巨潮的作家批评,这一另类的作家论作者本着自己内心的文学要求,在执着的艺术探索与追求中辟出了 1940年代现代作家论的另一重迥异于主流的批评空间。
身为“九叶”诗人的唐湜,便是这一类批评者中较引人注目的佼佼者之一。作为一名自觉的现代主义者,美,是诗人兼评论家的唐湜永恒的追求目标。即使是置身于 20世纪 40年代极其严酷的战争环境里,将艺术视为自己生命血脉的唐湜,仍然艰难而执着地行进在“要找寻自己渴望着的美/要找寻自己渴望的诗之美”[1](200)的幻美旅程中。以诗人的艺术气质撰写文学批评的唐湜,在本时期的现代作家论写作中,是以“人”为主题兼及现实关怀的批评实践和形象诗化的抒情性言说,实践着自己作家批评的幻美追求。毋庸置疑的是,正是凭借这种沉潜于自我幻美之旅的作家批评的艺术再创造,唐湜在把握时代与艺术的跳动脉搏中,用深情歌吟自己幻美追求的批评文字,为 1940年代的现代作家论舞台留下了一位幻美诗人绚烂而璀璨的探索足迹。
一、以“人”为主题的幻美历程
作为一名忠实于艺术的批评者,唐湜意欲像印象主义批评家李健吾那样“要读者跟着他去发现作为人的艺术家、诗人或散文、小说家”[2](212)的。于是,以“人”为主题的作家批评便成为了幻美旅者唐湜本阶段现代作家论写作的一种显著批评特色。
所谓以“人”为主题,即指唐湜在审视研究对象时,始终注目于作家是否写出了“个人的人性光彩”,是否在创作中体现出了“个人特殊的真挚气质”与“个人特殊的风格”[3](190),并以此作为评判作家价值和意义的重要砝码。善于将生活与批评结合起来思索的唐湜曾说:“文学批评如果远离了生活中‘人’的意义,只作些烦琐的解释,当然不能不流于机械论与公式主义。”[4](2)显然,着力考察、发掘研究对象独特的人性光彩、人生姿态与人性的不同表现形式,并以此来透视时代与历史的精神风格,成为了唐湜本时期现代作家论写作的主要聚焦点,而直接归纳概括作家选取了什么题材,意欲表现怎样的中心思想、主题意义等呆板的程式化批评则显然与唐湜无缘。因为在唐湜看来,一个艺术品必须也应该是“一个主观的个性的创造”[5](67)。进而,唐湜认为如果缺乏个人的人性光彩,历史的映现便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在他眼里,最好的作品应该是能反映真的“人”的生活和能让他人感受到血脉搏动的艺术再创造。于是在唐湜的现代作家论文本中,我们常常触及到诸如“人性”、“生命力”、“气质”、“血肉”、“热情”、“自我发展”等与人的精神风格息息相关的词汇。甚而在考察研究对象时,唐湜还用可以通过折射作用产生无穷变化的“三棱镜”作比喻,来透视研究对象独特的人性光彩。他说:“当历史的阳光通过人性的三棱镜而映现、凝定时,艺术才有了真实的跃动的生命。”[3](190)就这样,这位富有非凡想象力的批评者在以个体的“人”为批评主题的考察评析中,踏上了自己找寻美的作家批评旅程。
作为一位“唯美的现代诗人”[6]兼评论家,唐湜在作家批评之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显现出了自己特有的偏爱。那些具有鲜明艺术个性、富有人性光泽与重视以自我的精神风格接受历史的洗礼的现代主义诗人及“新生代”[7](21)作家,显然更易被纳入这位幻美诗人的批评视野之中。于是在唐湜本时期的作家批评里,我们聆听到了批评者在以“人”为主题的幻美旅行中,关于诗人陈敬容、郑敏、杭约赫、穆旦及小说家路翎等人的深情吟唱和智慧品评。正是在以“人”为作家论之批评主题的基础上,唐湜以评论家特有的敏锐洞察力和艺术鉴赏力,慧眼拾掇出了这些在当时处于边缘地位,难以让世人认可并接受的“新生代”写作者的艺术才情、人性光彩和他们各自独特的生命姿态与精神风格。例如在自己“最喜欢的女诗人”[8](79)陈敬容的诗中,唐湜指出了“没有呐喊,却时时生活在她的时代里,敏感地感应着风暴的震撼”的诗人的一种自觉的艺术家和近似历史学者的超越态度;发掘出陈敬容的女性气质与男性风格的和谐交融。认为在光怪陆离的驳杂中创造出“戏剧式的统一”[3](185)的杭约赫,在面向“新人类的早晨”的欢欣中,获得了“生之意识的新生”和“人性的提高与凝结”,并指出展现诗人心灵探索印迹和显现诗人本色的讽刺诗,大体上体现出了“诗人严肃的凝眸与深沉的感情”。[3](187)面对穆旦,唐湜则在深切体验诗人内心痛苦的焦灼与挣扎中,识得了经过苦难洗礼的诗人滞重不畅的文字表达下所蕴藉的“一种原始的健朴的力与坚忍的勃起的生气”;指出表现了一个真挚灵魂的风格的诗人,“在别人懦弱得不敢正视的地方他却有足够的勇敢去突破”[9](103);认为有着“肉搏者的刚勇的生命力”[9](91)、并自然地反映了历史时代之精神风格的穆旦,“以诚挚的自我为基础,写出他的心灵的感情”[9](104)和表现出了“他的全人格,新时代的精神风格、虔诚的智者的风度与深沉的思想者的力量”[9](106)。正是基于对穆旦“个人的人性光彩”与独特艺术个性的真切体认,唐湜断然判定了这位在当时让文坛感到陌生的诗人的伟大来:“穆旦也许……而且似乎也是中国有肉感与思想的感性 (Sensibility)的抒情诗人之一”。[9](91)评论小说家路翎,批评者则在探讨研究对象人性光彩的具体表现中,见出了路翎笔下跃动着生命的呼喊与神采的人性篇章所饱含的一种年青的单纯和浑厚的生命力来,并认为路翎的小说犹如一首首绚丽的人性的诗章一样澄澈透明、发人深省。可见,正是在考察研究对象独特的人性风采与艺术个性中,唐湜本阶段的现代作家论书写下了一位幻美追求者不平凡的作家批评之旅。
在 1940年代特殊的时代语境里,当许多批评者忽视个体的精神风格,放弃真挚的沉思,去寻求作家苍白空虚的外在表现的潜在意蕴时,将艺术视为作家的新生命的创造的唐湜,则在力图超越当时平庸的作家批评风气中,以“人”为主题的作家批评实践,追寻着自己心仪的艺术之美。
二、兼及现实关怀的审美品评
在唐湜作家论幻美的批评旅程中,那个曾经“驾一叶纯白的轻帆 /到蓝色的海上”[10](192)去寻求诗美的年青人,并非仅仅是一位单纯的美的探索者。他以“人”为主题的作家批评在幻美的批评追求中,并不排除对现实的关注。相反,本着批评者自身的社会良知与文学理想,执着于艺术的唐湜亦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严肃的社会现实。因此,唐湜本时期的现代作家论便在兼及现实关怀的审美品评中,丰富与拓展了其作家论幻美追求的批评内涵。
深信“文艺是从现实里涌现出来的”[11](149),并且“必须在那土地里深入地植下自己的根,才能有繁花硕果的希望”[12](1)的唐湜,是一位文艺的反映论者。他在《严肃的星辰们》一文中曾经指出:“这是一个严肃的历史时代,它要求一切属于这时代的严肃的声音。”[3](190)确定了这严肃的历史时代应有的文学姿态后,唐湜认为:“一个诚挚的诗人,……他必会是广大的社会思想史的蛛网里的一点,捕捉着来来往往、熙熙攘攘的气流。”[13](16)就这样,唐湜确立了文学经验植根于生活经验的文艺观,并以此为衡量研究对象的一条重要标准。不过,在认定现实生活是文艺之创作源泉的同时,唐湜又认为生活经验的直接揭露在艺术上实在并没有重大意义,因为没有相当的心理距离,迫人的现实往往不能写成很好的作品。受这样的文艺观影响,关注社会现实的唐湜在审视作家时,除着力探究批评对象是否在创作中展现了自己独具的人性光彩和艺术个性外,还考察研究对象是否在“入神于众多的人生光景”时“任意象自由地遨游”[14]。可见,唐湜本阶段现代作家论对社会现实的关怀其实是始终服从于自己的美学理想的。
具体到他的作家批评实践,其作家论兼及现实关怀的美学品评则往往对能艺术地再现现实生活和表现作家之精神风格的研究对象大加赞赏,而对试图反映现实、却“不能以更凝练更透明的光采来表现”“激荡的人生、激荡的世界”[5](77)的作家则提出善意的批评。例如面对忠诚于自己的时代和艺术良心,并能在诗作里将自己受难的精神历程,与中国新时代受难的历史过程互为佐证的穆旦,唐湜表示了由衷的激赏,他认为作为一名“搏求者”的诗人“是中国能给万物以生命的同化作用 (Identification)的抒情诗人之一”。[9](91)对于“一语天然万古新”的游吟诗人——唐祈,唐湜则注意到了诗人在严峻的历史时代,其创作由清新透明的牧歌世界向严肃时代的苦难悲歌的转变。即使是面对唐祈“在不当的时候作了虚伪的提高”,失去了“牧歌诗人的本色”的部分突进现实的创作,唐湜仍认为这类诗作在大体上“是一张和谐的画幅,时时有美学与社会学上的凸起构成一片连峦,一片深谷”[3](169)。评论莫洛,唐湜则将其称之为“自觉的斗士”[3](171)。批评者既为莫洛关于运河战斗旅程的情感抒写所体现出的“一份高贵的浪漫蒂克的风度”[3](172)而欣喜,也为诗人走进乡间、走进荒村、走进民众的生命呼号而动容。最后,批评者指出“诗人的心因为诚挚就与一切景象拥抱了,他用惠特曼那样的母性的柔和光辉来拥抱整个世界,世界就在他的光辉里变成了那么可爱的绕指柔,那么满盈的爱的感应圈。”[3](177)
同样,从这种兼及现实关怀的审美品评出发,唐湜识觉出了某些作家的不足。如评论郑敏,尽管唐湜为女诗人浑厚、丰富的艺术才情而叹服不已,但批评者仍然为诗人笔下闪烁着智慧光芒的诗作,“是过于绚烂、过于成熟的现代欧洲人思想的移植”,是“一种偶然的奇迹,一颗奇异的种子,却不是这时代的历史的声音”[11](156)表示了遗憾。评论杭约赫、陈敬容等诗人时,唐湜则对诗人部分逼视现实,却又流于浮泛的作品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杭约赫部分描画现实生活状貌的创作由于缺乏向“人类的精神生活的深切的楔入”,缺乏“必然的社会史的剖析与跟它相适应的人类精神生活的蜕变”[3](189)而存在艺术上不够成熟的弊病。即使是面对自己心仪的诗人陈敬容,唐湜在竭力赞赏之余,仍指出接受了进步意识感染的诗人在某些“向前跃进”的诗作中,由于没有真正进入到汹涌的时代的腹心,没有真实地与严酷的时代拥抱,“所以仅仅只能有稍觉虚浮的感染与逼视”,而不能有“突击的深入”和对现实作出历史的透视。[3](183)显然,作为幻美的作家批评的一内在组成部分,唐湜兼及现实关怀的审美品评常常在时时腾跃的现实浪花中,显现出其独具的批评魅力。
正是以兼及现实关怀的审美品评,唐湜本时期的现代作家论写下了一名执着的艺术人对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的理解与思索。虽然,其对现实的审视量度是被紧紧包裹于批评者美学的批评理想之内和作为其幻美的批评追求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但唐湜向社会现实投去的关注目光,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其作家批评的幻美内蕴。
三、诗意盎然的抒情评论
唐湜 1940年代的现代作家论引人注目之处,还在于它独特的评论风格。他曾经说:“我尝试着用一种诗意的抒情散文来写评论,把它们写成抒情的小品或细致的心理分析。”[10](193)可见,并不因注目世事而减少一点对美的追求的唐湜,是执意用一种诗意的方式和抒情散文的风格来构筑他的批评世界的。其实,早在写作第一篇评论文章——《阿左林的书》时,唐湜便产生了“用散文小品代替大块的论文”的念头,他说:“向人家说一篇长篇大论,还不如轻轻的提示一两句,给人一个亲切完整的印象”。[4](1)因为在唐湜看来,批评应该“是一种能表现青春的生命力或成熟的对生活的沉思的艺术”[4](1-2)。于是,以意趣盎然的诗意化方式解读、评论作家,成为了唐湜本阶段现代作家论的另一显著特色。其作家论诗意盎然的抒情评论风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形象生动的比喻手法的大量运用,使得唐湜作家论在充满诗意的抒情性评论中流光四溢。作为一位将批评当做一种情感的旅行和心灵的探险的评论家,唐湜喜好用感性灵动的比喻,来准确生动地表达自己对研究对象的艺术体悟与审美感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当注目到对历史生活有一种严肃的气度与反应,对新人类的理想生活与艺术的完成有着坚定的追求的唐祈、莫洛、陈敬容、杭约赫等诗人时,唐湜惊喜地感叹:“呵,又有许多严肃的星辰们出现在诗的天宇上了,又有许多光辉的彗星拖着它们的金车在巡礼了。呵,我们得注视它们,看它们运行的步子,看它们虹彩般的光弧怎样缀着诗的宝石闪光。”[3](164)满载诗情的比喻不仅以直觉的方式,形象地阐发了批评者对研究对象的审美感受,而且在引发读者的形象感知中,赋予了批评文本较大的艺术张力。解读路翎时,唐湜将其小说比作会发出梦幻般的瑰丽色彩的阳光,他说,路翎的作品“正是一片阳光,有变幻莫测的光采与灼人的热。而且还是早晨的阳光,会给人奇异的、疏阔的感觉。我们读他的《求爱》,仿佛正透过一片三棱镜来看望阳光下的世界,多么亲切可爱,而又多么奇异、多彩”[5](70)。鲜活、明朗的比喻意象和极具灵性的阅读体悟,唤起的是接受主体独特的艺术感知和心灵感受。评论莫洛时,面对诗人吟唱的关于新人类生活的诗篇,唐湜这样阐发自己的艺术感悟,他说:“读这些清纯的诗章就像在湖心里撑船,轻轻一点篙子就是一个灵魂的震撼,一片耀目的光会悄悄地流入你的心里。”[3](175-176)抛却了一般批评者繁复的演绎、推理与归纳,仅以一种形象化的比喻便展现出了一个新知识分子光耀的心灵世界。在唐湜本时期的作家论文本中,随处可以见到这种闪烁着批评者自由性灵和直觉感悟的生动形象的比喻。而恰恰是这种率性自然的大量形象化比喻的运用,使得唐湜作家论插上了诗意幻美的翅膀,在批评的王国里自由飞翔。
其次,抒情诗化的语言表达,使得唐湜作家论文本诗意盎然。作为一位习惯于用写诗和散文的抒情方式,去拾取研究对象高贵的思想的贝叶的幻美旅者,唐湜断然拒绝那种掉书袋或“俨乎其然的头巾气”[2](212)式的批评,他主张用一种抒情诗化的语言来品评言说批评对象。因此,唐湜本阶段的现代作家论便往往在以诗意化的抒情笔触评析研究对象时,深情款款地道出了批评者艺术探索的心灵感悟。为准确地理解体会唐湜现代作家论的这一批评特征,不妨引述他评论诗人郑敏的一段文字:
她仿佛是朵开放在暴风雨前历史性的宁静里的时间之花,时时在微笑里倾听那在她心头流过的思想的音乐,时时任自己的生命化入一幅画面,一个雕像,或一个意象,让思想之流里涌现出一个个图案,一种默思的象征,一种观念的辩证法,丰富、跳荡,却又显现了一种玄秘的凝静。如果我们把它颠倒过来,放在一个理性论的基础上,在它的画面上给加上一个合适的,不至窒息了它的盎然生机的镜框,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了一个梵乐希(Paul Valery)那样用清明的数学家的理智来写诗的诗人。[11](143)
在这里,流畅隽永、空灵飘逸的批评话语,使得唐湜作家论在诗意盎然的抒情性氛围里,散发出诗意的典雅和批评者睿智的哲思。听任性灵自由飞扬的唐湜,便是用这样一种充满诗意与抒情化的、具有鲜明感性意味的散文化文笔,在接近艺术真谛的感性话语表达中,完成了对研究对象的诗性解读。
综上而论,注重探讨“个人的人性光彩”、“人性”的不同表现形式、并兼及现实关怀的审美品味,和以富有诗意的抒情风格撰写作家批评,并将抒情诗化的感性韵味与细致慎密的理性分析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共同构筑起了唐湜 1940年代现代作家论的批评世界。显而易见,唐湜的这种敏感于研究对象之创造性特质的抒情评论,颇具 1930年代“京派”作家批评之遗风,它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京派”作家批评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变迁与发展。尽管在当时以政治批评为主体的作家批评氛围里,它的存在显得那么不合时宜,但执着于探寻艺术之美的批评者,却以批评旅程中艰辛跋涉的寻美吟唱,为当时特定历史文化语境里凸显政治化发展新取向的、整饬严肃的作家论写作和 1940年代的现代作家论舞台增添了一抹异彩。
[1] 唐湜.九叶诗人:“中国新诗”的中兴[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2] 唐湜.含咀英华——谈《李健吾文学评论选》·新意度集[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
[3] 唐湜.严肃的星辰们·新意度集[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
[4] 唐湜.意度集前记·新意度集[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
[5] 唐湜.路翎与他的《求爱》·新意度集[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
[6] 谢冕.一位唯美的现代诗人——唐湜先生的诗和诗论[J].诗探索,2004年春夏卷.
[7] 唐湜.诗的新生代·新意度集[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
[8] 唐湜.陈敬容的《星雨集》·新意度集[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
[9] 唐湜.搏求者穆旦·新意度集[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
[10] 唐湜.我的诗艺探索·新意度集[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
[11] 唐湜.郑敏静夜里的祈祷·新意度集[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
[12] 唐湜.论风格·新意度集[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
[13] 唐湜.论意象的凝定·新意度集[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
[14] 唐湜.辛笛的《手掌集》[J].诗创造,(9),1948年 3月.
I206.6
A
1673-0429(2010)05-0021-05
2010—08—30
谢丽(1973—),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重庆师范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中国现代作家论发展史论”(10XWB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