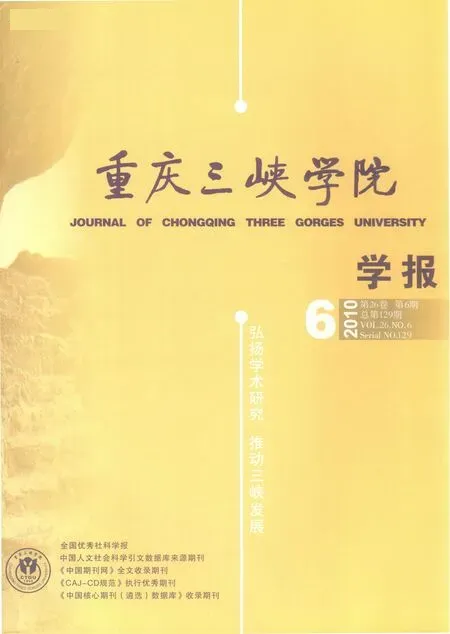视觉艺术视野中的三峡工程
2010-04-04王杰泓
王杰泓
(武汉大学艺术学系,湖北武汉 430072)
视觉艺术视野中的三峡工程
王杰泓
(武汉大学艺术学系,湖北武汉 430072)
三峡工程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作为人类技术与艺术高度融合的“中国纪念碑”,它以自身“大”而“崇高”的形体特征表征着国人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豪迈气概,同时也体现出华夏民族勇于直面伟大工程负面效应的忧患意识和民族自信。聚焦于上述看似对立实则辩证统一的正、负两方面,本文主要从国画、油画、摄影等三种艺术门类具体呈现“视觉三峡”的存在状貌与人文内涵。
三峡工程;水墨峡江;东方之子;新三峡
三峡工程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作为人类技术与艺术高度融合的“中国纪念碑”,它不仅体现为形体上的“大”和“崇高”,而且更表征着华夏民族在新的历史际遇下的一种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豪迈气概。其向世人所呈现的伟大工程给国人带来的心灵期盼、渴望和梦想,三峡工程建设者们改天换地的恢宏气魄以及创造了四百多个世界第一的胆略与智慧,中国人藉此表现出的生活态度、情感与信仰等等,无不令我们振奋。不仅如此,透过三峡工程负面效应所带来的忧患意识的增长,我们还能读出一种与豪迈气概互为正反面的民族自信。这种民族自信也就是最朴质的人文关怀。
事实上,人类的科学技术越发达,就越需要人文关怀。当科学技术被日常生活化以后,我们对三峡工程的关注更多地或许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人文问题,即全体中国人包括三峡人的情感问题、精神问题、心灵问题。因此,本文着意以“视觉三峡”为切入点,分别从国画、油画、摄影等三种视觉艺术门类以小见大地来正面回答这些问题。
一、“水墨峡江”:山水画廊及其图式化生存
地球距今200多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鬼斧神工地为后来的人类擘划出一幅“雄”、“奇”、“壮”、“险”的三峡画卷。这一造化的馈赠西起山城重庆奉节县的白帝城,东至水电之都宜昌的南津关,全长205公里。一带长江水蜿蜒穿行其间,奇艳之瞿塘峡、峥嵘之巫峡、秀险之西陵峡本身就构成了一条大美氤氲、意境幽绵的“山水画廊”。于是乎,三峡也就成了今天三峡库区文学艺术的文化之根,“蹩脚”的艺术家们纷纷磨墨展纸,试图以手指间的丹青画笔创造出一个尽可能逼真的、图式化的“第二自然”。
据笔者之统计,三峡工程开工前后,当代国画界较早表现大美峡江且成规模气候的,当数以岑学恭、黄纯尧为代表的“三峡画派”。画史上,以攒攫三峡为题材的作品应该说屡见不鲜;建国后,李可染、傅抱石、陆俨少、吴作人等名家亦相继创作了大量品肖神似、意境悠远的三峡山水画。在此基础上,作为徐悲鸿、黄君璧等大师的高足和“三峡画派”的鼻祖,岑学恭先生为了更好地表现三峡的雄奇、险峻,于长期画三峡中对“皴”这一传统山水画技法作了创造性地运用与发挥。在《望岳》、《三峡情》、《三峡放筏》、《三峡烟雨图》、《巫峡十二峰》、《巫山巫峡气萧森》以及曾获1988年汉城奥运会美展金奖的《三峡》等作品中,其“一线、二斧、三渲染”之笔墨运用的“岑三峡”特点尤为突出。“一线”指线条,即用“铁线”展示山的刚健与力度;“二斧”指斧劈皴,即用超大斧劈皴表现山之磅礴与气势;“渲染”指墨色,即墨色主淡,先淡后浓以显山之层次。其中,与点、染、擦等国画技法妙合无痕的“大斧劈点韵皴”可谓独一无二。不仅如此,在山同水的构图配置上,作品惯于采用中国传统的“中堂”和“条幅”形式,“高山低水”,将峡江滩流压至最低位置,而把层层山峦画到纸的最顶点,甚至直逼纸外,从而给人以雄浑苍郁、远及天穹之感。以水墨山水为代表的中国画素来讲究“气韵生动”,追求一种“状难写之景如在眼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意境。岑老的水墨山水往往信笔挥洒,于经意不经意之间传达出满纸真诚,同时又自然不自然地营造出一种诗一般的画境,无疑,其三峡画系列实可谓标举着中国画审美诉求的至上之“逸”品。
与“岑三峡”的声名不相上下,黄纯尧同样有“黄三峡”的美誉。自1946年首次路过三峡即为其雄秀同彰所折服开始,一生中,黄老曾先后23次过三峡,创作了以三峡为主题的画作2 500幅。概括起来,这些作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据写生、速写进而加工处理的“眼前的三峡”,如《巫峡》、《风箱峡》、《瞿塘放舟》、《夔门天下雄》等;一类是根据主题、意境的需要从而重新组合过的“胸中的三峡”,如《峡江图》、《峡江欢歌》、《长江三峡》、《长江汹涌破夔门》等。画法上也呈现出鲜明特点:如“一笔到底”法,即先立意、构图,定其大势,继而大笔散毫、落墨取势,顺次整形、点树,最后染色、染墨,一气呵成,正所谓“一笔到底三遍点,两次整形二遍染”(简称1322画法);再如“三峡皴”法,即适应于三峡山石结构纹理的诸皴法,有横纹皴、直纹皴、破网皴、朽木皴、折绉皴、粉壁墙皴、夹心饼干皴等等;又如“急流七字诀”,即画三峡浪流的七字心得,有干(干笔)、淡(淡墨)、岔(笔尖开岔)、虚(用笔宜虚不宜实)、变(水浪的变化)、提(近处略提以使水面有远近透视感)和染(沿主要波纹用色并用淡墨染之以增强立体感)。以上是就具体作品及其特定技法言,倘使再作进一步的精神升华,不难发现,这2 500件作品所凝聚的,可以说无外于黄老对三峡的爱恋和对三峡巨变的礼赞。“黄三峡,就是我自己的三峡。”[1]在黄老看来,所有这些画作记录了他的人生态度,其中包括对三峡老朋友一般的感情,“闭着眼睛都想得起它的容颜”,同时也包括葛洲坝、三峡大坝建成后内心的那份自豪和喜悦,“水平好行船”了。笔墨当随时代,黄老毕生的创作宗旨就是一定要为时代作证、替山川代言。“绘画是时代的镜子,要反映时代,鼓舞斗志,我认为这是爱国主义的核心,我作画之魂。”[2]因此,与大多数只愿把玩花鸟、寄情仿古山水甚或骨子里抵制三峡工程的国画家不同,老人家每次去三峡,其必写生、速写,必画三峡之巨变。所以,当今天观《春到小三峡》、《快船逐云飞》、《一路听帆歌》以及曾作为我国驻外使馆悬挂的《银线横空谱新歌》等作品时,我们不只是看到了祖国河山的大美英姿,而且还能聆听到一曲曲生产建设的赞歌,体味到时代进步给国人心灵带来的无比的自信感与自豪感。
除岑学恭、黄纯尧两位泰斗级的老先生外,“三峡画派“还聚集了像罗其鑫、叶瑞琨、姚叶红、岑小麟、林茂森、田旭中、李长江等一批优秀的中青年艺术家。此外,巨幅水墨画《三峡新貌》的作者胡怀玉、巨幅通景山水画《三峡史诗》主创及《高峡平湖图卷》的作者施江城、《西部变迁图》之大、小三峡卷的作者王陇花、水墨写实画家黄鹤、写意画家龙绪明等等,都是近些年来在描绘大美峡江、表现大美大坝方面的佼佼者。对于年轻的艺术家们来说,他们有赓续传统的义务,更有革故鼎新的使命。当下,随着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的开工与即将建成,山奇水秀的长江三峡正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伟业相唱和,共同奏响了一部雄浑浩荡的时代大乐章。可以认为,自旧三峡而新三峡、从大美峡江到大美大坝,三峡山水经历了一个中华儿女与大自然亲密对话的和谐变奏。在此情境下,三峡工程给当代艺术家也留下了两道考题:一道是如何留住国人对旧三峡“恋根”般的记忆,从而尽可能地将改变对人类情感的伤害降低到最低限度;另一道则是如何践行“诗性”的方式来表现新三峡,从而给传统国画艺术注入与时俱进的血液与活力。针对这两个问题,上述中青年艺术家分别作出了如斯之回答。首先是记载历史、抢画三峡。巴蜀诗书画研究院理事、“三峡画派”成员之一的画家李晖即认为,赶在大坝蓄水前抢画三峡尤其是将画笔对准那些尚未或部分淹没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是每个艺术工作者责无旁贷的职责。应该说,旧三峡那需要用画笔留住的风光实在太多了,我们记录她就等于记录一段不可逆的人类历史。其次,面对新三峡、新问题,多数艺术家主张绘画要有新视界、新方法。譬如又一“三峡画派”成员、中年画家林茂森就指出,多年来,虽然描绘三峡风光的作品数量不少,但有的画家甚至都没有到过三峡,没有现场感,作画的灵感仅源于图片资料或一己之想象;而且绘画技法上也较为单一,没有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不能不令人遗憾。而对三峡感情笃深的画家万体俊也认为,现在的很多三峡画作品都只停留于照搬风景的基础上,缺乏深层次的写意性描画,这无疑是三峡主题画的又一缺失。有鉴于此,自觉的艺术家们敏于时变,他们一方面秉承、发扬“长江万里图”、“三峡风光图”式长卷国画山水的主题传统,另一方面也格外注重内容的更新和技法的创新,“大坝入画”、“新景入画”、“写意融合写实”、“写实导向写意”成为了他们在指点江山的创作实践中竞相试验的关键词。
对于绘画艺术而言,技术是第一位的。要真正做到最佳地去描画山水、表现时代同时又风格多元、百花齐放,这需要艺术家务实的态度和不懈的探索,就像三峡工程的建设者们那样。不过可喜的是,众多艺术家在这方面已经卓有成绩。例如吴一峰的《夔门风雨》、谭学楷的《瞿塘夕照》等作品,其在传统写意中融入写实因子,并且在技术手法上吸取了油画、版画等西洋艺术的思想精华,譬如焦点透视、没骨套色等,可谓使国画三峡山水达到了又一新的境界。此外,迄今已不难发现,整个三峡库区也进入到了国画山水的艺术视野,其中不仅出现了像《乌江晨雾》、《大宁河剪刀峡之晨》这样的泼墨山水画,而且更涌现了如《小三峡》、《鹅岭春晖》等金碧重彩的山水之作,从而将三峡库区“山水画廊”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声部地昭示于世人眼前,共同上演着一支美景、美坝与美人的协奏曲。
二、“东方之子”:纤夫、建设者与三峡新移民的群像
“一切景语皆情语”,对于地球而言,再美的风景也无不是因为有人的存在方才显现出价值:长江如斯,三峡如斯,长江三峡航道上一件件大美的人化自然事物亦如斯。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视界,同时结合画种自身长于写实及人物造型的特点,当代油画界表现三峡、三峡工程又有另外一番风味。
河流文化给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带来的福祉是难以言表的;另一方面,大江大河给人类带来灾难同样也令我们刻骨铭心,譬如洪涝频发、交通阻隔等。对此,生活其间的峡江人体会尤为深切。出于生计的考虑,他们中一辈又一辈的人光着膀子,卖着力气,干起了纤夫这一铤而走险的营生,许多人因此而葬身鱼腹。随着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带来的三峡水位的上升,纤夫连同他们的川江号子即将成为千古绝唱。为了诠释从远古走来的母亲河,尤其是希冀铭刻艰辛而坚韧的三峡纤夫所代表的长江人文精神、中国精神,青年油画家陈可之延续了吴作人、余本等前辈艺术家衷情纤夫的做法,潜心创作出了长6米、高近3米的巨幅油画《长江魂——三峡纤夫》。与以往的纤夫画包括史上著名的俄国画家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有所不同,画中这群裸露的汉子并不显得悲苦,劳累在他们脸上刻下的相反是一道道阳刚、血性乃至悲壮的印痕。一根主纤绳连起十余个并不健硕的汉子,拼尽全力,负重而来,前驱的身体正拉动着舟船缓缓地绞滩上行,隐约的舟船宛若一只昭示着希望在前的命运之指,这使被动的生存瞬间转化为人性的不可战胜。从艺术性方面讲,《三峡纤夫》的特点亦十分鲜明。如其在处理人物形象及三峡礁石上特别突出肌理和质感,笔触刚劲,肌理分明,油画质感强烈,展现出一种立体凸现的浮雕效果。2000年,该作获得了文化部全国第八届“群星奖”美术金奖,同时还被首都观众票选为“我最喜爱的作品”第一名。“三峡纤夫”所代表的东方平民的奋斗品格,勤劳勇敢、积极向上、坚贞不屈、百折不挠,无论在中国还是全世界,都足以激起任何人心理与情感上的共鸣,因为它不仅是中华魂,更是一种人类共通的文化精神。
如果说纤夫们与自然空间阻隔的抗争主要体现为一种被动性的悲壮,那么,三峡工程工地上的建设者则更多地表现出改造自然、创造新生活的豪迈。2003年至今,宜昌市美协主席孙才清每周都要去三峡工地观察体验,每次又都会带回强烈的创作冲动,催促他去驾驭线条和色彩,连同自己的理解与感动,交相融汇,从而把工人们鲜活的形象永远地定格下来。因此,他在这段有着纪念意义的时间里先后完成了诸如《抬石头的人》、《风钻手》、《三峡大坝浇筑工》等“建设者”系列油画20余幅。作品中的大坝农民工无声地站在我们周围:有专注的浇筑工、从容的架子工、激情的管钳工、自信地微笑着的钢筋工,当然,其中还包括一群衣不合体、什么都干却也气定神凝的女勤杂工……一幅幅画面,讲述着建设者们一个个再平凡、普通不过的点滴故事。不仅如此,画家将视角对准农民工建设者又格外多了一层涵义:不是柯勒惠支笔下的矿工或者库尔贝笔下的修路工,没有城里人的光洁、体面,而且也不像其他建设者那样有企事业单位挂靠的的福利与身份,作为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干着别人不愿干的脏活、重活却未必能拿到与付出成正比的薪酬。然而即便是这样,他们照样活得充实,自尊与自强、执着与沉稳、乐观而弘毅、简单而坦然,如此一种祖祖辈辈即延续下来的原生态生活态度。在此意义上,“建设者”系列油画与《三峡纤夫》的主旨可谓殊途同归,那就是它们聊藉不同的底层劳动者之名,讴歌的却是同一种“老黄牛”抑或“中华魂”的精神。
在用油画观照三峡工程并向所刻画的底层人群投注无言的人文关怀的艺术家中,有一位显得较为特别,他就是《三峡大移民》和《三峡新移民》的作者、著名“新生代”画家刘小东。同样是源于民工、三峡建设与社会责任感的触动而拿起画笔,刘小东的三峡画作品却在“讴歌”的主题外多了一种“反思”的秉性,即在弘扬主旋律的基调上抛却思想的单向度与宏大叙事,执著于平凡细节的具象性写实始终透露着他对现实的忧患意识和对人性的深切关注。以《三峡新移民》为例,这是艺术家2004年在三峡写生时创作的一件大幅油画,长10米、高3米,整体呈倒三角形构图。画面以建设中的三峡大坝为背景,在灰白而略显混浊的江水下前方,未完工的坝体如灰色的庞然大物耸立其上,即将消失的村庄和刚刚爆破的废墟分立于V字形的左右侧,废墟边沿则站立着十余个面临搬迁命运的表情各异的移民:三个孩子手拿玩具枪嬉戏着,天真而顽皮;两名中年男子背身凝视漫起的江水,无言而呆滞;在他们身后,大抵是因为空中的一只野鸭遭射杀,另两名男子则正侧目盯着画外的猎手,敢怒而不敢言;后方不远处,两男两女四个后现代年轻人不约而同看起了热闹,表情亢奋而无聊。艺术语言上,全作延续了画家自“89大展”以来的“具体现实主义”风格,构图简洁,人物细部刻画冷峻、逼真。更为摄人心魄的是,依托这样一种看似“没有立场的立场”的手工纪实,《新移民》在思想内涵上也同时呈现出“美”、“刺”交织的矛盾与张力:一方面,无可否认,大手笔再现现代化进程中一段既宏伟又悲壮的历史,作品至少在客观上表现了“新中国的精神风貌”;另一方面,透过画中的人与物被剥离、被抽空后的受迫性呈现,作品事实上更表现出一种社会转型期“充满刺激和创痛的双重性”,尤其是为追求物质改善所付出的自毁家园的精神代价。正是在此意义上,刘小东曾不无伤感地表示,三峡大坝是国内最典型的毫无人情味的大型工程。然而,如果我们就此以为《新移民》表达的是一种单纯的批判,就像美国评论家、策展人杰夫•凯利所说,“他的作品正好和中国宣传式绘画唱了反调”,那么这无疑是简单化曲解了作者的本意。世界每天都有令人不安的事情发生,但“我感兴趣的是人类的情感”,刘小东说,“我想听到人类灵魂深处的东西”。“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对抗不只发生在中国,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有。我的作品是在表现这种冲突及伴随冲突的紧张气氛。”[3]《新移民》揭示出了发展中的中国社会某种容易被忽略的复杂性,譬如三峡工程,其防洪、发电、航运等物质经济效益举世可见,国人更是为之振奋,然而金币的另一面却未必还是“造福于民”——至少,对于上游21个市县、140多个乡镇共约130万的每一位移民来说,人生无常、背井离乡、悲哀于不能控制自己的生活恐怕才是他们的第一感受。艺术因人的情感和精神而起,窃以为,以《新移民》为代表的“呈现国家伤口”之作不但不是批判的、负面性的,相反是进步的、建设性的,因为,正视问题也是进步的一种表现。
除了陈可之、孙才清和刘小东,当代油画界在表现三峡、三峡工程方面还有很多优秀的艺术家,例如周才生、亚力、刘路喜、李文书、崔开玺、赵洪贤等。概括所有艺术家创作上的共性,不难发现,他们都试图在个性与主旋律之间谋求一种平衡,而联结这两极的中介点,就是他们同纤夫、建设者、百万大移民一样浓不可化、挥抹不去的“三峡情结”。陈可之曾作过一幅象征“少年中国”的画,叫《东方之子》,它似乎同样可以用来给这群坚韧亦不乏伤感的人们命名。
三、“新三峡”:定格历史的中国纪念碑
如同国画和油画,摄影也是近些年摄影家们喜欢采用的一种表现三峡、三峡工程的视觉艺术方式。早在一百年前摄影刚诞生之初,英国自然主义摄影家爱默生就曾说过,摄影具有一种可怕的真实性。这是因为,基于“记录”的最基本目的,摄影离现实太近了。虽然其后来不断生发出绘画主义、印象主义、写实主义等艺术化了的流派或门类,但“在纪实中直面人生”始终是它最基础的含义与使命。
三峡工程建成后,上游地区一个最现实的物质变化就是既有之“物”的改观乃至消失,其中包括原三峡风景、三峡民居以及存在了数千年的历史文物与人文景观等等。因此,摄影家的第一要务就是要记录过去、见证历史。在这方面,吴大益、佘代科、肖萱安、韩学章、魏启扬、陆纲、甘焯威、郑树德、郑云峰、宋华久等众多艺术家都有不俗的作品问世,聚焦的对象涉及像夔门、巫峡、瞿塘峡、白帝城、石宝寨、屈原祠、大昌古镇、土家吊脚楼等几乎所有可以想到的纪念物。其中尤值一提的是郑云峰和宋华久。郑云峰家在江苏徐州,本人是徐州摄影家协会主席。出于对三峡的挚爱,近十年来,他自费购置铁船沿三峡考察,并且还曾随凤凰卫视《永远的三峡》摄制组跟踪拍摄三峡工程,足迹遍布这里的山山水水。如今,记录三峡成了他最基本的生活方式,用他自己的话说,“三峡已然是我的生命了”。云雾、烟雨、山风、水色、草木、笑脸,尤其是与人情有关的纤痕、纤夫石、古盐道、三峡古栈道等等,所有这些无不为其镜头所捕捉。迄今为止,他所积累的关于三峡、三峡建设的图片资料已逾数十万张,同行们也因此誉他为“三峡摄影第一人”。宋华久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自1992年以来,他曾走遍了全库区的31个城镇,用去底片15万张,最后推出了摄影集《淹没线下的城镇》、记录2 000多位移民的《三峡百姓》以及获得中国图书奖的《三峡民居》等一系列摄影专辑,真实地记录了三峡库区的变迁。据他估算,现在一年四季,每天跑三峡库区和工地的摄影家不下200位。透过这一件件定格在“富于包孕的一刻”的无言的艺术作品,我们能强烈感受到历史所讲述的一个又一个感人肺腑的真情故事。例如《三峡民居》的一幅,作者采用并置构图,古老的民居和现代的大坝相映成趣,仿佛在言说着一种祥和,又似乎在诉说着一种眷恋与无奈。
在审美或形上的层面上,“物”无不属于人化的客体,其存在为意志之表象,而其消失则往往表征着“人”之精神、情感的失落。所以,记录三峡风物的变迁毋宁说是讲述三峡人一段情感碰撞、迁徙与升华的心路历程。于是乎,又有一批摄影家在聚焦现实、定格时代的过程中,相对侧重地去表现拆迁、废墟以及处于拆与建、废与立往复更迭中的三峡人。例如李风的《峡江拆迁》,纯黑的大背景中镂空出三个并置的白色小窗口,两个男人分立于左、中的两扇在挥锤拆墙,右边的一扇中,一个孩子的身影则正背对画面凝视着远山与眼前的一片废墟。可以想象,男孩或许正在念叨着“中国-China”(拆啦),废墟就像一张张开的大嘴多少令他有点难以消化;对于父辈和他来说,这里已然成了一座改变与留恋交织的“回忆之城”——它的拆解意味着家园不再,意味着记忆转型,同时也意味着自己从此可能要怀上一生都难以抑制的“怀乡病”……陈池春、陈文是父子,移民与废墟同样是他们接力式地要亲近的对象。陈池春的《劳动者•三峡乡民》组图,深入民生,生动再现了码头挑担工、卖蓑衣的男子、峡中担柴的农家子弟等。儿子陈文似乎显得更有想法,不仅是代表作《我的三峡记忆》、《三峡•废墟》、《三峡古镇最后的迁徙》等先后获得国内外各种大奖,而且还成立有“新三峡在线——水岸工作室”,创建了长江三峡原创摄影图片全集。陈文的镜头比较特别,他喜欢把焦点锁定在移民迁徙后留下的遗痕的左右前后,扫描曾与这些遗痕相伴的三峡人的形色生活,进而探讨两者间微妙甚至有趣的关系。这点上,其与大多数呈现三峡美丽风物的摄影者不一样,倒是与衷情展示“水位线”及即将被淹没地区民情的另两位年轻摄影家黎明和宋戈有较多的共同点。2007年春,三位摄影家为此还联名举办过一次“那山、那水、那人”的摄影展。也许此次以“三峡”为核心的联展同样存在观念上的微妙差异,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他们毫不犹豫地将镜头对准了峡江山水间的人(人情、民生、移民),而不是物。这样一种视角看似单纯,其实背后隐藏的价值立场却是弥足珍贵,譬如它至少提醒决策者以及那些容易把问题简单化的人们,“移民是人,不是物”。
当然,假如仅仅从审美的维度审视三峡移民乃至中国人的“恋土情结”,其固然令人感喟而且也能激起艺术表现上的强烈的冲击力。但是,我们且不说三峡地区原本就是“移民走廊”,也可以忽略生活贫瘠历来都是该地区人们的“生存之痛”的基本常识,单以现代意识和人类发展进步的内在必然性来看,对家园故土的过分迷恋、对既有生存状态的执著坚守以及对族群迁移的本能抵制,这种情感与行为本身就妨碍了文化可能性的探索,而在现实负面性方面也影响了人们前行的路。基于这样一种“向前看”的认识前提,不少年轻的摄影师饱满激情地将镜头对准热火朝天建设中的三峡工程。例如湖北省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欧阳卫红,其于2008年12月19日在由湖北省艺术馆、湖北省摄影家协会和三峡总公司联合举办的《圆梦三峡——欧阳卫红摄影展》上,浓墨重彩地推出了诸如《编织》、《崛起》、《似舰起航》、《三峡交响》等一系列再现三峡大坝建设的壮观之作,从又一侧面向世人展示了勤劳的中国人所造就的三峡工程这一伟大成果。作为业余摄影师的三峡总公司员工马宁,其《三峡工地交响曲》还曾获得全国第20届摄影展金奖和“中国摄影金像奖提名奖”。
“让我欢喜让我忧”的三峡工程,有人因之扼腕,认为它整个就把自然给毁了,旧三峡的气势与神韵不再,新三峡的诗意与浪漫无存;也有人为之振臂,觉得这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又一创举,旧三峡的“雄奇险峻宜观赏”固然是一种美,新三峡的“高峡平湖好行船”不也是一种美吗?对于这种毁誉之争,我们可以结合以上国画、油画、摄影等“三重视域”的探讨基础,来作一个总结性的“历史和合”的观照。马克思曾说:“自然是人无机的身体。”又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4]窃以为,将这两个命题联系起来理解才是明确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关键。换句话说,两个命题的合题当是“人与自然是对立中的和谐”。仍以三峡工程为例,如果我们一方面悬置全部与三峡有关,经由古今的文人墨客虚构与传递的神话似的文化想象,另一方面摒弃所有与自然抗争所形成,经由我们的祖先发起并沿袭下来的人类中心主义幻觉,权以一颗理性、客观的平常心,我们就会发现三峡自古就不是“纯自然”的存在,而是一种“人化自然”,一个处于不断变化中的“流动风景”;而三峡地区则更不是“纯人力”的结果,人的“本质力量”还不至如此之强大,今天的三峡地区当是人与自然冲突、对话、妥协的产物,是文化之美与自然之美碰撞、交流、和合的“历史结晶”。它不仅是科技的大坝,而且是人文的大坝;不仅是物质的大坝,而且是精神的大坝,是灵魂的大坝,是信仰的大坝。[6]美国生态哲学家罗尔斯顿就曾指出:“文化是为反抗自然而被创造出来的;文化和自然有冲突的一面。每一个有机体都不得不反抗其环境,而文化又强化了这种对抗。生活于文化中的人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我们重新改变了地球,使之变成城市。但这个过程包含着某种辩证的真理:正题是自然,反题是文化,合题是生存于自然中的文化;这两者构成了一个家园,一个住所。从斗争走向适应——这就是当生物学从早期达尔文主义,发展为成熟的进化生态科学时所实现的重要的范式转型。一种成熟的伦理学也要实现类似的范式转型。一种冲突的伦理——人作为掠夺自然资源的征服者——必须转变成一种互补的伦理:人应该以满意和感激的心情栖息于大自然中。”[5]有了这样一种“和谐”的历史视野,回头再来看三峡工程,我们不难得出一个最基本的结论,那就是作为“后三峡时代”的新景观,同时作为彰显华夏民族崇高人格的“中国纪念碑”,三峡工程是中国人与大自然又一次“会心”的握手,是人与自然关系史上一个富于“纪元”意义的崭新的开端。
[1]刘蓉.黄纯尧的“三峡”[N].四川日报,2003-06-06(12).
[2]黄纯尧.黄纯尧美术论文集[C].四川美术出版社,2000:5.
[3]苏珊·莫尼克.“大坝筑起的岁月”——评刘小东“三峡新移民”展[EB/OL].http://www.artxun.com/class_artxun_com/arti cle/02fc/fce9a86d6b9fd9261f4aa8fc1364096c.shtml.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6]王文斌.影视艺术视野中的三峡工程——影像三峡:自然、科技与人文[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0(2).
Three Gorges Project Based on Visual Arts
WANG Jie-hong
(Arts Depart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Three Gorges Project is the world biggest water control project. As a “Chinese monument”integrated highly human arts and technology, it reflects not only Chinese people’s spirit of being unyielding and tenacious, of working hard for prosperity, but also Chinese nation’s awareness of unexpected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confidence. Based on the seemly contradictory but dialectical two sides,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appearance and humanistic connotation of Three Gorges Projec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hinese painting, oil painting and photography.
Three Gorges Project; ink and wash of gorges; son of the east; new Three Gorges
I206.7
A
1009-8135(2010)06-0011-06
2010-08-03
王杰泓(1976-),男,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武汉大学艺术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郑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