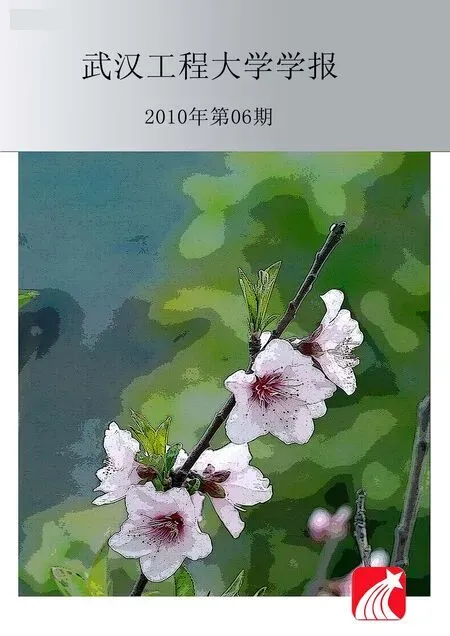张爱玲的读者意识与自译策略
2010-03-21范丽
范 丽
(武汉科技大学英语系,湖北 武汉 430079)
身为作家兼翻译家的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已不容置疑,而其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地位也逐渐凸显。张爱玲一生不仅著有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尝试了多种形式的翻译活动,其中不仅有将韩邦庆的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译为国语的语内翻译*1959年,美国著名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 从符号学观点出发将翻译分为三类: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也有将《爱默生选集》、《老人与海》等美国文学作品译为中文的语际翻译。此外,身为双语作家,张爱玲还有作品自译的习惯,如将自己的中文作品《秧歌》、《金锁记》等译为英文,而将自己的英文作品《Stale Mates》等译成中文,其中《金锁记》更是被其几度转译改写[1]。
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从不同侧面对张爱玲的翻译实践进行了研究。但与张爱玲的创作研究热相比,其翻译研究仍显得相当冷清,而对其自译的关注更是少之又少。张爱玲不仅有为数不少的自译作品,其自译的风格也别具特色。本文借用接受美学的相关理论对张爱玲的自译策略进行简要探讨,以期明确其读者意识与自译策略之间的联系,并试图指出其创作与翻译之间的共通之处。
1 张爱玲的读者意识
成名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张爱玲至今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其作品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这些与其强烈的读者意识不无关系。在《论写作》一文中,张爱玲也曾明确谈到了自己的读者意识:“要迎合读者的心理,办法不外这两条:(1)说人家所要说的;(2)说人家所要听的。……将自己归入读者群中去,自然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什么。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此外再多给他们一点别的……[2]”而在《写〈倾城之恋〉的老实话》一文中,张爱玲在记述自己一年前创作《倾城之恋》的心理时,明确解释了自己在创作实践中如何运用了这一意识:“写《倾城之恋》,当时的心理我还记得很清楚。除了我所要表现的那苍凉的人生的情义,此外我要人家要什么有什么,华美的罗曼斯,对白,颜色,诗意,连‘意识’都给预备下了:(就像要堵住人的嘴)艰苦的环境中应用的自觉……[2]”由此可见,张爱玲不仅具有明晰的读者意识,而且十分善于运用这一意识。
身为职业作家的张爱玲,要靠卖文为生,明知读者即其衣食父母,自然具有较强的读者意识。陈晖曾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对于张爱玲来说,创作是爱好,也是‘卖文’,读者是衣食父母,她的创作、成名都需要他们的接受和肯定。她对他们有自觉和不自觉的迁就。[3]”需要注意的是,张爱玲虽十分看重读者的需求与接受,但也并非一味地去迎合读者,而是要在此基础上“再多给他们一点别的”。在迎合读者的同时,“张爱玲保留了作家创作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让张爱玲在追求通俗的同时,避免了坠入‘低俗’,也区别于‘流俗’,而以‘雅俗’的品味,赢得更广泛的读者”[3]。然而,不管是“要什么就给什么”,还是“再多给一点别的”,都体现了张爱玲强烈的读者意识,即在创作过程中对读者接受的关注。
2 期待视野与自译
在翻译中自译者通常会以读者的期待视野为参照物。
2.1 期待视野
期待视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是德国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尧斯(Hans Robert Jauss)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文学接受活动中,读者原先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欣赏要求和欣赏水平,在具体阅读中,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审美期待。[4]”读者在阅读作品前,并非如同一张等待书写的白纸,被动地反应,而是受主观的和客观的、过去的和现时的诸多因素影响,已经形成某种阅读心理期待,具有某种思维倾向、审美要求和评判标准。期待视野不仅是阅读理解的基础,也受其限制。只有当一部作品与读者已有的期待视野符合一致时,它才会被读者迅速理解并接受。
2.2 自译
自译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翻译,与一般的翻译有所不同。自译者翻译的是自己的作品,拥有原作的版权,在自译时享有较大的主体性,其“译”并非一般的“译”,很大程度上“译”变成了“作”。刘绍铭曾指出,余光中和叶威廉在翻译别人的作品时中规中矩,但他们自译的诗篇,像叶威廉自译的《赋格》一诗的英文版,与原文出入很大,不能看作是翻译,而可视同于创作[5]。
自译的译者也是原作者,这使得传统翻译理论所认定的“一仆二主”的翻译关系在自译中发生了改变,自译者不再俯首于原作者,只需侍奉好一个主人即读者,因而在自译中,读者得到更多的关注。此外,许多作家将自己的作品自译成另一种语言,通常是希望能让自己的作品为更多读者所接受,如印度诗人泰戈尔,他自译了英文版的《吉檀迦利》,使其作品拥有了世界范围内的读者。因此,自译者自译的初衷也决定了其对读者的关注。
因此,自译的性质和自译者自译的初衷都决定了自译不同于翻译,自译的策略取向也会有别于翻译。自译者通常会给予读者更多的关注,在选取自译策略时会以读者接受为最终参照。
3 张爱玲的自译策略
自译者对读者较为关注,使得他们会利用自己在自译时所享有的较大主体性来为读者服务,在自译时自然会采取一些“为读者”的自译策略。而张爱玲具有较强的读者意识,这使其比一般的自译者更为关注读者。如前文所言,自译不同于一般的翻译,很大程度上“译”成了“作”,自然作家的创作意识会影响到其自译实践。此外,即使是把自译视同为翻译,也会受到译者个人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张爱玲的读者意识,作为其个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当然会影响到其自译。
事实上,张爱玲在自译自己的作品时,相当关注读者,也即关注读者的接受。为了使译文符合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张爱玲时常会对原文采取增删改写等灵活的自译策略。
3.1 解释性翻译
在自译时,张爱玲经常会对原文内容进行增补,即考虑到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知识可能欠缺,对一些语词所隐含的深层文化信息增添具体解释性内容以填补原文中的空白与未定点,降低目标读者理解的难度,从而使自译作品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更好地为读者所接受。如下面两例中译文的下划线部分:
(1)原文:坐了一会,炳发老婆低声附耳说:“姑奶奶可要上楼去歇歇?”[6]25
译文:Bingfa’s wife whispered, “Does Gu Nana wish to go upstairs and rest a while?” It was expected of the bride that she would want to be alone with the women of her own family and have a good cry.[7]26
(2)原文:The thought of inescapable doom does not drive him to despair, to slackness, to gluttony or excessive sensuality, which to the European may seem the logical reaction.[8]
译文:灭亡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他们并不因此就灰心,绝望,放浪,贪婪了,荒淫—对于欧洲人,那似乎是合逻辑的反应。像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人,一旦不相信死后的永生了,便便大大地作乐而且作恶,闹得天翻地覆。[9]354
3.2 删减式翻译
考虑到不同文化语境中读者文化背景的差异,为了让读者更好接受作品,张爱玲在自译时有时会有意删除超出译文读者期待视野的内容,从而使作品符合读者的阅读期待。如下例中,张爱玲即省去love-making一词不译:
(3)原文:It finds joy only in materialistic details, which explains why traditional novelists dwell so tirelessly on the unabridged items in meals and love-making (complete menus are often given for no specific purpose).[8]
译文: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9]353
3.3 改写替换
对于超出目标读者期待视野的内容,张爱玲在自译时除增添解释和直接删除以外,也会选择大刀阔斧地改换原文内容,即对原文进行重新改写,用新的内容替换原文内容,有意迎合目标读者的阅读趣味。如下例:
(4)原文:她们彼此开玩笑向来总是这一套,今天似乎太过分了,不好意思再往下说,但是仍旧在等着,希望她还会说下去,再泄漏些二爷的缺陷。[6] 76
译文:The brief respite from the constant terror of attending on mother-in-law turned their thoughts irresistibly toward sex and jokes about sex like soldiers in a war. They usually did not go far but they seemed to be still waiting, hoping to hear more about Second Master’s limitations.[7] 76
在此例中,仔细对比下划线部分的原文和译文,不难发现张爱玲在这里并不是如实翻译,而是全然改写。中文原文并未直接点出“性”这一话题,表述是相当含蓄的;而英文译文则相当直白,毫不避讳妯娌间谈论的即是“sex”。显然张爱玲这样处理也是考虑到了不同文化背景读者的不同阅读期待。
4 结 论
身为作家兼翻译家的张爱玲具有较强的读者意识,这一点不仅影响到其创作实践,也影响到其自译实践。在强烈的读者意识驱使下,张爱玲在自译过程中时常会有意采取一些“不忠”的自译策略,对原文进行大幅度地增删改写,使自译作品符合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从而为自己的作品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赢得更多的读者。
参考文献:
[1]陈吉荣.转换性互文关系在自译过程中的阐释:《金锁记》与其自译本及改写本之比较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2):69-72.
[2]张爱玲.写《倾城之恋》的老实话[C]//子通,亦清.张爱玲文集补遗.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333-334.
[3]陈晖.论张爱玲创作的通俗化追求[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62-65.
[4]朱立元.接受美学导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61.
[5]刘绍铭.到底是张爱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148-149.
[6]张爱玲.怨女[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
[7]Eileen Chang. The rouge of the north [M].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8]Eileen Chang. Demons and fairies [J].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43,5(6):421-429.
[9]张爱玲.张爱玲散文全集[M].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