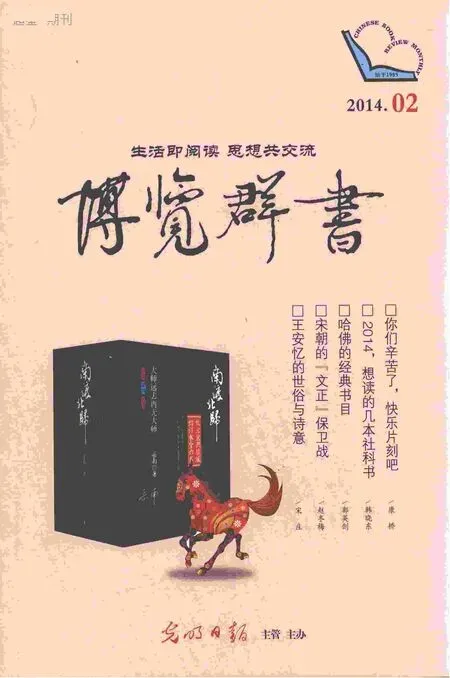争鸣,还是争宠?
2010-03-21柳士同
○柳士同
春秋战国,尽管战乱频仍,但思想却异常活跃,形成了一个被我们津津乐道的百家争鸣局面。这种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实在是中国历史上十分可喜而又难得的事情。先秦诸子为中国文化所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有史为证,就不必多说了。本文想探讨的是,诸子究竟是为何而争鸣呢?
诸子乃出自当时的“士”——不是拳勇之士,而是谋略之士,即知识型的谋士。在西周的封建等级制度中,士虽也属于贵族阶层,但却处于最低位置。待到春秋战国时代,由于诸侯间的战争与兼并,大批的士,尤其是那些知识型的士,便流落到民间成为“游士”。然而,尽管他们沦落了,但他们有知识有文化,是绝不会将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的。此时,各路诸侯为了争霸,正纷纷网罗文化名人,以扩大社会影响,协助自己成为霸主;而百家之学也只有为君王所用,才能得以彰显。于是,诸子便顺应潮流,纷纷投靠并依附于各路诸侯,以摆脱自己“食无鱼,出无车”的生存状况。齐桓公乃当年第一个舍得花钱养士的诸侯,并因招来一批杰出之士,从而使他成为中原的第一位霸主。他的成功范例,既使得招贤养士蔚然成风,又使得天下之士看到了自己的前程所在。如此一来,诸子便纷纷以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政治谋略”去打动当时各国的君王(或权臣),成为君王(或权臣)的谋士和策士。而让各国君王采纳他们的主张,并待他们为上宾,就成为他们美好的理想和毕生的追求。
他们不辞劳苦,周游列国,其目的就是为了博得某个君王的青睐,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样,他们的思想即便有一定的学术含量,那点儿学术也必须能为君王所用,其理想与追求才能得以实现。于是,如何协助君王统治国家、治理民众,就成了诸子百家思想的出发点乃至归宿。“争鸣”这一概念,原本指的是学术层面上不同观点的对话、论辩、驳难与交流,而诸子百家的学术层面却相当狭窄,大多局限在政治与伦理的范畴。这里言及的政治,实乃“治人”和“牧民”之术,与学术意义上的“政治学”并不搭界。所谓百家争鸣,各家所表白的无非是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治国方案,其中许多都是上不了学术层面的,最终,必然是让权术给站了上风。既不可能诞生如古希腊的逻辑学和几何学,更不可能诞生如伯里克利那样的政治家、苏格拉底那样的思想家、柏拉图那样的哲学家和亚里士多德那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诸子百家的学问多出于功利,更偏重实用,因此这些学问往往是支离破碎的和随机应变的,往往缺乏逻辑性,甚至时常流于诡辩。诸子最擅长的莫过于杜撰一些似是而非的“故事”,来附会自己所要阐述的道理。比如,至今仍为我们津津乐道的《晏子使楚》的故事。“橘”和“枳”,一个是常绿乔木,一个是落叶灌木,原本是两种不同品种的植物,可晏子偏要胡说什么“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以如此荒诞不经的说法戏谑一下颟顸的楚王,令其“反取病焉”,倒也未尝不可;但如此谬论居然还流传了两千多年,至今仍为不少人引用,就实在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了。由此可见,为了让君王能采纳自己的主张,诸子往往是不惜胡编乱造、生拉硬扯。如此流风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只要能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似乎并无什么不妥。史学界一度盛行的“以论带史”,大致就是这样提出来的。既然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可以任意筛选史实,那么必要时编造一下历史又有何不可呢?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不就在他及第进士的应试文章中,为了说明“刑赏忠厚之至”的论点,而凭空捏造了一个“当尧之时陶为士。将杀人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的故事么?考官们居然还都信了!尽管事后苏轼坦言了自己的荒唐,但说者听者也不过一笑了之,千百年来还一直把这当作“佳话”传颂。对此,我们不觉得有些可悲么?以此类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莫非就是这么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地撰写出来的?
先秦诸子之中能坚守自己的独立品格与学术思想,像庄子那样的智者,虽也不乏其人,但毕竟是凤毛麟角,更多的恐怕还是出于自身功利的需要,一心为统治阶级出谋划策。就连力主“清静无为”的老子,不也为统治者设计了“虚其心,实其腹;弱其智,强其骨”的愚民政策么?笼罩中国两三千年的蒙昧主义起于何时?正是起自被那些自以为超然物外者认作老祖宗的老聃啊!直到发现热脸贴上的尽是些冷屁股之后,老子这才骑着青牛“出关”,并为我们留下了《道德经》;孔子这才重返老家设帐授徒,“退而修《诗》、《书》、《礼》、《乐》”(司马迁)——这些实际上都是他们争宠不得之后的产物。而他们的弟子后学,则比前辈要乖巧得多,他们甚至不在乎自己师出什么学派,只要能投君王所好,才不管他是“王道”还是“霸道”,或者说君王想要什么“道”就在理论上给他提供什么“道”!争鸣原本是为了辩明真与假和是与非,而争宠者则根本无视真假是非,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十足功利化的“为我所用”。为此,他们不惜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在七国纷争无一不想灭掉其他六国而一统天下的形势下,法家和纵横家就是这样顺应潮流脱颖而出,最终争宠成功的。只是以法家重刑治国的秦朝历时短短的14年就覆灭了,这才给儒家的卷土重来提供了大好的契机。因为儒学实在难以为暴力统一天下出谋划策,却能为巩固专制统治提供相应的理论资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汉代的董仲舒终于得宠,并且“罢黜百家”而以“儒术”为“独尊”。
争鸣,乃是一种自由的表达,是表现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对于一个皇权专制的大一统帝国来说,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与自由,怎么可能出现争鸣的局面呢?自西汉以降,再无人与儒家相争,自然也就不存在什么“百家争鸣”抑或“百家争宠”了。“士”渐渐沦落成了“优”,尤其是如东方朔那样圆滑乖巧的“优”。就连清代的大文士纪晓岚,不也是被乾隆皇帝“倡优蓄之”么?直到20世纪初叶新文化运动发轫,国人这才终于迎来历史上第二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比起两千多年的那一次来说,这一次堪称真正的“争鸣”,因为随着西风东渐,独立的知识分子已开始在中国诞生。所谓“新文化运动”,原本就是一场人文主义的运动,是一次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它解放的是人,是人的个性。除了陈焕章、杨度之类的文人,还在“士为知己者用”地寻找自己的主子,甚至不惜投靠到一心复辟的袁世凯门下之外,更多的文化人则已不再依附豪门权贵,开始成为如陈寅恪所言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知识分子。而且,中国的学术领域也获得前所未有的开拓,众多的学科、众多的流派,色彩纷呈。知识分子是干什么的?其职责就是追求真理、发现真理、传播真理和捍卫真理。陈独秀、鲁迅和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完全做到了这一点,于是,在热烈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氛围里,知识界出现了一个亘古未有的活跃局面,这才是真正的“百家争鸣”!
然而,中国文人依附权力毕竟依附了两千五百多年,这种依附早已根深蒂固,早已成为一种“惯性”。他们很难做到不去争宠,倘有权贵高价赎买,那就越发趋之若鹜了。就以“文革”期间为例吧,诸如梁效、初澜、石一歌、罗思鼎、丁学雷之流(均为当时的御用写作班子),虽说一个个“毕竟是书生”,可一旦争起宠来,谁也不肯落后、谁也不会手软!遗憾的是,他们仅仅是沆瀣一气的一家,在“四人帮”的庇护下,其余九十九家不但噤若寒蝉,连性命都自顾无暇。到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随着思想的解放也出现过又一轮“百家争鸣”的局面,但随着文化教育部门的行政化和衙门化、文化教育事业的产业化和商品化,知识界的“争宠”已远非先秦诸子可比的了。因为当年如韩非、商鞅、张仪、苏秦那样的得志者毕竟是少数,而如今随着学位、职称销量的剧增,在那么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的诱惑下,参与争宠的文人,实在不是一个“车载斗量”可以形容得了的。当几十个教授去争聘一个处长的职位时,学界还有学术可言么?而且,他们“争宠”的对象已不仅仅是官方,还有商家。一个个巴不得早日跻身权贵的行列。随着传媒的“高科技化”,这些争宠者都可以在各种“讲坛”、“论坛”闪亮登场,几乎家家户户都能一睹他们的风采。如果说对当年诸子百家的争宠,我们今天只能依凭有限的想象的话,那么,如今那一个个口若悬河、眉飞色舞的姿态,却足以牵动每一位观众的心肠。但当今的中国学界究竟取得了多少学术成就呢?与“新文化运动”相比,根本就无法望其项背。一些所谓的“国学大师”,贩卖的不过是从两千多年前“争宠”的百家那儿生吞活剥来的货色。随心所欲地去歪曲历史、矫饰儒学、娱乐学术、宣扬和兜售五花八门的伪文化……老子不是说要“虚其心”、“弱其智”,“使民无知无欲”么?看看此类名家的装腔作势,听听他们的信口雌黄,竟然就那么轻而易举地实现了。
争宠乃是一种典型的臣妾心态,其目的无非是取悦权贵,以便自己也能爬上权贵的位置,至少也要分得一杯羹。而一旦我们的作家和学者都纷纷热衷于争宠而不再争鸣,他们还会拥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么?还会具备创造的能力,从而撰写出具有新意的作品和具有创意的论著么?当今中国,文学的乏味和学术的平庸恐怕已然是在所难免的了。好在泱泱中华乃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国度,历朝历代毕竟还出过一些“宁鸣而死”的真正猛士。但愿我们记住鲁迅的话,石在,火种就不会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