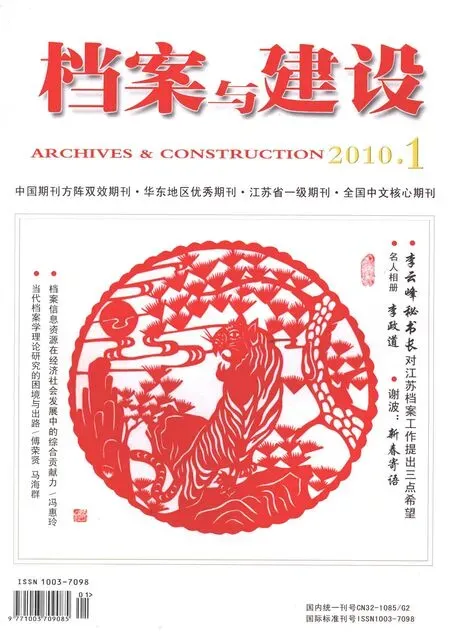泡 水
2010-03-12郑凤鸣
□郑凤鸣
泡水,是拿了容器到专供开水的老虎灶去花钱打开水。我读小学、升初中的上世纪60年代前后,大多数苏州人家里已经拆除了老式柴灶,用上了煤球炉烧水做饭,但是由于煤炉烧水跟不上需求,所以许多人家就提着热水瓶到巷口的老虎灶泡开水。那时这种老虎灶在苏州城内外到处可见,大多是一开间门面。而两开间门面的老虎灶,往往在里面放三四张方桌、几条长凳,就成了小茶馆。每天天还没有亮,老虎灶就生火了。一些老人的生活习惯是早上“皮包水”,就在老虎灶内吃早茶,肚皮里灌一饱茶水,成为街巷市民生活的一个风俗。
我家巷口的老虎灶在苏州的王天井巷,定船桥的北面。我记得老虎灶是一对中年夫妻开的,两人的长相都很清秀,个子都不高大。男的粗膀大脚,面色红润,是个好劳力,一板车一板车地往家拉木屑、砻糠、木柴作燃料用。女的是“矮脚鸡婆”,生了一男N女仍然风姿绰约。长子如父,面容端正,身板不错,已能时而帮助父母干些小活。几个妹妹活泼可爱。一家子兢兢业业,和和睦睦。
老虎灶以形状得名。水灶砌在店门口,烧水处的炉膛口开在沿街的正前方,如同张开了一只虎嘴;灶肚中烧木屑、刨花和煤炭,恰似老虎的腹部;再加上前面有像虎眼的汤罐;还有如老虎鼻孔一般的投燃料孔;再加上灶尾一根高高竖起的烟囱管,就像老虎翘起的尾巴,因此被很形象地称为“老虎灶”。


传统的老虎灶灶面置有三个灶眼,灶眼上放三只烧水的深口生铁汤罐,三只汤罐围绕一个加燃料的烧火口子。汤罐和烟囱之间还有两只很大的积水汤锅,直径有一米多。锅上箍的杉木桶高约二米。汤罐和积水汤锅上都用木盖子盖着。因为积水汤锅的口很大,所以盖分两半,靠里面的一半基本是不动的。设积水汤锅是为了利用烧开水的余热,给汤罐制造预热水。在汤罐需要添水时,把积水汤锅外半个木盖子移开,将已经预热的水舀入汤罐,汤罐里的水很快就会烧开,免得水客多等时刻。汤锅后的烟囱粗大,直竖,穿出屋顶。老虎灶最外档是一个方形的木版平台,供水客放置热水瓶等容器。早晨、傍晚,五颜六色的热水瓶、大小不一的“汤婆子”(铜质水焐子)布满平台,很是壮观。
泡一热水瓶开水只收1分钱,一水壶2分钱。起先,老虎灶1角钱卖5个硬纸水筹。水筹是用硬纸板剪成的小长方块,上面盖有店名章。后来用一段小竹片,上面用烧红的铁条烙一个特殊的印记,1角钱买1根竹水筹可泡12瓶开水,可以说是早期多买多送的经营手段吧。泡水凭水筹,既省得找钱,又便于店主知道顾客的需水量。水筹因经常被热水浸泡和在人们的手上流转,所以很快会变红、光滑。如果现在哪位还有这种水筹,倒不失为一个独特的收藏门类。
在等待水开的时候,水客们丢下水筹,掀开瓶盖,将瓶盖的平面相互对击,发出小小的“啪啪”之声,以解寂寞。相识者天南地北神侃一通,聊聊今天的菜价、孩子的学业、市井的新闻。灶主时不时打开烧火口子上的铁盖子,用大大的铁皮畚箕倒入一畚箕砻糠、木屑或者小的木柴,然后迅速关上铁盖,迫使黑烟从烟道排出。稍顷,他又会用一根钢钎伸入灶口,搅送燃料。此时,只听得炉膛里发出“蓬蓬”之声,掀开的灶口有火舌上蹿,撩拨汤罐,同时把灶主的脸映照得通红通红。这时,如果是男灶主掌钎,他俨然就是一位炼钢工人,如果是女灶主掌钎,她就是一位女关公。
待到“水熟无声”,灶主打开汤罐盖,一股蒸汽顿时喷涌而出,一个个沸腾的水柱上蹿下跳。灶主手拿一把漏斗,将下部管状“漏嘴”插入热水瓶的瓶口,另一手拿一把水勺,舀一勺滚开水,倒进漏斗。基本上不到两勺就可以灌满一热水瓶。开水稍有溢出,正好为热水瓶的外壳加温,保管水客提回去的开水滚烫滚烫。
冬天到老虎灶泡水的人就更多了,傍晚为甚。一些人带了铜汤婆子去泡水。因为铜汤婆子的进水口小,漏斗的嘴插不深,进水慢,常常发出“噗噗噗”排出空气的怪声。张三问:“天还不怎么冷,怎么已经泡汤婆子了?”李四答:“这是给我好婆泡的。”王五说:“满了,快盖上盖子。”灶主提醒:“路上当心,掉地上会烫伤人的。”这一幅有声有形的风俗画,现在是难得看到了。
春夏之交,勤俭的主妇提个脚盆,带上用肥皂擦过的湿被单床单,到老虎灶上用开水一泡,顺便买灶主的冷水,在老虎灶门口清洗干净,回家晒干、收藏,好不爽快。也有的带了洗干净的荠菜,到老虎灶一烫,回家凉拌,或者包馄饨,比那依靠煤炉烫菜省事多了。还有的为杀鸡宰鸭褪毛(那时卖鸡人是不给宰杀和褪毛的),也到老虎灶泡水。灶主会细心地帮他加些冷水,以免水太烫而连鸡皮、鸭皮也烫掉。
那时,清早和傍晚去老虎灶泡水是一些人每日的必修课,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去泡水时,提两只竹壳热水瓶,把家门用铁搭配一扣,并不上锁,便转身而去。那时天下少贼,老虎灶离家也才半条小巷,所以长期如此,家中竟无一次失窃。
失窃之事虽然没有,但是打碎热水瓶的事故倒有两次。一次是出门泡水刚到沿街的大门口,不知怎么的脚抬无力,过门槛时一绊,险些跌倒,双手各一的热水瓶的竹壳在门槛上反弹了一下,没有受损,但是两只瓶胆砸在门槛上,发出“砰”、“砰”两响,粉身碎骨。我们少儿时没有现在的少年这么金贵,天天做泡水等家务事是司空见惯。打碎了热水瓶不但不会撒娇,而且会因为闯了祸而特别心虚。至于有否为此而受大人训斥,现在已经记不清了。
另一次是我空手回家,路上看见同宅的薛大哥提了四只泡好水的热水瓶,显得有些吃力。出于好心,我主动提议帮他拿两只,不料在交瓶时一个失手,有一只热水瓶掉在了地上。一声大响,瓶破水溢,热气腾腾。我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薛大哥却大度地问我:“烫着了没有?”我摇摇头,不敢正视他的目光。他安慰我:“没烫着就好。如果你不想受到责怪,就千万别把这件事向你的家里人透露。”要知道那时买热水瓶是要凭票供应的呀!我噤若寒蝉,一直没敢声张,不知道他后来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我连一句“对不起”都没有说,就和他分手了。我内疚自责了几十年。最近,退休的薛大哥从无锡来苏州,我鼓起勇气说出了当年的尴尬,他却一脸茫然:“啊?还有过这等事?你太认真了。”

老虎灶周围常常有热水瓶滴滴答答流出的水渍,但是今天电水炉的水渍已不是当年的水渍了。对苏州的中老年人来说,这水渍不会立即消逝,它仍然留在他们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