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河万古仍滂沛——王国维在京都(上)
2010-03-03○苦茶
○(台)苦 茶
前 言
2009年底,我去日本京都走了一趟赏枫之旅。因为是自助旅行,出发前须作功课,买了几本旅游指南,研究交通路线,上网搜寻不可错过的美食、景点。在庞大的信息中,无意发现,京都永观堂竟然与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有密切关联:先生自号及其巨作《观堂集林》的“观堂”二字即是取自永观堂,有这样的说法。
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关联呢?继续研究,方知王国维先生曾经在日本京都住过,而且有“四暑五冬”之久。由于他和我即将前往的古都有这样的关系,我抱着极大的兴致搜寻他与京都之间的故事。想查清楚他何时去京都?旅居京都期间住在什么地方?去过哪里?做了什么事?认识哪些日本人?行前作了初步研究,自京都旅行回来后,对于其地形名胜、方位格局、人情风土有了基本概念,回头拾起相关的文献与资料来读,更觉亲切有味。
说来惭愧,对于王国维先生,我只耳闻(并未通读)他脍炙人口的《人间词》、《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史》、《观堂集林》等巨作,知道他是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还有他自沉颐和园昆明湖的悲剧。除此之外,我对他平生经历从来没有认真探讨过,差不多是一无所知。他曾经住过京都这件事,原已让我讶异;而经过查询相关著作及文献后,呈现出他和日本、日本人关系之密切,让我更加讶异。
读过这些零零碎碎的材料之后,我索性把它整理成这篇文字。称不上严谨考证,顶多是闲谈掌故。我试着把现成材料排列比对,取今之人地事与古时对照,挖掘各家传记所忽视的细节,在层层迭迭、或对或错、或有意或无意、互相矛盾的回忆录与传记中探索,或许可以展现王国维先生在大师光环遮盖下,凡人生活的一个侧面。
谈论王国维与京都,首先要了解王国维为何渡海到京都长住?有远因也有近因,促成他人生这场大变动的近因是辛亥革命。
辛亥渡日
1911年10月10日(农历8月19日),武昌爆发武装革命。起义军于11日凌晨占领武昌,革命党人成立湖北军政府,推举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宣布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于12日占领汉阳、汉口。
武汉三镇的成功,犹如给清帝国这根枯木点起一把火。湖南、陕西、江西、山西等15个省纷纷宣告独立,奉天、吉林两省也加入响应。清帝国眼看是命在旦夕了。
局势突然演成如此严峻,在北京中央政府工作的公务人员们很惶恐。庚子年(1900)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惨状还余悸犹存,说不定小皇帝这回也得弃宫出逃,满城文武官员不得不为自己及家人的身家性命做个打算。很多人携家带眷想往南方逃,因为陆路不靖,故纷纷奔赴天津抢买船票,想直接逃到上海等地。
时任学部参事的罗振玉在他的自传《集蓼编》回忆说:“武昌变起,都中人心惶惶。时亡友王忠悫公亦在部中,予与约各备米盐,誓不去,万一不幸,死耳。”已经和王国维约好,要誓死守在工作岗位上。罗振玉想给人的印象是,对于清室始终誓死效忠。罗振玉曾在文章中表示,随着局势变化,从辛亥革命、清室倾覆到溥仪被驱逐出宫,在这段期间内有好几次都想殉清殉主,不过从来没有付诸行动就是。
稍早前,他的好友汪康年(穰卿)先逃到天津,“招乡人(罗振玉)往,言留屋三间相待。乡人以行资无措,谢之”(据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天津离北京这么近,说“行资无措”似乎不太合理,这大概是婉拒的一种藉词吧。也幸好没去,因为才不过几天,汪康年就在天津去世了。
据说罗振玉这个“保皇派”本来就得罪了革命党,并且和袁世凯不对头(他的亲家刘鹗就是被袁世凯罗织罪名,流放新疆而死),将来不论是得胜的革命党或复起的袁世凯掌控北京,他都难逃清算一劫,待在天津与待在北京都一样糟。等到确定袁世凯即将再起复出政坛,他知道情势越来越危险。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位日本和尚找上门来。这和尚乃日本净土真宗本愿寺派(其大本山即今之京都西本愿寺)驻在北京的特派员,转达他的教主大谷光瑞的心意,想劝请罗振玉东渡日本避难,甚至愿意将大谷位于住吉驿、今之神户六甲山上的别墅“二乐庄”借给罗氏家眷栖住。
这位大谷光瑞(1876-1948)来头非常大,他不但是一方宗教领袖(西本院寺第22代法主,法号“镜如”上人),他的夫人九条筹子和大正天皇的贞明皇后是同胞姊妹,具有伯爵爵位,1913年见过孙文并受聘担任中华民国的最高顾问,巅峰时期他的本愿寺预算与京都市预算相当,宗教、政治、经济实力都雄厚。他还是文史学者、考古学家、探险家,留学欧洲,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曾经三次组队前往中亚及中国进行探险与考古发掘,挖掘出大量古代佛教遗迹、文物、文书及经卷,成绩颇丰。与罗振玉算是考古学界的同行吧?因此向罗伸出援手(也有人猜测其实大谷是看上罗收藏的珍贵文物),但是罗振玉与他素不相识,虽感其厚意,但心存犹豫不敢答应。或许他对大谷也起了戒心?
这时,罗振玉好友,几位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狩野直喜、富冈谦藏等人写信来劝说前往京都,承诺可以协调让罗大量藏书暂存京都大学图书馆,还可以预先安排住处。罗就近请教好友藤田丰八(字剑峰,1869-1929),藤田说就应诸位教授邀请吧,可以请大谷的本愿寺担保运送书籍、文物,到达京都后再还运费。藤田甚至愿意先回日本帮罗筹备一切事宜。有这么多朋友相助,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了。
早在1901年底,罗振玉即奉两江、湖广两督(刘坤一、张之洞)之命,率团前往日本考察教育、财政等制度,走访东京、箱根、横滨、京都、奈良、大阪、长崎等地,历时两个月零八天,事后将考察过程写成一文《扶桑两月记》。1909年阴历5月,又以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身分赴日本考察农学,走访京都、北海道、东京等地,历时约1个半月。两次考察让他开了眼界,日本当时的文明与强盛都看在眼里,对于下定决心举家搬迁日本这件事,想必有很大的推力。
大约11月初,凑巧赶在袁世凯复起组阁(11月16日)之前,罗振玉招集女婿刘大绅(刘鹗之子)与一路提携、当时任职学部图书局编纂及名词馆协修的王国维,共三个家庭大大小小约20人来到天津。搭乘小商船温州丸,渡过险恶风浪,抵达日本神户。藤田丰八等几位友人在当地守候,随即送到京都田中村住处。东京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救堂)远来相助,狩野直喜的夫人亲自烧饭煮菜款待。
王国维为何愿意跟着罗振玉一起到日本?他倚靠的清政府倒了,工作及收入当然也没了,能够在生活上、经济上支持他及一家妻小的,眼前只有罗振玉一人。且罗振玉会遇到的危险,对他说不定也构成危险,走为上策。当然,罗振玉应该也有相当程度地主动邀请或要求,让他很难拒绝。他在1912年11月15日写给铃木虎雄的信中自称“亡国之民”,可见当时的他视民国为敌国,既然是政治难民,逃到他国寻求庇护,做个“海外夷齐”亦得其所哉。况且王国维对日本这国家也不陌生。
10年前,王国维就来日本留学过。早年读书生涯里,对他学问影响最大的几位老师中,就有两位日本人。他懂日文、会说日语。京都大学几位汉学、东洋学教授是他的好朋友。他和日本国、日本人渊源很深。这就是王国维愿意举家迁住日本的远因。而这一切还是要从罗振玉说起。
东文学社
19世纪末,吸收西学(包含西洋及东洋)以经世致用是当时中国最热门的显学。甲午战争之后,30岁的青年罗振玉想多知道有关外国的事,向朋友借江南制造局的翻译书来读,发现“西人学术未始不可资中学之助”(据《永丰乡人行年录》)。中国以农立国,首先要让国人吃得饱吃得好,让国家富强,振兴农业为当务之急。他也体认到若要运用外国技术、学术,则国民教育现代化很重要,从此他的志业走向农业技术引进与教育革新推广。
1896年春天,罗振玉与徐树兰等友人在上海组织“学农社”、开设“农报馆”、发行《农学报》(1897年5月起),聘专人翻译欧美日本的农书及杂志,希望用现代的、科学的农业专业知识来增产救国。识见超凡,非常独到!东西洋信息的来源还不算太难,难的是急需大批能解读东西洋文字并译成中文的人才。有鉴于此,罗振玉与几位友人(据说是《时务报》同人汪康年、蒋黻、狄葆贤等人)合资开设“东文学社”,设址上海市新马路的梅福里(农报馆对面的萃报馆内),希望教育翻译日文的人才,将来为“学农社”、《农学报》所用。
该社聘请原本就为农学社翻译农书的日本学者藤田丰八为教授,等学生增多后,又增聘几位日人老师,例如上海日本副领事诸井六郎及书记船津辰一郎来担任义务教员(据《永丰乡人行年录》)。学社以日文教授各种学科,学生不但可以学习日文日语,还可以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甚至英文!据说它就是中国第一所日语专门学校。
1898年,王国维才22岁,放弃科举考试,来到上海谋发展。因在《时务报》当书记的同学许家惺[号默斋,名作家许啸天(许家恩)的亲兄弟]有事回乡,遂请国维代替他。《时务报》系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于1896年8月创办,梁启超曾担任主笔(当时不过才23岁),文采激扬,鼓吹维新最力,是当时中国最好最畅销的报纸之一。王国维在家乡时就常阅读《时务报》,可惜当他进报馆时,梁启超早已离开。
王国维于2月份进报馆工作,才到下旬就想跳槽去专门翻译西文的报馆工作,因为他很急着想吸收新学。父亲劝国维考虑人情世故,不要才刚上工没几天,连薪水都没领到就走人,让保人很难堪,也会给亲朋好友笑话。他听话留下。很快地,老天爷就给他开了另一扇门。
3月22日,培养翻译人才的东文学社开学(据袁英光、刘寅生编《王国维年谱长编》)。王国维取得《时务报》馆长汪康年同意,每天利用下午3小时时间去学社上课。入学之后,无意中以题在同学扇子上的一首咏史诗,“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句(一般作“西头”,误)受到罗振玉叹异赏识(但是王国维自己却没有提过这段往事),进而从学问上、经济上大力栽培,不遗余力。这两人从此成为生命共同体,是师生同学,也是朋友伙伴,先是儿女亲家,后又反脸失和,一生牵缠纠葛。
东文学社使用教材是日本小学读本,共7册。把大人当成小学生,一切从基本教起,即使如此,一开始王国维还是读得很痛苦。
3月24日给许家惺的信中说:“读东文后颇觉不易,苦无记性,不能从事他学,又不能半途而废,殊闷。”
4月13日信中说:“现在弟学东文,势难间断,已成骑虎之势。”
5月上旬信:“弟学东文苦不能读熟,恐致半途而废。”
6月18日信:“东文较西文诚易,但苦无暇读,因出馆后仍须温习,即有暇亦不肯读,是以不能精进。”(以上均据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
刚开始学习另一种陌生外国语文,难免不习惯,困难重重,况且当时中国的日语文教学与学习都在草创时期,不像现代有这么多辞典、学习书、MP3、CD、影片、计算机等教具教材可辅助,教与学双方都在摸着石头过河,过程当然难受,连王国维这读书天才都要叫苦喊闷。尤其他学习同时也要顾到本业工作,蜡烛两头烧,两边都作不好。看到“即有暇亦不肯读”句不禁会心一笑,当过学生的人都有这种偷懒心态,想不到大师也是如此。
在学习上,老师藤田丰八很照顾他,帮他想出一兼二顾的办法。6月30日王国维给许家惺的信中说:“弟学东文,因事冗所进甚浅,蒙教习藤田君垂爱,屡向穰先生(汪康年)说弟事多,于学问非所宜,嘱以旬报或日报译东报事畀弟,庶得一意学习。”汪康年同意让王国维担任为日报馆翻译日本报纸文章的工作。寓学习于工作之中,并且免去其它烦心杂务,从此王国维的负担减轻很多,学习上也能精进。
王国维刚入学时成绩不理想,学社考试不及格,差点被退学。但坚持下去就能进步。到8月份,学习已颇有心得,8月5日给许家惺信:“东文较西文难易迥别,但须取中东虚字列成一表(须东人优于中文者为之),则读其书甚易。弟于此事甚浅(同社六人惟弟最劣),果能专精事此,一年当能通之。”自信都出来了!已经知道学习关键何在。成绩虽敬陪末座,但只要专心用功一年可以读通。天才就是天才!
1899年秋天,罗振玉聘请日人田冈佐代治为助教。王国维向田冈先生学习英文,至1900年七八月学社解散为止,已学到第三读本,之后又买读本自修。他从田冈先生的文集中看到引用哲学家康德与叔本华的文字,很想深入研究,可惜还是有文字隔阂,尚无法读二氏之书。我猜,王国维除了英文功课之外,应该曾趁机向田冈先生请教过哲学问题。这是他对哲学产生兴趣的开端吧?
狩野直喜的回忆可为旁证,他说明治34年(1901)左右,他在上海留学,友人藤田丰八告诉他,在东文学社有一位学生“头脑清晰,善读日文,英文亦巧,且对西洋哲学研究深感兴趣,其前途大可属望”。狩野叹当时中国青年大都想学政治学经济学,却罕见想学西洋哲学的。后来才知这学生就是王国维。可见那时候王国维的学业已经进入佳境,获得日本老师们称许。狩野则要到10年后(1910)去北京调查敦煌写本时才与王国维本人相识。
除了日、英文外,东文学社充分运用人才,数学课竟然由史学家暨文学博士藤田丰八任教。大概是日本高级知识分子都修过通识教育?或者他们在中学、高校时代也学习过数理?虽然文、理殊途,藤田先生教起来却不含糊,使用当时日本数学大师藤泽利喜太郎(1861-1933)的算术、代数两种课本[可能就是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出版的《算术教科书》(明治29年)、《算术小教科书》(全二册,明治 31年、32年)及《初等代数学教科书》(全二册,明治31年)等书,因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在上海设有特约贩卖所,故很容易取得这些课本],习题大约上万题,三、四个同学把每题都解,老师也每题校阅批改。所以王国维不只是钻研古典、文物的国学大师,他还具备基础的数学程度,故日后去日本留学主修的竟然是数学,自日本回国后还翻译了藤泽利喜太郎的日本数学教育经典之作《算术条目及教授法》(二卷)。
留学日本
1901年岁次庚子,王国维25岁,得罗振玉资助,经藤田丰八老师建议与介绍,2月9日从上海出发前往日本,进东京物理学校就读。(此处年月与诸家传记及年谱均不同,系依据陈鸿祥先生考证,他以王国维父亲王乃誉先生的日记为依据。详见《王国维传》第三章P56-61)
当时日本私立学校设立算学科者,最著名的就是东京物理学校,“算学一科,机关最备”,学校自行出版学术月刊杂志,刊登高深之译文或自撰论文(据李迪著《中国现代数学的先驱──周达》)。
若能在这个学校里深造个三五年,继续攻读数学及物理学,王国维有可能成为第一位近现代中国数、理学大师!做个年份比较:他到日本留学那年(1901),数学大师华罗庚(1910-1985)、陈省身(1911-2004)还没出生。北京大学要到1912年才有数学系、1913年才有物理系。中国第一位数学博士胡明复,1917年才取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博士李复几,1907年才取得德国波恩大学博士学位。
可惜学业之路有意外发展。他在《三十自序》中提到,到日本以后:“昼习英文,夜至物理学校习数学,留东京四五月而病作,遂以是夏归国。”得的是脚气病,是一种由于缺乏维生素B1而导致心血管系统和周围神经损害的疾病,症状是心律失常、心功能衰竭、四肢麻木、疼痛、无力、肌肉萎缩、腱反射减弱或消失。王国维的身体一直不健朗,早在1989年就因得了俗称“鹤膝风”的病,一种退化性关节炎,几乎不能站立,只好回乡疗病。这次病痛也颇类似,身心折磨,只好辍学回国,于1901年6月26日返抵上海。
眼尖的读者或许会纳闷,既然主修数学不是应该白天上数学课,而利用夜间研读英文吗?为何反过来,物理学校变成夜间部?各家传记都没有提到这点。这是因为物理学校前身东京物理学讲习所创立时就是一所夜间学校,此后一直以夜间部为主体。自1886年起,东京物理学校与东京文会(“仏文”即法兰西文)设立的东京语学校共享校舍。这间校舍原本系东京法律学校所有,借给东京文会,教室于白天由东京语学校使用,夜间由东京物理学校使用。1889年11月,物理学校把文会校舍购入,直到1923年4月才实施日夜间部之二部制。要到1938年,日间部才成为物理学校主体(依据东京理科大学年表)。至于“昼习英文”是自修或是在哪上课,仍有待考证。我推测应是自修。
脚气病是辍学最大因素,其实就课业来说,王国维学几何也学得很痛苦,大概是短短研修两年的初等数学和日本大专程度相比毕竟有差距吧。查不出东京物理学校数学系当时教什么,但是当时日本公立大学数学系(算学科)“三年毕业,开设微积分、平面及立体解析几何、初等算学杂论、星学和最小二乘法、理论物理学初步、理论物理学演习、算学演习、函数论、代数曲线论、高等微分方程式论、整数论、代数学、力学、物理实验、高等几何学、椭圆函数论、变分法、高等解析杂论等”(李迪著《中国现代数学的先驱──周达》)。推测王国维要上的课程大概也是这些。
或许,他内心深处更想研究文史哲相关的学问。但是,我觉得学习代数、几何,是一种数理逻辑的训练,讲究数字与图像的推理,解数学题的过程就是分析、演绎、比较与归纳的过程,这对于日后作学问尤其是考证、考古等文史学术工作绝对有帮助,而传统中国文人几乎没有这种现代数理训练的经验。他日后在学术方面的成就,多多少少亦得益于当年的数学课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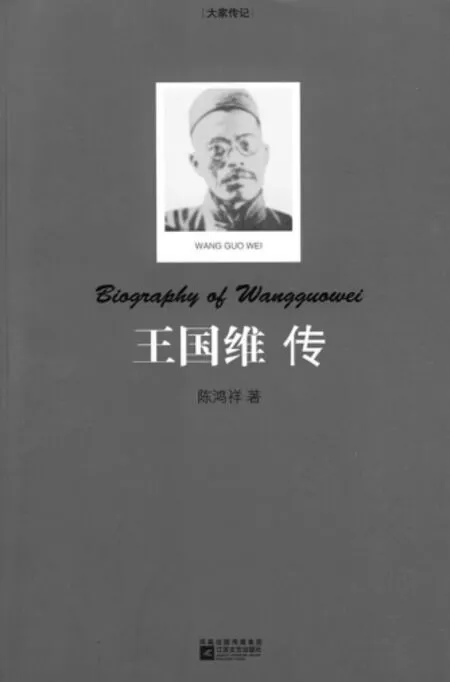
《王国维传》陈鸿祥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1月版,28.00元
依据陈鸿祥先生考证,1902年5月3日王国维又从上海启程往日本,5月5日抵长崎,5月 7日抵神户,6月12日回国,期间仅1个多月。此行系罗振玉委派他以南洋公学日文科执事身分,赴日聘请“译手”以编译开办新式学堂所需的教科书(《王国维传》P61)。看行程,此行去了关西,而且既然到了神户港,可能目的地就是大阪、京都等地。但是王国维留学东京,从未去过关西,并且当时京都大学的文科大学尚未成立,内藤湖南、狩野直喜、富冈谦藏等汉学家教授还没上任,不知道他要透过什么关系人脉去找译手?或许还是要靠罗振玉给他任务指示及名单吧?
而王国维病体尚未痊愈就再度出国,也未免太拼命。王乃誉1902年10月15日(阴历九月十四日)日记:“接静初八禀,言近身体瘦弱,为系漫病,已医治非能骤愈,颇为悬念。”可见这病拖了将近一年半,仍让父亲很担心,显示复原程度还不是很理想。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