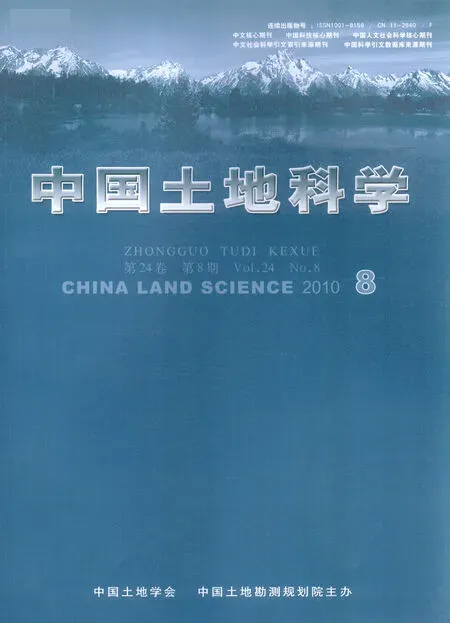股份合作是获取矿业用地的基本途径
2010-02-16康纪田
康纪田
(湖南娄底行政学院,湖南娄底417000)
股份合作是获取矿业用地的基本途径
康纪田
(湖南娄底行政学院,湖南娄底417000)
研究目的:求证获取矿业用地的基本途径。研究方法: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逻辑归纳法。研究结果:矿业用地制度缺失。学者们提出了获取矿业用地的许多途径,但都不适合保护土地权人的利益。征收土地后出让取得,缺乏启动征收的前提;按照国外经验承租获地,有损于弱势的土地权人;清朝末期矿业用地的“股份合作”是应当继承的基本途径。研究结论:十七届三中全会的政策创新为股份合作开辟了道路,股份合作的综合性收益是制度变迁的动力。
土地管理;矿业用地;土地流转;股份合作
到目前为止,《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中都没有关于矿业用地的规定,有学者提出,修法时应当明确把土地的征收、承租、入股等方式作为矿业用地的获取途径[1]。笔者认为获取矿业用地的基本途径应是“股份合作”。
1 征收方式的矿业用地存在不可逾越的制度障碍
中国85%以上矿业用地在农村,如果农村矿业用地由国家征收再出让,就存在两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一是法律制度障碍。《土地管理法》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必须在集体土地上进行建设的,由国家征收后依法申请使用”。按照这一规定,在农村设立矿山企业所需土地,应先由国家将集体土地征收后通过出让获取。但是,《宪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均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才能依法定程序和权限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农村矿业开发属于商业性经济利益,强制征收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二是出让程序障碍。矿业开发的非公益性决定了矿业用地不能通过划拨而只能按出让程序获取,所以市场化的出让程序不适用矿业用地优先原则。这种出让,对于矿山企业成交缺乏公平的机会,因为其他竞争者明知矿产资源属地的不动产性,不可能搬到其他地方去开采,正是其他竞争者投机竞价的动力。最终因为市场交易成本阻碍矿业用地的获得。
有的学者为了绕过征收方式在制度和程序上的障碍,提出矿业权优先于甚至对抗于原土地所有权而由国家征收土地[2]。殊不知,土地所有权、承包经营权与矿产权都属于物权,按照《物权法》关于物权地位平等的基本原则,不存在有“特权”的物权。而且,强制征收土地会导致集体及农民的土地产权残缺。因此,非因公共利益,国家不能运用征收手段,以免违背物权人意愿和损害物权人利益。
2 以承租方式获取矿业用地不适合中国
有学者认为,租赁是国际通行的一种矿业用地取得方式,是出租人把土地交给矿业权人(承租人)使用,矿业权人支付租金,并在租赁关系终止时将所使用的土地返还给出租人的行为[3]。国外的租赁方式有几种类型,一是以美国为主的分离式租赁。美国的矿产开采准入证就是“采矿租约”,因为矿产资源依附于土地并做为土地的组成部分而统一为权利的客体,要获取矿产权就只需获取土地权。因此,为矿而租地是由美国的资源体制所决定的。二是以澳大利亚为主的利用式租赁。澳大利亚各州矿产与土地分别成为权利的客体,矿业用地以承租为主。《西澳大利亚采矿》第19条规定,根据申请,公共事业部部长可授予他决定的采矿租地;第28条规定,经许可授权可在特定采矿租用的土地进入或停留;第29条至第39条规定,采矿租用地的持有人必须承担各项义务,事先向土地权人通知所要行使的权利及支付约定的土地租金等。三是以法国为主的地役式租赁。《法国矿业法》第71条规定,经批准,矿山开采者可占有必需的场地;矿地使用一年以上或使用完后不能恢复的,土地所有人可要求对方购买。第72条规定,占有和通过土地的地役权为土地主人及其权利所有人。法律标明这种用地方式为地役权,但依批准“占有”场地是为了发挥地面的多项用途,规定“购买”,这些是地役权所不能产生的结果。典型的地役权只是某一特定用途,因此这种用地方式实质上还属于承租方式。
国外矿业用地模式中,澳大利亚的“利用式”承租用地比较接近中国的矿业与土地机制,广西平果铝业公司已率先试行。但是,根据中国土地的稀缺程度、农民对土地的依附程度以及中国土地的历史发展状况等,国外的承租方式并不适用,尤其承租式的矿业用地有利于矿山企业,却损害了弱势的土地权人。一是土地的物权被债权取代。《物权法》强调物权性承包经营权而否认其债权性合同交易,就是为了保障农民的预期收益。然而,矿业用地承租属于典型的民事合同行为。合同的谈判、订立和执行成本往往由土地权人承担,而且土地权人因信息不对称的弱势地位将剩余权的好处让与了承租人。二是土地权人丧失了应有的财产性收入。土地货币化而不是资本化,导致土地权人不能分享土地的增值收益和转用收益,而这些收益被矿山企业独享。三是外部性成本增加。先前确定价格的承租,很难包括土地复垦的影子价格。而且,土地权人与土地利用相分离,无法控制使用者对土地的破坏,也不能制止矿山企业对土地的过度利用,最终由土地权人承担土地因使用后无法恢复的损失。正因如此,国务院2006年明令禁止“以租代征”,即禁止矿山企业为了收益而损害土地权人的承租行为。
3 矿业用地应当继承清朝末期的股份合作制
清朝末期为了制造船炮而重视矿业发展,于1907年颁布了《大清矿务章程》(以下简称《章程》),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比较完整的矿业法[4]。其中的矿业用地首选“股份合作”的制度设置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章程》对“地权”与“以地作股”都设专章规定,其中对“股份”作了明晰的界定:出资采矿的一方,不论是国内与国外的矿商出资,都称为“银股”;国内政府出资开采的称“官银股”;土地权人“以地作股与矿商合办者”,土地主所占的股称为“地股”;政府的土地参股称“官地股”。《章程》第15款规定,“矿地,除业主自开得兼有地权矿权两项外,其他矿商只有开采矿产之权,不能兼有地权”。法律对银股权的限制性规定,是为了维护封建土地制度。
矿业用地首选股份合作制。按照《章程》第14款规定,尽量以土地作为股份出资,如果土地权人不愿以地入股,政府按相当价值购买土地,由政府做为“官地股”,如业主不愿出售土地,可查询原委斟酌办理,按《章程》第18款的规定,“凡矿商开采所需之地,无论官地民地,如业主不愿以地作股可议作租用”。矿业用地被迫启用承租方式,说明矿业用地中的入股、政府购买、承租等方式不是并列式的,而是递进式的。
适用平等自愿原则获取矿业用地。法律将入股作为获地的基本制度,只有当业主不愿意时才最后选择承租制。《章程》第14款关于“矿商不得丝毫抑勒强迫致拂情”的限制性规定,是约束银股权人以及政府不能有丝毫违背土地主人意愿的行为。《章程》还强调了协商并要求订立合同,在《章程》第17款规定,“酌量情形,自与矿商妥,立合同”;第38款规定,所订合同“查核存案,倘有业主不谙订合同、租约,得禀明矿务委员会助其妥办”,即对不会订合同或租约的,政府安排专人予以帮助。
土地入股分红方式体现了“合作”性质。关于矿业经营的分红比例,在《章程》第18款规定,四分之一归土地主,四分之一报效国家,矿商得一半。《章程》第21款规定,矿山企业的事务,都由银股权人经营和管理;“如有亏耗,专归矿商承认”,土地主不承担亏损,也不得分红;但“地股之业户,得随时查考该矿商出入款目帐簿”。《章程》关于分红的规定,强调了地股权人在企业的身份,属于组织成员的“业户”;明确了地股权人在企业的管理地位,可随时干预矿里的财务;法定了企业类型,属于地权人与矿权人“合办”性质。
这些规定中的“地股”、“业户”及其“合办”等与现在股份制中的股民不同的是,土地股权人参与了管理并被称为“业户”,即目前“股份合作制”中的“成员权”。所以,清朝矿业用地制度应当是现代股份合作制的雏形,其基本规则对今天仍有利用价值。经查证,《章程》是在洋务运动后受资本主义影响,由两广总督张之洞派人向西方矿业发达国家学习并结合本国实践的结果。尽管《章程》未实施,但为民国矿业法打好了基础。
4 政策创新为矿业用地继承股份合作制开辟了道路
“股份合作”是1985年在中央1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的十项政策》中首次提出的。但是,20世纪80年代曲解了股份合作的实质,混淆了与合伙制、联营制和股份制的区别。对此,农业部于1990年下发了关于农村股份合作的规章,规范了农业股份合作。此后股份合作制虽然遍及全国,但是试点经验及理论研究都局限于农村土地间的单一结合,没有向农村土地与产业方面拓展。
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在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外,经批准占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非公益性项目,允许农民依法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开发经营并保障农民合法权益。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个政策有三方面重大突破:非公益性建设可以依法直接使用集体土地;允许农民直接参与建设项目的开发经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平等进入市场。打破了国家垄断建设用地市场的格局,从根本上将农民应有的权利返还给了他们,为农村矿业用地实行股份合作提供了政策依据:农地承包产权的完整性和农民参与开发的直接性,是“股份合作”的基本内容;开放集体土地建设经营性项目是“股份合作”企业设立的前提;统一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为实行“股份合作”而拆除了经营性建设使用集体土地的障碍。
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首次将“股份合作”与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等并列作为农村土地的流转形式,为矿业用地实行股份制开辟了道路。这些流转形式中,转包与互换不能改变土地用途,只能适用于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内部流转;出租和转让经依法批准可以改变用途,实现由承包经营地转换为农村建设用地,但不是农民参与开发经营项目的直接结合;股份合作形式的土地流转,既可以依法改变土地用途,又可实现农民参与开发经营的目标。
以股份合作形式获取土地所设立的矿山企业,不仅实现矿产与土地间的资源产权合作,还实现了矿产权人与土地使用权人间的成员合作。“入股是出资财产形态的变化,本来是物权,现在却变成了股权”[5]。但是,设置土地“入股”矿山企业制度时,必须走出两个误区。一是股份合作混同于股份制,有的学者将“土地股份合作制与土地股份制一并论述,因为两者在实践中较难区分”[6]。实质上,股份合作是成员和资本的双重合作,股份制是资本的联合。二是突破土地股份合作的局限。农村土地功能相同的“叠加型”股份合作,是单一的土地股份合作,矿业用地的股份合作是土地转用途后的功能“互补型”股份合作。土地与矿产属于异质性资源产权的合作,其特点不在资本要素而在于资源功能,属于异质资源“互补型”的资源配置,这就与功能“叠加型”资源配置的土地股份合作有根本区别。资源功能合作的区别说明股份合作形式的多元性,矿地股份合作与土地股份合作已并列存在。
5 农村矿业用地遴选股份合作属诱致性制度变迁
有学者认为,农村土地股份合作模式是来自基层农民实践的一场诱致性制度变迁[7]。农村土地入股后可能的规模收益、土地增值收益、规避风险和损失收益等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引发了自下而上的土地股份合作运动。然而,对于矿业用地股份合作,除了土地股份合作的可能收益外还有更为诱人的收益。
一是土地转用收益。土地股份合作并没有改变土地用途,土地本身的价值在入股前后没有变化。土地与矿产的“互补型”资源合作,因土地用途改变而能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促使土地增值,获得级差地租。但资源功能互补型合作的潜在收益不是来自级差地租,而是股份合作制度使潜在的收益得已实现才表现为级差地租。因此,农地产权人能够在多大程度分享农地流转引起的增值,是由产权制度特别是农地权利的流转制度决定的。
二是负外部性内部化收益。矿业开发中以其他途径获取土地,土地承包权主体与土地利用相脱离,在土地的破坏、土地环境污染和土地复垦等方面造成损害,让土地承包人意外地承担损害的成本。股份合作是负外部性内部化的有效方式,土地权利人与土地利用继续结合,土地承包权人仍是土地利用者,在企业决策中能通过其享有的剩余控制权尽可能地避免或减少对土地的损害,并修补损害后果,以保护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三是企业替代市场的收益。矿业开发中以其他途径获取土地,企业与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谈判、交易、执行成本都比较高。当矿业用地采用股份合作时,土地交易将市场行为转化为企业内部行为。在企业内部,市场交易被企业的指令代替。“企业存在的原因可以说是为了避免每天在市场里进行所有的交易”[8]。减少的交易成本置换为企业的净收益。
6 立法建议
应尽快构建矿业用地的系列制度,在《矿业管理法》中设专章规定“矿业用地”,对矿业用地的途径、市场准入、土地权人的利益、矿地保护以及矿地复垦等作出规定;《土地管理法》应将矿业用地与矿业立法的规定相衔接,对矿业用地的规划、耕地保护、转用途审批、农村土地市场及政府部门监督职能等作出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要与物权法、矿业法、土地法相衔接,从明晰土地所有者与承包人关系、保护农村土地、规范土地流转和稳定农民收益等方面对矿业用地作出规定。总之,矿业用地涉及多元的执法主体和复杂的制度环境,要充分考虑立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以防止立法的冲突和空白现象。
(References):
[1]骆云中,许坚,谢德体.我国现行矿业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资源科学,2004,(3):116-122.
[2]胡健,吴文浩.油气资源矿权与土地产权的冲突[J].资源科学,2007,(5):8-15.
[3]袭燕燕.关于我国矿业用地取得制度构建的思考[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04,(12):25-28.
[4]傅英.中国矿业法制史[M].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2001:26.
[5]江平.物权法的理想与现实[J].社会科学论坛,2007,(11):1-6.
[6]唐浩,曾福生.农村股份合作制产生的原因解析[J].中国土地科学,2008,22(10):46.
[7]林冬生.成渝实验区背景下的农村土地股份合作模式研究[J].农村经济,2008,(5):39-40.
[8]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63.
Stock Cooperation is a Basic Pattern for Acquiring Mining Land
KANG Ji-tian
(Loudi Administration Academy of Hunan Province,Loudi 417000,China)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basic pattern for acquiring mining land.Methods employed include the combination of normative research and empirical study and logic induction.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due to the deficiency of institutions on mining land,the patterns for acquiring mining land proposed by scholars can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protecting the interests of land owner.For example:(1)the proposed pattern of conveying the mining land after the land is required from the farmers cannot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land requisition policy;(2)the pattern of acquiring land following with foreign experiences is harmful to weak land owners.Thus,the principle of“stock cooperation”established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could be the basic pattern to be inherited.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policy innovation in the 3rd Plenum of the 17th CPC China Central Committee has opened the way for stock cooperation,and the comprehensive benefit of the stock cooperation pattern is the driving force of such institutional change.
land administration;mining land;land transfer;stock cooperation
F301.2
A
1001-8158(2010)08-0027-04
2009-04-23
2010-06-04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矿业管理立法及其相关问题研究”阶段成果(0804031B)。
康纪田(1957-),男,湖南新化人,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矿产资源法。E-mail:kjt809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