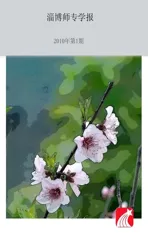关于晚年郭沫若佚作中“大寨”的几点看法
2010-02-16逯艳
逯 艳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一、一首《重到晋祠》,诗性的自觉追随
在郭沫若晚年佚作中首次涉及到“大寨”的是刊登在1966年1月1日《光明日报》第四版《大寨行》组诗中的首篇《重到晋祠》:“康公左手书奇字,照眼红墙绕晋祠。周伯低头迎旧识,铁人举手索新词。欲流荇菜情难已,惊见睡莲花未衰。悬翁山头松失翠,顿憎旱魃费鞭笞。”[1]1966年的中国,被一股令人窒息的政治氛围所笼罩。当许多知名文人在文坛销声匿迹时,作为中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却是幸运的。京城全国三大报刊之一的《光明日报》(另两家是《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在元旦这一天的文艺副刊“东风”专版上以醒目的位置刊登了郭沫若的组诗《大寨行》,标题以手迹套红印制,相当引人注意。组诗共十八首,压轴为《颂大寨》。1977年3月“由作者重新校对过”而出版的《沫若诗词选》选入其中九首,并在《大寨行》标题下加了一则小序:“1965年11月19日,曾往山西参观农村社教工作。归途于12月7日,参观大寨。先后成诗十六首,辑为《大寨行》。”[2](P2)《光明日报》作为京城权威性报刊之一,在元旦之际高调刊发大型组诗《大寨行》,毫无疑问看重的是组诗的政治宣传作用。但是,为什么要把歌颂的对象放在大寨上?拿大寨大张旗鼓地说事儿,说服力和权威性的支点在哪?这也许关涉到政治走向。
1964年之后的数年,毛泽东提出了“新三面红旗”——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为全国各界树立楷模。在口号提出的1965年,“学大寨”更多强调的是艰苦斗争、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但不能否认其中孕育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胚芽。这个从1936年就大快人心地说“党决定了,我就照办,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3](P80)的“传声筒”,尽职尽责地“喇叭”到1966年。除了政局的强力之外,或许也是一种久成的习惯性的思维套路,由此深谙政治玄机的郭沫若不可能意识不到领袖决定执行口号背后的动机和意图。所以在参观了设在太原的大寨展览馆之后,郭沫若为之题词匾额并当场作诗:“大寨人人是愚公,神州争效此雄风。百年基业防旱涝,千年山头待柏松。勤奋力将全国学,虚心赢得普天同。为防自满寻差距,决不因循步自封。”在亲自接触到大寨劳动人民时,握着老农布满茧子的手,看着他们饱经风霜的脸,登上虎头山人造小平原,郭沫若写出了山西之行的一首五古:“全国学大寨,大寨学全国。人是千里人,乐以天下乐。狼窝变良田,凶岁夺大熟。红旗毛泽东,红遍天一角。”诗中直接指涉到领袖毛泽东的名字,满溢着政治宣传色彩。1966年刊发的《大寨行》组诗“不但因内中不少篇幅揄扬大寨,即就切和时宜而言,也是最为醒俗的”。[4](P12)但是,问题就出现在一九八四年出版的《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五卷,既未说明小序中的“先后成诗十六首之误”,又“将《大寨行》中未收入《沫若诗词选》的八首诗附录如下。”所以,读者误认为组诗共计十七首,其中为首的七律《重到晋祠》被删除了。这首诗之所以被逐出全集之外,目前的说法是因为诗的首联“康公左手书奇字”中涉及到了“康公”,也就是当时中国政坛知名人物康生。我们权且不论86岁沉疴在体的郭沫若在“重新校阅”这组作品中如何的勉为其难,但是以因为“康公左手书奇字”碰触了政治禁忌为理由加以删除的官方辞令,着实牵强。无论什么原因,《重到晋祠》终究是被删除在全集之外。我们认为,进不了史册的往往是有悖官方意志的。所以,《重到晋祠》也许是一个契机,一个了解郭沫若置身政治之外的、摒弃了为政治服务的负重,遵循诗性的勃发,表达自我隐蔽情愫的心灵探照灯。
《重到晋祠》,这首游记诗未标明创作日期,据推测(冯锡刚)是在参观社教工作之后归途中所做,时间当是12月中旬。这首诗是《大寨行》这组纯粹政治宣传诗组中不直接涉及政治的诗篇,也是十八首诗中最有诗意的一首。颔联“迎旧识”表明作者是继1959年初游晋祠之后第二次来访,当年诗人曾吟咏着“隋槐周柏矜高古”,今日重游却有“欲流荇菜情难已”之语。“欲流荇菜”语出《诗经·关雎》“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是脍炙人口的爱情诗篇,这也是此诗最出彩的地方。在那个谈情色变的年代,年过七旬的郭沫若却能雅致地语出这样的“禁忌”,不管是不是借助典故来障眼,多少都能流露出郭沫若作为诗人的直率和坦然。尾联对照初游晋祠时的“悬翁山溪碧玉盘,飞梁荇菜布葱荇”不难体会诗人为生存环境的恶化而倍感焦虑和担忧。虽然被删除在全集之外,这首诗作为晚年郭沫若所有诗作中数量罕至的不直接干预政治、讴歌时政的作品对后人研究郭沫若晚年那种故地重游突觉物是人非,为知识分子精神空间日渐狭促、生存环境岌岌可危的生存状态的隐忧,具有一定的指引意义。
二、灰撒虎头山,精神的自我回归
于立群在《化悲痛为力量》中记载了郭沫若在病重期间近似遗嘱性质的话:
四、五月间,沫若的病情几次恶化。
他要孩子们把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华主席关怀他的照片好好珍藏起来。
他把我和孩子们叫到身边,要我们记下他的话:“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
“对党的关怀,我特别感谢,我在悔恨自己为党工作的太少了。”
“我死后,不要保留骨灰。打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5](P10)
在举行了高规格的追悼大会之后,郭沫若的骨灰在1978年6月下旬洒到了大寨的层层梯田之中。从此,虎头山上耸立起一座“郭沫若同志”纪念碑。有意思的是,五年之后原先的大寨领班陈永贵在北京逝世后作出了魂归故里的后事安排,于是虎头山出现了文坛泰斗的纪念碑和全国劳模墓碑并峙相映的奇特的人文景观。
郭沫若一生和农民相涉甚少,为什么选择大寨作为自己的归宿?单单是对中央政策的至死维护和遵守吗?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郭沫若作此决定,不会没有原因。目前最容易为人接受的观点是他视为知己的周恩来首先决定把骨灰撒在大寨,他之所以效仿可以看成是对故友的一种独特的追随。我认为这除了单纯的追随之外,或许还要加上一份深幽的忏悔。何出此言?1974年江青借“批林批孔”之名行“批周公”之实,威逼郭沫若写揭发周恩来的材料。但是郭沫若最终用庄严的沉默维护了老战友周恩来,不过有一点“晚节不保”意味的事件却发生在了1976年。5月12日他作了《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到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胜。
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巨挥手,团结大进军。[6](P12)
早在1972年,周恩来主持工作,批判极左思潮,各项工作出现转机。不久便遭到毛主席的否定,继而为江青一伙污蔑为“右倾回潮”。1975年11月下旬开始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使病重的周恩来忧心如焚。1976年3月间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党内那个走资派把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资派扶上台”,这样赤裸攻击的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矛头所向——周恩来、邓小平。郭沫若以“走资派、邓小平”入诗,表达的却是“奋螳臂”、“妄图倒退”、“复辟罪行”!九泉下的周恩来要是知道老友语出此种“颂歌”,会是一种怎样复杂的心情?当这位故友的骨灰养肥了大寨之后的两年,郭沫若做出也要灰撒虎头山的决定时,再联想到这位知己生前是如何关照自己和家人,会有一种怎样的内疚和忏悔的心情?所以,与其说郭沫若灰撒虎头山的决定是说给家人的遗嘱,不如当成是给总理的一种致歉。
“文革”结束后不久,1976年12月下旬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重申了周恩来生前总结的“三原则”(政治挂帅、思想有限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同时夹杂着不少“新经验”。次年2月,郭沫若做了《望海潮·农业学大寨》。当然,假如用这种形式为了重遵周恩来当年的政治决策,来表达自己对友人的忏悔和歉意也应该足够了。郭沫若作为知识分子的精英代表何以要在临终对代表农村和农民的“大寨”表现出如此重视?所以其执意将骨灰撒在大寨,单靠追随知己这一说恐怕有一点单薄。我们认为应该还有一点缘由,这就涉及到精神世界的自我回归上。
早在年轻时,郭沫若创作《凤凰涅槃》时就曾经有诗情来了难以自抑,便抱着大地亲吻的常人难以接受和理解之举。可见,他是一个感性的诗人。1921年他在杭州游览,于雷峰塔下面看见一位锄地的老农,在描绘“他那慈和的眼光”、“健康的黄脸”、“斑白的须髯”之后,出人意料地用以下诗句作结:
我想去跪在他的面前,
叫他一声“我的爹”!
把他脚上的黄泥舔个干净。[7](P433)
时隔44年后的1965年,当郭沫若系统地参观了大寨展览馆之后,当他握着老农布满茧子的手,看着他们饱经风霜的脸,登上虎头山眺望一块块人造小平原时,那种想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冲动和大呼要“把他脚上的黄泥舔个干净”,或许是碍于久经人生的战场已经可以控制情感表达尺度的岁月沉淀,或许是碍于自己当时所处的时局和身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一句“大寨人人是愚公”,使“愚公”成为貌似许多难以直诉情感的浓缩产物。带着这个观点再看1976年的《望海潮·农业学大寨》:
四凶粉碎,春回大地,凯歌声入云端。天样红旗,迎风招展,虎头山上蹁跹。谈笑拓田园,使昆仑俯首,渤海生烟。大寨之花,神州各县,遍地燃。
农业衣食攸关,轻工业原料多赖支援。积累资金,繁荣经济,重工基础牢坚,主导愈开展,无限螺旋。正幸东风力饱,快马再加鞭。[8]
这也是一首不折不扣的政治宣传诗,谈不上什么诗意。农业之所以“衣食攸关”,因为它关系到“轻工业原料”和“重工业基础”,经济要繁荣就要“积累资金”,“基础愈牢坚”“主导”才能“愈开展”。摒除迎合政治那些粉饰之语,结合郭沫若人生不同阶段曾经对农民的感情,这首诗貌似是可以浮现出诗人对 “大寨人人是愚公”那种愚公精神的礼赞,对“谈笑拓田园”的创造精神的敬畏。
笔者截取了以上1925年、1965年、1976年三个时间段的三首诗作,通过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郭沫若在情感表达上经历了由自在的狂放恣意到不忘迎合政治的谨小慎微到最后的政治口号淹没了真实情感的“三级跳”。当然,这一个“三级跳”在今天看来更多的是倒退的“三级跳”。但是,对于当时处于特定环境和时局的郭沫若而言或许也是无奈之举。其中的缘由,作为不是当事人的我们当然不可能主观的去下结论。透过这一个“三级跳”,我们或许可以了解到当时的知识分子精神空间的狭促和寒碜。也许郭沫若有未卜先知的特异功能,早在二十年代就预示到自己最终只有在离开人世之后才能重回自由的、肆意的,我口说我话、我手写我心的本我吧。所以执意将骨灰撒在大寨不独是看重“大寨”的政治意义,实则应该是由“大寨”勾起了郭沫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由自在舒唱的“凤凰”到粉饰政治的“喇叭”那种扭曲蜕变的哀思,灰撒虎头山、魂归大寨,或许可以重回那个自在妄为、恣意洒脱的精神世界。
[1] 郭沫若.大寨行[N].光明日报,1966-01-01.
[2] [4][7]冯锡刚.郭沫若的晚年岁月[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3] 季国平.毛泽东与郭沫若[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5] 新华月报资料室.悼念郭老[C].北京:三联书店,1979.
[6] 郭沫若.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A].诗刊[C].1976,(6).
[8] 郭沫若.望海潮·农业学大寨[N].光明日报,1977-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