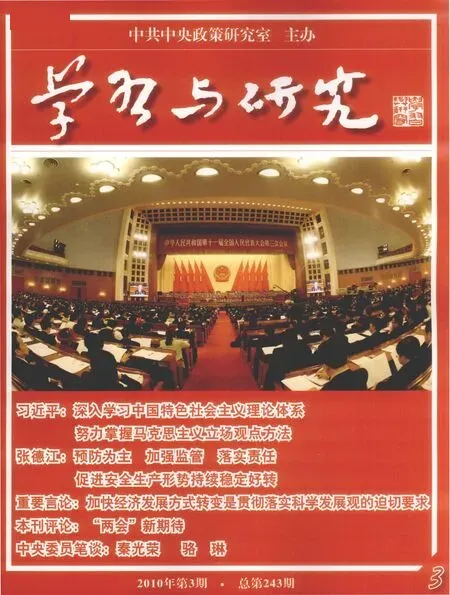论吕留良的思想文化成就及其历史地位
2010-02-16吴光
吴光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5)
论吕留良的思想文化成就及其历史地位
吴光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5)
吕留良坎坷奇落的一生,造成了他的特立独行及其思想文化成就。吕氏博学多才,在文史哲、天文历算、医学和出版等各方面都有深湛的造诣。他的思想成就,主要表现为主张“夷夏之防”及“尊朱辟王”论。
明末清初;思想文化;吕留良
晚村先生吕留良(1629—1683)是我国明末清初一位颇有影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时文评选家。他独立特行、博学多才,在哲学、文学、史学、医学、天文、历算、书法、出版等方面均有深湛造诣,可谓三教九流,了然于胸,但用力最勤、影响最卓者还是在儒家政治思想的阐发以及时文评选方面。由于清代雍正、乾隆二朝皇帝的著名文字狱案对吕留良及其家族的残酷迫害,更成就了吕留良的反清声望。那么在满汉一家、中华一统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吕留良的思想成就与历史贡献呢?在此,我想贡献一得之见,求教于方家。
一、吕留良的出身背景与生平事迹
吕留良生活的时代,是明清交替、天崩地解的时代。吕留良的一生,经历了南方抗清武装斗争从举义到失败的全过程。这是形成吕留良强烈反清民族主义性格的时代背景。
吕留良是今桐乡市崇福镇人。崇福镇在明代属于崇德县,在清代属于石门县。民国恢复崇德县名。1958年合并桐乡、崇德二县为桐乡县,今改称桐乡市。
崇德吕氏原籍河南开封。宋室南渡后,有吕继祖者任崇德县尉,无法北归,于是定居崇德,成为崇德吕氏的始祖。明代中叶以后,崇德吕氏成为名门望族。吕留良的高祖吕淇,曾任明朝锦衣卫武略将军。淇子吕相,嘉靖年间任江西鄱阳县主簿。相子吕熯,即吕留良的祖父,号心源,少年持重,颇得淮庄王朱佑揆的赏识。朝廷赐封淮庄王之女为南城郡主,封吕熯为“淮府仪宾”,即王爷的驸马。吕熯夫妇在吕相死后,得到皇帝特许,辞去宗室爵禄,回到崇德老家奉养老母,开了郡主随仪宾回籍侍养的先例。吕熯为纪念皇帝的恩典,特意在祖居兴建“许归堂”。吕熯长子元学,为万历年间太平府繁昌县(今属安徽)知县。元学的正室郭氏育有四子:大良、茂良、愿良、瞿良。晚年又娶侧室杨氏。崇祯元年(1628),元学去世,吕留良为遗腹子。出生后因寡母杨氏无力照料,于是将他交给同父异母的三兄吕愿良夫妇抚育。吕留良从小聪慧过人,敬重三兄愿良,视为“严父”。
吕愿良(1602-1651),比吕留良大27岁,字季臣,颇有文誉。参与了南明政权的抗清斗争,曾为抗清名将史可法的军前赞画推官。其子吕宣忠(1625-1647)字谅功,也与吕愿良、留良一起积极参与了抗清斗争。他们“散万金之家结客”,召募义勇,出没湖山,窜伏草林,备尝艰苦。顺治三年(1646)三月,宣忠与太湖义师领袖吴昜配合作战,大败清兵。五月,吴昜兵败被害,宣忠削发为僧,不久被人告发,于顺治四年(1647)三月以“号众为叛”的罪名被清兵杀害于杭州,年仅二十三岁。临刑,吕留良冒险相送,宣忠视死如归,谈笑如常,无一语谈及家事。吕愿良、吕宣忠父子的忠孝节义对吕留良民族气节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影响。
这便是吕留良出身的时代与家庭背景。
吕留良的一生,主要做了三件事,即早年抗清,中年评选时文、尊朱辟王,晚年义不仕清,坚守民族气节。
吕留良又名光轮,字用晦,又字庄生,号晚村,别号耻斋老人。生于明崇祯二年(1629),卒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他是吕元学的遗腹子,呱呱落地,便为未曾见面的父亲披麻戴孝。三岁时,又为三嫂戴孝。孤子无依,他被过继给叔父吕元启,便为叔父披麻戴孝。十三岁时,生母病故,又为之服丧三年,诚如他自己所说,“自始生至十五岁,未曾脱衰绖……人生孤苦,无以如此”,这也促成了他自强自立的坚强性格。
吕留良从小跟着三兄读书习文,颇有天赋。崇祯十四年(1641),崇德名士孙爽集合十余人在崇德禅院(西寺)结征书社。他看到吕留良的文章,惊为畏友。于是欣然邀请留良入社。其侄宣忠抗清失败被杀害以后,吕愿良、留良身心受到沉重打击。顺治五年(1648),吕留良结束在山中的流亡生活,移居东庄,遁迹田园。不久,三兄、四兄先后去世,挚友孙爽病逝,吕留良郁然寡欢,发出了“生才少壮成孤影,哭向乾坤剩两眸”的沉痛哀号。
顺治十年(1653),吕留良为免遭仇家陷害,改名光轮,参加了清廷的科举考试,以第二名成绩取得诸生(秀才)功名。在这前后,他结识了崇德名士陆雯若、吴之振、吴尔尧等,很快成为知交。十二年(1655)冬,吕留良应邀与陆雯若至江苏吴门为科举考试评选范文,编成《五科程墨》,这是吕留良从事时文评选的开始。他在崇德组织了新的文社,名流会聚,百里之内,号称“人伦奥区”,“诗简文卷,流布宇内,人谓自复社以来未有其盛”(吕葆中《行略》)直到顺治十七年(1660)由于清廷严禁文人结社,吕留良才中断时文评选。他选辑自作八股文三十篇,题名《惭书》印行。
顺治十六年(1659),吕留良结识了余姚名士黄宗炎,次年经宗炎介绍,又结识了黄宗羲和名医高旦中。黄氏兄弟早年曾经出没于抗清阵营,并抱定不仕清廷之志,其气节学问,受人尊崇,吕留良与他们交往,深受教益。顺治十八年(1661),吕留良在三兄茂良的督责下,谢绝社事和选事,设馆于城西家园之梅花阁,专教子侄辈读书,并订出了制度严格的《梅花阁斋规》。
康熙二年(1663),吕留良邀请黄宗羲执教于梅花阁。此后,吕、黄与高旦中、吴之振、吴尔尧等经常在水生草堂雅集,诗文唱和,一起选编《宋诗钞》。这时的黄宗羲,刚刚在余姚山中、蓝水溪畔完成他脍炙人口的名著《明夷待访录》,其中强烈的反清民族主义和批判君主专制的民主启蒙思想给予吕留良以极大的心灵震撼,促使吕留良的民族意识重新激活,他开始对自己的“失脚”往事痛切反省,决意离开科场,归隐南村。这从他在康熙四年(1665)所作的《耦耕》诗中可见一斑。其诗满含悔恨地写道:
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
雅集图中衣帽改,党人碑里姓名非。
苟全始信谈何易,饿死今知事最微。
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素裹头归。
这是吕留良与清廷划清界限的宣言书。次年,当即将进行府学例考时,吕留良向学官陈执斋出示了他的《耦耕》诗,并陈说了自己误入科场的苦衷。这位学官始而非常惊讶,继而十分理解、敬佩吕留良的志节,于是对吕留良深作一揖,说:“此真古人所难,但恨向日知君未识君耳。”(吕葆中《行略》)吕留良断然放弃“诸生”(秀才)头衔,宣告了他不仕清廷、蔑视科举的心志。这是他一生的重大转折。
吕留良离开科场之后,由于学术主张、立身旨趣的歧异,遂与黄宗羲分道扬镳。在此后的岁月里,吕留良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提囊行医,四处出游。吕留良在与名医高旦中的密切交往中,学到了高氏的医技,四出为人治病,声名鹊起。后来因求医者络绎不绝,吕留良不堪应酬,才在朋友的规劝下,于康熙十二年(1673)停止行医。二是重操选政,评选时文。吕留良十余年前初事选文,无非是为了谋生和填补精神空虚。康熙五年后重操旧业,却是借以阐发他那夷夏大防的政治见解和尊朱反王的学术主张。吕留良评选刻行的时文选集很多,均以“天盖楼”名义发售,风行海内。但他不甘心被人视为仅仅是一位“时文选家”而埋没其民族思想,乃于康熙十二年结束了选文生涯。其三则是致力于表彰朱熹之学。吕留良创立了南阳讲习所,设馆授徒,并请桐乡理学家张履祥来家讲学,一面刻印程朱遗书。吕留良尊朱辟王,不遗余力,在清初学术界反响强烈,当时有“朱子以后一人”的崇高赞誉。
吕留良晚年“身益隐,名益高”,但初衷不改。康熙十七年(1778),清廷开博学宏词科,浙江地方当局将他列入荐举名单中,吕留良以死相拒,总算躲过了一场招安风波,坚持了民族气节。康熙十九年(1689),嘉兴知府又要以“隐逸”荐举吕留良出山做官,吕留良嗤之以鼻,索性剃发入山,在吴兴(今湖州)的埭溪妙山上结庐而居,命名“风雨庵”,做了一个“不参宗门,不讲义录,有妻有子,吃酒吃肉”的和尚。但他并没有“四大皆空”,而是忧国忧民,心情郁闷,体力日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仅五十五岁的吕留良便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然而,在那个专制高压的时代,士子们的反清民族主义和反君主专制的启蒙思想很难免祸。就在吕留良死后四十余年,即雍正十年(1732),由于震惊全国的曾静反清案的牵连,吕留良及其长子吕葆中、学生严鸿逵被开棺戮尸,幼子毅中惨遭杀害,整个家族流徒黑龙江宁古塔为奴,从子吕新平避吴为舵工,侄孙吕懿谋也避祸浙东。曾静案使吕氏家族几乎灭门,但也成就了这位反清斗士的极高声望。辛亥革命胜利以后,吕留良的千古冤案得以平反昭雪,他被作为先贤入祀于西湖的“三贤祠”。
二、吕留良的思想文化成就概述
吕留良博学多才,涉猎甚广,在哲学、文学、艺术、宗教、出版、医学、教育诸领域均有精深造诣。连“难得糊涂”的清代名士郑板桥也对吕留良推崇备至,赞扬吕留良“自批点文章而外,尚有二十四绝技,如医学、女工、驰射,皆精妙绝伦”(郑板桥《板桥先生印册》)。吕留良一生著述甚丰,计有《吕晚村文集》八卷,《续集》四卷,附录《行略》一卷,《东庄吟稿》七卷,《惭书》一卷。他评点的时文集有《天盖楼偶评》六卷、《程墨观略》十九卷、《江西五家稿》五卷等十馀种,汇集他的时文评语的有《天盖楼四书语录》四十六卷、《四书讲义》四十三卷、《吕子评语正编》四十二卷等多种。他还和吴之振、吴自牧、黄宗羲等合作选编了《宋诗钞》九十五卷,和张履祥合选《四书语类钞》三十八卷等。后人刻印他的遗墨有《晚村先生家训》四卷。此外见于清代《禁书总目》的还有《易经详解》、《诗经详解》、《吕氏医贯评》等三十三种。今存各种版本的诗文集有《吕晚村文集》八卷、《续集》四卷、《东庄吟稿》七卷、《何求老人诗稿》七卷等近十种,评点时文集十余种,时文评语汇集三种,另有《宋诗钞》及家训、家书、医书、经解等若干种。尚存著作不下百卷,可惜未经整理成为全集,当寄望于桐乡学子。(徐正先生对推动吕留良研究和整理《吕留良诗文选》贡献卓著,应予表彰)。
综观吕留良在思想文化上的成就,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成就
吕留良的思想成就,主要表现为“夷夏之防”与“尊朱辟王”两大方面:
(1)“夷夏之防”论
吕留良思想中最突出、最有影响并且因而受祸的思想主张,是他的“夷夏之防”论。其论包含了三大思想主张:一是“尊王攘夷”论,二是“复井田、复封建”论,三是民族气节论。以下分别论析之。
吕留良多次以《春秋》经传所载齐桓公“尊王攘夷”事迹以及《论语》中孔子对管仲的赞语为例,表达了他强烈的反清爱国思想。他说:“孔子何以许管仲不死公子纠而事桓公甚至美为仁者?是实一部《春秋》之大义也。君臣之义固重,而更有大于此者。所谓大于此者何耶?以其攘夷狄救中国于被发左衽也。”在他看来,儒家经典中所讲的君臣伦理固然很重要,但还有更重要的伦理,那就是“夷夏之防”。这明显是针对由“夷狄”入主“中国”的清王朝政权的。
我们还可以从清朝雍正皇帝用以声讨吕留良“罪行”的谕旨及其亲撰的《大义觉迷录》中看到吕留良“反清复明”思想的激烈程度。
清代王先谦编的《东华录》雍正七年卷记载了曾静案的来龙去脉。卷内所载曾静的供词说:“(静)因应试州城,得见吕留良评选时文,内有妄论‘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语,遂被蛊惑,随张熙至浙江吕留良家访求书籍。吕留良之子吕毅中授以伊父所著诗文,内皆愤懑激烈之词,益加倾信。又往访吕留良之徒严鸿奎与鸿奎之徒沈在宽等,往来投契,因致沈溺其说,妄生异心。”案发后,雍正帝在谕旨中大骂吕留良“悍戾凶顽,好乱乐祸”、“追思明代,深怨本朝”、“以博学鸿词荐则诡云必死,以山林隐逸荐则剃发为僧”、“号为明之遗民……著邪书,立逆说,丧心病狂,肆无忌惮……所著书文以及日记等类……皆世人耳目未经,意想所未到者。……何其悖乱之甚乎!”这样的“大逆不道”,在清朝统治者看来自然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了,所以雍正帝恨极了吕留良,不仅对吕氏父子剖棺戮尸,而且要株连其家族。不仅如此,雍正帝还因吕留良而株连浙江一省之人,竟称:“朕向来谓浙省风俗浇漓,人怀不逞,如汪景祺、查嗣庭之流,皆以谤讪悖逆,自伏其罪,皆吕留良之遗害也。甚至民间氓庶,亦喜造言生事。……此皆吕留良一人为之倡导于前,是以举乡从风而靡。甚至地方官吏,怵其声势之嚣凌,党徒之众盛,皆须加意周旋。……此其陷溺人心、浊乱世俗,害有不可胜言者。”
吕留良的“复井田、复封建”论是与其“夷夏之防”论合为一体的。诚如曾静供词所说,他是“得见吕留良评选时文内有妄论‘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语”才被“蛊惑”,乃致“沉溺其说,妄生异心”的。那么,吕留良的“井田、封建”理论主张是怎样的?我们大致可从流传至今的由吕留良评选而由其门人编定的《四书讲义》可知一二。
在《四书讲义》中,吕留良指出,三代以上的“圣人”建立井田、封建等制度,是为天下人民着想,而“不曾有一事一法从自己富贵及子孙世业上起一点永远占定、怕人夺取之心”,然而秦汉以后的许多制度都是出于君主“自私自利”的“本心”,而后世儒者“议礼”,又“都只去迎合人主这一点(自私自利)心事”,他们“所谓‘封建、井田不可复’”的意见,都只是“从他不仁之心揣拟”出来的“谬论”。他说:“自秦并天下以后,以自私自利之心,行自私自利之政。历代因之。后儒商商量量,只从他私利心上要装折出不忍人之政来,如何装折得好?不得已反说井田、封建、学校、选举之必不可复,此正叔孙通希世度务之学。”他认为,战国至秦汉时期之所以废除了封建、井田而推行郡县制,建立起大一统的君主制是形势所迫,却并不合理,恰恰成为乱源而非致治之道。他说:“封建、井田之废,势也,非理也;乱也,非治也。后世君相因循苟且,以养成其私利之心,故不能复反三代。孔、孟、程、朱之所以忧而必争者正为此耳。”又说:“君臣以义合。……但志不同,道不行,便可去。只为后世封建废为郡县,天下统于一君,遂但有进退而无去就。嬴秦无道,创为尊君卑臣之礼。上下相隔悬绝,并进退亦制于君而无所逃。而千古君臣之义为之一变。”
吕留良的这番议论,表明他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主张立君为民、执政为民,另一方面,也说明他的复封建、复井田的主张,并非复古主义,而是托古改制,甚至透露了他批判君主专制、主张君臣平等的思想倾向。这一思想倾向,与黄宗羲在《留书》中的“复封建”论及《明夷待访录》中的“君害”论思想如出一辙,可以说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性质。黄宗羲《留书》第一篇题名《文质》,是谈“夷夏之别”与文明进化问题的,其第二篇题名《封建》,则是严厉批判秦“废封建之罪”而主张“复封建”的。吕留良在封建、井田、君臣之义等问题上的见解,显然是受梨洲思想影响的结果。
极力主张严“夷夏之防”、主张恢复井田制和封建制的吕留良,理所当然地非常重视保持民族气节和士子节义的问题。这方面,他痛悔自己也曾“失脚”(即在顺治十年参加了清廷的科举考试并取得秀才身份),所以决然放弃了秀才身份,从此与科场决裂并拒绝当局举荐,誓不仕清。这是他恪守民族气节的表现。而自中年悔悟之后,吕留良始终重视出处气节,把恪守民族气节放在第一位,认为严守“夷夏之防”比谨守“君臣之义”还要重要。他以管仲可以不死于君臣之义为例,指出:“君臣之义,域中第一事,人伦之至大。……看‘微管仲’句,一部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之伦,为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论节义大小,不是重功名也。”又说:“圣贤于出处去就、辞受取予上不肯苟且通融一分,不是他不识权变,只为经天纬地事业,都在这些子上做,毫厘差不得耳。”可见,吕留良所耿耿于怀、反复致意者,就在于他严守“夷夏之防”的民族气节。他以此为标准去衡量历史人物品格的高下,对坚守民族大节、誓不降敌的爱国志士文天祥等人推崇备至,写下了“请看宝祐四年榜,六百一人何麟麟!宇宙只愁文陆谢(指文天祥、陆秀夫、谢枋得),其余五甲皆灰尘”的诗句,而对一些投降“夷狄”、甘为异族臣子的名儒则十分鄙视。如他在与友人书中批评背宋事元的名儒郝经、虞集、吴澄,许衡等人说:“以《春秋》视数子,曾不如其无有耳,岂数子之著作讲学犹有未工哉?亦或失其义也。”在吕留良看来,郝、虞、吴、许等人并非没有学问,但却丧失了民族大义,所以不屑一顾。
(2)“尊朱辟王”论
众所周知,吕留良学术思想的最大特点是尊朱辟王。但在当时,“尊朱辟王”的思潮并非始于吕留良,而是清初思想界的一股风气,或者说是一种时尚,就连清初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也是“尊朱辟王”的。当然,清统治集团的“尊朱辟王”与民间反清学者的“尊朱辟王”在思想动机、尊辟重点与目的方面大异其趣,不应混为一谈。尤其是在清初,“辟王”之风颇为盛行,很多人都把明朝亡国的责任,归咎于王学(或“王学某流”)的“清谈”学风上。例如,顾炎武就说过:“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显然,顾炎武是把“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责任归之于高谈“明心见性之空言”的“清谈”的,而他所谴责的“今日之清谈”,主要是指“王伯安(阳明)之良知是也”。当时另一位与顾炎武齐名的学术大师王夫之也把明末的政治腐败归咎于王学。他批评说:“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为刑戮之民、为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理事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
其实不仅是顾、王,明清之际不少学者都发出过类似“王学亡国”的批评声音。如颜元、李塨、朱之瑜、张履祥、陆世仪、陆陇其等大率如此,吕留良堪称“其尤著者”也。
吕留良对于自己的“尊朱”立场毫不隐讳,但对别人说他“攻王”则有所保留。他说:
某平生无他识。自初读书即笃信朱子之说,至于今老而病且将死矣,终不敢有毫发之疑,真所谓宾宾然守一先生之言者也。……某尊朱则有之,攻王则未也。凡天下辨道理,阐绝学,而有一不合于朱子者,则不惜辞而辟之耳。盖不独一王学也,王其尤著者耳。……今日老兄与某得以尊信孔子之道者由孟子也,而得尊信孟子以及孔子者由朱子也。……夫陈献章、王守仁皆朱子之罪人,孔子之贼也。……盖某之辟王说也,正以其畔朱子也。
这里所谓“尊朱则有之,攻王则未也”,说明他对“攻王”的指责有所忌惮。但既称王守仁是“朱子之罪人,孔子之贼”,则不是“攻王”又是什么?所以,说吕留良“尊朱辟王”或“尊朱攻王”、“尊朱反王”都不为过。问题是吕氏所尊、所攻、所辟、所反的内容如何?
从现存吕氏《四书讲义》和《吕晚村文集》等著作看,吕留良所谓“尊朱”,所尊者并不是朱子学中那一套十分复杂的义理之学,而主要是尊崇朱子学中有关纲常名教、存理灭欲、崇仁义黜功利的政治思想,并借尊朱而发挥其严“夷夏之防”、重“出处去就”的反清思想。其所谓辟王,所辟者也并非是阳明学所论“心即理”以及“知行合一”、“致良知”的一套道德形上学,而是重在攻击王阳明及其后学“蔽于禅学”、“为佛作伥”以及“生心害政”、“祸乱生民”的“弊害”。他在《答吴雨若(晴岩)书》中说:
朱子平生所严辟者三焉:一金溪(陆九渊),一永康(陈亮),一眉州(苏轼)也。金溪之为姚江(王守仁)不必言。若永康之功利,眉州之权衡,兼挟文章之奇,尤足以痼学士大夫之疾,故朱子辟之甚厉。
又在《复高汇旃书》中说:
道之不明也,几五百年矣。正(德)、嘉(靖)以来,邪说横流,生心害政,至于陆沉,此生民祸乱之原,非仅争儒林之门户也。……金溪之谬,得朱子之辞辟,是非已定,特后人未之思而读耳。若姚江之非,窃佛氏机锋作用之绪余,乘吾道无人,任其惑乱。夷考其生平,恣肆阴谲,不可究诘,比之子静之八字着脚,又不可同年而语矣。而所谓朱子之徒,如平仲(许衡)、幼清(吴澄),辱身枉己,而犹然以道自任,天下不以为非。此义不明,使德祐以迄洪武,其间诸儒失足不少。……故姚江之罪烈于金溪,而紫阳之学自吴、许以下已失其传,不足为法。今日辟邪,当先正姚江之非。而欲正姚江之非,当先得紫阳之是。……今示学者似当从出处去就、辞受交接处画定界限,扎定脚跟,而后讲致知、主敬工夫,乃足破良知之黠术,穷陆派之狐禅。
由此可见,吕留良的“尊朱”,首先尊的是朱熹对“异端邪说”的批判精神,是朱学重视在“出处去就、辞受交接”上站稳立场、坚守气节的人格精神,然后才是朱学讲究“格物致知”、“穷理主敬”的一套理论。而所谓“辟王”,攻击的重点乃在于从陆九渊到王阳明“窃佛氏机锋作用之绪余”以惑乱人心、害政祸民的“良知之黠术”与“陆派之狐禅”。所以在吕留良那里,“朱学明道”、“王学祸国”的思想倾向是很明显的。正因如此,吕留良特别重视朱熹推崇的“四书”,而把大量精力花在评点八股时文、阐述“四书”的微言大义上面,最后形成了一部洋洋数十万字的《四书讲义》。《四书讲义》的基本内容,是阐述其崇仁义、黜功利;严“夷夏之防”、重“出处去就”;效法三代,恢复井田、封建、学校、选举制度;君臣、朋友皆“以义合,不合则离”的政治思想,甚至主张“君臣义绝,则可为寇仇”,这不能不说是惊世骇俗的观点,表明吕留良是一位既有激烈反清民族思想、又有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并具近代民主启蒙思想萌芽的思想家。
2.文学成就
吕留良在散文方面的成就并不很大,但却是一位刚劲深沉的民族主义诗人。他的诗歌创作是和他的民族思想、反清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吕留良诗中最突出的主题是华夷之辨、故国之思与气节之颂。
(1)揭露清统治者的暴行,反映人民疾苦。
吕留良目睹清兵南下血腥屠杀抗清军民的暴行,写下了不少悲壮激烈、动人心魄的诗篇,如《乱后过嘉兴》写道:“兹地三年别,浑如未识时。路穿台榭础,井汲髑髅泥。”“粉黛青苔里,亲朋白骨中。新来邻里别,只说破城功。”揭露了清军攻陷嘉兴,大肆屠杀百姓,把繁华的嘉兴城夷为废墟的罪行。又如五言古诗《田家女》就直接描写农民的苦难生活:“田家惜人工,踏车用寡女。但愁苗叶干,岂问荒机杼!天风割骨寒,尚有皮肉阻。刀剑攒肌肠,智勇不堪煮。”诗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寡妇,她不得不荒废纺纱织布的家务活而到田野踏水车救旱苗,是多么强烈的比较!
面对国恨家仇,吕留良写下了不少令人感怆的诗篇,如《手录从子谅功遗稿》、《友人示以季臣兄唱和稿感赋》等,都是抒写作者深沉的故国之思和丧亲之痛的。在抗清失败、遁迹田园之时,他悲愤莫名,“残身直与天心迕,踯躅吞声不敢言”,“孤臣剩有汍澜泪,卧听悲笳时一倾”,写出了抗清失败之士的共同心情。但他仍然希望有所作为,故在《剑客行》等诗篇中借干将、莫邪和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来表达他复仇的愿望。即使到了晚年,吕留良病魔缠身,仍念念不忘反清斗争。在他逝世前一年(康熙二十一年),他在《十九日暮同诸子登天宁寺塔》一诗中写道:“昔闻弱水东,楼船或过之,中有珠贝宫,可接扶桑枝。古仙既羽化,传法儿童痴。洞府日零落,鱼龙将安依?”诗中表现了诗人吕留良对郑成功死后台湾抗清斗争的关切。
(2)坚守民族大义,寄托故国之思
吕留良重视民族大义,他的诗多写国家民族兴亡的大事,充满着深厚的民族感情和炽烈的爱国精神。他的诗歌中留下了诸如“那堪荆棘铜驼影,又哭冬青杜宇魏”,“甲申以后山河尽,留得江南几句诗”的悲壮、深沉、令人感怆的名句。其《次韵和黄九烟民部思古堂》诗写道:
跃马谁当据要津,骑牛何处会真人?
闭门甲子书亡国,阖户丁男坐不臣。
黥卒敢争莝豆食,髡钳未许漆涂身。
纵然不死冰霜下,到底难回漠北春。
这首诗,集中地反映了诗人不甘失败,不臣新朝的心情与志气。这种表现故国之思的诗篇在吕留良诗集中俯拾皆是。如《季臣兄卧病欲荒园》、《东庄闲居贻孙子度念恭兄》、《甲辰一日》等都是直抒胸臆,其中“十年台榭浑春梦,三月风花抵太平。夹道晓星怀北阙,横江雨夜想南京”、“廿年不检戊申历,一日刚占甲子经”等诗句就是作者故国之思的表露。
(3)歌颂抗清志士,嘲讽屈节仕清者
吕留良在诗集中热烈赞颂那些为国捐躯或坚持民族大义,终身不仕清朝的志士仁人。他写下了七律《九日书感》以歌颂坚持抗清英勇就义的民族英雄张苍水:
九日常年话一樽,今年覆斝卧支门。
亭隅独下西台泪,岛畔谁招东郭魂。
无复鹤猿依正统,独凭蛟蜑记华元。
腐儒自有伤心处,不共宾僚说旧恩。
诗中用南宋遗民谢翱在严子陵钓台哭祭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典故,抒发他对民族英雄张苍水壮烈牺牲的敬仰和哀悼之情。又如《同德冰晦木孟举自牧官村看菊》一诗,把坚持民族气节的黄宗羲等友人喻为“名花”,并称“人生良友真如此,一日须看一百回”,可见诗人的爱憎所在。而对那些屈节仕清的士大夫则给以有力鞭挞,嘲讽他们“入拜朱门旁,出为蓬户豪”、“朝结王侯袜,暮接公府鞭”的丑态,可谓入木三分。
吕留良与黄宗羲、吴之振一起,构筑了清初浙派诗人的宗宋风格。他们相与编辑选刻了《宋诗钞》九十五卷,从而在诗坛掀起了一股宗宋诗的潮流。在艺术实践上,吕留良诗重个性,反模拟,主宋调,反唐体。其诗学苏黄、学杨范、转益多师,不主一家,沉郁坚苍而又不掩其奇崛孤傲的个性,不愧为清初浙派诗的开山健将。
3.出版成就
吕留良曾长期从事评选八股时文。起初是当时明末文人结社的风气使然,其次是岐路傍徨而失足下海。自康熙五年之后,吕留良再选时文,却旨在反清复明、尊朱辟王,具有强烈的经世色彩。吕留良利用富裕的家庭条件,雇请刻工,以“天盖楼”署名,在家开局刻书。经他评选印行的各种时文本子,通过南京书商发售全国。康熙间,“天盖楼本子风行海内,远而且久”(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二《时文选家》)。吕留良评选时文十八年,选刻时文有《大题观略》、《小题观略》、《程墨观略》、《东皋续选》、《归震川稿》、《黄陶庵稿》等多达20余种。又在张履祥等人协同下,陆续印行《中庸辑略》、《延平问答》、《近思录》等朱熹遗著多种。康熙十二年(1673),吕留良专程奔赴南京,结识藏书家黄虞稷、十竹斋主人胡正言等人,将其所刻时文等著作运往南京承恩寺书坊发售,发行量不断增加。吕留良因此成为名噪一时的出版家,影响了一时文风。
吕留良的思想文化成就是多方面的,这里仅举其大者而已。他在医学、书法艺术方面的成就也是值得称道的。
三、吕留良的历史地位平议
吕留良在中国政治史和思想文化史上,是以反清名士、尊朱理学家和宗宋诗人著称于世的,也是明末清初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教育家。
作为一名思想家,吕留良的以“夷夏之防”为中心的反清民族主义思想,既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又有历史的局限性。其合理性的一面在于,清王朝的建立,是一个文明发展阶段比较后进的游牧民族(满族)以武力征服了比较先进的农耕民族(汉族)的结果,在其征服的过程中对汉族反抗者进行了野蛮、血腥的镇压与屠杀,如震惊江南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强迫汉人剃发易服,就是典型的民族征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这样一个残暴的异族政权展开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是势在必行、天经地义的,既有爱国主义的崇高精神,又有捍卫先进文明的内在动因。吕留良以儒家经典的《春秋》大义——严“夷夏之防”为武器开展反清斗争,在本质上并不只是要恢复明王朝的腐朽统治,而在于反抗野蛮、血腥的民族征服,在于力图捍卫当时比较先进的汉族文明,以“救中国于被发左衽”为使命。吕留良思想中的严“夷夏之防”,虽有民族斗争的色彩,但主要是思想文化斗争,其思想中的“复井田、封建”,则有反对君主专制、提倡以民为本、主张君臣平等的民主启蒙思想成分,其主张民族大义、大节的思想,对于当代激励爱国主义、维护民族尊严的教育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奠定了吕留良作为一名进步思想家的历史地位,我们应当给予积极的评价。
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吕留良的反清民族主义思想是有历史局限性的。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是由多民族交流、融合而成的民族大家庭,在这个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中,免不了会有民族之间的征服、征战与冲突,但更多的是交流与融合,而且往往是大冲突之后的大融合,昔日所谓“夷狄”今日已经是中华之民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个民族大动荡、大融合的时期,当时所谓“五胡十六国”如今都是华夏民族、归属中国版图了。所谓严“夷夏之防”的理论,作为反抗外来民族压迫的思想武器是有其积极作用的,但是它也可能成为阻挠与反对民族交流、融合的借口,甚至可能成为推行民族沙文主义和压迫少数民族的工具。事实上,如果真的不折不扣地严守“夷夏之防”的话,那么就没有多民族之间的融合与交流了,甚至连中华民族本身都不存在了。在这点上,雍正皇帝的《大义觉迷录》中有一句话倒是对的,他说:“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俨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事实上,吕留良的“夷夏之防”论,在当时就未免失之于极端,他看不到从顺治到康熙时期清统治者政策的变化,看不到民族矛盾趋于缓和以及社会由乱到治的进步,而是一味坚持他的“夷夏”论与“遗民”观,所以他容不得丝毫的妥协精神与务实精神,把对清政权的妥协与务实面对一概视为投降变节、视为追求功利。乃至连黄宗羲这样曾经是战场同志、文坛好友的前朝遗民都难以久与,最后分道扬镳、绝情断交,竟至在与人书中谩骂黄宗羲“议论乖角,心术锲薄”、“学骂之巨子”,又把黄宗羲比作哭于歧途的杨朱,自比为落魄逃亡而誓报大仇的伍员。这对于一个始终坚守遗民气节、不仕新朝的儒家知识分子而言显然是不公平的。
在如何分析评价吕留良的民族思想和学术成就问题上,过去有的学术论著的评析是有相当程度的主观性、片面性的。如撰著《吕留良年谱》的包赉称颂吕留良为“民族思想运动的代表者”、“实践民族运动者”;钱穆先生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吕晚村”一节,称吕留良“明夷夏之大防,以脱斯民于狐貉”、“晚村言出处事业,一以(程朱之)理判”,这都有片面抬高吕氏反清民族思想及其尊朱倾向之嫌。究其原因,大概有三:一是由于包、钱二人的著书时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处于中华民族深受“外夷”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害,故特别需要“明夷夏之辨”以号召国民抗击外族侵略,吕留良的“夷夏之防”论正可成为抗击外族侵略的有力思想武器;二是包、钱二氏同为民国之顺民,而民国之建立,不仅是推翻帝制、而且是推翻满清“夷族”统治的结果,所以为被满清统治者“剖棺戮尸”的吕留良平反昭雪是理所当然的;三是包、钱二氏在学术倾向上基本属于尊朱一派,所以他们特别称颂吕氏的学术成就甚至有拔高之嫌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笔者认为,在当今时代,我们来研究吕留良的思想与学术,尤其是评价他的“夷夏”论、“遗民”观和民族气节问题,应该采取平实态度,既不应贬低吕留良反抗民族压迫、主张“复封建”、重节义等民本、启蒙思想的历史价值,也不应站在狭隘民族主义立场上,或站在明朝遗民、民国顺民的立场上去过高评价其“夷夏”论的积极意义,而应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
作为一名尊朱反王的理学家,吕留良的“尊朱辟王”思想,就其积极意义而言,其坚守民族气节和坚持士子人格精神与学术批评精神的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因为在暴政面前,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尤其可贵。吕留良不屈服于清朝统治者的淫威,坚持士子“当从出处去就、辞受交接处画定界限,扎定脚跟,而后讲致知、主敬工夫”。他在反思严酷的社会现实时尖锐地指出:“今日之所以无人,以士无志也。”因此孜孜努力于知识界正义人格的培养,尤其注意激发人们的民族气节,把民族气节视为“立身之根本”、“域中第一事”。这确实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同时,吕留良所辟的王学,是指那种空谈心性、与禅学合流的空疏学风,这也是切中王学末流的时弊,应当予以正面评价的。
然而,吕留良的“尊朱”,未能洞察程朱理学在当时已走向教条化和思想僵化的弊端,尤其未能深刻认识八股时文与科举取士制度的积弊,而慨叹“欲使斯道复明,舍目前几个识字秀才无可与言者,而舍四子书之外,亦无可讲之学”,则未免有盲目“尊朱”之嫌了。而其“辟王”,则一概抹杀了王阳明心学在当时有批判程朱理学、促成晚明思想解放的积极作用一面,抹杀了王学“良知”理论的道德教化作用,甚至将明朝亡国之祸归咎于王学,宣扬“王学祸国”论,则不仅是一种学术上的门户偏见,更是一种过分夸大学术文化对于社会治乱兴衰的作用而忽略政经制度作用与现实政治力量消长变化的“文化决定论”,是思想的误导。而这种思想的误导,在明清之际已经存在,而在民国时期有所强化,其流风所及,则影响至今而被当作“当然之理”。因此,很有重新审视的必要。笔者作此放论,无非是想在客观平实地评价历史人物及其思想学术的作用方面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罢了。
作为一名文学家,吕留良在诗歌创作方面是有很高成就的,其风格是“诗言志”、“诗言理”和“诗记史”相结合的写实主义诗风,并且力图摆脱教条主义的宗唐诗风而开创宗宋诗风,从而在清初诗坛起了开风气的作用。
作为一名教育家,吕留良并没有广受门徒,而是用他敏锐的眼光和犀利的笔锋,通过评点八股时文而为士子树楷模,开风气,从而影响了广大的士子学人,起到了一个社会教育家的作用。这种经世致用的精神是应当肯定的。但他以评选八股文为对象,迎合着士子通过科举考试出仕做官的心态,而对科举制度的弊端认识不足,而且这种八股时文的评选与当时(明清之际)出现的新古文运动是背道而驰的,这也暴露出吕留良的教育思想,并没有站在时代的最高处。
总之,吕留良是明清思想文化史和浙江思想文化史上一位杰出的反清斗士,文化奇才,思想文化成就值得大书特书,其历史地位应当充分肯定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注释:
(责任编辑 梁一群)
B249
A
1008-4479(2010)03-0106-09
2010-01-12
吴 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兼任浙江省儒学学会常务副会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