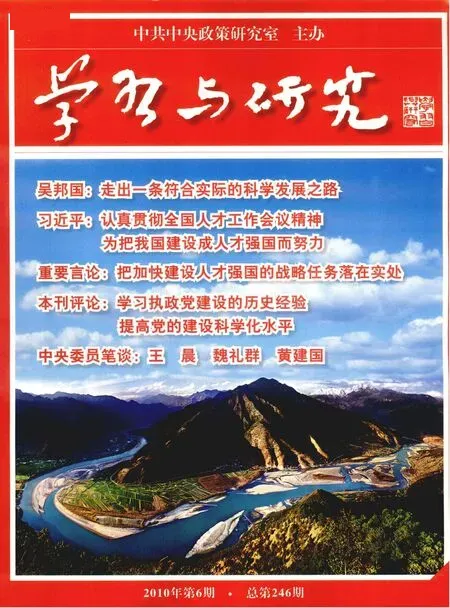浙东朱子学的链接——何基与朱熹、黄 榦的思想关联
2010-02-15高云萍
高云萍
(中国计量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何基(1188-1269),字子恭,金华人,学者称为北山先生,帝显德祐元年(1275年)加赐谥号“文定”,被称为金华北山学派的首庸、开创者,二十多岁时受父命与兄求学于朱熹女婿兼高足的黄榦,自此接受了理学思想。以后他隐居故里盘溪,对朝廷的任命均呈以辞牍,潜心研究朱熹遗书,探求其中义理蕴奥,以叙师友渊源、承述道统、传播朱学为己任,著作(其中《大学发挥》、《中庸发挥》、《大传发挥》、《易启蒙发挥》、《通书发挥》、《近思录发挥》等皆佚)主要是对师说的进一步发挥,现存《何北山遗集》四卷。通过《遗集》四卷、《宋元学案》及《宋元学案补遗》中《北山四先生学案》,可窥见何基思想的大致。
一、何基所处的历史环境及所负的思想使命
随着理学获解禁进而得到理宗的重视,向往理学者众多,使得士人人数空前,因而科举中第的机会日益减少,又科举所引导的并不能让人真正领略圣贤义理之真,如何基解释朱熹《斋居感兴诗》第十七首中所指的科举之弊,“每三年群天下之士为一大扰,所得者何益?而斲丧人心,败乱风俗,其害有不可胜言者。”[1](p.81)因此陈淳早就指岀:“故凡今之学者,如欲有志于圣贤之学,须是屏除举业一切新奇意见,放下世俗一切人我态度,脱然一意于此,”[2]何基就是弃早年从陈震所学举子业而一心于伊洛之学的;此时理学虽获朝廷承认,但“嘉定而后,阳崇之而阴摧之”[3](p.3153),朝廷的权力结构没什么改变,仍是权相专政,理学人士获显赫地位但并无决策的能力,只是朝堂的一种装饰,加之庙堂上“士大夫以讲道论学为梯,荣干进之媒,理学之坛有市心焉”[4](p.125),故而真正的理学人士已不像十一世纪那样热衷仕途,宁可回到理学中,加强自身道德修养的同时以引领社会文化导向。故何基在受教后归隐潜心朱学,力辞朝廷的任命。
他所处的思想环境,首先是直到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才弛解的长达七年之久的庆元党禁后,朱学思想已是“知之者希”,[1](p.96)需要大量的重振工作。就地域层面看,按包弼德考证指岀,在吕祖谦、朱熹等人死后,婺州曾经兴盛的新儒学渐入寂静,也亟待复苏,而复兴首先要完成的就是重述的任务。再就是朱门内,朱熹梦奠后的情状,黄榦的概括极是:
自先师梦奠以来,向日从游之士,识见之偏,义利之交战,而又自以无闻为耻,言论纷然,诳惑斯世;又有后生好怪之徒,敢于立言,无复忌惮,盖不待七十子尽没,而大义已乖矣。[3](p.2037)
面对朱熹去世后朱学的这种变异发展及理学“正学化”引出的欺世盗名的伪理学倾向,并要回应陆门的发展挑战,朱门亟待“强毅有立,趋死不顾利害之人,相与出力而维持之”[3](p.2037),要“维持”的就是朱熹建立的《四书》学理论体系,并将之继续传播。朱熹以深衣传付的黄榦所做的具体工作就是对这一使命的力践,有通释朱熹《四书》著作、诠释《礼书》的文本建设,生活中推广朱学所确认的礼仪、精心安排讲学组织的践履,因思想自身发展需要将朱熹思想向内省性功夫推进强调“主敬”的思想建设。他对弟子的教诲自然也不能失却此使命,何基就学时黄榦“首教以为学须先办得真心实地、刻苦功夫”,[1](p.84)真心实地”即为学心要诚、敬,“刻苦功夫”即要力下功夫以格物穷理,总体即强调居敬穷理,而居敬穷理恰是朱学的根本原则,“临别告之以但熟读《四书》,使胸次浃洽,道理自见”[1](p.84),即以《四书》为入门,因为通过《四书》的阅读可以使为学者具备圣传系统的价值标准与鉴别能力,正是朱熹强调的为学者入圣贤之门的必要阶梯,是“大本”。黄榦实际把“维持”朱学的任务传递给了何基。何基自此以担道为己任,兢兢研读,承续师说。
二、何基对师说的继承
首先,他严守黄榦临别的嘱托,精读《四书》,并参考《文集》、《语录》等精义对朱熹若干著作做了进一步解说,他以《发挥》为题的诸作品就足以证明。他的治学原则是“治经当谨守精玩,不必多起议论,有欲为后学言者,谨之又谨可也”,因而被定名为“北山之宗旨,熟读《四书》而已”,黄宗羲对他这一确守师说的解释恰到好处,“盖自嘉定以来,党禁既开,人各以朱子之学为进取之具,天乐浅而世好深,所就日下,而剽掠见闻以欺世盗名者,尤不足数。……然则,若人者,皆不熟读《四书》之故也。”[3](p.2727)熟读《四书》自此成为北山一派的家法。何基弟子王柏教金履祥读书要自《四书》始,对他早期著作《读论语管见》的评说更是足见此派“熟读”《四书》的含义及传承所在:
宝祐甲寅立冬日,兰溪金吉父来访,以《读论语管见》一编示余,观其立说,则曰:“凡有得于《集注》言意之外者,则书。”余窃惑焉。夫孟子之所谓自得,欲自然得于深造之余,而无强探力索之病,非谓脱落先儒之说、必有超然独立之见也。举世误认自得之意,纷纷新奇之论,为害不小。且《集注》之书,虽曰开示后学为甚明,其间包涵无穷之味,益玩而益深,求之于言意之内尚未能得其仿佛,而欲求于言意之外,可乎?此编尽有见处,正宜用力,奉以归之,不敢有隐,苟能俛焉,孳孳沉潜涵泳于《集注》之内,他日必有验余之言矣![5]
他们的熟读非泛泛读过,而是虚心研读原文,涵咏于“言意之内”,即朱熹要求的读书要字字考验,句句推详,使己意与圣贤意思泯然无间,不见彼此之隔,并非一心求超越。熟读《集注》,自然要“沉潜涵泳于《集注》之内”,深造玩味其中包含的开示后学的无穷义理,推眀演绎以反朱子之约,以求道,反对脱落先儒之说、追求新奇的力求牵强,正如金履祥对何基《发挥》的评价,“惟先生纂师言以发挥,剔众说之繁芜,以为朱子之言备矣!”[1](p.89)也是对当时“纷纷新奇之论,为害不小”的纠正,因而能够传绪不差,到了许谦,这种研读仍能够保持,对《四书》的崇奉更为严格,“学以圣人为准的,必得圣人之心,而后可学圣人之事。圣人之心,具在《四书》,而《四书》之义,备于朱子。顾其词约义广,安可以易心求之哉!”[6](p.4318-4319)研读《集注》以掌握朱熹穷其一生建立的《四书》学理论体系,求圣人之心,从而建立起圣传系统的权衡规则,以应万事,这应是北山学派被称为朱学嫡传的真正内涵所在了。
何基将这一恪守师传的研读精神贯彻到了其它理学书的发挥中,如《大传发挥》、《易启蒙发挥》、《通书发挥》、《近思录发挥》等,顾名思义,这些著作是对“致广大而尽精微”师说的阐释,更容易让人理解,对朱学思想起到了很好的传播作用,有的甚至是对一直就没有解说本的理学书的发挥,如《近思录》,“若文公、成公所辑周、程、张子之微言曰《近思录》者,宜为宋之一经,而顾未有为之解者,亦随文笺义为《近思录发挥》,未诠定而文定殁,”[5]虽然未完稿,但对从没有解说本的著作做尽量忠于原作精神的阐释,阐释者的恪守原则是很值得肯定的。
何基在研读时还用朱熹、吕祖谦点抹读书法点读《四书》,学生王柏也是如此,且点读朱熹著作更多,这些点读本很快得以刊布,“何氏(何基)所点《四书》今温州有板本,王氏(王柏)所带点《四书》及《通鉴纲目》传布四方”[7](p.290)。他们基于《四书》学理论体系的作品在当时是深得认可的,何基的“《大学》《中庸》《易大传》《启蒙》《通书》等五《发挥》刊行已久”[7](p291),程端蒙在《读书分年日程》中将之及王柏、金履祥的著作都列入参读书,应该是对何基一门对师说传述的认同了,且到了清代也是获得肯定的,“何、王、金、许之书皆不可不看,而文定所著《大学》《中庸》发挥、《启蒙发挥》、《通书》《近思录》发挥及文集尤要紧。”[8](p.113)
其次,黄榦非常强调持敬,认为持敬可以有诚、正、修、齐、治、平之效,能够外立规模、内尽精祥,是先师得统于二程的所在,学者存心于居敬、穷理、克己、存诚,是圣贤传道教人的宗旨。何基为学“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力学以致其知,躬行以践其实”[1](p.97),与黄榦强调的“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克己以灭其私,存诚以致其实”[3](p.2023)相较,前两句即黄榦的“居敬以立其本”,但多了立志的坚定,第三句与黄榦第二句基本一致,最后句中对义理的“实”,黄榦是“存诚以致”,何基则“躬行以践”,多了实践的强调。总体,在居敬穷理的共同关怀下,何基更表现岀对“道”的躬行。
躬行之初要有力行之志,他的立志源于对“耻”的破。何基一再申明士人要“知耻”,然后才能谈得上以师教授人,“廉耻一事在吾道中固非深奥,为士者最所当谨。岂有廉耻尚不知守而能明师教以淑人心乎?”[1](p.74)因为有些士人为利禄所惑而沽名钓誉,甚至“挟古人之似而争以谋利于辞受间”[1](p.73),即入圣门首先要端正态度,非为谋利而来,知的就是这个耻,这与朱熹曾经对学生的告谕无二致,
学者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真是无着力处。只如今人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须反复思量,究其病痛起处,勇猛奋跃,不复作此等人,一跃跃出,见得圣贤千言万语,都无一字不是实语,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积累工夫,迤逦向上去,大有事在,诸君勉旃,不是小事。[3](p.2923)
朱熹已注意到士人的俗念,“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作好人,”只是没有明确用“耻”来界定,点到要甩掉这些俗念立志为圣学,强调了志乃为学“着力处”的主要作用,这些都被何基很好的继承了。
何基对耻的“破”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立”志,立志于圣学,并且把立志放在为学的首要位置,认为“为学莫先于立志”[1](p.85)。这一方面是因为“圣门事业远难攀”[1](p.77),非有志于学者难有所成,另一方面是因为志在为学中的作用,“学者志不立,则学无其本,而教无所施尔。大抵人之气体固有强弱,而其勤怠则在于志之立不立。志茍立,则日进于精明,虽弱而必强;志不立,则日入于昏惰,虽强而亦弱。是故君子为学,必先立志。此志既立,则如木有质,如墙有基,而后雕杇之功可加矣。”[4](130)作为朱学弟子,他的确是把知耻立志当作大事来传承的。他要求立的志当如朱熹《远游》诗中所含的有纵横宇宙规模的大志,因规模不大则心志不坚,志立后就要“不问难易,不顾生死,鞠躬尽力,以必至为期”[1](p.99),以求实现。这就是他注重的“立志以定其本”。他对学生的传授也是如此,教王柏“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务之表,敬行乎事物之间”[3](p.2726),王柏又将之传于金履祥等弟子,到许谦,仍旧强调“为学之道先立志”(《读论语丛说》“雍也第六·冉求章”),可见,立志为学乃是北山一派首要澄清的入门规范。
他的注重立志定本,与黄榦的直接居敬立本比,更适合初始用功者,也更易操作,因立志比居敬更容易把握,或可以说立志是居敬的前奏,在志立工夫渐熟后,就需要居敬以持进而穷理了。何基一承秉黄榦而来特别强调“主敬”。他认为“自古圣贤惟一敬畏之心”[1](p.73),敬乃“入道门”[1](p.77)。继承了二程将“敬”为“主一无适”的训释,但对“主一”和“无适”的解释则显示了他的着力处,
主一者,指示所以持敬之要,若止曰整齐严肃,则难捉摸,惟曰主一,则用力之方昭然易见。然所谓主者,静固要一,动亦要一,朱子所谓“身在是则心在是,而无一息之离”,此静中之主一也。所谓“事在是则心在是,而无一念之离”,此动中之主一也。若“无适”二字则又是为“主一”两字再下注脚,谓如心在东而后移之西,又移之南之北,则是静不主一,他有所适而非敬矣。又如本是一事而复贰以二,又叁以三,则是动不主一,他有所适而非敬矣。主一自然无适,无适方为主一,此两语只是展转相解。只观程子“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敬”二语,敬之为敬,可得而持矣
不满于朱熹对“敬”的回答“不用解说,只整齐严肃便是”[9](p.189),认为如只是说整齐严肃,让人很难捉摸,也不同于朱熹“主一无适”的解释:“遇事临深履薄而为之,不敢轻,不敢慢,乃是‘主一无适’,”[9](p.444)强调小心畏谨,他基本同于真德秀的解释[3](p.2701),注重专一,但与之相比,何基的注解字里行间注重的是“用力之方”,如何做才是敬,重视可操作性,他的这一解说倾向流露出的是一种形而下的关怀。
到了王柏他们,对“主敬”,沿着何基着重可操作性的理解,直接由“持敬”的内敛延伸到了“肃容貌”的外敛,与吴澄的内敛更向内心诉求不同,践实了朱熹的“不用解说,只整齐严肃便是”,领会了朱熹敬要“正其衣冠,尊其瞻视”(朱熹《敬斋箴》)的训示,遵循了“足容必重,手容必恭”(同前)等一系列规矩,表现在了对外貌整齐严肃的要求。王柏平日“日用从事,夙兴见庙,治家严饬,闭阁清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见也”[3](p.2730),许谦将心静貌恭写进了《八华山学规》,“心静明理之本,貌恭进德之基。刚毅乃足自励,谦让可以集益。有善当与人共,有恶勿忌人攻。”[10](p.721)临死前,正衣冠而坐,门人提醒他视稍偏时,“先生更容而逝”[3](p.2757),可见他们对外貌整齐严肃的要求。许谦甚至有由“敬”向“静”的发展,实行静坐,《宋元学案》中载他一日静坐,门人入久才发现,恰似当年程门立雪再现,以此来涵养本原,晚年“尤以涵养本原为上,讲学之余,斋居凝然。”[3](p.2756)这种静坐与道佛枯槁寂灭的静坐自是不同,是儒家读书应事闲暇的静坐,心中有物,有主宰、操存,是在思索、体认义理,但与原初强调的侧重方法论相较,侧重在目的了,心静是为了明理,流露出心学迹象。
何基一生研读朱熹著作,是在“力学以致其知”,但并非没有“躬行以践”圣学。他对知行的认识是:“功夫真处在持操,外泽中干亦谩劳。独探圣言求实用,岂同末俗为名高?”[1](p.77)学不为求名,求实用,要内外合一,这正是朱熹“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9](p.134)的知行观,重视“躬行”道德实践的重要性,是儒者经世致用的基本体现。得君行道在当时政局中难以实行,但可以首先通过自己“躬行”道德,慢慢来利益群生,他的践履,王柏在其《行状》中就评价为充知于身而践行的:
无疾言,无遽色,无窘步,无叱喝声。不逆情,不逆诈。不伐善,不较利害。事父母尽其孝爱之道,婉容柔色以得其欢心;事兄长尽其和孺之乐,恭敬退让,曾无间言;处族姻,崇仁厚之风;交朋友尽忠告之责;御婢妾则宽而有制,见田夫野叟,必劳之有恩;贫困者必施,不计其有无;患难者必救,不问其远近。捐逋己责,不以为难,迁善改过,尤及其勇。凡闻一善言,见一善行,喜行于色,若己有之。[1](p.84-85)
圣学的仁义、诚信等,他都心领神会且付诸实践,完成了“修”、“齐”即注重道德修养的为己之学,而最终归宿的“治”、“平”即利益群生,他没忘怀,身栖草野而心系国事,“先生见士友远来者,首以朝廷边报、人才用舍、四方休戚为问,有快于心,喜不能已,其或不然则尤形于色。”[1](p.101)“或朝有阙政,四方有警,辄恻不乐,至忘寝食。”[1](p.98)宋濂在《题北山先生尺牍后》中讲:“北山虽居山林而忧国之切,故有庙堂议和子文除擢之问……”[11](p.15),可见后人对他并非不闻世事的肯定。
三、何基对师说的发展
何基虽以羽翼朱子闻名,不主张标新立异,但并非没有自己的创见。“虽一本于朱子,然就其言发明则精义新意愈岀不穷。”[1](p.102)
作为朱熹思想的忠实阐发者,就应包含朱熹思想中具有的怀疑创新精神,既要忠实阐发,又要勇于疑,对这一矛盾的最好解释,就现存材料看,首先,他是肯定疑经精神的,从他解释朱熹《斋居感兴诗》第十二首中赞成朱熹不满于汉儒错乱经文可知。再有,何基对朱熹的看法也有疑义处,并且委婉地表达出来,如就《论语·学而》“人不知而不愠”中“愠”的解释,朱熹解释“纡问反,含怒意”,何基含蓄的指出朱熹的“含怒意”与君子气象的矛盾,认为应训为“闷”,说:“有一朋友言愠作含怒意,固下得轻,然终有怒字在,不见君子气象。惟训闷字惟是。”[12]并举《南风》诗“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来论证训闷的正确性,“暑气何可怒,但令人闷耳,熏风则能解人之愠闷也。”更用《集注》中引程子语以证明。对二人解释的差异,虽有调和之说,但从中可知何基对儒家所注重的“君子气象”培养的重视,做到中庸,但显然已有教条化倾向。
对于师说重心的“理”,他认为理乃“事物恰好处”,与程颐所说心、性、天即理,朱熹定义的宇宙根本“太极”比,将“理”缩小到了事物“恰好处”上,缺少形上层面的解释,是对朱熹“而今不是一本处难认,是万殊处难认,如何就万殊上见得皆有恰好处”[9](p.618)的发展,并举例指出:
理者乃事物恰好处,天地间惟有一理散在事事物物,虽各不同,而就其中各有一恰好处,所谓万殊一本,一本万殊也。三圣所谓“中”、孔子所谓“一贯”、《大学》所谓“至善”,皆是此意。圣贤相去数百年而谓以是传之者,皆是做到此耳。然义理无穷,未易便到极处,则吾辈讲学,正要相与合力精思明辨,讨个分晓的当受用处,又要各辨得个耐烦无我之心。耐烦则不厌往复,无我则庶无偏私,纵有未明,虽十往反而不惮,如是则始得个至当之归。[4](p.125)
与“太极”比,“事物恰好处”更具体,更有行动要求,“恰好处”是要努力去事物中“讨”方能得到,且需要心无偏私得反复以求,是格物的“理”,多了对事事物物的重视,可以说是有用无体,这一对“理”形上的削弱必然影响到对“理一分殊”的认识。在朱熹,理一分殊说是用来说明宇宙根本之理与具体事物之理关系的一种着重形上的理论,而在何基,则更多的理解为一种积累格物穷理功夫、最后归于一理的方法、实践,更强调实践、分殊功夫,即使有“实德”之质,也定要分殊到与天理之正无毫厘之差,强调格物穷理,因为:
圣贤有见成之条法,不考之则无以为入道之方;事物有当然之至理,不穷之无以为明善之要,故虽尽力于孝弟、谨信,待人接物之间,而不知毫厘之差、千里之谬,或以善为之,而未必合天理之正而不出于人欲之私,甚则陷父为孝、误兄为悌,无礼之谨,复言之信,泛爱而失于无择,亲仁而未必识仁,其弊有不可胜言者……[4](p.126)
何基将之传于门人,金履祥在《再奠北山先生文》中记载何基对他的教导:“谓凡事物,用各不同,曷云万殊,一理所通。盖凡事物,有恰好处,万殊一本,维此之故。谓昔程子,上蔡初来,曰此可望展拓得开,予亦谓子于此,可进难乎,有常戒尔。”[1](p.90)金履祥将之展拓开来,注重理一之分殊,格物致知,重视经史研究,并将之传于许谦,“吾儒之学,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3](p.2756)到许谦,对“理”的单纯解释就很少,涉及者多侧重理在分殊中的体现,“太极生阴阳,而太极即具阴阳之中;阴阳生五行,而太极、阴阳又具五行之中,安能相离也?何不即‘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之言而观之乎!”[3](p.513)解释倾向在五行乃至事物中体现太极,在分殊中求理,这与何基以来对理形而下的引导不无关系。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对《四书》,主张“由传以求经,由经以求道”,对传的重视理解难免发展为专注于分殊而忘却本体,流于训诂、制度,导致得鱼忘筌之病。
北山一派虽然秉持朱熹理学理论,但是由建立初的重在形而上的阐述,流露出理论成形后形而下的运用上,这样,更利于思想的广泛传播。
此时的朱学经历了民间到官方的转化,又将步入回到民间的历程,大有变异发展的可能,特别是在黄榦去世后,朱学面临失真的境遇,在朱学发展链条上需要接续朱学原貌以回归民间,因而,何基一依朱学为归依,发挥师说,并将其传给从学者,从而出现了端平后中振朱学的金华一支——北山学派,总观而言,何基对金华朱学起到了很好的链接作用,是完成了师门所委之任的,度宗时人对他的评说可谓精当:
或疑先生之学有体无用也。朱子曰:“天下无无用之体,亦无无体之用。”先生之体立矣,而其用固有以行矣!年运而往,精神逾迈,因以不用用之,非无用也。况自伪学胎祸天降,割于斯文,考亭辍响,伊洛之学孤立无助。勉斋先生续遗音于弦断丝绝之余,鼓而和者不过十余人。先皇帝崇尚正学,表意《四书》,跻五子于孔庙,风历之意甚切,而老师宿德相继零落,后生晚辈散漫无依,科举利禄之诱反甚于前,其能卓然自立者难矣
何基的谥号本身是对他生前行迹的肯定,“识见孔多可无愧道德博文之义,操履无玷所宜膺践行不爽之称”[1](p.89)勤学好问,对师业见得定、守得定,因而,对何基的为己之学,不能简单视作闭门避世之举,应理解为对身负传道重任的践行,对继承、延续文化命脉的一种自觉和努力,而对博大精深的朱学思想某方面的强调,则显示了朱学思想本身具有的自我调节能力、与时俱变的儒学发展规律,也预示了理学的发展转向。
注释:
[1][宋]何基.何北山遗集[M].续修四库全书,第1320册.
[2][宋]陈淳.北溪大全集.答陈伯澡十(卷二十六) [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2册.
[3][清]黄宗羲等.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王梓材冯云濠同辑.北山四先生学案补遗[A].宋元学案补遗(卷八十二)[M].
[5][明].徐袍.宋仁山金先生年谱[A].率祖堂丛书.光绪十三年补刻本.
[6][明]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7][元]吴师道.礼部集(卷二十)[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2册.
[8][清].戴殿江编.金华理学粹编(卷二何基条)[M].四库未收书辑刊,6辑12.
[9][宋].黎靖德.朱子语类[M].长沙:岳麓书社,1997.
[10][清].王崇炳.金华征献略[M].四库存目丛书,史部119册.
[11][明]宋濂.宋文宪公全集[M].四部备要本.
[12][宋]金履祥.论孟集注考证(卷一)[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