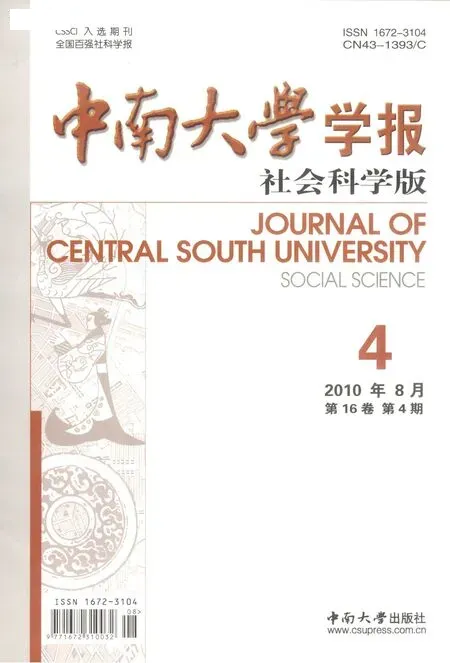道法自然,唯神是守——试论道教对老庄天人哲学思维的继承与宗教化发展
2010-02-09李为香
李为香
(济南大学历史与文化产业学院,山东济南,250022)
一、内外兼顾:老庄天人哲学思维的特质
老庄天人思想的核心是道法自然。从宏观意义上讲,天就是自然、天然,事物本来的状态,而人则是指人力所为,天人合一就是合于自然,要求人们回归到本然的状态。老庄极为推崇自然之道,即“天之道”[1](七十七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二十五章)老子所崇尚的理想境界是“万物将自化”[1](三十七章)的自然无为状态。庄子则崇尚天人一体不分:“人与天一也。”[2](山木)庄子更为明确地说明了“天”的本然意义以及“人”的人为意义:“何谓天? 何谓人? ……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2](秋水)就是说,牛马生来四条腿,这就是所谓天然或“天”;用笼头把马头络住,把牛鼻子穿个孔,让牛马供人役用,这就是人为或“人”。由此,他主张一切因于自然:“以天合天。”[2](达生)而不主张“以人灭天”、“以故灭命”,“以得殉名”,[2](秋水)即不要以人的行为灭除自然万物的天然本性。老庄反对人为而因循自然,主张天下万物本于自然,法于自然,自生自灭,无须人为地参与其中。
具体到个人,“天”则是人的自然本性,那么这个自然便不再是上文所述事物的本然状态,而具备了另外一层含义,即顺乎自然、复归天然的心理状态:“以畏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1](六十四章)实际上,老庄认识天的方法是向内求诸于自身的。老子四十七章:“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王弼注:“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在老子看来:天之道如人之道,人的知与不知,全是由人自身决定,重在察己,可以不出户而知天下。《庄子》中则更明确地说:“天在内,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反要而语极。”[2](秋水)其内涵在于:“自然本性蕴藏在心内,人的行为显露于外,大德在于顺应自然。知晓自然无为与人的有为,立本于自然无为,居位于悠然自得……便可以复归大道之要而谈至极之理。”可见庄子极为重视人的本然心态以及内在的自得感受,将之视为返归无极的重要途径。他还说:“虚无恬惔,乃合天德……故心不忧乐,德之至也。”“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2]主张只有内心保持恬淡清静无为而乐,才能到达最高境界,得到精神修养之道。在这个意义上,天人合一实是合于自身的内心体验。
“天人合一”所适应的范畴可以大到宇宙,也可以小到个体,在天人合一思维方式之下,无穷大的宇宙与无穷小的个体合而为一,宇宙可以合于自身,自身也可以是无穷大宇宙的缩小。故在老庄思想中,个体的形体与精神也被理解成人和天的关系。对于庄子的“天在内,人在外”,既可以抽象地理解为本然与人为的关系,还可以以具体的人为参照理解为内在精神与外在形体的关系。如果按照后者来解释的话,那么可以说庄子将“天”看作是内在的精神性的,将“人”的形体看作是外在的,天人合一就是内外合一或形神合一。庄子具体地论述了形神合一及守精神的重要性,指出要长生,就要保持形体与精神相守合一:“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女神将守形,形乃长生。”[2](在宥)庄子还认为,精神是可以四通八达、无所不能的东西,所以对于人体来讲,只要能守住精神,便可以和精神一样上通于天而合于天:“精神四达并流,无所不极,上际于天,下蟠于地,化育万物,不可为象,其名为同帝。纯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与神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伦。”[2](刻意)庄子崇尚绝对的精神自由,认为只有守住精神,才能够达到与天伦合一的自由之境。
如上所述,老庄的天人思想涵盖了宏观的宇宙与微观的个体,体现出内外兼顾的本质特征,即对于人体以外的“自然”与人体自身的“自然”(即庄子所谓的精神自由状态)同等关注。这一特征为后世道教所传承,并被赋予宗教化的解释。
道教信仰的本质亦在于“自然”二字:“道已毕备,便成自然。”[3](472)求仙得道的最终结果便是合于自然,复归无极:“夫道者,乃无极之经也。”[3](25)这是就宏观而言。在微观上,道教中“形神俱妙、与道合真”是老庄唯神是守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特征,成就了道教既可以向外探索自然奥秘又可以向内求得真心的双向发展。
与老庄的崇尚自然相承续,道教崇尚长生成仙,与天地相融。道教修炼的最终目的和最高境界在于实现个人的长生不死,即不死成仙。在如何成仙的探求中,道教徒实践着向外与向内两种不同的修炼方式。这两种修炼方式是互为包含、互相促进的,如葛洪曾说:“服丹守一,与天相毕,还精胎息,延寿无极,此皆至道要言也。”[4](41)实际上就包括了内外两种修炼方式。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其最终宗旨均是为了修炼成仙,与天地长存。
二、道教外丹:天人思维的外向化
向外求索是道教独特的修炼方式。道教中的“洞天福地”可以视为向外探求的理想之境。其方法是归于大地名山,求得与天地自然的合一。道教将远离喧嚣、清静幽深的名山赋予强烈的神秘意义:“山无大小,皆有神灵。山大则神大,山小则神小也。”[4](273)并进而将许多名川大山当作神仙居住、统领与通天之地,如道教中的“三十六洞天”即为通天之山洞,“处大地名山之间,是上天遣群仙统治之所”,[5](199)“七十二福地”①[5](99−204)则亦“在大地名山之间,上帝命真人治之,其间多得道之所”。[5](201)洞天福地拥有诸多神灵统帅,那么,人若在洞天福地中修炼,必能与神仙相接,达成与神仙的会合,得到神仙的点化而列身于仙班。如此,向往洞天福地,归于大地名山,成为道教独特的修炼境界与方式。洞天福地既是一种虚幻的神仙世界,同时也是实际存在的名山洞府,归于天地之间,既是道士对神仙境界的向往,同时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求仙问道的过程。在体验洞天福地的通天绝地、无穷漫妙之际,道士们可以真正与自然融为一体,回归生命的本然,实现与天的合一。
对于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来说,如果寻求到了“洞天福地”,那么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要让自己的生命长生不老,才能真正实现永恒意义上的与天同存。外丹术是道教实现这一根本目标的最重要途径。道士进行外丹炼制的材料包括强身健体的植物药材、物理性状变化多端却不腐不朽的各种矿物。在归于山川之间的逍遥中,道教徒不仅可以拥有精神上通仙的静谧境界,而且还可以获得炼制丹药必须的草药、矿物等,山上“皆生芝草,可以避大兵大难,不但于中以合药也。若有道者登之,则此山神必助之为福,药必成。”[4](76)但人服用芝草“可得延年,不免于死也”。[4](65)而且:“草纵有灵,水浸则腐,火焚即焦,又岂能长久乎? 皆不通理者也。”[6](281)显然灵芝一类的草药虽有神灵助之,却遇水火即失,被认为不能达到长生不死的目的。而要能够长生不老,与天不朽,就应当寻求本身不腐不朽的物质用以转化为人体本身的不朽不老。对此,葛洪曾有精妙之语:“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4](62)他认为,人若服用变幻无穷却“毕天不朽”的金丹,必定也能够“人寿无穷已,与天地相毕,乘云驾龙,上下太清”。[4](65)所以“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成为道教外丹术的原理根基。根据借助于外物之力而达至自身不朽的道理,外丹实践家们认为:“唯丹砂一味能存神与形,是以世人欲心惕乱则砂尸,欲不朽则用水银,水银感阴阳之气,八百岁而成砂,三千岁而成银,八万岁而成金,愈久愈坚,千变万化,圣人运水火法阴阳之气,而毕其功,所谓夺得造化机者也。由砂以至银,由银以至金,金液还丹,取而服饵,长生之理,端在乎此。”[6](281)所以要长生成仙,必须将丹砂金银等自身不灭的特性转化到人体当中,若人体能够获得这种长久的特性,便可实现长生的目的。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道教外丹术的基本理论依据在于“天人合一”,它将天地“阴阳之气”运用于丹术修炼的过程中,从而将外丹修炼看作是与天地宇宙的变化运行相合。所以,欲求长生而炼制外丹之士必须“上知天文,下明地理,洞达阴阳,穷通爻象;并节气休王,日时升降,火候进退,鼎炉法则;然后会龙虎法象之门,识铅汞至真之妙。”[6](220)只有通晓天地阴阳变化之道,明确铅汞金银变换之理,才能够自觉地将天地阴阳与丹炉火候相配合,寻求“与天地相毕”的至理。
总之,道教外丹的宗旨在于与天地自然相融相通:“天下有自然之道,万物有自然之理。不得于理,物且不通,而况道乎?”[6](281)若要得自然之道,达到人天相通相合,必须明晓自然变化之理,正如葛洪所言,“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4](259)“得夫自然之道也,故其能之”。[4](261)若能与天相通,那么人就可以获得天地之力,变化无穷却能不老不朽,这种境界就是神仙境界。
三、道教内丹:天人思想的内向化
在道教看来,不仅金液还丹能“存神与形”,通过向内求索,即进行精神炼养,亦可以追求形神合一。而且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兼须内明道德,外施慈惠,心与丹合,自达真形。”[6](220)就是说,外丹炼制的同时要进行内心道德的完善与社会慈善的施行,这显然属于道教向内求索的内容。不仅外丹修炼以掌握自然之道为本,道教的向内求索亦以守自然之法为根本,因为“自然之法,乃与道连,守之则吉,失之有患。比若万物生自完,一根万枝无有神,详思其意道自陈,俱祖混沌出妙门,无增无减守自然”;[3](472)“道畏自然者,天道不因自然则不可成也。故万物皆因自然乃成,非自然悉难成”。[3](701)根据这一道理,只要是想得道成仙,无论采取什么方式都必须“道法自然”。所以向内探求也必须遵循这一法则,能够因循自然,守住自然,使自然天成,做到无增无减,才可得道。
道教向内求索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是“形神俱妙,与道合真”,这是一种形神合一、绝对自由的生命状态。形神合一的绝妙状态也可以称作“守一”:“古今要道,皆言守一,可长存而不老。人知守一,名为无极之道。人有一身,与精神常合并也。形者乃主死,精神者乃主生。常合即吉,去则凶。无精神则死,有精神则生。常合即为一,可以长存也。常患精神离散,不聚于身中,反令使随人念而游行也。故圣人教其守一,言当守一身也。念而不休,精神自来,莫不相应,百病自除,此即长生久视之符也……守一者,真真合为一也。人生精神,悉皆具足,而守之不散,乃至度世……”[3](716)既然形者主死,精神主生,那么形神合一的关键便在于守精神:“故精神不可不常守之,守之即长寿,失之即命穷。”[3](731)精神历来被道教中人认为是长生之本,只有保持精神完全而不失,才能驱逐百病、毫无损伤,真正做到守一,得以长生成仙,而归于“无极之道”。除此,《太平经》将守精神用于天地山川以至万物:“天不守神,三光不明;地不守神,山川崩沦;人不守神,身死亡;万物不守神,即损伤。”[3](727)道教认为,万物都必须守神,方可保全自身,不会消亡。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道教其实是把“人”看作天地万物之中的一员,天地万物都有神,都必须守神,才可以不受损伤,这是道教独具的自然伦理观。
守精神的最终目的在于人道与天道的契合,回归于无极,与天相毕。天、地、人若都能守一,便可实现天地清明、万物自存而长久,对于人则可以生命长生,生活平安,家庭和睦,国家安定。《太平经·圣君秘旨》中说道:“夫守一者,可以度世,可以消灾,可以事君,可以不死,可以理家,可以事神明,可以不穷困,可以理病,可以长生,可以久视。”[3](743)“守一之法,老而更少,发白更黑,齿落更生。守之一月,增寿一年,两月,增寿二年;_以次而增之”,“守一之法……可终其世,子得长久”。[3](740)反之,若失去了“一”,则天“失其清”,地“失其宁”,日“失其明”,月“失其精”,星“失其行”,神“不生成”,人“不活生”。以此来指导人们:“一之为本,万事皆行。子知一,万事毕矣。”[3](743)只有在自身修炼中,坚持守一、达至形神相须、保守自然,才有可能实现长生,进而与天同存。
向内求索的精神炼养到隋唐之际发展为内丹术,亦是依照阴阳五行学说,将人体比喻为小宇宙,内丹修炼则是实现人体内部元素运转的动力,人体宇宙通过修炼之后,不仅实现自身的循环,同时还能与天地宇宙相通,从而实现宏观与微观世界的相通,这大概是“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四、结语
将道教的守自然与守精神向上追溯,我们不难发现老庄的“道法自然”与“唯神是守”的历史承续及其宗教化过渡。从传承的角度看,崇尚自然与精神自由始终是道家与道教修养的两大主题。从道法自然、返朴归真到神仙信仰、守一抱朴,道教承继了老子的回归式思维,并将之应用于现实修炼与体验当中。事实上,道教的神仙信仰与丹术修炼是天人合一思想的进一步发挥,是实现天人理想化境界的神秘化尝试。纵然道教较之老庄具有了更多的神秘主义因素,但在“自然”与“求真”(精神之本真)的核心问题上,二者具有相同的旨归。正是在这一点上,道教具有了与儒家伦理得以争衡的内在底蕴,从而能够在社会领域之外的更广大的空间具有儒家思想所不及之处。同样是在本然、“求真”这一点上,道教对中国古代科学的贡献更是非儒家所能比及。这些贡献,曾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忽视或曲解。道教中人坚持不懈的长生努力固然显得异常荒诞,但时至今日,他们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正被国内外学人所重视和研究。这何尝不是一种长生,不是精神意义上的“天人合一”?
从过渡的角度看,天人合一思想的核心是人道与天道的契合,道教的神仙信仰为天人合一找到了最为理想的契合点,神仙是有着绝对自由的人,是天人合一的最高存在。在道教这里,老庄哲学意义上的“天”或“自然”逐渐成为宗教意义上的神仙境界。在道教中,形神合一、长生不死称为“仙”,是能与天地四时共同变化的长生者。仙只是现世人们依照现实生活而幻化出的的一种理想生活境界,从本质上说,它是在世即不脱世而又离世的。[7](46)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尘世到底是真实的,天堂却是不真实的,人类生活在这个真实的尘世和不真实的天堂的中间是多么幸运啊!”[8](页码??)老庄的天人合一在道教这里被演变成了一种令人神往的神仙境界,即“仙无穷时,命与天连”。[3](403)对神仙境界的无限想象和极力化而为仙的不懈探求成为道教深入人心的信仰引力。在这一宗教精神的驱使下,人们逐渐展开向外界及内心的探索与回归。如果说老庄的天人合一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人对浑沌境界的内心体验,那么道教的天人合一则呈现出双向的体验。②神仙信仰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宗教化实践。反过来,神仙信仰的最终目的是使人合于天,合于自然,成为一种永恒的存在,这一终极关怀成为道教得以在民间绵延不衰的内在源泉,也使得道教成为中国本土宗教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奠基者与集大成者,正像鲁迅先生所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9]
注释:
① 关于“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的名称,可参考参考文献[5].
②道教的双向体验,其向外的对自然界的探索与体验是成就其自然科学贡献的根源所在。而向内的精神体验则成就了后期道教由外丹向内丹的修炼转向以及中国文化史上的三教合流。但遗憾的是这种转向却成为中国古代科学进一步深入发展的严重束缚。
[1]王弼.老子道德经[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2]郭象.庄子[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3]王明.太平经合校[M].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4]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M].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5]道藏·22册[M].北京: 文物出版社; 上海: 上海书店;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6]道藏·19册[M].北京: 文物出版社; 上海: 上海书店;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7]李养正.道教概说[M].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8]林语堂.生活的艺术[M].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8.
[9]鲁迅全集·卷9·致许寿裳[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