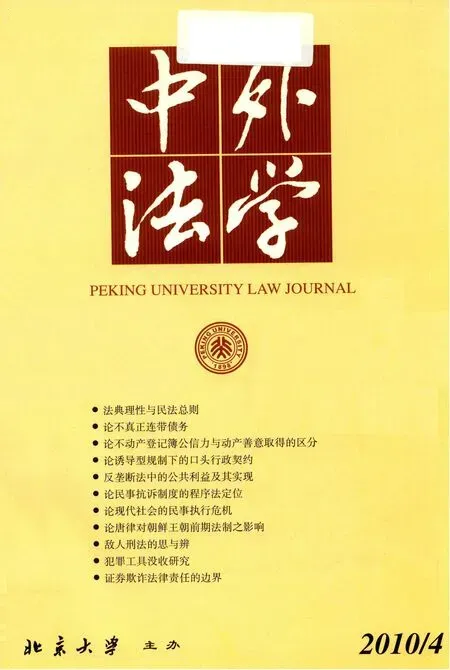论唐律对朝鲜王朝前期法制之影响以“华化”与“土俗”之关系为中心
2010-02-09张春海
张春海
论唐律对朝鲜王朝前期法制之影响以“华化”与“土俗”之关系为中心
张春海*
1392年,李成桂推翻高丽王朝 (918-1392),建立朝鲜王朝 (1392-1910),在即位教书中宣布:“前朝之季,律无定制……自今京外刑决官,凡公私罪犯,必该《大明律》。”〔1〕《朝鲜王朝实录·太祖实录》太祖元年七月丁未条,首尔大学奎章阁本。从此,《大明律》便成为朝鲜王朝五百余年间适用的基本法典。半岛对中国传统法制的移植模式也由选择性引进转为全面移植,此即朝鲜王朝实行的全盘“华化”政策。〔2〕本文用“华化”来表示中国文化对朝鲜的影响方式,用“华制”来代表中国制度。朴秉濠使用了“中国化”一词,认为朝鲜初期有制度上的“中国化”运动,其含义和我们所说的“华化”相似,只是并未进一步论证而已。(韩)朴秉濠:《韩国法制史考——近世法社会》,法文社 1974年版,页 334。同所有的文化转型过程一样,半岛法制的转型也不可能由某项政策的实行便发生突变。在朝鲜前期,由于在社会、文化、习俗等各个层面均和明朝存在诸多不同,对朝鲜自身语境下的不少具体问题,《大明律》或是没有规定,或是难以适用,于是便产生了移植而来之明代法律与本国“土俗”〔3〕本文用朝鲜人常讲的“土俗”一词来表示半岛的固有制度、传统、习惯等文化形态。间的张力,唐律成了《大明律》的补充或替代性资源中的一种。
目前学界关于唐律与半岛关系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唐律对高丽王朝的影响上,涌现出了不少成果,〔4〕关于对这些研究成果的评述,可参考拙文:“高丽律、唐律关系研究评述”,刊于《韩国学论文集》第十七辑,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9年版,页 54-61。但对唐律与朝鲜王朝法制关系的研究则颇为忽视,成果相当有限。最早注意到这一问题的是韩国学者朴秉濠,他在其专著《》中指出:“在朝鲜时代,特别是在世宗时期,《唐律疏议》在《大明律》的解释、适用乃至立法方面经常被参考,同时还对律学产生了重大影响。”〔5〕,1986年 ,页 50。不过,他只是以列举的方式罗列了十余条史料而已,并未做深入的分析。另外,他还断定:“世宗以后,《唐律疏议》基本上已失去了参照的价值。”〔6〕同上注 ,页 50。但并未给出证据,显有武断之嫌。多年以后,他又著有《朝鲜初期法制定社会相——<大明律》一文,在论述《大明律》的适用问题时指出:“当时即使国典和《大明律》有规定,为了公正起见,朝鲜仍会参照《唐律疏议》、《至正条格》、《议刑易览》、《元史·刑法志》、《无冤录》等,对法条或量刑做出变通。”〔7〕(韩)朴秉濠:《朝鲜初期 法制定社会相——<大明律 >实用》,(韩国 )《国史馆论丛 》第 80辑 ,,1998年 ,页 18。对之前的观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韩国学者郑肯植、赵志晚则指出朝鲜在适用《大明律》时,在具体的定罪量刑、构成要件的补完和修正等问题上,会将唐律作为参考对象。〔8〕(韩)郑肯植、赵志晚:《朝鲜前期 <大明律 >受容变容 》,《震檀学报 》第 96辑,2003年,页 227-229。总的来看,既有研究基本上都是在探讨《大明律》的具体适用问题时,将唐律的影响作为一个附带事项略加讨论,缺乏深度和系统性。笔者不揣浅陋,尝试对这一问题做较为详尽的探索,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唐律在朝鲜前期的地位
唐律曾在新罗和高丽初期两次大规模传入半岛,〔9〕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讨论,参见拙文:“论唐律文本传入高丽的途径”,刊于韩国《亚洲研究》2008年第 1期。对半岛法制产生了重大影响,《高丽律》就是模仿唐律制定而成的。《高丽史·刑法志》序:“高丽一代之制,大抵皆仿乎唐;至于刑法,亦采唐律,斟酌时宜而用之。”〔10〕(朝鲜)郑麟趾:《高丽史·刑法志》,中册,(韩)亚细亚文化社 1990年版,页 833。高丽还在学校设有律学,在科举中设有“明法”,〔11〕《高丽史·选举志》载“仁宗朝式目都监详定学式”:“其律学、书学、算学皆肄国子学。律、书、算及州县学生,并以八品以上子及庶人为之。七品以上子情愿者听。……律、书、算学只置博士。律学博士掌教律令,书学掌教八书,算学掌教算术。”中册,页 626。在刑曹设有律学博士。〔12〕《高丽史·百官志》:“刑曹:掌法律、词讼、详谳之政。……又别置律学博士一人,从八品,助教二人,从九品。”中册,页 664。律学所学、明法所考的主要内容便是律和令。〔13〕《高丽史·选举志》载仁宗十四年十一月下旨:“凡明法业,式贴经。二日内,初日贴律十条,翌日贴令十条,两日并全通。第三日以后读律,破文兼义理通六机,每义六问,破文通四机。读令破文,兼义理通六机,每义六问,破文通四机。”中册,页 591。因《高丽律》过于简单,不成体系,〔14〕关于此,可参见拙文:“高丽移植唐代法制之变形及其历史背景”,《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哲社版)》2008年第 3期。不论是律学还是明法,唐律都是重要的学习和参照文本。由于明法登科较易,许多两班贵族子弟及贡士多是通过明法科入仕。高丽仁宗十八年 (1140)闰六月,中书门下奏:“明法业但读律、令,其登科甚易。且于外叙,必六经州牧,实为出身捷径。缘此,两班子弟及贡士求属者渐多。”〔15〕《高丽史 ·选举志 》,中册,页 593。这种制度性的安排使唐律在半岛的影响进一步扩大,逐渐取得了崇高的声誉和地位。
朝鲜取代高丽后,实行了全盘“华化”的文化转型政策,〔16〕当时“一遵华制”已成为王朝的主导性话语,史料中反映这一历史事实的事例甚多。太宗六年(1406)三月,权文毅上疏请行号牌之法,云:“恭惟国家,立经陈纪,一遵华制……依中国之制,皆给号牌,出入佩持。”《(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太宗六年三月甲寅条)九年三月,司宪府上时务数条,其一云:“今我国家典章文物,悉遵华制,而女服之制,独因旧习,不可不更也。”《(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太宗九年三月壬戌)不再一一赘举。明朝制度取代之前的唐、宋、元等中国前代制度成为半岛的主要移植对象。然而,由于明朝制度与半岛国情的差异较大,所以遭到了来自“土俗”的较为强劲的抵制。这种态势从太宗后期开始就较为明显地显现了出来。太宗就曾对大臣们说:“今《大明律》,若大逆等事则已矣,其余未合于我朝《六典》者多矣。”〔17〕《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太宗十三年十二月丁巳条。唐律因为和半岛“土俗”有长达四百余年交融的历史,正好可以侧身其中,起到调节、补充乃至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大明律》本身存在的缺陷在其与半岛“土俗”间存在张力的背景下,使唐律本身具有的优越性更加明显。世宗就曾对大臣们说:“《唐律疏议》,盛唐之制,而极为详明。”〔18〕《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世宗二十六年十月甲寅条。因此,在朝鲜前期,唐律在半岛精英阶层心目中的地位不减。世宗八年 (1426)十月,下令:“自今择文臣之精通者 ,别置训导官 ,如《唐律疏义 》、《至正条格 》、《大明律 》等书 ,讲习可也。”〔19〕《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世宗八年十月丁亥条。在第二年 ,又“颁铸字所印《唐律疏义》于中外官”。〔20〕《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世宗九年三月辛亥条。世宗十一年六月,刑曹启:“议刑之际,《唐律疏议》最有益,不可不知……请自今四孟朔,取才及律科,并试《疏议》,通计等第。”〔21〕《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世宗十一年六月戊寅条。这就使得半岛精英阶层对唐律非常熟悉,在法律上,他们以唐律为线索,将高丽以来的固有法制较好地接续了下来。
朝鲜前期在文化转型过程中存在的“华化”与“土俗”间的复杂关系还使唐律保持了强大的论证力,成为王朝制定与论证新定法律合理性的重要依据。有时,朝廷的有关机构或官员会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一些不同于《大明律》的立法或司法建议,这些建议可能和唐律并无直接关系,但他们仍会以唐律的原理为依据,对于那些涉及关键性“土俗”的立法尤其如此,其中又以奴婢法制最具代表性。
世宗十四年三月,详定所启:“本朝之法,奴娶良妻者有禁,而婢嫁良夫者无禁,男女异禁,诚为未便。谨按《唐律疏议》曰:‘人各有耦,色类须同。良贱既殊,何宜配合?’……乞依唐律及时王之制,自宣德七年七月初一日以后,公私婢嫁良夫者一禁,如有犯令者,依律论罪。”〔22〕《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世宗十四年三月乙酉条。奴婢法制是半岛历史悠久的固有法制,有“我国奴婢之法,自箕子行之,为东方不易之典”之说。〔23〕《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光海君七年 (1615)二月己卯条。是作为执政集团之两班贵族赖以存在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世祖十三年 (1467),梁诚之上疏:“而况中国,自唐尧至大明,凡二十三代;东国自檀君至今,才七代。此非徒华夷风俗淳漓之不同也。以东方大家世族,布列中外,虽有奸雄,不得睥睨于其间也。夫大家世族之为大家世族,以其有奴婢也。”〔24〕《朝鲜王朝实录·世祖实录》世祖十三年八月己亥条。因此,奴婢制度一直被视为半岛最重要的“土俗”。《高丽史·忠烈王世家》载忠烈王上奏元朝皇帝表文云:“昔我始祖垂诫于后嗣子孙云:凡此贱类,其种有别,慎勿使斯类从良。……故于至元七年小邦去水就陆之时,先帝遣达鲁花赤以治之。于时因人告状,欲变此法。确论闻奏廷议明断,俾从国俗。……伏望……俾从先命……消风土变更之叹。”〔25〕《高丽史·忠烈王世家》,上册,页 648-649。就是以“土俗”为由对抗时任征东行省平章的阔里吉思依据中国制度进行的改革。
然而,高丽末期以来,由于社会的巨大变动,半岛以“一贱永贱”、“从贱不从良”、“父母一贱则贱”〔26〕关于此,可参见拙文:《高丽律对唐律变形之原因探析——以“华化”与“土俗”之关系为视角》,《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 2期,页 91。为基本原则的奴婢法制有所松动。朝鲜初期,渐有高官、贵族婢妾之子从父为良之事,这种做法有明朝制度为依据,然而对于严格的奴婢制度而言,却是一个不小的漏洞。成宗九年七月,刑曹在上疏中就提到:“顷承传旨:‘本国良贱之法,与中国不同,凡定罪,难以一概据律施行。’”〔27〕《朝鲜王朝实录·成宗实录》成宗九年七月戊子条。因此,详定所建议严禁公私婢下嫁良夫,所生男女也要严格按照传统的“父母一贱则贱”的原则确定其地位与归属。这一半岛的固有法制和唐律的精神是背离的,〔28〕张春海 ,见前注〔26〕,页 91。详定所仍以唐律为立法依据,就是试图以唐律中的只言片语增强立法建议的论证力和说服力。这种情况表明当半岛“土俗”与移植而来的明制发生冲突时,只有借重唐律在半岛和东亚法制体系中的崇高地位,才能使王朝的立法获得较为充分的正当性支持,尽管有时他们提供的依据和其立法建议之间仅有牵强而微弱的联系。由此可见,唐律是朝鲜前期文化转型过程中为解决新移植而来的外来法制与本国固有制度之间矛盾与冲突的重要资源。
当然,唐律之所以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是以唐律与半岛“土俗”之间的长期融合、它与《大明律》之间存在的差异以及本身的优越性为前提的。以下我们将分两节对此进行详细的分析与说明。
二、《大明律》的特点与唐律对朝鲜前期法制发生影响之关系
和唐律相比,《大明律》本身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是明朝在制律过程中变革唐律的结果,多与半岛的国情不符,在具体适用的过程中,便和半岛的“土俗”及朝鲜在文化转型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新传统发生了矛盾与冲突,而“土俗”在朝鲜前期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为唐律继续发挥其作用与影响力提供了空间。
(一)“重其所重”的特点与半岛的轻刑传统相抵触
《大明律》具有“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特点——在刑民钱谷方面,较唐律为重;在礼乐教化方面,较唐律为轻。这两个特点和半岛的旧“土俗”及新传统不合。
首先,轻刑是高丽以来半岛法制的一个突出特点。宋人孙穆在出使高丽后著有《鸡林类事》一书,他观察到的高丽法制的特点是“夷性仁,至期多赦者”。〔29〕(宋)孙穆:“鸡林类事”,载杨渭生等编《十至十四世纪中韩关系史料汇编》(上),学苑出版社 1999年版 ,页 25。并描述高丽执行刑罚的状况云:“有犯不去巾,但褫袍带,笞杖颇轻,投束荆使自择,以牌记其杖数。……其犯恶逆及骂父母乃斩,余止杖肋,亦不甚楚,有降或不免。”〔30〕同上注,页 25。徐競曾在北宋宣和时出使高丽,对此也曾亲有所见:“笞杖极轻,自百至十,随其轻重而加损。”〔31〕(宋)徐竞:《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日)近泽书店 1932年版,页 81-82。《高丽史·酷吏传》序亦云:“高丽以宽厚为治,刑无惨酷。”〔32〕(朝鲜)郑麟趾:《高丽史·酷吏传》,(韩)亚细亚文化社 1990年版,下册,页 669。朝鲜取代高丽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将这一传统继承了下来。成宗(1469-1494)在给议政府的教书中说:“明慎刑罚,我祖宗家法。”〔33〕《朝鲜王朝实录·成宗实录》成宗六年八月壬寅条。正祖 (1776-1800)亦云:“我朝制置之仁厚,即相授之家法。”〔34〕《朝鲜王朝实录·正祖实录》正祖十四年八月戊辰条。明朝法律在他们看来却是“大抵明律条例尚严”。〔35〕同上注。如此一来,《大明律》与半岛的固有法律传统便发生了抵触,如何解决,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及对相关法益的判断加以权衡。由于半岛精英阶层对唐律较为熟悉,而唐律和半岛“土俗”又有较好的融合,同时它和《大明律》又具有不同的特点,所以在朝鲜前期,当司法官员遇到《大明律》中那些畸重的条款时,常会以唐律的有关规定取而代之。
薛允升云:“贼盗及有关帑项钱粮等事,明律又较唐律为重。”〔36〕(清)薛允升着,怀效锋、李鸣点校:《唐明律合编》卷九,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页 170。循此线索,我们从贼盗与钱粮两个方面着手,通过一些具体事例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先看“贼盗”的情况。由于推动适用《大明律》是王朝的基本国策,所以朝廷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前后并不一致。比如,就对三犯窃盗如何处罚的事项上,朝鲜前期一直存在争论。在最初的二十余年间,因积极推动“华化”政策,在这一问题上主要依《大明律》“凡窃盗,三犯者绞,以曾经刺字者为坐”的规定处理。从太宗后期开始,“华化”的速度放缓。朝鲜精英阶层对《大明律》的局限性日渐有了清醒的认识,在“华化”与“土俗”之间开始更加顾及本国的传统与“土俗”。世宗二十八年六月,就下教议政府:“《明律》非本国要须遵守者也,故本国虽用《大明律 》,因时俗事势 ,或轻之 ,或重之 ,或别立新条者多。”〔37〕《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世宗二十八年六月癸卯条。
对于制盗之法,也渐感依《大明律》处罚太重,从世宗十五年开始已改按唐律执行,不用《大明律》中的那些严刑重法。世宗十五年,朝廷对“窃盗禁制之方”进行了集议,皇甫仁等人提出:“其赃证明白者,虽不服招,一依唐律科断。如此数年,以观其势……严刑重法以弭盗,于治道未便。”除提出依唐律科断的原则外,还特别点出“严刑重法以弭盗,于治道未便。”显然是针对《大明律》而言。领议政黄喜等也说:“虽日设禁防,终无益也。莫若依《唐律疏议》,赃证明白者,虽不承,辄行科断,使之利小而害多,则庶弭窃盗矣。”〔38〕《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世宗十五年十一月甲申条。世宗本人也持同样的看法,从此依唐律之法制盗便成了王朝的一项基本政策。
朝鲜王朝弃《大明律》而用唐律之制,是“华化”与“土俗”之间的冲突与妥协在法律层面的后果之一。在世宗时期,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曾有深入的反思,其结论就是要在一定程度上向“土俗”回归。这在当时的精英阶层中已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世宗五年七月,许稠对世宗说:“中国之礼,安可尽从?”〔39〕《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世宗五年七月辛巳条。世宗十四年十一月,许稠又云:“臣观上国之事,不可则效者多矣。”〔40〕《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世宗十四年十一月戊午条。世宗二十五年七月,在谈到官制改革的问题时,世宗对宰臣黄喜等人说:“我国之事,不能如中朝者多矣。”〔41〕《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世宗二十五年七月庚申条。这股潮流对朝鲜在法制层面推动适用《大明律》的工作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二十八年六月,世宗在其所下的一份教书中就讲:“建文时,本国请《大明律》,诏旨不许曰:‘仪从本俗,法守旧章。’是则《明律》非本国要须遵守者也。”〔42〕《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世宗二十八年六月癸卯条。有了这样的舆论基础和观念上的转变,用与本国“土俗”更为契合的唐律中的规定取代《大明律》中那些和本国“土俗”冲突比较厉害的条款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制盗之法基本政策的改变为在三犯窃盗问题上改变政策创造了条件。大约在世宗十五年后不久,对三犯窃盗便改用唐律规定的制度了。世宗十七年七月,刑曹上疏:“谨按《唐律疏议》曰:‘窃盗经断后更行盗,前后三犯徒者流,三犯流者绞,止数赦后为坐。’……《大明律》通计赦前,至于三犯,则处绞……本朝初依《大明律》,不拘赦前后施行,厥后依唐、元之制,立赦后为坐之法,宽仁至矣。”〔43〕《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世宗十七年七月戊戌条。说明在世宗十七年七月之前对三犯窃盗已适用唐律中的相关条款了。
对“帑项钱粮”事务同样如此,在此只举一例,不再赘论。世宗十九年七月,成均注簿宋乙开上言:
律文 (指《大明律》律文——引者)内“收粮违限”条云:“若夏税连限至八月终……欠粮人户,各以十分为率……若违限一年之上不足者,人户里长杖一百、迁徙,提调部粮官吏典,处绞。”……臣窃谓……但以违限一年之上处绞,用法似酷,故考诸唐律:“输课税之物,违限不充者,以十分论一分笞四十,每一分加一等;专违期不入者,徒一年。”罪不至死。臣愿守令于税户,挟私不收,使有欠粮,以致违限一年之上不足者,宜坐此律。〔44〕《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世宗十九年七月戊戌条。
指出了《大明律》在帑项钱粮等事项上刑罚苛酷的弊端,提出了以唐律补《大明律》不足的建议,议政府经过讨论后,接受了这一建议。〔45〕同上注。
(二)“轻其所轻”的特点与朝鲜新“土俗”的矛盾
朝鲜前期的文化转型政策可用“华化”一词概括,而此“华化”的核心则是“儒化”。当时,“儒化”主要集中在排佛和提倡儒家的纲常名教及与之相应的各种礼仪制度等方面,目标是建立一个儒教国家。〔46〕关于朝鲜前期儒教政治的发展情况,可参考 (韩)崔承熙:《》一文的有关论述,《》22《》,,1995年。正因为如此,对礼乐教化方面的成就,朝鲜人非常自豪。成宗十二年(1481)六月 ,李晏在上疏中云:“我国言语 ,不通中国 ,而人伦五常 ,侔于中国。”〔47〕《朝鲜王朝实录·成宗实录》成宗十二年六月壬子条。对“儒化 ”的不懈追求逐渐在半岛形成了一些以严格的纲常礼教为基础的不同于中国的新传统、新“土俗”。〔48〕这种在严格礼教基础之上形成的不同于中国的新传统、新“土俗”的过程,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且已溢出了本文的主题之外,除下文的有关内容外,在此再举一例,以为佐证。肃宗三十年 (1704)九月,司宪府在上疏中云:“我国无出妻之法,故虽有悍妻、恶妇,莫敢相绝,以至于丧家而灭伦者多,事之痛惋,莫此为甚。”(朝鲜王朝实录·肃宗实录》三十年九月辛酉条)“无出妻之法”就是这种新“土俗”之一。因此,在礼制问题上,朝鲜常不遵明礼,而是遵从唐礼等更为严格的古礼。太宗十一年九月,“欲请中朝祭礼”,礼官偰眉寿、许稠等曰:“当今明礼甚简……我朝皆仿唐礼。”〔49〕《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太宗十一年九月甲申条。丁若庸在《丧礼四笺》中云:“《大明律》升母服为斩衰,此亦时王之制也。今之士大夫援据古礼,断然服期者,何欤?沙溪答曰:‘父在为母期,千古不易之典。国朝从古礼,最得无二尊不贰斩之义 ,更何疑邪。’”〔50〕(朝鲜)丁若庸:《与犹堂全书》第三集《礼集》第十卷《丧礼四笺》卷十《丧期别一·母子二》,民族文化推进会本。
在礼、法混融之古代东亚法制的语境中,《大明律》在礼乐教化方面处罚较轻的特点和朝鲜以“儒化”为核心的文化转型政策及由此形成的新传统之间出现了脱节,其相关条款不能为精英阶层所满意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世宗二十八年六月的一道教书对此表露的尤为明显,其文略云:
本国之俗,行百日之丧,自高丽之季,始行三年之丧。自后虽甚不肖者,皆勉而及之,于终制之内,或犯宴游之罪,物论排之,终不齿于士类。今闻中国之俗,遭父母之丧,未过数日,饮酒食肉,笑语宴乐,无异平昔,众论不以为怪,朝政不以为罪。……向者本国立法,父在为母期,以吉服心丧三年。此法虽据礼经,而数十年间,不以为安,皆痛恨也,故近日因世俗之情,令世子以浅淡服,心丧三年。中国世俗之情,如彼其薄,制律者岂不知不孝莫大之罪,而曰“匿父母夫丧者,杖六十徒一年。”……匿父母夫丧之罪,止于杖六十徒一年,可乎?予谓当今立法,匿父母夫丧者及奉养父母有阙者,皆置极刑,然就其中或有情理之重与不重,推鞫之明与不明,是可虑也。故杀之则太重,以杖一百流三千里施行,何如?〔51〕《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世宗二十八年六月癸卯条。这道教书中所提到的行三年之丧,如果在此期间“或犯宴游之罪,物论排之,终不齿于士类”的惯例就是从高丽后期理学传入开始逐渐在精英阶层中形成的新“土俗”之一。〔52〕当然,这种新传统的形成有相当复杂的原因与历史背景,既和儒学在两国兴起的时机、背景有关——当时,半岛理学初兴,因而倾向于追从古礼,也和统治集团本身的文化素养及当时的现实政治条件有关:高丽末到朝鲜前期的统治集团为有较高儒学修养的新兴士大夫阶层,而明朝的建立者则是出身社会底层的濠泗集团。这种新“土俗”和明代礼教日益松弛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故而,《大明律》中关于礼教部分的条款既不能为朝鲜的精英阶层所满意,也不符合当时朝鲜文化转型的需要,因此世宗建议彻底废弃《大明律》的相关条款,别立远较《大明律》为重的法条。
对于世宗的提议,宰相黄喜、河演等经过研究后认为:“扶植纲常,使民归厚之虑至矣……其匿不举哀者,杖六十徒一年,虽若罪重而律轻,然考之唐律及《至正条格》,或流或徒而无杖,或有杖而无徒流,皆不至杖一百流三千里……凡亲丧及国丧一应忘哀之罪,各照本律论断后,并皆除名不叙,以征薄俗。”〔53〕《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世宗二十八年六月癸卯条。认为世宗的提议太重,于是在世宗建议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变通,加大了对官员的惩处力度,而他们所依据的就是唐律。因为唐律和朝鲜正在逐渐形成的新“土俗”正好契合,所以在有关礼教纲常的问题上,朝鲜法制多向唐律靠拢。
朝鲜前期文化转型的需要和新传统的逐渐形成,使朝鲜君臣对事关礼乐教化的犯罪非常敏感,为了加重对这类犯罪的打击,有时还会直接适用唐律的条款。世宗十二年二月,命义禁府释放被囚禁的金氏,并对金宗瑞说:“奇尚廉断继母发,反接之,告刑曹……《大明律》干名犯义条云:‘子孙告父母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诬告者绞。’唐律云:‘子孙告父母者绞。’”〔54〕《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世宗十二年二月己亥条。世宗直接指出了在子孙告父母的问题上,《大明律》与唐律规定的不同,不满《大明律》处罚之轻,更倾向于适用唐律。大臣们的看法和世宗基本相同。许稠说:“母子之间,虽有过失,相为容隐,义也。今尚廉告母者,欲害其母与弟,贪取财物奴婢耳。不除如此大恶,则人道灭矣。请依唐律论断。”为了将这种意见上升为法律,世宗下令:“唐律虽非当时所用,据唐律定制,然后施行可也。”并立新法云:“今后子孙告父母者,依唐律论断。”〔55〕同上注。于是,唐律的一些条款以王朝特别法的形式取代了作为一般法之《大明律》的有关内容,成为了朝鲜国内法的一部分。
总之,因为有旧“土俗”和新传统的支持,在朝鲜王朝推动的以明朝制度为基本移植对象的“华化”过程中,唐律对《大明律》中那些不符合、不适应朝鲜本国国情条款的取代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这是由当时唐律在朝鲜的特殊地位决定的。首先,唐律是中国古制,是广义“华制”的一部分,采用唐律和当时实行的全盘“华化”政策并不矛盾,故而可以为在本国居于主流地位的“华化”派所接受。与此同时,唐律早在高丽前期就已经被移植到了半岛的法律体系之中,和半岛有四百余年的融合历史,故而在某种程度上又可被看做是广义“土俗”的一部分。柳梦寅 (1559-1623)在其《送冬至使尹佥知 (存中)敬立序》中讲到一件事:“去年余见华儒吕英命,(英命)道:‘尝见中原有蓄古器、古服者,今尔国器服皆唐制,古朴可观,其用唐朝文物也可征。’”〔56〕(朝鲜)柳梦寅:《於于集》卷三《送冬至使尹佥知 (存中)敬立序》,民族文化推进会本。可为间接之佐证。因此,采用唐律也能够为“土俗”派所接受。可见,唐律在朝鲜前期的法律转型过程中实际上起到了沟通与润滑“土俗”与“华制”的作用,减少了两者之间的冲突,从而也就避免了由此可能会引发的社会震荡与法制建设上的曲折。
三、《大明律》的缺陷与唐律适用之关系
《大明律》对唐律的内容虽多有继承,但由于时代变迁之关系,又多有取舍,在增加了不少新罪名、新条款的同时,也删除了唐律的不少内容。〔57〕关于这一问题较为详细的讨论,参见张显清:“《大明律》的形成及其反映的时代特点”,《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 4期。薛允升在对两律做过详细的比较后论云:“明代则取唐律而点窜之,涂改之,不特大辟之科任意增添,不惬于人心者颇多,即下至笞杖轻罪,亦复多所更改。”〔58〕(清)薛允升著,怀效锋、李鸣点校:《唐明律合编·唐明律卷首》,页 1。又云:“明律虽因于唐,而删改过多,意欲求胜于唐律,而不知其相去远甚也。”〔59〕(清)薛允升著,怀效锋、李鸣点校:《唐明律合编·例言》,页 1。指出《大明律》因删改唐律过多出现了不少严重的问题。当存在这些问题的《大明律》被以政治力在短期内即迅速以全盘“华化”的方式移植到半岛这样一个和明朝存在重大差异的社会时,问题就更为突出了。朝鲜人在适用《大明律》的过程中,对此有切肤之感,以至有“人之犯法,至多端也,而律无正条者,十常八九”〔60〕《朝鲜王朝实录太祖实录》太祖七年四月丁酉条。的感叹。在这种情况下,便不得不用与本国“土俗”有密切关系且在体系上详备严密的唐律予以弥补了。
(一)以唐律补《大明律》中存在的空白
如薛允升所言,《大明律》对唐律删改过多,致使法典中出现了不少空白,不少现实的社会关系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而自高丽成宗以来,半岛的各项制度便多依唐制创立:高丽兵制是模仿唐前期兵制的“府兵制”;〔61〕《高丽史·兵志》序:“高丽太祖统一三韩,始置六卫,卫有三十八领,领各千人。上下相维,体统相属,庶几乎唐府卫之制矣。”中册,页 775。其官制是模仿唐制的三省六部制;〔62〕《高丽史·百官志》序:“(太祖)二年立三省、六尚书、九寺、六卫,略仿唐制。成宗大新制作,定内外之官:内有省、部、台、院、寺、司、馆、局;外有牧、府、州、县。官有常守,位有定员 ,于是一代之制始大备。”中册 ,页 656。其田制也借鉴了唐代的均田制;〔63〕《高丽史·食货志》:“高丽田制大抵仿唐制,括垦田数,分膏脊,自文武百官至府兵、闲人,莫不科授。”中册 ,页 705。礼制则如《朝鲜王朝实录 ·世宗实录 》所言“高丽《详定礼 》,出于唐制 ”,〔64〕《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四年正月甲子条。《高丽律》也是模仿唐律制定,所以和半岛“土俗”已深度融合的唐律便成了朝鲜人解决这些问题的首选资源。对此,我们不妨举两个具体事例加以说明。
为了迅速传递信息,在继承前代制度的基础上,唐王朝建立了一套相当完备的烽燧制度,制定了相应的法律规范——兵部的《烽式》和“法令”——予以调整,〔65〕关于此,参见程喜霖:《汉唐烽堠制度研究》第十二《唐兵部“烽式”及烽垠的职能》,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页 288-308。在唐律中也有专门条款。《唐律疏议·卫禁律》烽候不警条:“诸烽候不警,令寇贼犯边;及应举烽燧而不举,应放多烽而放少烽者:各徒三年……若应放少烽而放多烽,及绕烽二里内辄放烟火者,各徒一年。”〔66〕刘俊文点校、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页 195-196。高丽以来,半岛也依据唐制建立了自己的烽燧制度。然而,到了明代,虽仍实行烽候之制,可是不知何故,在修《大明律》的过程中“烽候不警”条却被删除了。在法制上全盘移植并适用《大明律》之后,朝鲜人在遇到“烽候不警”的问题时,便出现了无法可依的局面。世宗二十八年十月,议政府启:“烽燧之法,关系边警,利害不小……若前烽不准 (举),则依唐律……移文兵曹。”〔67〕《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世宗二十八年十月庚子条。对烽候不警之事,议政府建议依据唐律处理。世宗予以认可,成为了王朝的正式法令。〔68〕同上注。
图4为轨道单点高低变化仿真。由图4可知,在3根轨枕范围内,轨道单点高低变化对轨道直线度具有显著影响。由于悬浮架长度为2.8 m,略小于3根轨枕的长度,存在4个监测探头均监测直线位置的情况,此时直线度为0。
在传统社会,刑讯逼供为合法取得证据的方式,但因其存在的巨大弊端,又不能不严加限制。唐律基于此意,在《断狱》等篇对拷讯的方法与限度做了详细的规定,其中一条为“拷囚不得过三度”。可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大明律》却将该条删除了,在司法实践中就容易导致滥刑的后果。于是,世宗传旨刑曹:“唐律,拷囚不得过三度,总数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过所犯之数。疏议曰……是乃律文本意。今京外官吏拷讯之时,本犯虽是该笞,拷讯之数,过于笞数,有违钦恤之意……其拷讯之数,毋得过本犯笞杖之数。”〔69〕《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世宗十三年十一月丙寅条。也是以唐律的规定填补了《大明律》的空白。
(二)以唐律弥补《大明律》存在的缺漏
《大明律》还对唐律的不少条款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改,致使律条出现了缺漏或不周延的问题。朝鲜司法机构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时常会因为这些漏洞,陷入窘境。为了彻底解决问题,他们常用唐律补《大明律》的不足。世宗十二年十月,刑曹启:
中外官吏有犯当论者,或迁官、或去任,则依《大明律》卑官犯罪,迁官事发,在任犯罪,去任事发,犯公罪笞以下勿论。其事发去任者,则律无所载,各依本犯罪名,按律科断。谨按《唐律疏议》无官犯罪条云:“卑官犯罪,迁官事发,在官犯罪,去官事发,或事发去官,犯公罪流以下,各勿论,余罪论如律。”注云:“事发去官者,谓事发句问未断,便即去职。”请自今事发去官者,亦依《大明律》去任事发例,犯公罪笞以下勿论。〔70〕《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世宗十二年十月丁亥条。
对于官员犯罪,在司法实践中,朝鲜司法机构发现了《大明律》没有规定“事发去官”的漏洞。如遇到这种情况,就会出现无法可依的局面,从而造成法律适用上的不平衡,因此建议依据唐律的原理,将之列入法律的调整范围,具体的处罚则比照《大明律》“去任事发”的规定处理,部分地采纳了唐律的内容。
世宗十四年十月,就《大明律》斗殴及故杀人条的适用问题传旨刑曹:“《大明律》斗殴及故杀人条云:‘凡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故杀者斩。’今官吏等未能辨斗杀、故杀,任意行之……虽因斗,用刃杀者,即有害人之心;以手足殴杀者,初无杀人之意,同置绞刑,甚为未便。考诸唐律,斗殴杀人者绞;以刃及故杀者斩,虽因斗而用兵刃杀者,与故杀同。疏议曰……自古 (今)斗殴、故杀人罪,依唐律施行,何如?”〔71〕《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世宗十四年十月乙巳条。在复核死刑时,世宗发现《大明律》“斗殴及故杀人条”存在较大的缺陷,即纯以客观之行为定罪,不考虑犯罪人的主观方面,导致了司法官员在定罪量刑时“未能辨斗杀、故杀,任意行之”的结果,故而,建议从此以后,对于斗殴、故杀人罪,依据唐律定罪量刑。
刑曹于次年九月启:
在接到世宗的指示后,刑曹对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针对《大明律》条文的缺陷提出了详尽的修改意见。
首先,他们提出,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对这一问题一般做两种区分。其一为于“四肢不紧之处”用金刃伤杀,对于这种情况,可判定为“初无害人之意,偶致于死”,以斗杀论。其二为于“虚怯处刺杀”,这种情况稍微复杂,因《大明律》条文的缺陷,司法实践中常以犯人的口供为准:承认故意杀伤的,就论以故杀,坚持出于无意的,就论以斗杀。这就造成了量刑的不平衡,故而建议对这种情况依唐律的规定施行。其次,他们又指出《大明律》对于“同谋共殴人”的判定也缺乏明确的规定与标准,造成了“牵合取辞”、“生死颠倒”的弊病,因此也建议按照唐律的相关规定处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大明律》本身存在缺漏与其条款和本国“土俗”发生冲突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缺漏只是意味着《大明律》某些律条的不完善,但这些律条本身和朝鲜的“土俗”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和冲突,因此朝鲜人采取的是以唐律对缺漏之处进行某种程度的弥缝,而不是径直以唐律的条款取而代之。也就是说,在《大明律》条款存在缺漏的情况下,唐律只能居于次要的地位,律条的主体仍是《大明律》的规定,唐律作用的发挥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是由朝鲜全盘“华化”政策的总方向决定的。十二年十二月,世宗在朝会上对大臣们说:“古有讯杖不过本罪之法,其法美矣。今以犯笞之人,滥下讯杖,因而致伤者,或有之。予欲行古人美法,然《大明律》无此法,故未敢行耳。”许稠对曰:“此法虽美,然《大明律》所无,安可易以行之乎?”世宗说:“《大明律》,斟酌轻重,而定其罪之高下,不可违越。”〔73〕《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世宗十二年十二月丁卯条。可见,只要不和本国的关键性“土俗”相冲突,《大明律》对朝鲜具有强大的约束力,这种地位是唐律所不能撼动的。
(三)以唐律矫正《大明律》的不合理之处
全盘“华化”并不等于全盘照搬,在朝鲜前期的文化转型过程中,朝鲜人对明朝制度的态度还是比较审慎的,特别是在移植之后具体适用的过程中并不盲从,而是有自己的鉴别和判断。在法制的层面同样如此。一般来说,《大明律》的不合理之处常常是在朝鲜司法机构具体适用法律的过程中被发现的。遇到这种情况,司法机关常会向国王建议以唐律的有关规定予以矫正。
世宗十五年二月,刑曹启:
《大明律》名例云:“若以赃入罪,正赃见在者,还官主;已费用者,若犯人身死,勿征。”京外官吏据此律文,犯赃当死者费用之赃,亦令征之。然既以赃当受重刑,又征其已费之物,情所不忍。且犯强盗者,决不待时,奚待尽征?三犯窃盗者,必待时,故尽征之。若是则罪重者免,而反征其罪轻者,轻重失宜。况二人共犯赃,一人先死,一人当死,虽死有先后,其罪一耳,岂可先死者独免,而犹征于后死者乎?考诸《唐律疏议》云:“已费用者死及配流勿征。”议曰:“因赃断死及以赃配流,得罪既重,多破家业,赃已费用,矜其流死,其赃不征。”自今因赃断罪当受重刑者,见在正赃外,已费用之赃,勿征。〔74〕《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世宗十五年二月乙酉条。
对于犯罪征赃问题,《大明律》的规定过于粗疏,特别是其中的“若犯人身死勿征”一节尤为不合理:不是以罪定刑,而是以人的存亡来决定刑罚的执行与否,显然不合乎刑事法律的基本逻辑和原理,造成了罪重者免、轻罪者征,先死者免、后死者征的反常现象。因此,刑曹提出了修改法条的建议,其法理基础就是为他们熟知且和半岛“土俗”更为契合的唐律的方法和原理。唐律“死及配流勿征”的规定是以刑定罪,其中的“死”是指死刑,而《大明律》依此条制定相应的律条时却将之改为了“身死”,看似直白易懂,实际上完全误会了唐律的本意,招致了严重的后果。
因为半岛有长期依据唐律原理适用法律的历史,朝鲜的司法官员对唐律又较为熟悉,两相对照,他们很快就在司法实践中发现了《大明律》存在的不合理之处,于是建议依唐律做出修改,这样就能较为有效地避免适用法律不平衡的问题了。
(四)以唐律校正《大明律》中与朝鲜其他制度不配套的条款
律典中不少条款的适用是需要以其他制度的存在和配合为前提的。朝鲜前期,在制度上对前代的因袭甚多,其本国的第一部法典《经济六典》就是在因袭和损益高丽旧法的基础上修成的。金驲孙在上疏中就讲:“夫《元》、《续六典》,祖宗之法也。古今论者必曰:‘无改祖宗之法。’以祖宗虑患深、更事多,立法必无不周也。意者,《元》、《续两典》,非创制于太祖,太宗因高丽旧法而损益,如《明律》之因《唐律》耳。今之《大典》,源出于《元》、《续两典》,而因时损益……”〔75〕《朝鲜王朝实录·燕山君日记》燕山君元年五月庚戌条。这些因袭、损益自高丽的制度又有不少是来自唐制的,和明制的差异甚多。如此一来,即使是那些在明朝运行良好的律条拿到朝鲜适用,也会出现一些特殊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朝鲜人当然也要以唐律的有关规定加以弥补。
世宗十一年四月,刑曹启:
今考《大明律》祭享条云:“若百官已受誓戒,而吊丧问疾、判署刑杀文书及预筵宴者,皆罚俸钱一月……”失仪条云……。讲读律令条云……。照刷文卷条云……。盗贼捕限条云……。《唐律疏议》云:“诸大祀在散齐,而吊丧问疾、判署刑杀文书决罚者,笞五十……”《疏议》则非当时所用之律,而俸钱之罚,亦非本朝所行也。前此,上项犯罪者,不论一月半月,或以违令,或以不应,为比律科断,实为未便……请以一月准笞三十,半月笞二十,一十日笞一十,两月笞四十施行。〔76〕《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世宗十一年四月戊戌条。
刑曹所列举之《大明律》的多个条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所有这些条款均涉及罚俸。罚俸制度出现在唐律基本定型之后,〔77〕关于唐代罚俸制度的具体讨论,参见拙文:“唐代罚俸制度论略”,《史学月刊》2008年第 11期。故而在唐律中并无反映。高丽依据唐律文本创制本国法典时,自然也就没有设立类似的制度,而朝鲜的制度又多来自高丽,所以也无罚俸之制。如此一来,《大明律》中这些涉及罚俸条款的适用便成了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只能以比附的方式定罪量刑,产生了不良的后果,因此,朝鲜人便以唐律的规定取代了《大明律》有关条款的罚则部分,即以唐律的笞、杖刑代替了《大明律》的罚俸刑。
四、小 结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朝鲜前期,尽管实行了全盘“华化”的文化转型政策,全面移植并适用《大明律》,但由于明制与半岛的国情差异较大,所以《大明律》受到了“土俗”较为强劲的抵制。而《大明律》本身又存在缺陷,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就使唐律本身具有的优越性更为明显,取得了崇高的声誉和地位,深受半岛精英阶层的重视,不仅是律学的主要科目,而且还具有强大论证力,是王朝制定与论证新定法律合理性的重要依据。
其次,和唐律相比,《大明律》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然而,由变革唐律而来的这些特点却和半岛的“土俗”及其在文化转型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新传统发生了矛盾与冲突,这就为唐律发挥影响提供了空间。《大明律》具有“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特点,而轻刑是半岛的传统,故而在刑民钱谷方面,朝鲜对《大明律》中那些畸重的条款常以和本国“土俗”有深入融合的唐律条款取而代之。高丽后期以来,半岛精英阶层对纲常名教的强调日益严格,并逐渐形成了一些新传统,《大明律》中那些以礼教松弛为基本背景的关于礼教纲常的条款便不能为朝鲜的精英阶层所满意,对此,朝鲜人也常以与本国国情更为契合的唐律中的条款取而代之。
第三,因《大明律》对唐律删改过多,律典中出现了不少空白,某些条款还存在缺漏和不周延的弊病,这些问题在《大明律》被移植到半岛这样一个国情与明朝存在重大差异的社会就更为突出了,所以朝鲜人也常以唐律的规定加以弥补。
从总体上看,由于有旧“土俗”与新传统的支持,唐律对《大明律》中不符合、不适应朝鲜本国国情条款的取代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这是由唐律在朝鲜的特殊地位决定的。首先,唐律作为中国古制,是广义“华制”的一部分,采用唐律和朝鲜的全盘“华化”政策并不矛盾。与此同时,唐律早在高丽前期就已经被移植到了半岛的法律体系之中,和半岛有四百余年的融合历史,故而在某种程度上又可被看做是广义“土俗”的一部分。因此,在“华制”与“土俗”之间,唐律起到了润滑与沟通的作用。对于处于制度转型过程中的朝鲜而言,是一种珍贵的制度性资源。但是,为全盘“华化”的政策所决定,《大明律》对朝鲜具有强大的约束力,在《大明律》本身只存在缺漏、不周延等细小、局部性问题,和本国的关键性“土俗”没有重大冲突的情况下,唐律只能对这些缺漏进行某种程度的弥缝,而不能直接取而代之,其作用的发挥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
* 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