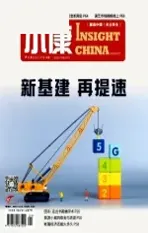再续犹太人“上海方舟”传奇
2010-02-06马欣然
文|马欣然
再续犹太人“上海方舟”传奇
文|马欣然
我们依稀知道:上海,曾是纳粹屠杀下数万犹太生命最后的庇护地。然而,两个民族在战争阴霾下是怎样的患难与共,我们仍知之太少。还好,有亲历者再次为我们谈起曾经的点点滴滴
上海画家刘小曼女士的家庭聚会很特别。2010年4月10日一早,她与同辈亲友纷沓而至上海长阳路62号的摩西会堂,这里有一套她提供的欧式餐桌椅正在展出。亲友们纷纷赶来,看老家具或许还在其次,重要的是他们可借“观看”回顾一段历史,重温发生在上海的那段犹太故事。
摩西会堂,又称“犹太难民在上海纪念馆”。
1938年,希特勒开始大规模“反犹”、“屠犹”。纳粹狂热分子走上街头,疯狂捣毁犹太人的店铺和住宅,烧毁他们的教堂,迫害、凌辱,直至大肆逮捕犹太人,一大批本已在欧洲安居乐业的犹太人顷刻间无家可归。
不计其数的犹太人千方百计想要逃离令他们生命受到威胁的统治政权。然而,当时许多国家拒绝接纳犹太难民或制定犹太人入境限额。就在这绝望的关口,犹太人发现了上海。1937年至1939年的秋天,上海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座外国人无需签证和担保就可进入的大都市。于是,犹太人带着他们唯一可携带的物品——护照,流亡上海,他们中绝大部分人在一个叫提篮桥的地方度过了一段艰辛而又不乏温情的岁月。
如今,摩西会堂中,摆在刘小曼那套老家具周围的,还有当年避难上海的犹太人的居住证、结婚证、祈祷经书等,它们作为3月初举行的“犹太难民上海情系列活动”的陈列品一同展出。而这些分属26位难民的珍贵老物件,也牵出了一个个上海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患难故事。

上海“寻根” 2006年4月27日,两名犹太人在寻找当年他们的祖父辈曾经居住于此的房间。当天,约有一百多名分别来自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犹太人参加“2006全球犹太名流代表团”访问虹口的活动。
家具传情
严格意义上讲,刘小曼应算她提供的那套欧式餐桌椅的第二位主人。其原来的主人是当年避难上海的犹太难民,后来成为美国实业家的杜德纳。
刘小曼回忆,当年自己家与邻居杜德纳一家并无深交。1949年杜德纳全家在国际犹太人遣返委员会的帮助下移民美国,刘小曼家则搬进前者的住所——昆明路60号。杜德纳家离开时,很多家具被留了下来。刘小曼至今还记得老邻居家典型的欧式陈设,“一进门右手边是衣挂区、深色的衣柜大橱、3尺多宽的单人床,一看就不是中式的,花纹很特别。”另外,这些犹太家具都是会木工手艺的杜德纳父亲亲手打造的,几十年后,当刘家人想移动它们时,巨大的衣橱根本挤不出大门。
除了留下的家具形成某种关联外,两个中犹家庭此后一直各自生活,并无往来,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后,刘家突然到访一批批蓝眼睛、高鼻子的外国人,这对刚刚迎来开放的中国人而言是件令人费解的怪事。但刘家人很快明白了,他们并非唯一一户接待外国游客的上海人家。那些坚持在他们家中每个房间依次拍照的外国人,或是自己、或是长辈曾经在提篮桥生活过。多年后,他们是带着感恩之心再回上海,感念故人,探访旧居。
到了1999年,刘家那套老家具的主人也回来了。
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上午,杜德纳带着女儿重返上海,满头白发的老人熟门熟路地走进昆明路上一个不起眼的沿街门洞,摩挲着狭窄楼梯的扶手,登上二楼,来到他曾经居住的小屋前,叩响房门。
那天不是公休日,家中本不该有人。但似乎冥冥之中的安排,刘小曼恰巧有事回家。门开了,老人被现在的屋主热情迎进房,当他环顾四周后,目光最终停留在那套颜色斑驳的旧桌椅上,雕花木椅的椅背造型如花瓣,中间还有一个镂空的桃心。犹太老人满目含泪,“这是我50年前用的家具。”老人几度哽咽,不再说话,他女儿抹着眼泪,泣不成声:“我终于见到了爸爸生活过的地方。”
临别时,杜德纳挥着手,用上海话对刘小曼说:“再会,明朝会。”此后,刘小曼与杜德纳不断书信来往,犹太老人寄来明信片、贺卡和自己在滑雪胜地度假的照片,刘小曼则寄去了自己的国画作品。
其实,住在虹口区提篮桥的很多上海居民都和刘小曼家一样,与犹太难民有过或多或少的接触。
已故上海画家陈逸飞是较早关注“上海犹太难民史”的人,他先后完成相关题材电影《逃亡上海》、《上海方舟》。《逃亡》一片讲述了维也纳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手童年避难上海、拜师学艺、最终成为艺术家的经历;而在《方舟》一片中,陈逸飞则以纪录片方式,描绘了17位上海犹太难民故地重游的情景。
陈逸飞拍摄《上海方舟》的缘由在于,1990年他在纽约举办第5次个人画展,其间遇到一位外国老妇人,她竟用地道的沪语与他打招呼:“侬好!侬阿是上海人?”陈逸飞震惊不已,老妇人随后向他叙诉了在上海避难时的往事。老人的讲述,打动了陈逸飞。于是,他飞到世界各地找到了17位当年的欧洲犹太难民,让他们重回上海故地。这些犹太人虽离开黄浦江畔已有50年,但一踏上这片使他们获救的土地,便都热泪盈眶。
资料链接
中国“辛德勒”

何凤山,这位1938年至1940年间的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为犹太人签发了多少张“生命签证”,至今仍是个谜。据一些档案资料估算,平均每月500多个,有时达900个。但何凤山生前很少提起这段在奥地利任领事时的经历。1997年,定居美国的何凤山在加州逝世,其女儿在报纸上登了一则讣告,其中一句话提到父亲在维也纳的工作。历史学者及曾经受帮助的犹太难民这才注意到他。
犹太难民辗转登上“上海方舟”
当年,欧洲难民主要经由两条线路逃往东方,大部分人从法国辗转意大利,登上轮船,穿越苏伊士运河,最终抵达上海。而另一部分难民则坐上火车,穿越茫茫的西伯利亚,向东行先到日本,再转到上海。
1938年,犹太人以每月1000人的流量涌入上海。他们一点都不了解这个城市,包括这里的气候。在潮湿的天气里,他们穿着不合时宜的厚大衣,等走出码头时,浑身已是汗水淋漓。
难民来到提篮桥地区后,各式各样的西式小店铺随之兴起。以舟山路为中心的街区,到处可见德文店招牌,奥式露天咖啡馆也出现在屋顶。这一带因而被称为“小维也纳”。少年们在摩西会馆举行成人礼,新人在屋顶咖啡馆举行婚礼,犹太人自己的文化影响了这个客居的城市。文化学者办起德文报纸,音乐家办露天音乐会演奏肖邦、德洛夏克名曲。
这些“老上海”走进石库门,来到梧桐树下,爬上小楼屋顶,他们回忆当年在上海生煤球炉、吃大饼油条的乐趣。片中一对名为保罗的夫妇说,为了纪念在上海的这段历史,结婚时,他们特别用犹太和中国婚俗分别举行了两次仪式。

融入中国 避难上海的犹太人不仅为他们客居的城市带来了各式各样的西式小店,他们自己也在生煤球炉、吃大饼油条中找到了乐趣。

《上海方舟》里还有这样一处细节,曾住在舟山路的马丁,按过去的地址寻找上海老家,但因为他出生得晚,离开上海时尚不谙世事,所以很多事记不清了。然而,就在他迷糊乱撞时对面走来一个老妇人,一见他就兴奋地喊起来“你是马丁?”之后,两位老人紧紧拥抱。
根据学者大卫·克兰茨勒在其研究著作《日本人、纳粹和犹太人——1938~1945年的上海犹太难民社区》中的记载,和马丁一样,幼年时就离沪的犹太难民至少有500人。但犹太作家索妮娅却认为数量可能更多,因为她自己就没被大卫统计在那本专著里。
索妮娅1939年10月26日出生在上海,离沪时刚满8岁。
家乡陌生,异乡却美好
当4月10日刘小曼一家正在摩西会堂聚会时,索妮娅再次重返“故乡”上海。她专程赶来参加“犹太难民上海情系列活动”的读书会。
当年避难时,尽管生活拮据,但上海却给索妮娅一家带来无可比拟的安全感。“我爸爸妈妈后来曾跟我说,万一有什么事,你随时可以回到上海,因为你有上海的出生证。”
二战结束后,索妮娅一家回到德国,她学习教育学,之后成为德语和英语老师。一直以来,索妮娅都会向学生讲述自己在1939年至1947年间的经历,她把对上海的感觉概括为两个字——感激。
索妮娅曾给学生们朗诵过一首诗,“你们终于要出发了,离开了这么久,这么遥远,再到达你们都不熟悉的家乡,你们不应该忘记上海,不要忘记你们在这里见过的稻田、宝塔和中国帆船。欧洲同龄的孩子会为此羡慕你们,因为这些年他们只有恐怖的岁月……” 索妮娅说,每每读到这儿,她都会满面泪水。
同样在上海长大的,还有杰瑞·摩丝。当年,杰瑞的父亲在历史上最丑恶的迫害犹太人暴行“水晶之夜”中被投进监狱,他母亲决定拼死一试,带着三个孩子去见盖世太保指挥官,求他准许在自己和孩子们的出境许可证上盖一个章。“让我去上海,或开枪杀了我们。”最终,勇敢的母亲带着当时7岁的杰瑞、13个月大的弟弟和9岁的姐姐成功逃亡到陌生的东方。踏上外滩的土地,杰瑞觉得这里堪比天堂。至今,他还记得和中国伙伴一起踢毽子、跳房子的情景。
丹尼尔·雅各布森同样也在上海长大。多年后回忆往昔,丹尼尔带着股孩童般的顽皮:“从学校回家只要走几分钟,但我总要逛上好几个小时,因为好多人在街上做好玩的事,在马路上还有人耍大刀、跳舞卖艺,我是如此着迷。”
在上海长大的著名生物学家卡尔·贝特汉姆,年老时重返“故乡”时,指着提篮桥地区著名的街心公园霍山公园说:“这是我们的公园。我们家住在许昌路,可以走路来。”和杰瑞、丹尼尔一样,贝特汉姆也清楚记得当年和中国伙伴玩耍的情景——“有次玩捉迷藏,我躲得实在太好。过了很长时间都没被发现,当我自己走出来时,大家早就在玩别的游戏,他们都以为我已经回家去了呢。”

苦难的印记 摩西会堂是当年犹太难民的宗教活动中心。解放后,这里曾辗转做过帽厂、药厂等,1992年被定为“犹太难民在上海纪念馆”。
或许,当年上海紧张的战争气氛会让杰瑞、丹尼尔、贝特汉姆这些来自西方的犹太孩子物质生活不如以往。然而,他们却在中国度过了一个单纯快乐的童年。尤其和留在国内的同胞们相比,他们更是幸运儿——1945年纳粹投降后,上海犹太难民开始通过国际红十字组织打听亲人的下落,结果是,所有没能逃离欧洲的家族成员几乎全部被屠杀,死在集中营的犹太人达到600万,而逃亡来到上海的犹太人,除病老死亡外,都奇迹般地生存下来。
萍水相逢,缘分难尽
如果说,上海当年无需签证担保便可进入的政策,为数万犹太人打开了一扇生命之门。而让犹太难民能够真正安定下来,更多还是依赖上海民众对他们真心的帮助。
随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殖民者把上海推入更黑暗的深渊,同时受到波及的还有避难上海的犹太难民。虽然1942年德国向日本施压准备屠杀在沪犹太难民的“梅辛格计划”没有实施,但从1943年2月起,日本当局还是建立起“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命令所有1937年后抵沪的犹太难民迁入,这个隔离区约包含有15个街区。隔离区内那些狭小、破旧的弄堂房子,在灰色的天幕下显得死气沉沉,隔离区内挤满了来自德国、奥地利、波兰、匈牙利的犹太难民。
“我们这一层里的16个人只有一个卫生间,顶楼另一个卫生间12个人共用。”犹太作家伊·贝蒂·格列宾希科夫在自传《我曾经叫莎拉》中回忆。
不过,在犹太老人弗雷迪·赛德尔的记忆里,“隔离区”的生活也有好的一面,“没有中国人对我们说,‘我们还吃不饱饭,滚吧’。” 在那段最艰难的岁月里,与“隔离区”犹太人杂居在一起的上海民众给予了前者无私的帮助——让出房间安置犹太难民居住;帮助他们寻找工作;安排犹太儿童同中国儿童一起学习。弗雷迪记得,1945年7月,一场空袭造成31名犹太难民死亡、250名难民受伤,当时周围的中国居民同样伤亡惨重,却仍奋不顾身冲入火海营救他们。
而当年的“隔离区”一带,至今也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两条犹太人居住最密集的弄堂,一度被日本人在出口焊上铁栅门,禁止出入达一年之久,被困在弄堂里的两千余人,最后大都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是居住在周围的上海市民,采用“空投”,将面饼等食物掷过去而救助了他们。
“在战争阴霾下,用‘患难与共’来形容上海人与犹太人恐怕最贴切不过。两者来往并不密切却饱含深情,萍水相逢而又缘分难尽。”作家索妮娅这样对记者说。只是,当年究竟发生了多少上海人与犹太难民的患难故事,已无人说得清。与此相关的资料不多,亲历那段历史的上海老人如今在世的也不过几十位。
或许今天,我们尚能听到这样的故事——老人王发良时常回忆曾住隔壁的一对犹太老夫妻:“他们带着一个孙女,由于家境贫困,很少点灯。”当时王发良在美孚公司做事,时常会拿些煤油接济他们。“虽然这样,我们依旧很少说话。但有一次对话让我印象非常深。”那位老先生问王发良,“What is the mightest strength in the world?(什么东西在世界上最有力量?)”王发良愣了一下,“Is nature?(自然界?)”犹太老先生则回应:“Nothing!”王发良说,他到现在才明白,这是一个难民对权力世界的感慨。
今后,随着一个个历史见证人的离开,当年发生在上海的那段犹太传奇,其点点细节终将离我们远去。或许,这正是许多中国人、犹太人一次次集体怀旧的原因——就像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者埃尔利·维泽尔所说:“每一个今天倾听的人,将来则是一个见证人。”
(本文部分人物故事素材选自“犹太难民上海情”展览)
责编 罗屿 LuoYu778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