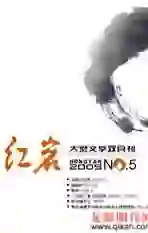我在《红岩》结交的作家朋友们
2009-10-10李耀国
一个刊物,必须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作家群,这样才能保证刊物的稿源和质量。当编辑的组稿就成为很重要的工作。而要让作家把自已的新作首先交给你,除了刊物本身的影响之外,编辑和作家之间的友谊也是很重要的因素。我参加《红岩》复刊到调离,在编辑部工作了14年,因而也结交了许多作家朋友们,虽然我己退休多年,离开《红岩》的时间更久,但是我至今仍然和他们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当重大节日,总会收到他们手机发来的问候短信和贺卡,如果路过重庆,也会来看望我,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我常常感到,在作家协会这个行业里,我虽然没有什么作品可以炫耀的,但是作为一个编辑,我是成功的,特别是在我退休之后,还被聘为一些文化单位的审读和文学顾问,至今每天还要审读大量的文稿,不能不说是社会对我的承认。在这点上,我应该感谢《红岩》,是《红岩》培养了我。
我的老师成了我的作者
《红岩》复刊时,最犯愁的就是稿源。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作家队伍正是青黄不接的时侯,而《红岩》又是大型刊物,以发表中篇小说为主,更难约到这方面的稿件,于是主编王觉就叫我们先联系自己熟悉的作家,我自然想到我在部队的战友,不过准确地说,应该是我的老师。
在飞往昆明的飞机上,我凝望着窗外明净的天空,早已逝去的往事就像朵朵白云不断涌现在眼前。我是1961年入伍的,因为参军不久就开始发表小说,受到部队重视,很快就调到昆明军区文化部学习。昆明军区在1957年以前,因为文化部长冯牧的关系,培养了一大批在全国很有影响的作家和诗人,如白桦、徐怀中、公刘、彭荆风、周良沛、季康.......但我到昆明时,许多人都因成了右派,离开部队散落到全国各地。我初见彭荆风时,他也是刚从下放劳动改造的农场回到昆明,还没有恢复军籍。彭荆风这个名字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也许有些陌生,但他在解放初期所创作的电影《边寨烽火》、《芦笙恋歌》,却对50岁以上的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由于当时还戴着右派的帽子,很多人还不敢和他接近,而那时我还年轻,不懂得什么叫阶级立场,出于对他的敬佩,常溜进他的小屋,聆听他谈文学,这对我今后的文学创作,受益匪浅。不久文革风暴乍起,我复员回到了重庆,便和他失去了联系。但凭我的直觉,彭荆风在这场风暴中也难逃厄运。后来果然听说他被投进监狱关押了8年之久,直到文革结束才平反昭雪。如今他巳担任昆明军区文化部长,仍然笔耕不辍。到了昆明,他派车将我接到宾馆,约好笫二天见面。但笫二天他在饭店请客时,我才发现同桌的还有好几家刊物的编辑,都是冲着他来的。我不免有些担心,他哪有那么多稿子打发我们这群千里迢迢赶来对他抱着希望的编辑们?因为都是同行,席间都不谈约稿的事,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明白,他最终决定把稿子交给那家刊物,主要取决于那家刊物在全国的影响和他与编辑的私人感情。果然晚上他约我单独见面时,当我提出向他约稿,他显得有些激动地说:“我对《红岩》是很有感情的,电影《芦笙恋歌》就是根据我发表在《西南文艺》(即《红岩》的前身)的小说《当芦笙吹响的时侯》改编的。”说着,交给了我他刚完成的中篇小说《雾茫茫》,后来发表在《红岩》1982年1期上。从此,荆风又和《红岩》建立了长期的联系,1998年《红岩》复刊100期时,虽然我早己离开了编辑部,但编辑部的当家人仍然不忘邀请他。去年,荆风80华诞,又是从事文学创作60年,他的女儿鸽子给我打来电话,希望我能到昆明参加庆典,我因杂事缠身,不能如约前往,遗憾至极,便给他发了一封贺信,我在信中说:“人的一生,过程并不重要,关键是看结局,你一生坎坷,但结局这么圆满,足矣!”
我到昆明,还有一个我迫切想见到的人,他就是张昆华。1963年,我从连队到军区文化部学习,接触最多的就是昆华。那时他还年轻,虽然不是专业作家,但是己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昆华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对昆明部队的文化建设上。昆华是个对作者热情而诚恳的人,不管是在部队或是复员在《云南日报》副刊工作,经他扶持和帮助的作者不在少数,有的后来成为了全国有影响的作家。去年我回昆明,见到当年和我一样从事文学创作的战友,大家不约而同地回忆起昆华当年对自已的帮助,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年我给《重庆日报》投了一篇散文,因为在昆明很难看到外地报纸,加上我又缺乏自信,所以也没有特别关注这篇散文能否发表。一天,我在军区大院散步,老远就看见昆华骑着自行车向我挥手奔来,脸上堆满了灿烂的笑容。骑到我面前,他停车递给我一份剪报,高兴地说:“你的文章发表了!”他的神情,就像自己的作品发表了一样。我接过剪报,看见昆华已在上面用红笔标明了发表的报名和时间,这使我十分感动。这份剪报是这篇文章惟一留下的纪念,我一直珍藏着,后来申报职称和出书,也因为它的存在而少了一份遗憾。每当我看见这张剪报上昆华留下的笔迹,我就能感受到昆华那颗真诚的心。我后来在《红岩》当编辑,对作者的真诚相待,不能不说是受了昆华的影响。20年过去了,我又在当年和他相识的地方见到了他,虽然时过境迁,但那份温情还在。昆华一见我,便行了个军礼,称我为“年轻的老战友。”虽然我己不再年轻。这个称呼一直延续到现在,不管时间的流逝,也不管相距多远,我们记住的,还是年轻的时代。我从昆明返回重庆不久,就收到昆华寄来的中篇小说《蓝色的象鼻湖》,发表在《红岩》1980年2期上,随即被天津新蕾出版社的一位编辑看到,很快于1981年3月出版单行本,以后又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许多著名文艺评论家也纷纷发表评论文章赞不绝口。这部中篇小说后来被中央文化部和国家出版总署联合评为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一等奖。就是这部在上个世纪80年代给昆华带来广泛声誉的作品,昆华心里却始终有着遗憾。原来当年《红岩》发表这篇小说时,因为版面的原因,对小说作了大量压缩和删减,新蕾出版社也是根据《红岩》的刊发稿出版的,原稿中的许多内容,读者一直无法看到。然而昆华的这个遗憾,终于得到了弥补,2006年,晨光出版社全文出版了《蓝色的象鼻湖》,使这部早己绝版的作品,重新闪耀波光浪影,重新发出野象的吼声......
我在昆明,我还拜望了许多当年蜚声文坛的军旅作家,也是我的战友和老师,如曾写过《边疆晓歌》的黄天明,这部长篇小说后来成为支边青年人手一册的教科书;还有写过电影剧本《五朵金花》的公浦;以及写过具有浓烈云南边地风情的《赶马人的故事》的李钧龙......他们也热情地给了我不少新作,虽然《红岩》最终没有采用,但是并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战友情谊。
还有一些我当年结识的军旅作家,他们己转业离开了昆明,如写过《金色的群山》的吴源植、写过《在昂美纳部落里》的郭国甫,他们己转业回到了江西。我最遗憾的是在昆明不能见到张勤。张勤原和我在一个部队,我参军时,他在全国已是很有影响的作家了。茅盾在《1961年短篇小说欣赏》中,对他的短篇小说《民兵营长》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当时在师文化科,离我所在的连队很近,我不时带着自己的初稿,登门向他请教,张勤总是不厌其烦地指导我,我初期发表的作品,很大程度得益于他的帮助。后来他调到北京《解放军报》工作,便推荐我接替了他的位置。直到1983年我第一次到北京组稿,这才了却了我的心愿。当我们离别近20年相逢时,对彼此的变化,难免有些感伤,张勤已是满头白发了。这次我带了他的一部中篇回来,很快在《红岩》发表了。以后张勤主要从事长篇小说创作,并且题材和风格,也很难适应《红岩》了,虽然他没有再给《红岩》寄稿,但是我们的友谊并没有因此而中断,至今我们还经常打电话互致问候。
在我的战友和老师中,在文艺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冯牧了。虽然我当兵时,冯牧早已调离昆明军区,后来他到中国作协任《文艺报》主编,但由于他对云南和部队的深厚情结,十分关注云南和部队的文学创作。我初次见到他是在1962年5月,我到大理军部出席“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座谈会上,也许我是出席会议最年轻的,引起了他格外的注意。会议空隙,他便找到我,要我和他通信,我和他的通信一直持续到文革中他失去了自由。我调到《红岩》后,很想和他恢复联系,但我又担心他己忘记我了,因为我知道冯牧接触的作家很多,而我又是毫不知名的。1981年王群生到北京改稿回来,向我谈起他去见了冯牧,无意中提到我在重庆,他便要群生给我带来口信,要我“勤奋”。我知道,他是没有在杂志上看到我发表的作品了,也许他对我还有所期望。以后我到北京,总要到他家里坐坐,在那儿不仅可以听到许多文艺界的最新信息,还可以见到许多著名作家。特别使我感动的是,《红岩》在1989年发表了一篇反映四川公路建设的长篇报告文学《噫!蜀道》,交通部和《红岩》联合在北京召开作品研讨会,考虑到冯牧在文艺界的影响,若他能出席并主持会议,将会大大提高会议的规格和影响,于是我给冯牧打了电话,他很爽快地答应了,由于冯牧的莅临,京城许多著名作家也跟随参加。在我的印象中,这是《红岩》复刊以来在北京召开的最有影响的一次会议。冯牧1999年去世后,我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但当中国作协征集各地作家写的纪念文章集结出版《远去的冯牧》一书时,我却没有勇气寄去,我内心始终有种羞愧,我让一直关心着我的冯牧失望了。
一篇作品改变了
一个人的命运
1989年初,我突然收到一封署名叶晓玲的来信,信中说:“尊敬的李老师,也许你己记不得我了,如果不是八年前你鼓励选发了我的笫一篇文学作品,我也不会有今天......”我接触的作者很多,叶晓玲是谁?我实在记不起了。不久我到成都出差,特意到《四川日报》副刊部,找到了叶晓玲。当我笫一眼看见她,我就认出她是谁了。原来在1981年春,成都军区举办了一次笔会,邀请了我参加。我记得参加笔会的有严歌苓、樊晓玉等人,她们己有不少作品见诸于报刊,自然引起我格外关注。严歌苓后来去了美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创作了不少优秀作品,去年轰动一时的陈凯歌导演的大片《梅兰芳》,就是她写的剧本。叶晓玲当时还是甘孜里塘一个野战医院的小护士,人长得很瘦,高原的阳光晒得她的皮肤呈紫红色,显得活泼、天真而富有朝气。这次笔会,实际上是一次改稿会,与会者多是部队的基层业余作者,带有初稿来修改的,我被邀请,是因为需要一个发表阵地,我是来选稿的。我看了所有的稿子,只看中了叶晓玲那篇,虽然还缺乏思想深度和艺术技巧,但是却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真情实感,我提了一些意见让她修改后,决定将她的稿子留下,带回编辑部推荐给主编审定。笔会结束时,她对我说:“草原盛开鲜花的时侯,简直美极了,你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对于我来说,那个地方实在是太遥远了,我至今没有去过,而她在笔会中修改的稿子,却在《红岩》上发表了。以后她没有再给《红岩》投稿,我们也就失去了联系,她在我的脑海里渐渐地消失。没有想到,当年在《红岩》上发表的这篇作品,竟改变了她的命运。她对我说,她复员之后,能够被《四川日报》接纳,靠的就是这些发表的文学作品,而在《红岩》上发表的笫一篇作品对她来说,是最重要的, 她因此而有勇气在这条道路上坚持走下去。作为一名编辑,因为选发了一个初学者的稿子,无意间改变了她的运命,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大好事。
像叶晓玲这样的例子,在我的朋友中,不乏其人。在过去的那个时代,许多有才华的人,因为政治原因,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很早就进了工厂,当了农民,由于对生活的热爱,即使在严酷的环境中,仍然坚忍不拔地去追寻着自己的文学之梦,从而改变了自已的人生道路。我又想起了一个人,一个被阶级斗争的风暴吹得四处躲藏的流浪汉......
复刊在即,稿子却没有凑齐,正在为难之时,一天,主编王觉告诉我,说合川有个叫邓兴林的作者,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寄给《四川文学》,因为《四川文学》不发中篇,已将稿子退了,但他们认为写得还不错,建议我们找来看看。由于不知道确切地址,笫二天我赶到合川,先到县委宣传部打听。接待我的副部长正好知道这件事,他告诉我,邓兴林由于是个地主子女,在农村受尽了折磨,从小就跑到外面四处流浪,最近才落实了政策,安排在七涧中学当代课老师。于是我又乘长途汽车,赶到七涧己是傍晚了。七涧中学坐落在一个小山上,茂密的树林掩盖着校舍,在夕阳的映照下,显得十分幽静,我找到校工,他热情地带我到食堂去,还没走到食堂,他就指着一个正蹲在路边吃饭的人对我说:“他就是邓兴林。”我上前去对他打了个招呼,他扭过头来,一脸的茫然,眼神里有种不易觉察的恐惧。我想,他也许把我当作搞外调的了。我说明来意后,他满是皱纹的脸,才露出一丝笑意。他慢慢地站起身来,洗得灰白的蓝色中山服皱巴巴的,胡子上还残留着饭粒,一副邋遢的样子,实在不像一名为人师表的教师,只有戴着的那副深度眼镜,才使人感到像是有文化的人。他领我到他的寝室,找出一摞稿纸,纸张很差,但字却写得很工整,我很快瞟了一眼标题,上面写着《写给马克思的报告》,我估计有七八万字。我来不及拜读,想赶末班车回去。不料当我赶到车站,发现末班车早已开走,我只得又返回学校求宿。这一夜,我和邓兴林摆谈了很久,他的身世引起了我更多的同情,他出身一个地主家庭,从小就受到不公正待遇,只好离家出走,到处流浪,当过江湖郎中,卖过假药,多次被收容遣返,捆绑吊打,又一次次脱逃......我渐渐意识到他写的这部中篇小说的内容了,他是用血泪在控诉极左路线对人性和人的尊严的践踏。尽管当时“伤痕文学”己风靡全国,但邓兴林这篇小说也写得过于灰暗和低沉了,我带回编辑部讨论时,大家觉得应作大量删改,因此在《红岩》复刊笫1期发表时,只有三万多字,标题也改为《苦难》了。不久《红岩》召开创作会议,自然邀请了邓兴林参加,我这次见到他时,他的模样已大大改变了,依然穿得很朴素,但却很整洁,脸上的笑容也多了。他告诉我,他己正式调到县文化馆工作了。由于他的工作主要是创作曲艺节目,文学作品写得少了,我们也就渐渐失去了联系,2005年夏天我去合川讨论电视剧本《钓鱼城》,会上见到县里的文化干部,才知道邓兴林已经去世,我感到深深的惋惜。
我还记一件使我至今仍然觉得好笑的事。一次我到成都组稿,路过一家新开张的火锅店,门口贴着一张告示,上面写着:“成都著名作家贺星寒最近在《红岩》上发表一篇文章,若能说出标题,免费招待火锅一顿。”我暗自得意,进店找到老板,我对他说:“这顿火锅我吃定了。这篇文章的标题叫《矮个高身影》,对不对?”老板显得有些惊讶:“你咋会晓得的呐?这期刊物还没有出厂嘛!”我自豪地笑了笑:“我就是这篇文章的责任编辑,未必还说错了?”老板知道遇到了真人,忙让我坐下,一边端茶送水,一边对我说:“贺星寒简直把我踏屑惨了,不过我就是他写的那种人。”其实一看文章的标题,就明显带有贬意。文章中的主人翁叫罗亨长,是个热爱文学,但又缺乏才气,跻身文学圈里,出了不少洋相。在发稿之前,由于担心损害名誉权,我特意给星寒打了电话,问他罗亨长是否同意发表?星寒笑着说:“你尽可放心,罗亨长看过稿子,他不仅同意发表,还坚持要用他的真名。”我想这篇文章也许让罗亨长有所醒悟,他己开始寻找自已生活中的真实位置,他所开的这家火锅店,办得很有文化特色,他取的菜名,就很有内涵,如鸭肠叫浪里白条、肫片叫雄鸡高唱、藕叫观音断臂......他的文学知识,终于派上了用场。过了几年,我到都江堰市组稿,又碰到了罗亨长,原来他在这里办起了连锁店,他的生意是越来越红火了,而贺星寒却己作古,人的命运真是难以预料。
我的作家朋友成了
影视圈的名人
电影《焦裕禄》、《飞虎队》、电视连续剧《黑冰》、《苦菜花》、《叶挺》的导演王冀邢对我说过,他和其他导演相比,他的优势在于他发表过文学作品,具有文学功底。正是因为他的文学素养,才使得他导演的影视剧一部部获奖,受到观众的欢迎。在我的印象中,他的文学作品,基本上是在《红岩》上发表的。记得有一年春节期间到成都组稿,我选择春节是因为容易找到作者。那时全国各地的刊物经常举办笔会,拉着作家到处游山玩水,意在联络感情。我借上门拜年的机会,向冀邢索稿。冀邢告诉我,他手里正好有一部刚完成的中篇,但是为春节过后四川省作协和《当代》杂志联合举办的笔会准备的。如果《红岩》想要,一是要取得省作协副主席周克芹的同意,因为这次笔会是由他负责的;二是《红岩》要承诺近期发表出来。我取回稿子,当晚一口气读完,深为作品中人物的命运震撼,激动万分,第二天一早,我就迫不及待地给主编马戎挂了个电话,把情况汇报之后,马戎爽快他说:“那你就答应他,下期就发。”我仍然不放心地问:“马老,你还没有看过,万一你认为不行怎么办?”马戎的回答使我至今难忘,他说:“都是老编辑了,怎么连这点判断力都没有?”主编的信任,使我十分感动,我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冀邢,并将稿子带回了重庆。春节过后,马戎一上班就看了这部作品,也认为写得相当不错,发表是没有问题,但如何向克芹解释?马戎有些为难了。我让马戎放心,这件事由我来处理,我相信克芹对《红岩》的感情和我们之间的友谊。我给克芹打了个电话,希望他支持,他也不好再说什么,毕竟《红岩》当时也是省内的刊物。后来我到成都去他家里,他还开玩笑地说:“耀国,你现在一在成都出现,成都的刊物都很紧张,都说李耀国的魔爪又伸来了。”冀邢这部12万字的中篇在《红岩》发表时取名为《十点钟的太阳》,许多读者看了这篇小说都认为是《红岩》近几年发表的最好的一部作品。不久当冀邢成了导演,他亲自将这部作品改编为30集电视连续剧,改名为《兄弟》,拍摄场地就选在老文联大院,这是因为他过去经常来《红岩》改稿,熟悉这块地方,并有着深深的感情。我也被他拉去客串了个角色。冀邢后来去了北京,我们的联系也就很少了。但他在给我的信中曾写道:“你为我做了很多很多,我将永远珍惜我们之间的友谊。”
我常常想到,冀邢这部作品能够在《红岩》上发表, 除了我对作品的判断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主编对编辑外出组稿时给予的信任,如果我不能当面承诺,这部作品就会被其他刊物拿走。我还清楚地记得,1983年我到北京组稿,当时中国作协举办了文革过后的笫一期“文学讲习所”(现改名为鲁迅文学院),录取了一批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来京深造,因而“文讲所”的驻地便成了各地文学刊物组稿的重要目标,众多的编辑在学员的寝室里窜来窜去,简直成了自由市场。我找到四川南充来学习的魏继新,他因为写了《燕儿窝之夜》而名声大振,但他对《红岩》还是相当有感情,《红岩》在1982年举办的笫一次笔会,就邀请他参加过。他对我说,别看这么多编辑来组稿,实际上作家手中的稿子都不会轻易出手,不管你编辑当面说得多好,大家还是担心你作不了主,稿子给你带回去,万一被主编枪毙,或是积压很久,对于急于想发表作品的青年作家来说,觉得太不值了。你要约到稿子,除非你有决定权。我打电话向主编马戎作了汇报,马戎对我说:“你看了认为不错的就带回来,这批青年作家都有一定的功底,相信不会差得太远的。”有了主编的授权,我选了一批稿子带了回来,基本都在《红岩》相继发表了。我记得有陕西作家王蓬的中篇《笫九段邮路》、山西作家京夫的中篇《光电声色》,以及湖南作家聂鑫森的一部作品,还有其他作家的,我已记不清了。
至今和我还保持着密切联系的作家要算雁宁了。我认识他的时侯,他还是达县师专的一名学生。由于对文学的痴迷,也由于勤奋,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的文学作品在全国各地刊物频频出现,其中许多作品在全国获奖,因此他和国内很多刊物的编辑都有着广泛的联系,但是雁宁不管在什么场所,总会称我是他的“启蒙老师”,这使我感到很惭愧,尽管雁宁早期的作品有些是在《红岩》发表的,但是他的处女作是发表在《重庆日报》副刊上,他这样抬举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一直保持深厚的友谊。那时重庆还隶属于四川,成都便成了文化中心,雁宁常到成都开会或改稿,重庆便成了中转站,他和达县一帮作家如谭力、杨贵云等就到我家里小憩。那时要弄到一张火车票和轮船票是很不容易的,我经常为过往重庆的作家搞票,花费了不少精力,因而也在文联造成一种印象,认为我不务正业,但恰恰这种不务正业,使我结交了不少作家朋友,使他们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最好的作品给我。我在《红岩》期间,发稿量和获奖数是最高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雁宁是个很现实的人,也许少年时代穷怕了,他想靠写作尽快富起来,于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他转向写通俗小说,现在40岁以上的读者也许还记得,当时雪米莉的系列小说铺天盖地,这就是雁宁的杰作。其实雁宁还是很爱护自己的名声的,他写通俗小说不用自已的真名,他还写过武侠小说,用的是青莲子,蒋子龙夸奖他“写什么像什么”。这也给雁宁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也许他是中国靠写作最先富起来的作家,他在成都早就买了别墅,我到成都,一般都住在他家里,不仅他夫人做的饭菜可口,更重要的是在他家里可以见到很多知名作家。雁宁交际很广,对人诚恳,很多外地作家到了成都,都会找上门去,你的组稿任务,便可在他家里完成。我离开《红岩》以后,刘阳继续和他保持着联系,后来我在《红岩》上看到著名作家周梅森、赵玫、王干、陈源斌的作品,我心里就明白刘阳是在什么地方认识他们的。现在雁宁去了北京,主要从事影视剧的创作,正好我退休之后,又到电视台的传媒公司抓剧本,正好有了更多的合作机会,我所在的公司投拍了他的《深度打击》和《首富》,另有一部大片也正等着他来担任编剧。但是雁宁却常对我说:“其实我还是更喜欢写纯文学作品,我还有很多生活经历没有写出来,等过了一段时间,我还会静下心来完成我的夙愿。”
我离开《红岩》很久了,但我一直很怀念那段生活。我在《红岩》工作期间,条件还相当艰苦,编辑部没有一张像样的桌子,房间也没有空调,夏天酷暑难耐的时候,我们讨论稿件或开会学习,就跑到楼下的文联礼堂,穿着短裤,赤膊上身,连老同志也不例外。文联党组书记王觉、主编马戎、副主编杨甦和熊小凡都长得很瘦,毫无遮掩地暴露出搓衣板似的排骨,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好笑。直到赵晓铃来到编辑部后,这种不雅观的现象才算改变。
1992年当我调离《红岩》时,我是很不情愿的,无奈这是组织的安排。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红岩》情结也在渐渐淡去,不久前因为搬家,在清理资料时,找出了一大堆申报职称时我编辑的作品,觉得对我已再没有什么用处,于是付之一炬。我当时以为,我和《红岩》的关系也就从此了断,没有想到,当现任主编刘阳为纪念《红岩》复刊30周年约我写篇稿时,我才知道,我是作为历史永远地留在了《红岩》。而在写这篇稿子时,许多早已逝去的往事又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每当我写到早己去世的《红岩》的老编辑王觉、杨甦、熊小凡;作家冯牧、周克芹、贺星寒、邓兴林的名字时,我就禁不住热泪盈眶。我希望现在《红岩》的年轻编辑能永远记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