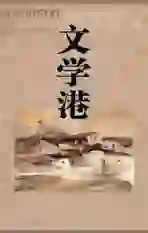民谣记述(二题)
2009-09-30李新立
李新立
炮台上的烟火。炕眼门。锅底的烟墨,年三十的夜。
——民谣《四大黑》
炮台上的烟火
麦黄六月,正是雷雨多发季节。天晴格朗朗的,北边就突然涌出几朵白云,慢慢地。由白变灰,越积越多,越积越黑。从北边山口卷进来的风,顺势掠起田野上的土,在禾苗、树梢、屋顶上空弥漫、膨胀。乡亲们说:“黄风土雾来了。”雾是土做成的,风是黄色的。站在屋檐下,可听见千军万马纷至沓来,横扫而过。不一会儿,一道闪电从黑云中钻出。呈放射状伸向远方,雷声滚动的时候,雨幕和着冰雹,没头没脑地砸落下来,夯一样,落地有声。暴露在田地里劳作的人们和成熟的庄稼。面对自然的淫威,显得渺小、无奈,我们几乎可以听见人和物的叹息声。
为了对付雷雨,村里决定在北边的山顶上建一处炮台。站在村庄的任何一个位置来观察四周的地势,北山并不是最高的山峰,可考虑到雷雨一般多从北边发起,北山虽然不高,也就成了拦截雷雨的“要冲之地”。从此,每到天上的灰云潮一样涌起时,我们就会听到极具节奏的“铛哧、铛哧、铛哧”的声响,那是炮手们为钢炮填充火药时,钢钎与大锤相撞发出的声音。他们捣实火药,用黄土堵塞好炮口,然后在炮口置放一块瓦砾——这个瓦砾将带着热气进入云层,和高空的冷空气进行较量。因钢炮的威力巨大,人们就又尊它为“铁将军”。几乎整个夏天,村子里的空气里都漂浮着青草、麦子、苜蓿的混合味儿和火药燃烧过的硫磺味。
炮台是村庄里的禁区,不允许闲杂人靠近,但谁也禁止不了孩子们的好奇心。一天中午,我和伙伴轮流盯着看守炮台的人是否回家吃饭。发现他回家后,我们顺着北山顶的路,急匆匆爬了上去。小心翼翼地接近炮台上的那间小屋,趴到用木头套成格子状的窗户往里一看,总算弄明白了这里的秘密。简易的房子里,立着大中小三门钢炮。每门炮上绑着一节红绸带。看上去神秘、威风。据说,雷雨初发时,一般先请二将军上阵,如果雷雨来势凶猛,同时请大将军助阵。三将军很少上阵,三将军性烈,轰隆一声呼啸,飞出的瓦砾必然在空中划出尖利的怒号,大半个炮身也会陷入土地中。我看着默默挺立的三门钢炮,心中不禁一阵发紧。在山村,它们是佑护庄稼丰收的神器。
那时,很多村庄都有类似的炮台,火药都是村子里自己加工的。那些风干了的树根或者木段是加工火药的主要原料。快要入冬时,饲养院里的那个大灶膛,一直在烧这些木头,甚至。队里还向每户人家摊派了任务。木头不能燃烧得只剩下浅白色的灰,先得烧制成木炭,收集到一块儿后,用石碾子磨着粉末,再用细筛子过掉渣滓,兑上一定比例的硝酸甘油和硫磺就算完成了。好成色的火药细腻,两个指头揉搓绵如面粉,燃烧快,留下的硫磺成分少。炮手们把制成的火药管理得十分严格,绝对不送给他人使用。我和许多孩子们一样,有一个半匝来高的小钢炮,过年时节拿出来放几下,给因贫困而无味的春节增加了不少喜庆。可火药一直是我们难以解决的问题。便依照大人的做法,自己加工。于是,腊月里有那么几天,我的脸是黑的。连手掌上的纹路里面也是黑的。前些日子老家修葺房屋,竟然从一堆旧物中翻腾出了这只小炮,不由地怀念起昔日时光。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附近一个村庄的炮台上的三位老手,经常玩火药的大人们,不知什么原因,将炮台的火药不慎引燃,可想而知,那是一场不小的灾难,大半个天空被火光染红,空气里充斥着火药燃烧时的硫磺味,山下的人们看见三个火团在奔跑,在奔跑……自此,我对火药敬而远之。
给你漫个“花儿”
那一年,有一条叫“向阳红”的水渠从村庄穿过,浩浩荡荡地水利工程专业队在我家门前屋后驻扎了下来。几个月中,他们把我家院后的大山劈去了一小部分,在那平整的土面上用铁锨刻下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八个整齐的大字。那时我上小学,好像家庭作业不是很多,那些日子里,一旦放学,我喜欢往工地上跑,去看他们热烈的劳动场面,是的,那可真是红旗招展,人来车往,
“一派社会主义建设的繁荣景象”。
其实。他们不是什么真正的工程专业队,都是从邻近的生产大队抽来的精壮劳力,男女老少都有,还有我们家的亲戚,所以,那一段时间我们家特别费开水。工程专业队有一位姓王的大叔,个子低低的,脸膛黑黑的,大概四十多岁,据说没有结过婚,一个人孤零零的生活着。我想搞清楚他没有结婚的原因,但可能是由于我的年龄太小,没有谁愿意告诉我。虽然如此,他的“花儿”却漫得特别好。工程专业队中午歇缓的空儿。男男女女却都喜欢往他身边凑,并且你一言我一语:“给咱来一支。”“漫个好听的,打个乏气。”他总是谦逊着不肯。如果有谁给他敬上一锅旱烟,或分给他一点糜面馍馍,他便会应允了。
“山里的野鸡红翎子,
不叫哥哥叫名字。
山里的野鸡白脖子,
给妹打上对银镯子,
山里的野鸡红冠子,
给妹打上对金簪予。
镯子簪子妹不爱,
要和哥哥过上一辈子,”
他的声音不是很高,平常那种,但漫得十分婉切,十分动情。并且字句清晰,大家都能昕得见、分得清,好像是天生的漫“花儿”的材料。起调的时候,先低低地“嗨……哎……哟……”,继而猛地一停,紧接着细雨一般洒开,好像专门是为抓人的心似的。唱完后,大家都叫着好。有人意犹未尽,大声说:“再漫一支,再漫一支。”也可能是他漫得高兴了,并不推辞,接着就来。
他漫“花儿”的时候,有些男男女女的嘴巴一张一合,跟着他的调子,小声地哼着。刚唱完,有几个男的把几个妇女推搡着,叫给姓王的大叔给个舌头。有几个妇女嘻笑着翻身跑了,有几个妇女半真半假的要姓王的大叔主动走过来,然后才给个舌头。他看着大家这么高兴的样子,也傻傻地笑着。这该是一个多么和谐而且美妙的时刻!数十年后的今天,我依然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位漫“花儿”的姓王的大叔。他的人生经历,或许曲折多难,背后的爱情故事,也许凄婉动人……
(选自浙江作家文学论坛《文学港》精华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