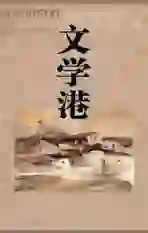老宁波小宁波的口头禅
2009-09-30张冠贤
张冠贤
老一辈人的中秋,大概是随着金桂飘香而至的,而在我这样的“80后”记忆里,提醒我们中秋将至的。总是一盒盒一袋袋包装精美的月饼。它们让我想起远在苏州的爷爷,以及他那句让我纳闷很久的话——“要说月饼啊,还是阿拉宁波的好吃”。
爷爷最喜欢说“要说什么啊,还是阿拉宁波的好”,简直就是他一辈子的口头禅。
爷爷是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老宁波”,高中毕业后到杭州上大学,之后曾赴南京教书,最后又定居苏州。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两大人间天堂都呆过了,可打心眼里觉得样样是宁波最好”。他总惦记着城隍庙的小吃,惦记着三北豆酥糖,就连风景都说“自然是好山好水的宁波美”。
我猜想这是爷爷的固执,近60年的离别早已厚重地美化了记忆中的故乡,在反反复复的思念和回忆中,家乡已成为一个近乎完美的绘图。
爷爷在外漂泊这么多年,不知经历过多少落魄和苦难。而每当面对苦难,远方的故乡就成了他最大的慰藉,因为那里,有家,有根。因此,我明白爷爷为什么总是带着甜蜜、向往却又心酸的表情。说着他的口头禅。
还记得。去年我高三毕业,以一分之差与心驰神往的学校失之交臂,录取我的是宁波大学。得知消息,我的眼泪不断往下掉。我生在宁波,长在宁波。只想趁着读大学。背上行李,去往远方,看看不一样的风情。
那段日子里,心急又担心的爷爷总是打电话来安慰我。早已忘记了他做的各种理性分析,却还清楚地记得爷爷一直重复着。“留在宁波,多好啊!爷爷羡慕都羡慕不来!你年轻,觉得外面的世界总是好,可爷爷却觉得能在咱们宁波读书,是再好不过。”
我早已听了太多遍爷爷的“宁波最好”,心中只觉得爷爷守旧,带着一肚子不甘到学校报到。
大学开学晚,还没来得及认清每个同学的脸,就赶上了中秋节。这是我在这片土地上过的第19个中秋节,却是我在大学度过的第一个中秋节。
作为本地人的我,中秋能够回家与爸爸妈妈团聚,但大多数同学只能在电话里和家人互道节日快乐。都是第一次离开家乡的孩子,初入学校的不适应夹杂想家的情绪,让他们分外失落,有的甚至躲在被窝里哭。没想到,学院送来了一份礼物——每人一个月饼,包装上还写着学院对我们的中秋祝福。那是一个小小的月饼,果味的馅,没有常见的精致包装,可放在手掌中,却透着一股长长的暖意。望着周遭同学的微笑,我忽然觉得,这大概会是我们吃过的最美味的月饼。
紧接着,学校又送给我们一份节日礼物——精彩纷呈的中秋诗会。2008年是个不寻常的年份,中秋佳节的思乡之情。汶川地震后的感动、感激、感怀之情,北京奥运会点燃的爱国之情,每一首诗都让台下的观众动容。但没有人知道,坐在角落里的我,在最后一首诗的最后一个字结束时泣不成声。
那是一首追忆宁波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诗,屏幕上闪过的照片中。一张张一幅幅都是如此熟悉的画面,灯火辉煌的三江口,国际品牌齐聚的天一广场、万达广场,巨轮云集的北仑港,长长的杭州湾跨海大桥……每一张画面都引来同学们由衷的赞叹。这些印在我的成长轨迹中,我早已习以为常的种种,第一次让我骄傲和自豪到热泪盈眶。
在那个中秋,我在这个我最熟悉的城市,感受到了一种崭新的感情,那是一种眷恋,一种不舍得离开的眷恋。
我开始珍惜能在这块土地上驻留的时光,我开始明白爷爷的口头禅。我喜欢每个周末回家时看到的变化——刚竣工的永丰桥、庆丰桥。在建中的莱福士,动工的地铁,新开张的和义大道……每当看到宁波的变化,我总忍不住在电话里告诉爷爷,我喜欢听他的口头禅,因为我在心里深深地认同着。
我也喜欢经过那些我再熟悉不过的大街小巷,找一找我曾经最爱逛的店,我喜欢坐上公交车可以安心地闭眼小憩,因为即使睁开眼不是我的目的地,也不怕迷失回家的方向。这个如此熟悉又日新月异的城市,只有她能让我安心又欣喜。
直到有一天,和大学同学争论哪里的杨梅好,竟冒出一句“要说杨梅啊,还是我们宁波的好!”惊讶地发现,爷爷的口头禅,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我的。
转眼一年过去,这是我在宁波度过的第20个中秋节了。能和父母一起,在自己眷恋的土地上过中秋,再欢喜不过,再圆满不过。而我知道,爷爷也会在这个月圆的日子里,眺望这片他眷恋着的土地。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吃着鼎鼎有名的苏式月饼,爷爷依然魂牵梦萦着家乡的月饼。
老宁波和小宁波,我们认识的宁波或许有太多不同,我们尝过的月饼或许有太大区别,可我们在这日子里,有一句同样的口头禅——“要说月饼啊,还是阿拉宁波的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