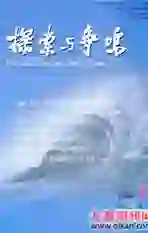“五四”所昭示的历史规律性要素
2009-07-28徐清泉
徐清泉
内容摘要“五四”昭示出的事关国家和民族发展的规律性要素,突出体现为:只有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有机统一”的先进力量,才能最终成为引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主力;任何时候面对落后的东西都需要有破旧立新的勇气和能力;真切关心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志士仁人总会适时涌现;文化创新是国家和民族发展进步的策动力之一。
关 键 词“五四” 主力 破旧立新 志士仁人 文化创新
历史上的“五四”,是一个具体的政治事件、革命事件,但它也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分水岭,是中国经历长期量变后发生质变的开始。一个具体的“五四”标示了一个时代。以青年学生罢课、工人阶层罢工、工商业者罢市等“救亡图存”活动为高潮的五四运动,只不过是整个“五四”的一个时代序幕。如今,“五四”虽已成为了记忆中的历史,但“五四”的影响可以直抵百年甚至更远。“五四”昭示出的事关国家发展和民族前途的规律性要素,正是我们今天反复重读“五四”时需要关注和提炼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一,既尊重规律又追求先进才能成为引领发展的主力。应当说,中国共产党是五四运动的最大受益者,是“五四”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最大继承者和发展者。五四运动尽管爆发于1919年5月4日,但它从酝酿到爆发,再到影响扩散,却整整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期。整个“五四”,为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诞生到随后的不断发展,提供了较为充分的干部准备、思想准备,也为党日后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良好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及舆论基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五四”昭示出它以后的时代是一个高扬“爱国”和“进步”、追求“民主”和“科学”的时代,也是一个西学(包括马克思主义)东渐、现代性启蒙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所有以旧秩序、旧权威、旧传统及旧利益卫道者和保护者自居的保守势力,所有对既发的社会变化无动于衷、麻木不仁的人,都成为了最不合时宜、最有可能被时代所抛弃的人。
在此情形下,究竟谁能成为引领中国未来发展的主导力量,事实上就成了一个亟待现实回应的重大问题。而在这个时代,恰恰有一批历经“五四”个性觉醒洗礼且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人,适时聚集起来,走到了历史的前台。回望五四运动9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可以发现,唯有能够认清并遵循历史的发展规律,并能及时巧妙地把握历史机遇的社会力量,才能成为引领时代发展的主人。中国共产党用极富感染力的、极合时代民意的社会实践成为引领时代发展的主人。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所宣称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因此他们能够最终成为引领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的主力。
第二,面对落后的东西需要有破旧立新的勇气和能力。“五四”扯起的大旗首先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传统礼教束缚。“五四”的号角一吹响,就打破了以往的历史纪录,它在从未有过的空间范围内、时间跨度内最大程度地动员起了全国各个阶层的民众,把斗争的矛头同时指向了多个讨伐的对象。一是将革命和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肆意践踏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帝国主义列强。尽管这些帝国主义列强大多具有坚船利炮的实力,具有觊觎和侵略中国的野心,并且大多曾以“八国联军”既得利益诉求者的身份侵略过中国,但是“五四”斗士们照样无所畏惧,勇敢抗争。二是将批判和革命的矛头直指儒家旧礼教旧传统,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尽管儒家封建礼教具有几千年的厚重坚固的传统,并且早已通过社会历史积淀的方式渗透到了社会公序、宗法规约、祖训家传及民族心理的方方面面,但是“五四”斗士们却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勇敢地挑战它。最重要的是,“五四”斗士在向帝国主义和封建礼教大声说“不”的同时,还能设法拿出一整套用以取代帝国主义和封建礼教命定的旧秩序、旧传统的愿景方案——这就是被高度概括了的“五四”精神核心内容:“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具有现实说服力的地方在于,“五四”斗士及随后成长壮大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百废待兴的中国大地上,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式,将愿景方案付诸实施到了具体的治国理政及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
这种“既破又立”,正是将扬弃批判和开新创造实现了有机的结合。“五四”斗士的智慧之处就在于:他们既抨击批判帝国主义贪婪侵略、丑陋自私的一面,但也同样学习借鉴源自帝国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如马克思主义学说;他们在批判儒家传统中的封建糟粕的同时,也对儒家思想中诚、信、义、勇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给予扬弃性继承。艾思奇指出:“五四文化运动无情地反对了中国民族文化中一切陈腐的东西, 但并不是绝对否定了中国民族文化。”而且,“五四文化运动曾介绍了各种西洋的学术思想, 但不能说这新文化的内容仅只在于外来文化的输入”。输入外来文化的“真意义”“在于帮助建立新的中国民族自己的文化”,也就是说,“必须根据它的前进的实际任务,发展自己民族文化中的优秀传统”,而“不是依靠外来文化的模仿”。[1]以往一些民粹主义者及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检视“五四”时,大多论定其对于中国文化传统具有割裂作用,其实这种论定难免流于主观和表象。因为在传统中真善美的东西必定也是具有生命力的。“五四”精神启示我们,面对势力强大、阻碍发展的旧威权,面对传统中落后的东西,不仅需要具备扬弃批判的勇气和能力,而且更需要具备开新创造的勇气和能力。
第三,真切关心民族发展的志士仁人总会适时涌现。“五四”发生前的中国,本来就体现出国家积贫积弱、民族水深火热、政府腐败无能的诸多病象,为此,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及鲁迅等一批志士仁人,始终都在奔走呼号。当时,也有不少人对于国人能否摆脱礼教及专制的束缚充满了忧虑。马一浮在1904年的留美日记中就表露出和后来的五四运动主将陈独秀一样的情绪,他认为,“中国经数千年来,被君权与儒教之扼,于是天赋高尚纯粹勇敢之性,都消失无余,遂成奴隶种姓,岂不哀哉”。[2]特别是鲁迅为了唤起国民自觉性,更是做出了长期呕心沥血的努力,他还一度对国民底层大众的麻木不仁感到悲观失望,但是“五四”的发生特别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红色进步力量的出现,让他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显然,先前以来的历史尤其是“五四”以来的历史均一再表明:中国并不缺少有血性的志士仁人。每当国家民族危难时刻,总会有志士仁人勇敢地站出来。“五四”的发动靠的就是他们,因为他们深知自己的前途命运已经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密不可分。“五四”及其开启的革命时代,实际上就是志士仁人唤起更多的民众为国家民族命运展开殊死抗争的时代。“五四”参与者傅斯年在《中国狗和中国人》中说得好:“我对这五四运动所以重视,为它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人类生活的发挥,全以责任心为基石;所以五四运动自是今后偌大的一个平民运动的最先一步。”[3]
从一定意义上说,“五四”就是志士仁人唤起民众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头驴子身上加稻草的开始,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断推进,随着稻草越加越多直至最后一根稻草的落下,这头驴子终于不堪重负、应声倒地。“五四”以及随之而来的革命实践表明:让代表激情的血性、追求科学进步的理性与国家民族的存亡发展乃至人类世界的向美向真向善紧密结合起来,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世界才会有生机、有希望。“五四”精神教育我们,个人、群体的前途命运总是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越是国家民族遭遇危难的关键时刻,越需要有、也一定会有更多的志士仁人为它呼号呐喊、担当道义乃至冲锋陷阵。
第四,文化创新是国家和民族发展进步的策动力之一。五四运动不同于历史上一般的农民暴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地方在于:它除了激发青年学生罢课、工人阶层罢工、工商业者罢市外,更主要的是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脱胎换骨式的新文化运动。早在“五四”之前,新文化运动即有一定的成长发展,“五四”的即日爆发无非是在更宽广的领域里,以更公开、更猛烈的形式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属于相当典型的文化创新运动,比如白话文的面世流行,新文体的创制推广等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特别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代表的新思潮新学说的引进传播,更是为在现代性语境下深陷发展困境的儒释道等传统思想带来了摧枯拉朽般的冲击。
“五四”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实际上就意味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先进文化,开始与以儒家思想为突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展开了激烈的交流碰撞。由于这个“交流碰撞”不只是在玄谈神汇的书本上展开的,更主要的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方式展开的,因此交织在其中的文化创新是和政治、经济及社会方面的创新实践相互呼应的。其成果就是不仅建立和发展了新中国,而且创造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
参考文献:
[1]艾思奇. 五四文化运动在今日的意义. 新中华报,1939.4.18.
[2]马一浮集(第2册).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317.
[3]随感录(六七). 新青年(第6卷),1919.11.1.
编辑杜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