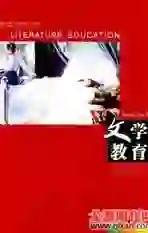《错误》的诗性之美
2009-07-24黄辉
黄 辉
郑愁予的《错误》具有含蓄、典雅、幽深的婉约风格,是一首具有现代主义内涵,同时又具有纯诗知性美的诗。下面就从这些方面具体阐述它隽永的美。
一.古典美
(一)意象与意境
《错误》是一首短小的诗,它首先给人隽永意味的是诗中古典意象的运用和它创造的幽深含蓄的意境,这是形成其强大的感染力之所在。因为“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①
这首诗短小而又精悍,句句如串串珠链,其中的每个意象都闪烁着最耀眼的光芒。诗的首句“我打江南走过”写出了“江南”这一古典意象。“江南”这一中国古典诗词中常见的意象代表着秀美、清新、意蕴无穷的美。小桥流水,凉风拂面;夕阳斜挂,檐燕低语;烟柳画桥,亭台楼榭;菱歌泛舟,靓男媛女;风荷影动,游鱼惊窜;风雨凄迷;美人凝眸……这是一个如此令人向往,宛若仙境的地方。古来多少人倾倒于江南的浓情密雨之中,既有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能不忆江南”的无限回忆流连,又有“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的美好情态,“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的恋情神往,以及“初篁苞绿箨,新蒲含紫茸。海鸥戏春岸,天鸡弄和风”的勃勃生机。这一包含无限韵味的江南意象为全诗营造了一种幽深隽永的气氛,奠定了全诗典雅而又哀怨的情感基调。
“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等待的容颜应该是一位江南美丽的妇人。然而青春易逝,红颜易老,她曾经绰约的身姿,如花的笑靥,凝眸的顾盼,纤纤的素手,娥娥的粉妆怎经得起岁月的等待?“莲花的开落”暗示着红颜的消陨。莲花象征着那等待的女子,它的盛开灿若星辰,而短暂的绚烂之后是香消玉损。这是一个哀怨的江南女子。“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你的心如小小寂寞的城”。“东风”是复苏万物吹醒大地的东西,而在此时的江南它仍未到来,柳絮也无法轻扬那秀美的衣袖。沉闷,冷清,这就是此时的江南,一切都无生机,心儿更是寂寞的。那女子的心也如同这死寂的三月一样,寂寞如空荡的城。诗到这里运用了强烈的反差手法,先是写了江南这一美好秀丽的意象和妇人的哀怨、寂寞的凄婉形成强烈对比,然后本应“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柳絮弥漫飞舞的明媚春光的意象与东风不语、柳絮不飞的死寂三月形成鲜明反差。这种以乐景写哀景的手法,更加衬托出哀怨忧愁的诗意。因为意境具有超越性,它所包含的意蕴不仅有具体的物象,还有令人玩味无穷的弦外之音。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这句诗包含了夕阳、黄昏、青石街道这几个意象,营造出一种黯淡的意境。幽幽的黄昏,几缕夕阳还不忍这么快告别白昼,作着垂死的挣扎,留恋不舍的向白昼作最后的凝视。它们隐隐地挂在云边,为云片织成灿烂的裙裾,最后像轻烟似的消散。青石的街道在这幽寂的黄昏里,显得更加暗淡,凄凉,那肃穆如怨如诉,如歌如泣。“跫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这样一个凄婉的黄昏,连轻轻的脚步声也无从听到,那颗等待的心在失望了无数次之后,再也不忍揭开春帷,让失望再一次降临。她紧紧地关着心的窗扉。“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在她已经紧掩窗扉的时候,达达的马蹄声忽然从远方传来,愈来愈近,妇人的心再也无法安静。她的心开始有些动乱,终于在马蹄声离她最近的时候,再一次满怀希望地揭开了窗帷。而“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这时候对那个等待已久的江南女子应该是一种“过尽千帆皆不是……肠断白蘋洲”的感觉。
“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言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②内心的精神为人的情志所支配,外物接触到耳目,靠优美的语言表达。诗人用优美纯净的意象,纯粹的情感表达一种悠远的意蕴,完成了意境的统一。
(二)形式和结构
形式即内容,这首诗的形式和结构对意境意蕴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西方形式主义文论者看来:“诗歌的显著特征在于,语词是作为词语被感知的,而不只是作为所指对象的代表或感情的发泄,词和词的排列、词的意义、词的外部和内部形式具有自身的分量和价值”。③首句“我打江南走过”,是一个短句,形式上的短表现了“走过”的主题,暗含“我”只是走过路过这里,只是个过客,停留的短暂,暗含末尾“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同时也象征一种流浪意识。“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是一个长句,花开花落,表现等待的漫长。“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两个短句,“你的心如小小寂寞的城”又是一个长句,表现寂寞的蔓延和绵长。这种长短相间的句式增强了表现主题的效果。这种形式和结构又非刻意雕琢而成,而是自然的表达,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
二.现代主义内涵
这首诗的现代主义内涵主要表现在它采用了象征主义的手法表达了精神无所皈依的流浪、孤儿意识这一主题。“象征意味着既是它所说的,同时也是超过它所说的。”④象征在现代主义文学里不仅仅是一种表现手段,而有着更内在的联系。现代主义文学要求读者更加关注象征寓意。诗中的一些意象从更深层次来说具有象征性:莲花是佛的宝座,在古典诗歌中又象征着精神的皈依,信仰的回归。莲花的凋落也可以理解为信仰的缺失,精神的无所归依。在历史上,从甲午中日战争《马关条约》的签订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之后,台湾人就有一种流浪、孤儿意识。他们认为自己是被祖国抛弃的孩子,又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过着屈膝的生活。他们把自己称为“中国的孤儿”、“亚细亚的孤儿”。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回到祖国怀抱被国民党占据,他们的这种心理并没有改变甚至进一步增强。如《悲情城市》表现的主题,他们在中国人眼中被怀疑为日本的间谍,又被日本人监控着。他们受着不公平的理解,在精神上形成一种不安全,无所归属的心理。虽然与大陆一水之隔,经过政权的更替和政治人物的操弄,他们的国家认同心理逐渐被分裂,孤儿意识增强。末尾“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也象征着自己的无所归依之感,强调自己只是个过客,只是个流浪儿。
三.纯诗的知性美
现代诗社针对反共文学提出了“反对诗的政治色彩”的信条,同时追求诗的纯粹性,强调诗的知性。
什么是纯诗?“所谓纯诗,便是摒除一切客观的写景,叙事,说理以至感伤的情调,而纯粹凭借那构成它底形体的原素———音乐和色彩———产生一种符咒似的暗示力,以唤起我们感官与想象底感应,而超度我们的灵魂到神游物表的光明极乐的境域。像音乐一样,它自己成为一个绝对独立,绝对自由,比现世更纯粹,更不朽的宇宙;它本身的音韵和色彩底密切混合便是它底固有的存在理由。”⑤纯诗是反对抒情主张思辨和哲理的。瓦雷里认为诗应该是感与思的融合。他说:“诗歌与艺术都以感觉作为起点和终点,但是这两端之间,智力的各种思维才能,甚至是最抽象的,同各种技巧才能一样都能够,也应当得到施展”,这思想理智的“施展”就是本身对诗中描绘的瞬间的直觉、变动的感受、游移的情感、飘忽的梦幻等感性元素的观照与把握,以使“物质的属性自然地被利用来再现精神的属性。”⑥现代诗社诗人反对抒情,正如纪弦所说:“在诗歌里抒情是被禁止的。”但是纯诗只是一种诗歌理想,是很难企及的,“纯诗的概念是一种不能接受的概念,是一种欲望的理想范围,又是诗人的努力和强力所在”。⑦虽然提倡诗的纯粹性是现代诗社的信条之,但他们也没有做到诗的纯粹性。
但《错误》这首诗的知性美不能否定。他们主张知性,主张诗歌对生命的体认,对生命真谛的探索。“知性”,可以理解为“理智”或“悟性”。洛夫认为“调整知性与感情,表现生命的流动,既有真挚性而又含有超越性的诗是现代诗发展的三个过程。”⑧《错误》中的孤儿意识就是对精神皈依的感慨和体认。这种对于生命的孤独、流浪感的探索恰是对生命尊重的体现。“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更多的让人陷入对精神归属的沉思,给人以生命的启发,有着纯诗具有的知性美。
参考文献:
①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叶燮著《原诗》。
②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远方出版社,90页。
③霍克斯著,瞿铁鹏译:《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63页。
④劳·彼林著:《谈诗的象征》,《世界文学》1981年第五期,第248页。
⑤《谈诗》,《诗与真·诗与真二集》,第95页。
⑥瓦雷里:《论玛拉美和魏尔伦》,陈力川译,见《世界文学》1983年第2期。
⑦瓦雷里《论纯诗(之一)》
⑧洛夫,《中国现代文学大系:诗卷》序,中国现代文学大系:诗卷[C],台湾:故乡出版社,1972年。
黄辉,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