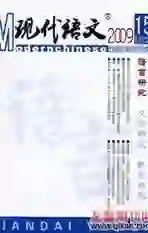指示语“我们”与“咱们”的异同及其语用含义探析
2009-07-15李忠美陈海庆
李忠美 陈海庆
摘 要:汉语普通话中第一人称复数指示语有“我们”和“咱们”两种表达形式。本文在汉语语料的基础上,对第一人称代词“我们”和“咱们”的由来、地域差异、语体差异、语用差别及其特殊语用含义等进行了分析对照,并对它们在具体应用中的特点进行了基本归纳。
关键词:“我们” “咱们” 人称指示语 语用含义
一、引言
指示语(deixis)是指在口语语篇或书面语篇中对某个人或某些人或事物进行指称的用语。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Fillmore就已经对指示语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将其分为人称、时间及地点指示语(何自然,1988)。随后,Levinson(1983)对指示语做了更为全面而详细的阐述,按照指示功能将其划分为五大类,即人称、时间、地点、语篇和社交指示语,并且指出人称指示语是指谈话双方用话语来传达信息时的相互称呼,人称指示语的体系由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构成。
目前,我国学者对人称指示语的研究基本参照国外的相关理论,但对汉语语料中人称指示语的分析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近年来,许多学者从语用学的角度对指示语进行了探讨。陈令君、马坤(2006),潘福刚(2007),赖彦(2007)等从人称指示语的语用及交际功能方面进行了研究;古伟霞(2005)从礼貌功能角度进行了探讨;李永(2003)对汉语人称代词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和展望;郭启平(2008)对汉语的个别人称代词做了专门讨论。然而,我国学者对汉语人称指示语“我们”和“咱们”在实际使用中语用含义的异同研究还不够全面。本文在分析汉语语料的基础上,对“我们”和“咱们”进行语义、语用方面的比较分析,探讨两者之间的异同以及这些异同点的语用特征及规律。
二、“我们”和“咱们”的由来
(一)“我们”的由来
表示第一人称的“我”最早见于甲骨刻辞中,表达的都是复数意义,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我们”。例如:
(1)师不余我见?(《甲骨文合集》)
(2)乙丑其雨,不唯我祸。(同上)
但在两汉以前的汉语中,“我”既可以表示单数,也可以表示复数。例如:
(3)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汤誓》)(复数)
(4)公曰“尔有母遗,医我独无!”(《郑伯克段于鄢》)(单数)
在宋元时期,一些作品中出现了“懑”“满”“瞒”“门”“每”,并出现了与“我”结合使用的表达形式,相当于“我们”,既可以表示单数意义,也可以表示复数意义。例如:
(5)不因你番人在此,如何我瞒四千里路来?(《齐东野语》)(单数)
(6)小衙内同杨金吾上:“老包性儿沙,荡他活的少。若是不容咱,我每则一跑。(《陈州粜米》第三折)(复数)
到了明清时期,基本上采用统一的“我们”的表达法,而且多用于表达复数意义。翻开长篇巨著《红楼梦》,就可以发现许多例证:“‘果然拿不出来也罢了,金的银的圆的扁的压塌了箱子底,只是累掯我们。……我们虽不配使,也别太苦了我们,——这个够酒的够戏的呢?说的满屋里都笑起来。”(《红楼梦》第二十二回)
(二)“咱们”的由来
相对于“我们”的历史渊源,“咱”从何而来,学术界尚未有确切的定论。翻开先秦的作品,可以查证出上古汉语中没有“咱”的表达法。宋元时期的作品中“咱”和“我”的应用初见端倪,但在用法上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例如:
(7)“你道是咱不该,这招状供写的明白,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我只道官吏每还复勘,怎将咱屈斩首在长街?”(《窦娥冤》第四折)
李作南、李仁孝(1993)认为,宋元时期北方话中有一个表示“自己”的代词“自家”,它的合音字就是“咱”(读做zá)。“咱”及“咱们”产生于宋元时期的论断,还可以从文献中找到依据。例如:
(8)你若无意向咱行,为甚梦中频相见。(柳永《玉楼春》)
(9)(二旦白)思量偺们的好处哩(《牧羊记·望乡》)
(10)想古今喒这人过日月好疾也呵!(关汉卿《关大王独赴单刀会》第四折)
在明清的作品中,“偺们”和“喒们”基本不用,而只写作“咱们”,现代汉语中也一律使用“咱们”。
三、“我们”与“咱们”使用中的地域及语体区别
从“我们”和“咱们”的由来可以看出,“我们”与“咱们”起源于不同的地域。在普通话中,在指称包括说话人一方的复数意义时,通常都用“我们”。但是,指称包括说话人和听话人时,北方人(以东北三省为代表)基本上都使用“咱们”,而南方人(以湖南、四川等省份为代表)则用“我们”。也就是说,南方人说普通话时,在指称自己一方时,用“我们”,在指称自己一方和听话人时,也用“我们”,而北方人在指称自己一方时,用“我们”,但指称自己一方和听话人时,则用“咱们”。我国南方很少用“咱们”进行指称,从南方作家的作品中就可以找到许多佐证。例如:
(11)“虞姬,我们完了。……我们现在只有一件事可做——冲出去。……”(张爱玲《霸王别姬》)
(12)“我们四川社会里卫道的人太多了。他们的势力还很大。他们一定会反对。……”(巴金《家》第二章)
(13)“……我们这次若去,又得打火把回家;你记不记得我们两人用火把照路回家?”(沈从文《边城》第六章)
“咱们”虽然也属于普通话指示语之列,但它起源于北方,因此在北方话,特别是在东北方言中出现较多,体现了使用地域的差异性。郭宝昌的《大宅门》中凡是指称说话人和听话人时,使用的都是“咱们”。据统计,《大宅门》前三章中“咱们”共出现了29次。难怪北京大学中文论坛中有人认为“江淮话里没有‘咱,更没有‘咱们,我认为‘咱‘咱们是北方话的说法。”①值得一提的是,东北人对“咱们”的使用可以说是俯拾即是,在刻画、描写与东北人相关的作品中“咱们”的出现频率极高。例如:
(14)张作霖一摔碗,道:“就这么的,挑个好日子,咱们到关帝庙去烧香,磕头,拜把子。”(《张作霖传》第二章)
(15)李勇奇:好哇!首长!咱们真是一家人哪!(《智取威虎山》第七场)
(16)赵本山:乱了,乱了啊!这样啊,谁喊的不要紧!你看咱们缕一缕啊,谁先喊的?(赵本山小品《功夫》)
其实,在上述情境中,“咱们”的指称和“我们”没有区别,都指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只是由于地域的不同,说话人用“咱们”来替代了“我们”。
“我们”与“咱们”所存在的差异还体现在语体方面。“我们”常用于政论性书面语篇或正式文体中,特别是当包括说话人和听话人时,“我们”用的要比“咱们”多。例如,在开幕式致词、演讲、汇报、教材、科技语体、政论语体以及描述性语体中,一般不用“咱们”来指代说话人和听话人,而用“我们”指称。其作用是要取得一种公正、客观、正式的文体效果。与此相反,“咱们”多用于口语语体和文艺作品中。
四、“我们”与“咱们”的一般语用差别
宋元时期,“我们”和“咱们”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但在元末和明朝的时候,由于汉语和蒙语的相互影响,在蒙汉语言的相互翻译中,逐渐形成了二者的差异。“我们”表示第一人称的复数形式,与第二人称相对,简称排除式;“咱们”也表示第一人称的复数形式,与第三人称相对,属包括式。例如:
(17)张千、李万道:“你丈夫自要去拜什么年伯,我们好意容他去走走,不知走向哪里去了。(冯梦龙《沈小霞相会出师表》)(排除式)
(18)但咱门,虽宦裔,总皆通。(《张协状元》)(包括式)
“我们”与“咱们”的排除式和包括式的分工,经元末的产生、明朝的发展,到清朝已经完全得到了巩固。《红楼梦》中关于二者的区别使用就比较严格。例如:
(19)袭人冷笑到:“你问我,我知道吗?……从今咱们两个人撂开手,省的鸡生鹅斗,教别人笑话。……我们这起东西,可是‘白玷辱了好名好姓的。”(《红楼梦》第二十一回)
例(19)中的“咱们”显然指说话人袭人和听话人宝玉;而“我们”则指包括袭人在内的伺候宝玉的丫鬟们。
随着历史的变迁,“我们”和“咱们”的用法也产生了一些变化。现代汉语中,“我们”既可用于包括式,也可用于排除式;而“咱们”只用于包括式。如例(20),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和“咱们”的语用变化及功能:
(20)秦母高兴地合不拢嘴:“小宁,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你们俩都是我的孩子,秦芳走了,我就把你当成女儿,我祝你们俩相亲相爱,白头偕老!”秦岩接过来说:“来小宁,咱们俩敬妈一杯。”待夏端起杯子,“妈,我爸不在这么多年,我知道你不容易。我们以后一定好好孝顺你,让你过个幸福的晚年。”
可见,用于排除式时,只能用“我们”。而当两者都用于包括式时,语义上没有任何差别,可以相互替代,但在语用上,由于受地域、语体等语境的制约,又不可随意替换使用。
五、“我们”与“咱们”的特殊语用含义
虽然“我们”与“咱们”通常指第一人称的复数形式,但我们不能单从语义学的角度来衡量其真假值,因为有时“我们”与“咱们”的使用反映了说话者的意义(speaker's meaning)或意向(intention)。因此,探讨两者在具体语境中的语用含义是非常必要的,更有利于听者弄懂说话者的弦外之音或言外之意。
关于“我们”与“咱们”的特殊语用含义,可以用下表进行归纳分析:

可以看出,“我们”和“咱们”的语用意义远远超出了第一人称复数的意义,不同的语境赋予它们不同的含义,因此,它们的指称意义随着语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首先,“我们”和“咱们”都可以用来表示第一人称的单数含义。有时说话者为了表示谦恭和礼貌,有意不突出自己,用“我们”来代替“我”。但是,有时说话者用“我们”来指称“我”是为了趋同性的需要。在科技论文写作或演讲文体中,作者/说话者常用“我们”来指自己,使自己所陈述的观点显得公正客观,其目的是加大读者/听话者接受其观点的力度。如果将“我们”替换成“我”,语用效果将会受到一定影响,原因在于其主观性强,有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之嫌。与之不同的是,“咱们”用于指第一人称单数的意义时,则传达了某种委婉的意向或情感。
其二,“我们”和“咱们”还可以用于表示第二人称的指称信息,用于模糊说话人和听话人间的界限,将自己引入对方所处的某种情景,以这种虚拟的“共同处境”来拉近交谈双方的距离,增加亲密感,从而有助于说话者有效地实现其言语交际的目的。
其三,“我们”还可用于表示第三人称。在通常情况下,“我们”所指称的对象通常处于交际劣势中,而说话人通过使用“我们”,将自己的交际优势转嫁给指称对象,使形势有利于指称对象。
其四,“我们”在表复数含义时,除指人外,还可指机构、公司、团体等,以拟人化的手法来达到某种交际目的。
除此之外,“咱们”用于歌名、电影名或文章标题中,有赞美、直抒情怀之意。
六、结语
人称指示语是语用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仅仅对人称指示语“我们”和“咱们”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从中可看出,在不同的语境中,其语用含义是丰富多彩的。毫无疑问,人称指示语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语义层面上,还应从语用层面上进行分析。只有将指示语放到一定情景语境和社会文化中进行研究,才能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其语用含义和运用规律。此外,以文学作品中的语料为分析和研究的对象,目的就是把“我们”和“咱们”放在一个比较规范、普遍和相对稳定的语言环境内进行考察和评价。这一方法虽不如从现实生活中搜集的语料来得直接,但也从较大程度上反映了语料来源的可靠性和规范性,为今后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
注 释:
①参见北京大学中文论坛www.pkucn.com《汉语语言学·汉语方言》。
参考文献:
[1]何自然.语用学概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2]Levinson,S.C.Pragmatics[M].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3]李永.汉语人称代词复数表达形式的历史考察[J].广西社会科学,2003,(9).
[4]李作南,李仁孝.论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发展和蒙语对它的影响[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4).
[5]孙仁生.现代汉语新编[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
(李忠美 大连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116034;陈海庆 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116024)